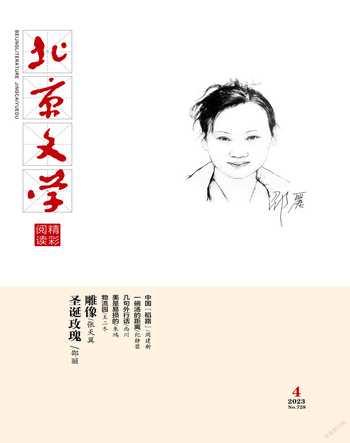雄安三章
吳海濤
土,是最沒有價值的東西,隨處可以抓一把,若把“土”和“地”聯在一起,就不一樣,我們賴以生存的土地,養活著萬物生靈,每一次戰爭,都是用生命捍衛土地的主權,每一次革命,都用土地改變命運,歷史記載早就證實了這一點。
我就珍惜土地,特別是養我的故鄉土地,國家在這塊土地上有重大開發,是自深圳的經濟開發區、上海的經濟自貿區之后新的雄安新區。這片熱土,巧逢偉大的時代,正發生著史無前例的重大巨變。
生在京南不大的縣城,歷史卻冠上一個霸氣的名字,雄州即現在的雄縣。承載著厚重而悠久的歷史,燕南趙北,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彰顯出豐富多彩的歷史,脫穎出許多英雄人物。
金戈鐵馬宋遼之戰,揮戈煙云十六州的邊防之地,有旌旗蹄奮的六郎大堤,有地下長城暗道,有藏隱的古跡,土地上留有鐵甲紅纓,鮮血浸染風采的英雄歷史。
穿越茫茫青紗帳的敵后武工隊,劃動船槳在荷花淀上的雁翎隊,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八路軍在這里戰斗,其中有兩位開囯將軍,深深眷戀這方熱土,永久長眠冀中平原的土地,像萬古長青的松柏,挺立在雄安。
一條九曲十八彎的大清河,像一條血脈把橫跨的三縣相連在一起,中心一條漢白玉石橋將其分成南北,南邊是荷花稻谷伴魚香的白洋淀,東面是百里麥浪無垠的黑膠泥地。一條蜿蜒曲折的大堤分隔成堤里堤外,在面積不大的地方,分別建有三屬之縣,雄縣、容城、安新,譜寫出跨時代的名字——雄安,一座未來的城市,在這里緩緩展開。
我的家鄉就在不知名的中心小鎮,昝崗,現為雄安新區容東片區。
昔日,華北平原中部,小鎮歷史悠久,地處白洋淀與渤海灣的一條泄洪大河,溝通東西,其主要承載著太行山麓的九龍吐水,是泄洪東流的必經之路。多年分洪的沉積泥沙,養育著肥沃的土地,主要農作物小麥、果蔬、玉米、大豆、高粱,劃歸雄縣稱之為鄉府,小鎮不小,四周散落著大大小小的幾十個村子,每逢三、七為小集,逢五排十的大集,聚集十里八鄉的百姓,在小集買賣。
特別是改革開放后,雄縣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借助改革的春風,小鎮上人民勤勞致富,以機電、農資產品為主,富裕了小鎮,他們借助北京、天津、保定大中小城市建設,發展了全縣,改革開放初期雄霸天下。
今日,在偉大的新時代,一座新型現代的城市,在這里崛起。現代化的基礎建設,已經在這片土地上基本完成。最大的高鐵站,將在昝崗建設。
初春,揣著好奇,驅車看望將要逝去的村莊,在鄉間小路,停車駐足,遠望著紅藍相間,磚與彩鋼建起的低矮房屋,被一層淡淡的輕霧籠罩。坐在車上,望著一馬平川的農田,給了我無窮無盡的遐想,到那時這片土地上,肯定是宏偉的建筑群。
曾騎單車穿梭在那里,行駛在這片童年無數躺臥過的熱土,感受到母親胸懷般的溫暖,曾經的悲切與厭倦,在這綠色的海洋,顯得自己如此的渺小和微弱,硬化的叢林小路,再也沒有原來的泥濘,車輕松地把我帶進如畫的世界,增添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
深深地吸上一口家鄉的空氣,嗅出清馨,失去了炊煙裊裊的味道,欣賞著童年田野里曾結出的玉米、高粱,被羞澀紅潤的蘋果所取代。大面積的多品種、多棵類,像一個叢林博物館,讓人眼花繚亂,闊葉地、窄葉地、針葉地、高植地、矮植地、叢植地、單植地,讓不懂植物的人,無法辨認更無法準確地叫出它的名字。
土地里崛起的大雄安,讓我為故鄉感到自豪。
成立雄安的第二年。
鄉親們歡悅的心情,已經少了些興奮,姐姐一家也有了變化,她那火暴的脾氣也有了些收斂,老實巴交的姐夫憋屈了一輩子,地里刨食的人失去了土地,心情壓抑寡歡。
已到打春,厚厚的棉夾已脫去,姐夫張老漢,獨自蹲在院子臺階上,狠狠地抽著煙,燃燼的灰依然掛在未吸的半截。吐出的煙霧,在涼颼颼的清晨,伴隨著空氣飄出小院,悶葫蘆似的脾氣,就是用力地壓,也未必能碾出個屁來,呆滯的表情也不知在想什么?
姐夫心里壓抑的火,就是年前那片租出去的土地,讓自己永久的失去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命根子。他不愿意爭執,更不愿意理論,去年用這雙粗糙的手,顫巍巍地簽上自己的名字,從落筆之初,就是在老婆的催促下,咬著后槽牙才簽上去的,用現實的話說,“我后悔了”。可他生氣歸生氣,心里的惆悵卻不能說,更不敢說,三口之家,也得講民主,要少數服從多數,先說兒子同意,土地退耕是為雄安新區“植樹造林”,老婆同意,說是為雄安新區“千年大計”。只有自己為這一畝三分地,吵架拌嘴,不值得,兩口子吵了一輩子,老婆子總把離婚掛在嘴邊,說跟著張老漢,這輩子就一個字“怨”。歲數都大了不找氣生,遇事也就隨她去吧。
張文淵,多富有文化內涵的名字,是書香門第的老人起的,祝愿張文淵,從小聰明過人,長大后知識淵博。誰知趕上了六七十年代的運動,沒有學到知識,倒受家庭成分牽扯,被運動卷入的狗崽子,吃了不少瓜落,村里人背后都稱他“張文怨”。把“淵”字改成了“怨”,直到那年全村辦身份證,他才有幸改回這個“淵”字。
要說他知識淵博還真不知道,大字不識的他,是村里出名的莊稼把式。犁、耩、鋤、耙樣樣精通,特別是那套節氣邏輯,確實有一番哲理,而且很受莊稼人的追捧,他對《二十四節氣》農耕時令,從立春至大寒農人口訣精通,也從實踐中得到驗證。
房門開了,驚得張文淵的手顫抖一下,將燃燼的煙灰瞬間掉在地上,而余下的煙頭也燎疼了手指,疼得他快速扔了煙,隨后用腳恨恨地輾轉。
屋里走出了張文淵的老婆,也就是我的姐姐,人沒出屋,那連珠炮式的快言快語,早就從屋內傳出,驚得那狗呀、雞呀都搖晃著尾巴,圍在門口等待女主人的出場。
“你說你這糟老頭子,擺什么臭架子,人家村主任找你們幾趟,說請你帶領人去南洼地里種樹,看你這個酸勁,頭搖晃得跟撥浪鼓似的,這不行,那不行。我還不知道呀,你他媽的就想撅著眼子,種你那塊破地,不愿意新區建什么千年秀林嘛。”
邊說邊數落,邊把簸箕里的糧食撒給雞吃。
“行了行了,別嚷嚷了,還讓不讓我早晨睡覺,我這一會兒還去鎮上報到哪,起早就吵,休息不好我可不去!”
說著,一個威猛的小伙子,伸著懶腰,打著哈欠,從屋里走出來。
“洗臉,吃飯吧,老頭子吃飯,一會兒跟我一起去報名栽樹去,好歹,一天能掙百兒八十的,比待著強。”
說著話兒子的電話鈴響,從他那說話的口氣就能聽出是對象來電話,遮遮掩掩的語氣里帶著甜蜜,也帶著私密。“好嘞,行,行”之類的口氣。
掛上電話,他握緊拳頭,狠狠地甩了一下,扭回頭說:“媽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娟,學習結束了,讓我下午去車站接她,說學習已經結業,分配到雄安種植中心‘千年秀林’項目。”
當媽的聽兒子這么說,當然高興。兒子叫張壯,準兒媳婦叫李秀娟,都是部隊的復員軍人,縣復員軍人辦公室分配兒子到鄉武裝部下設的森林消防。李秀娟則被分配到中鐵水電二局,剛成立的“千年秀林”項目部,一家人都是“千年秀林”的骨干人員。
紅彤彤的太陽,春和日暖,空曠的田野里,飄動無數面五顏六色的彩旗,連排的旋轉鉆井挖坑機同時作業,隆隆的機鳴聲響徹在雄安容東的“千年秀林”工地。全面實施機械化挖坑作業,五線水平激光儀,配合衛星定位,準確地開掘每個坑位。大型水灌車和滴灌補水管線配合,后面跟著從南方引進的苗圃運輸車,上帶自動定位吊機,準確無誤地將樹苗,放置坑內,張文淵扶正,撒上植物生根粉,水滲透后,用機械填埋黃土,老伴在樹周圍扒一個坑以備澆水,微滲的滴灌管引進樹坑。隨后技術員李秀娟,登記造冊,錄入電腦微機,所有數據存儲,誰參與了種植,成活率,都明確地記入檔案,有據可查。
張文淵這時才意識到自己錯誤的判斷,他想幾千畝的黃土地,要人工種植,挖坑、澆水、培土,沒有個三四年種不完,把人累個半死也未必成活。
夕陽的余暉灑在故鄉的土地,金燦燦的,弧形旋轉式種植從衛星上看,像一個大型的綠色魚形,那明亮的一淀水正是魚眼。沿綠波向遠方望去,在消防隔離帶上,一條寬廣的馬路上,一輛紅色消防巡邏車,緩緩向這里駛來,由小變大,張壯在副駕駛室,伸出大手,向工地揮動,車上傳來呼喊聲,娟子——
聲音由遠及近,身穿黃馬甲,頭戴藍頭盔,漂亮的姑娘,揮手向車的方向喊去,張——壯——
站在身邊手扶樹的張文淵,低著頭不語。
一干活的工人問我姐,“大嬸,你是怎么和大叔不交流,也過了這多年?”
她說,“家庭要想幸福,要把缺點包容成優點,他悶葫蘆不言聲,沒有立場,我永遠是對的,不信若把缺點當重點,天天打架,早他媽的離了,你說是不是這個理。”
大家聽后覺得有點道理,哈哈一笑。
雄安新區給這一家人帶來綠色的歡樂。
沒有長鳴的汽笛聲,一條白色的長龍,從遠方蜿蜒著疾駛而來,毫無聲息穩穩停住,潛伏在綠色波浪潮涌里,停泊在一片碩大的荷葉下,這就是高鐵站——雄安站。
遙遠的蒼穹俯瞰,與一汪清水的白洋淀相依,也像一粒散落的明珠,新落成的雄安高鐵站,給華北冀中平原,增添了一道靚麗的風景。
我生長在這里,這里是我的家鄉,這里是一片貧窮而富有的士地。
那還是2020年,回老家的第二天,由于久別故土情緒高漲,天剛亮,我就急不可耐地推開院門,只見外面聚集著幾個人,頭戴藍色安全帽,身披橘紅色馬甲,聚在門口等待班車,準備去工地。我看年輕的家鄉建筑工人倍感親切,幾句寒暄得知,他們在雄安高鐵站工作,其中一位虎頭虎腦的年輕人,正是本家的侄子,短暫交談得知,雄安站在昝崗鎮上的左各莊村,已經開工建設,故鄉將建設亞洲最大、功能最全、設施最先進的高鐵站。
對故鄉由衷的熱愛,對建設工程的興趣,讓我總想去工地參觀學習。
今天是個好日子,表妹的兒子結婚,請我喝喜酒,昨晩從北京趕回,住在了與昝崗相鄰的老家。久旱逢甘霖的喜雨,沾上新婚慶典的喜事,趕上故鄉高鐵建設的喜愛,我心里美滋滋地爽,不由自主地哼唱“今天是個好日子……”
坐在后邊的媳婦指責我,“人家表外甥結婚,你當表舅的,跟吃了蜜似的高興什么?”我的回答也勾起了她的興趣。
“你知道嗎?每次回老家都來去匆匆,總想去昝崗雄安高鐵站建設工地看看,看咱老家新區,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今天有幸參加婚禮,完事咱去建設工地參觀。”
媳婦由衷的高興,她和我一樣,牽掛著故鄉的變化,可能是懷有游子心愿吧。
故鄉的婚禮別有趣味,盛大的場面,高懸的大紅綢緞下的圓桌坐滿賓客,帶有鄉土氣息的酒席上,有位來自雄縣建設局的領導。酒席間交流,他高談闊論高鐵站建設的高科技設計理念。
他說:“雄安站,作為雄安新區,首個標志性重大工程,也是門戶工程,國家鐵路集團和雄安新區共同出資建設,組建綜合交通樞紐。京雄高鐵雄安站不是一座孤零零的車站,站城一體化和站城深度融合的理念,初期勘察、設計、施工、監理的先期工程早已完成,在新區指揮部,規建局、發改局、公安局、住建局大力支持下,由中建八局承建,為了不影響進度,正在熱火朝天地施工,不久的將來會成為一條靚麗的風景線。”
聽他介紹更增添了我參觀的信心。
美味的酒席留不住我的期待,心早被勾引到了雄安站,沒有理由辭行,必須馬不停蹄地前往。
曾經不知走過多少次的鄉間土路,建成寬敞的柏油馬路,兩邊停放無數車輛,是建設工人臨時停靠點,豎立的藍色圍墻阻隔了我的視線,保安把我攔住,他直言工地施工隊伍眾多,一萬多人的建設工地,縱橫交錯管網溝道,高高的腳手架,進去無法保證你的安全。
只能透過門口的縫隙看勞動的場面,眾多大型的設備,機聲轟轟,我被熱火朝天的場面震撼,我曾走過不少工地現場,看到如此龐大的建設現場還是第一次。高空的輕軌架橋,猶如一條長龍,蜿蜒地伸向遠方,那變形金剛似的鐵臂,向遠方鋪設路基。建設工地焊接火花四濺,強烈的藍光里射出紅黃的火焰,似怒放的煙花在古老土地上釋放出青春活力。
媳婦提醒我,不是有個侄子在工地施工嗎?看是否能通過他,咱進去看看。我撥通了電話,那頭傳來標準的回答:“您所撥打的電話不在服務區,有事請留言。”聽到后我明白,工作期間無法接打電話,理解,非常理解,但還是遺憾沒有親臨現場,感受工地的熱情。
疫情阻隔了回鄉的情懷,再了解高鐵進展,只能從媒體和手機上了解。也曾打電話詢問表妹,她說她新結婚的兒子和媳婦,都報名參加高鐵招工,兒子被招高鐵保安,將巡視保衛高鐵的安全;兒媳婦被分配到售票處,學習電子商務,管理網絡購票統計。表妹夫被環保局招聘為垃圾清運工人,負責開車清運垃圾到葛各莊建成的雄安垃圾處理場。表妹還告訴我說,從雄安坐高鐵到北京45分鐘,從雄安高鐵到大興機場38分鐘,縮短了與首都的距離,也給雄安人走出世界建起最短的橋梁。
京雄鐵路的雄安站,是一張徐徐展開的濃墨重彩的畫卷,繪出了雄安美麗的藍圖。京雄鐵路的開通,雄安新區乘上了高速列車,駛向美好的未來。
特約編輯 驀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