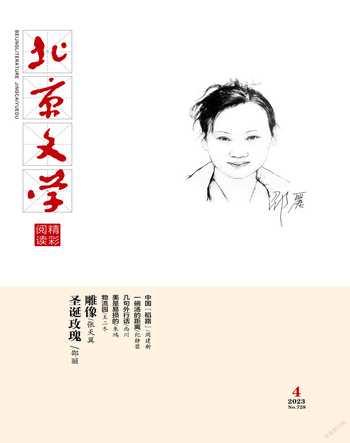嗩吶之晨(組詩)
姚輝
虔敬的人由石頭
構成? 他用九種霜色
排列的遺忘
依舊陣勢浩大
土與太陽。我在——
柏樹高擎黃金之幡
那翔舞的字跡
讓云向東面滑動
大風不一定存在
但風依然吹拂
遠離的人從紙頁邊緣
經過? 他們彼此
點頭致意
晨光這么空曠
一定有一只鳥曾錯過
燈與懷念? 我錯過
什么? 在躍上
山脊之前? 太陽
重復燈的承諾:
我在。霜痕堆砌的晨光
逐漸泛紫? 幡
將一部分苦難還給了
太陽
一只螳螂
將柏樹之影
搬到赤云正面
虔敬者讓所有
習慣疼痛的石頭
醒著——
不可能只以風的方式
談論父親
銅鑼模擬旭日之芒
它那么沙啞
它談論的父親
是否仍風一樣活著?
舉燭的手忽略過
正午的哪一種遼闊?
燭將懷念的尺寸
一再縮減? 直到燙傷
指紋及我們曾
試圖改變的命運
山脊被什么覆蓋?
我向草說起父親的
渴望? 但我為何又總是
辜負這些渴望?
石頭談論父親時
會找到比較堅固的
淚水……
我說的是那塊
刻滿文字的石頭
它站在風中
它寧愿把這些文字
當作父親的冥想
一顆星
將父親的身影
留在山脊上
請學會以星空的方式
談論父親
先拜謝東方。我嘶啞的
呼喊可能并不該驚動
沉睡的你? 你的囈語那么
深長? 而太陽仍被
青銅之殼緊鎖著
云飄動。我已經可以
停止呼喊了? 香案上山勢
綿延。且拜過西方
澎湃之河? 斷槳界定
歷史? 而你既不在歷史A面
也不在歷史的B面
歷史逐漸露出第三種
切面? 鑼鼓驟響
一匹馬從絹帛中躍起
它想超越其他
嗩吶規定的方向
想卸下? 肩上
變色的旌旗
再叩謝南方藏匿的
巨鳥? 鳥的秋天有些空曠
請給神一個固定的位置
請給骨頭一個
略高于神的位置
菊花卷過曠野
鳥成為花事的一部分
而鳥與風云不想
代替對父親最初的追緬
誰還能虛構那顆
六角藍星? 它占據了碑石
頂端? 必須告別的人
為所有奔跑的石頭流淚
……再朝拜北方
花束縮在雪的路途上
我? 等候什么?
掛滿泥墻的嗩吶正在
喪失呼喊的勇氣
我在與人
說來年種菊的事
來年? 鴻雁在天
露水掛在旌幡陳舊的
灰燼中? 一個
四處找尋父親的人
出沒于漫漫菊香
他? 忘記了
該如何以合適的
方式哭泣
但今晨的露水包括了
更為多面的來年
說到種菊? 我熟諳
風傾斜的表情
風? 吹亂了
菊繁復的根系
有一種冷起于
與菊平行的骨殖
誰想在石頭內部
種植露水?
這與我的苦痛極度
對稱的種植
可能會帶來更多
蒼茫之菊
指出玄鳥行跡的人
站在街面上
秋天屬于泥土
也屬于玻璃
畫滿鳥影的玻璃
藏起巨幅稻香
露水滑動? 旭日將
泥土和稻合并成
秋的標記……
云把三滴藍色露水
送到父親用舊的
皇歷上
風翻過的皇歷
印證? 鳥的夢境
在哪滴露水中
父親佇立? 像一句
讓石頭飛翔的
諺語——
風烈:稼穡與山河
互為尺度
那只嘗試貯存
露水的鳥? 已隨旭日
退至玻璃不懈
顫抖的臆想內側
紙船有虛擬的汛期
但此刻? 它還
停靠在一片
干硬的風聲上
誰給予廢棄的紙以
漂浮的輪回?
一滴水的流向
重復紙錯雜的折痕
虹躍出水滴
將大量紙質槳聲
鋪進風與
太陽的骨骼
有人想成為
船的倒影? 既契合于
盤旋的水勢
又與具體的水拉開
適當距離
而紙角涌現的
波瀾? 變得重要
你為紙船預設的渡口
正從返航者
夢境邊緣匆匆滑過
父親并未錯過這個日子
他在山中? 他指引
九月從柏樹的
側影里緩緩通過——
寒暑被一陣蟲聲
均分? 這只黑色蟲子
剛從風里拾回
父親舊年的足跡
誰把雷霆刻在山的
背脊上?一只紅色蟲子
用雨遞上的泥堵住了
它六角形的窗戶
田野變得寬泛
父親在田野上找尋
上個黃昏的回響
他看見遠處的河再次
涌過那些遺失
多年的稻粒
父親已不可能再錯過
任何日子了? 一只
藍色蟲子從燈的
肋骨上躍下
它? 掌握著秋天
多義的方向
特約編輯 驀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