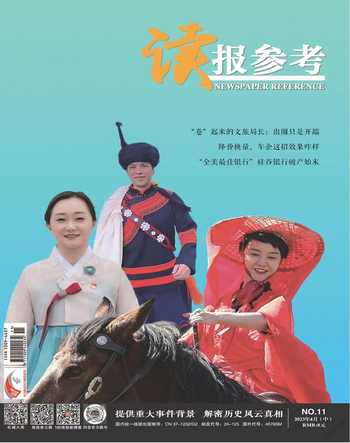把自己的余生托付給機構,靠譜嗎?
“我的余生可以托付給誰?”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重,越來越多的老人在晚年生活中遇到涉及人身照顧、就醫、財產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可以根據自己意愿確定監護人的“意定監護”,為解決此類問題提供了新的路徑。在通常選擇親屬和好友作為監護人之外,如今,專業的社會組織也成了可選項之一。2021年3月20日起施行的《上海市養老服務條例》已明確規定,支持專業性的社會組織依法為有需要的老年人擔任監護人或者提供相關服務。
意定監護需求大但機構少
所謂“意定監護”,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與其近親屬、其他愿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或者組織事先協商,以書面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在自己喪失或者部分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由該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
一般來說,意定監護的效力優于法定監護,因其可以自行選擇監護人,受到不少人歡迎。一位從事過意定監護公證業務的上海公證員告訴記者,從年齡段分布來看,目前進行意定監護公證的主要是老年人,年齡跨度在65歲至90歲之間。“從數量上看,每年我們要做200例左右,但咨詢量要翻好幾倍。”
“意定監護需求的增加,和獨居老人或孤寡老人等群體的增加密切相關。”從2015年起,上海申浩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張玉霞開始從事老年普法,她在調研中發現,子女不在身邊的老年人群體呈現增長趨勢,這部分老人面臨嚴峻的養老問題。
近年來,人口和社會結構變動,也讓公眾對監護的需求越來越大。張玉霞發現,第一代獨生子女成家立業后,由于工作繁忙、搬遷流動等原因,其父母往往會面臨無人可為其養老的困境。“特別是在上海,子女在外地或國外的情況比較普遍,獨居或者只有老兩口的家庭客觀上越來越多,他們對晚年的擔憂是現實存在的。”
“還有許多特殊群體也存在強烈的監護需求。”前述公證員說,近年來,進行意定監護的人群呈現多元化、低齡化趨勢。
但要找到一個值得托付、可信賴的監護人,并非易事。部分老人轉而尋求組織機構的幫助,通過簽訂協議,把社會組織、養老機構或村居委會等設置為自己的監護人。但由于意定監護在執行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風險,愿意主動承接這一需求的組織機構并不多。張玉霞發現,目前普遍存在需求大但機構少的困境,且監護機構多在一線城市,中小城市較少。
上海是意定監護服務最為活躍的城市之一。2020年8月,上海探索成立全國首家專門從事監護服務的社會組織——上海閔行區盡善社會監護服務中心。這也是目前上海唯一一家專門從事此類服務的社會組織。該中心法人代表顧春玲告訴記者,截至目前,中心已收到近200例咨詢,其中深入對接52例,簽約公證15例。
但顧春玲坦言,由于監護模式尚不成熟、老年人生活習慣等原因,目前,社會組織從事監護服務仍處于探索階段。
社會組織比親友更可靠嗎?
對大部分選擇意定監護的老人來說,首選的監護人是身邊的親友,實在不得已才會選擇機構。記者了解到,目前每年辦理的意定監護案例中,僅有5%左右的案例監護人為社會組織,其余大部分案例中的監護人仍然為個人。
在業內人士看來,相較于個人,機構的親情感較少。“在工作中,我們反復強調,監護人不是照護人,但在實際生活中,兩者往往是不分的。委托親屬、朋友、同事、鄰居做監護人,其中有情感因素在,監護人會做一些職責范圍之外的事,但機構不會。”前述公證員說。
機構的優勢在于穩定性和專業性。比如,有的老人會選擇年紀相仿的親朋好友作為監護人,一旦監護人的健康狀況不穩定,或者臨時改變主意等,就會產生無法履行監護責任的問題,機構則一般不存在這個問題。
此外,作為監護人,往往要承擔事關老年生活的諸多責任事項,包括選擇養老院、請護工、陪同就醫、手術搶救、存款領取、固定資產出售、身后喪葬、遺囑執行等,這些事務對缺乏相關經驗的個人來說難度較大。機構相對來說掌握的社會資源更豐富,比起個人更容易作出適合老人實際情況的安排。
在成立“盡善社會監護服務中心”前,顧春玲在養老行業做了10年,主要從事針對認知障礙老人的社區服務。多年的養老從業經歷,讓她對上海的養老和醫療資源比較熟悉,在承擔監護責任時,往往能為老人選擇更適合的服務。“比起個人,我們很清楚不同養老機構的側重點,也有同事專門負責就醫看病等事項,從這個角度看,團隊整合形成的專業性比個人強得多。”
盡管有諸多優勢,老人在選擇機構時仍顧慮重重。顧春玲告訴記者,在深度跟進的案例中,從老人和機構初次溝通到最后簽約,花費的平均時間將近半年,甚至有一位老人在中心還沒成立時就來咨詢,直到最近才正式簽約。
即便已經簽約,機構也不會立刻代替老人作出決策。顧春玲解釋說,和老人簽訂的意定監護協議分為代理期和監護期兩個階段。在老人意識清醒的情況下,大多數服務處于代理期,這期間由老人自行決策,機構僅輔佐決策或幫助執行。如果老人突然昏迷或者喪失行為能力,機構自動履行監護責任。“意定監護里最主要的原則之一,就是以老人的意愿為準。”
相關配套制度仍有待完善
許多人對意定監護的顧慮很大程度來自他人是否值得信任。 盡管法律已經支持社會組織提供監護服務,但對其監護服務的監管尚缺乏細則。“比如,當事人行為能力已經產生問題,難以在監護人有不當行為時自行維權,那這時由誰來監管監護人?法律還不明確。”張玉霞說。
記者了解到,實際操作中,往往是意定監護申請人、公證處和社會組織等多方共同根據實際情況擬定協議,缺乏可參考的法條或標準。但在近年來的實踐中,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比如,機構和老人簽署協議并公證時,明確監護服務和老人的財產不掛鉤,以避免“以房養老”騙局再次發生。
“如果以老人財產作為監護條件,那監護人很有可能希望老人活得越短越好,以盡快獲得財產,在一些國家,發生過此類悲劇。”前述公證員說,吸取國外經驗教訓后,目前國內的社會監護組織明確提出不介入老人的財產安置,在以服務時長收費的前提下,機構當然希望老人活得越久越好。
從目前的實際案例來看,較為普遍的操作是老人把房產賣掉后,將大部分資金放入公證處進行監管,小部分自留。老人住養老院的費用、護工費、生活費,以及監護組織的服務費,由公證處審核后從監管的資金中支付,社會監護機構如有先行墊付的費用,再找公證處報銷,每年底公證處會給老人一份詳細的資金使用報告。
在實際操作中,公證處、法院、村居委會或者民政部門都是天然的監督人,在費用支付等方面,監護機構也會定期形成監護報告。顧春玲介紹,為了進一步降低可能的風險,根據監護協議,老人和機構雙方均保留隨時終止服務的權利。此外,老人也可以設置第三方作為監督人,監督監護服務的執行。
“制度探索是一個過程,從長遠來看,建章立制是很有必要的,也需要有相應的法律依據。”張玉霞建議,規范監護行為以及監護機構和工作人員的獲利行為,加強監護機構與法院、公證處、居委會等部門聯動,監護機構應通過公證處簽訂協議,保障監護協議實際履行。
(摘自《解放日報》顧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