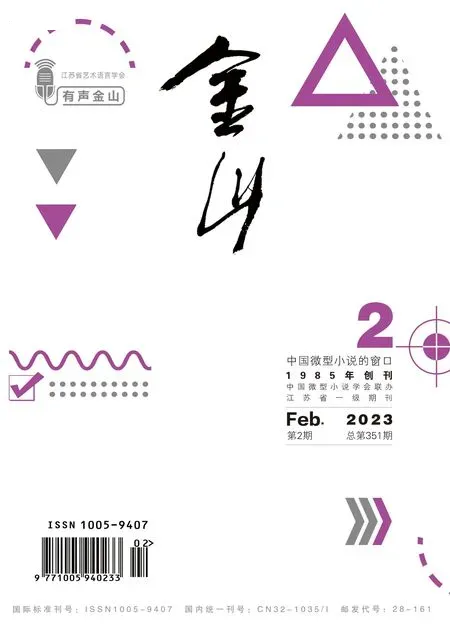老戴
新疆/林振國
老戴去世多年了。他曾贈予我兩本書,一本《甲骨文字帖》、一本《白鵑樓印蛻》——都是當時市面上買不到的。每當我瞥見架上這兩本書就不免會想起他,朋友贈物時說留個念想,大概就是此意吧。
老戴的父親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經學家——戴家祥。《白鵑樓印蛻》是戴老私人印集,治印者為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理事、中日蘭亭書會名譽顧問的方介堪,封面題簽為原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作序者亦皆為大家,足見此書分量。
《甲骨文字帖》作者為四川大學歷史系何崝,名為字帖,其實是用甲骨文寫的一首歌行,綜述甲骨文的發現及后世對它的研究,作者系戴老的高足。
我和老戴算不上深交。他和我先后調入同一所學校,他教物理,我教語文,也不屬同一年級組,不搭界。倒是聽說過一些他的事:北京農大生,來學校之前在69團。再有就是他老婆很漂亮,聽辦公室李建新說,他老婆剛來時,一時間轟動了整個69團,人們都爭相一睹其芳華。
有次老朱來我這兒,說:“戴定國住哪兒?走,去他那里看看。”我才了解到老朱和老戴下放時曾在一起待過。這也是我與老戴的交往之始。
老戴到兵團后境遇并不算糟,因為他學的是農機。全國最早用拖拉機的是兵團農場,一色蘇聯制造。訓練拖拉機手、如何維修拖拉機……正需要老戴這樣的人才。雖身處邊疆異鄉,但能把所學的專業派上用場,這一點想必老戴應該是頗感欣慰的,我想。
有回我同他一道去66團,落腳在老鄰居張建輝家。現在也想不起究竟因何而去了,我是從小在這兒長大,自有一份眷戀,但那兒也是令我傷心之地,所以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是不會去的。印象里好像是老戴要去66團,拉我作陪。無意中,老戴問起張建輝:“這兒有個張杰現在在干嗎?”
真是巧了!張建輝正是張杰的大兒子。原來張杰正是老戴當年培訓過的學員之一,后來任機運股股長。
還有件事,是老朱告訴我的,這里也記一下。時任教育處處長的梅林泉先生系老戴父親家祥先生在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時的學生。大概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老戴已近退休,學校開始給教師評定職稱。機會只此一次,老戴天真地想起了這層關系,于是把情況告訴了戴老,本意是希望父親能向這位昔日的弟子打聲召呼,走個捷徑。可沒有想到的是,老先生倒真的給梅林泉先生寄去一函,可內容卻是要梅先生公事公辦,不得徇私情。因此,老戴直到退休也只是中教一級。
老戴還有個弟弟,學物理的。因年齡相差,時代不同,因此境遇也迥然不同。老戴的弟弟最終留學、定居于美國。老戴給我看過胞弟的照片,氣宇不凡、一表人才。范縝有句比喻,命運如同一樹上的花,一陣風吹來,有的飄進人家窗戶,落在茵枕間;有的卻翻過籬笆,掉入溷藩。
這就叫命。
退休后,老戴常常去跳舞。這恐怕是他唯一的愛好。跳舞當然是和異性跳,為此便引起一些物議,我亦有所聞。有的人吃飽了專好管閑事,繪聲繪色添油加醋的,著實讓人無語,但這“倒霉蛋”卻并不以為意。
每次街上碰見,他仍夸張地高舉右臂:“嗨!”算是招呼,然后繼續匆匆趕路,鮮少停下來寒暄。常見他戴頂大禮帽,著一件短大衣,禮帽檐太大,和他削瘦的臉極不相稱。高大的身材,卻瘦得一根蔥似的,但精神好,走路跨步大,一沖一沖的,如同什么急事在等著他。
至于他的長相,網絡上搜索“戴家祥”,見其父如見其人。
后來,老戴搬去了石河子兒子那里。再后來聽說他去世了,死于癌癥。清癯非壽者相。沒想到!他不吸煙,亦不喝酒,幾無不良嗜好。
在我看來,老戴是很單純的一個人。在校時,我們交談并不多。除了集會時遇見,站在一起或坐在一起時會聊上幾句無關痛癢的家常外,幾乎無話題可說,大約是他學理我學文的關系吧,總有些雞同鴨講之嫌。所以一般都是他找話題,同我談文史方面的事,問我些唐詩宋詞,大概是在考我吧。
但一天他突然對我說,送你兩本書——就是文初所提到的那兩本。扉頁上竟是工整的行書,豎寫:“送給林振國老師惠存。戴定國敬贈。九六·三月。”還鄭重其事的在他名字下加了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