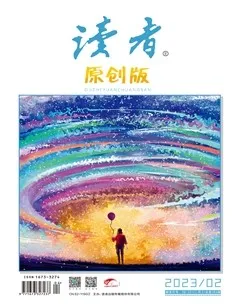燈塔日落時(shí)
文|譚斯萌
一
經(jīng)過(guò)兩次臺(tái)風(fēng)的洗禮后,被稱為“霧島”的花鳥(niǎo)島的真正魅力才初現(xiàn)端倪。
一切都恢復(fù)了安靜祥和,只有掉了漆的門把手和殘缺的院落盆栽顯示著臺(tái)風(fēng)“來(lái)過(guò)”的痕跡。清晨,于門口迎見(jiàn)淡藍(lán)色天空和金色海岸線的那一刻,我覺(jué)得經(jīng)歷任何都是值得的。
和許多在內(nèi)陸長(zhǎng)大的人一樣,對(duì)于沿海城鎮(zhèn)和島嶼,我總是有種天然的親切感,對(duì)于燈塔更是心向往之。而這座號(hào)稱遠(yuǎn)東第一燈塔、亞洲第二大燈塔的花鳥(niǎo)燈塔于我而言,無(wú)疑是一處向往之地。
從花鳥(niǎo)島碼頭通往燈塔,僅有一條瑪塔線公路,而唯一的交通工具便是島上的觀光車。
在前往燈塔的路上,我的腦海里不斷回放著記憶庫(kù)中有關(guān)燈塔的一切片段:在法國(guó)電影《燈塔路口》中,它是世界的盡頭,可以讓兩位小主人公逃離成人世界的枷鎖與世俗的規(guī)訓(xùn);在愛(ài)爾蘭動(dòng)畫《海洋之歌》中,燈塔猶如彼岸的歸宿;而在蘇菲·布萊科爾的凱迪克金獎(jiǎng)繪本《你好,燈塔》中,孤立的燈塔中蘊(yùn)藏著個(gè)體生命的無(wú)奈,卻也不乏家庭的溫暖。
相比之下,位于花鳥(niǎo)島西北角—花鳥(niǎo)山之巔的這座燈塔的所指更加返璞歸真,它集光波、電波和聲波等多種導(dǎo)航功能于一體,在建立之后的150余年里晝夜不息地運(yùn)轉(zhuǎn),與下坡處燈塔村供奉媽祖的天后宮隔海相望。由此,海島上最不可或缺的兩座建筑共同庇護(hù)港灣,照拂每一艘漁船平安歸來(lái)。
在花鳥(niǎo)島燈塔村,半山腰處廢棄的房屋隨處可見(jiàn),海岸邊停靠數(shù)只漁船。至9月下旬,花鳥(niǎo)島終于迎來(lái)風(fēng)平浪靜、陽(yáng)光普照的日子,讓人幾乎忘卻了它的“霧島”桂冠。
從碼頭出發(fā)的燈塔觀光車井然有序,下午4點(diǎn)以后,到燈塔去的日落專線也開(kāi)始投入運(yùn)行—畢竟,在花鳥(niǎo)燈塔前觀日落是大部分游客登島的首選“打卡”項(xiàng)目。
二
為了不浪費(fèi)有限的便利條件,我決定在駐島的最后一周,憑借駐島作者工作證,搭乘每天下午5點(diǎn)鐘的最后一班車,到燈塔去。
從游客中心出發(fā),乘著觀光車一路暢通,15分鐘后便可到達(dá)燈塔前。在一大批瘋狂按動(dòng)相機(jī)快門的游客群里,一位身穿制服、身材瘦削的中年男子十分醒目,他一會(huì)兒熱心地幫阿姨們拍照留念,一會(huì)兒和年輕人侃侃而談。他便是這里的燈塔看守人。
有他在的地方總是笑語(yǔ)不斷,他那口不太標(biāo)準(zhǔn)卻鏗鏘有力的普通話,伴隨著附近員工宿舍喇叭里時(shí)而傳來(lái)的廣場(chǎng)舞音樂(lè),在遺世獨(dú)立般的燈塔前,形成一片對(duì)立卻也詼諧祥和的氣氛。
波蘭作家亨利克·顯克維支曾在《燈塔看守人》中這樣寫道:“沒(méi)有比燈塔上的生活更單調(diào)的了。總而言之,這是一個(gè)僧人的生活,實(shí)際上還不止于此—這簡(jiǎn)直是一個(gè)隱居苦修者的生活。”
如今,燈塔看守人的職業(yè)似乎已變成一個(gè)被過(guò)度浪漫化的符號(hào),在許多文藝愛(ài)好者看來(lái),更是一種神秘的存在,是游離在陸地喧囂之外的詩(shī)意個(gè)體。然而,花鳥(niǎo)島上這位快樂(lè)的守塔人卻讓這個(gè)“世界上最孤獨(dú)的職業(yè)”徹底祛魅。
我鼓起勇氣,當(dāng)面詢問(wèn)這位大叔尊姓大名,而他那拗口難辨的舟山口音讓我無(wú)法確定。
“劉—seng—long—你自己到上面去看哦!里面有我的介紹呢。”他指了指燈塔陳列館。
來(lái)到燈塔陳列館,我終于在展廳的員工介紹欄上看到劉主任的大名:“劉生龍,1963年生于舟山岱山……”想不到這位渾身散發(fā)青春活力的大叔竟然比我的父母還要年長(zhǎng)。緊接著是一段密密麻麻的守塔履歷,總之就是在一座島守塔,然后搬到另一座島,之后又來(lái)到下一座……前后足足40年。而花鳥(niǎo)島,他從2008年就在這兒了。
“請(qǐng)問(wèn)我可以到燈塔上面參觀嗎?”為了不枉此行,我再次回到燈塔下,揮了揮手里的工作證。
“你要上去做什么?拍照片?這上面沒(méi)什么好拍的嘛……”他遲疑一下,又利索地掏出鑰匙,一邊打開(kāi)燈塔的大門,一邊嘟囔著,“算了算了,放你進(jìn)去吧!有什么好看的?里面有油漆味道……”
塔內(nèi)機(jī)器運(yùn)轉(zhuǎn)的聲音規(guī)律而平緩,蓋過(guò)了周遭的一切。我仔細(xì)觀察著這里的每一處結(jié)構(gòu),又順著陡峭的磚紅色金屬旋轉(zhuǎn)樓梯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爬。花鳥(niǎo)燈塔高約17米,內(nèi)部總共有三層,每層的樓梯銜接處都配有鏤花的白色支架,極簡(jiǎn)和質(zhì)樸中透著幾分精巧。
塔頂那顆直徑1.84米的巨型四面牛眼透鏡以每分鐘一周的速度旋轉(zhuǎn),光線射程達(dá)22海里。眼前的它在夕陽(yáng)的映照下閃爍著淡黃色的光暈。
從包裹著塔頂?shù)陌胪该鞯牟AТ跋蛲馔ィ@嗽谀_下翻滾,讓人仿佛置身世界盡頭,所有的焦慮和煩躁都在看到日落的那一刻消失殆盡。
此時(shí),塔下傳來(lái)一陣模糊的喊聲,將我從沉浸中喚醒,不知不覺(jué),我竟在塔頂足足逗留了20分鐘。我擔(dān)心破壞了規(guī)矩,于是不待劉主任催促,便自覺(jué)地沿著陡峭的扶梯向下走。抵達(dá)二樓時(shí),幾位游客歡欣鼓舞地進(jìn)來(lái)了,領(lǐng)頭的女士正是我所搭乘的那班觀光車的司機(jī)。
她看到我驚訝的眼神,抑制不住興奮地解釋道:“我們也上來(lái)瞧瞧,今天我們也能進(jìn)來(lái),真是幸運(yùn)啊!”
他們一行人的背影快速消失在三層的樓梯口。劉主任已在大門口守候多時(shí):“上面好看嗎?我說(shuō)你要是學(xué)工程的還好,寫文章的根本沒(méi)必要上去嘛!”
的確,對(duì)于塔內(nèi)的結(jié)構(gòu)和設(shè)備,我這個(gè)文科生一頭霧水。然而在塔頂看到的一切,足以讓我終生難忘。
劉主任還不時(shí)擔(dān)心地朝燈塔里喊:“同學(xué)們,小心一點(diǎn)兒!上去之后快點(diǎn)兒下來(lái)!真是的,有什么好看的嘛……”然而,留在燈塔之外的人群卻蓋過(guò)了他的聲音:“快看!日落太美了!”
燈塔頂上的游客也應(yīng)聲在窗戶邊排成一排,目不轉(zhuǎn)睛地望向海岸線。劉主任也轉(zhuǎn)過(guò)身去,竟也和游客們一樣掏出手機(jī),對(duì)著海平面拍攝起那段極致的日落。
“今天確實(shí)美。”
的確,守塔人的生活數(shù)十年如一日,但每一天的日落又不盡相同。
此時(shí),落日漸漸褪去橙黃色的外衣,變成淡淡的緋紅色。燈塔之光不知何時(shí)已悄然點(diǎn)亮,在晚霞中散發(fā)著淡淡的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