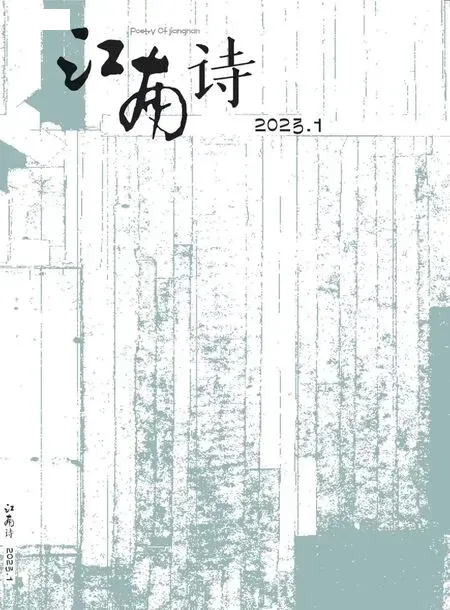渡 河(六首)
竇鳳曉
兩種眼淚
八月中旬。我將去另一個地方。
重新開始。包括寫作。
記憶到技藝為止。那兒。
可提供的糧食更少。誕生幸福骨感。
書信絕跡。情詩表達無從準確。
失去耐心。關門閉戶。老年將至。
坡度有其黃昏。隨口說出:
雨!商略黃昏雨。清苦之甜。
匆匆。可推翻的未來
紛紛趕來。前瞻性的鳥兒:在前方。
一尺之遙。鱗粉繽紛閃爍。
收斂的雙翅垂向大地。近還是遠?
“帶我去……”
“不。就在這里。現在。哪兒也不去。”
雛 菊
你不會告訴戀人,由于
切實的雛菊,你會放任
更多的微風,因為你不敢。
你不會告訴他
時間在雛菊的鋸齒邊緣
所聚成的細小風暴
將會波及你和他,僅留下眼淚。
甚至你不會告訴他,
由于這未知的危險,
你將取消
整個草原。
當雛菊取消草原,
告別會變得遲緩
渡 河
剛巧,在我要渡河的時候,
那船噠噠開了過來。
我說:“等等,我要渡河”
那是一艘有年歲的船了
藍色與紅色的條紋上
褐色鐵銹猶如耀斑
河上曾駛過這樣的一艘船嗎?
從前怎么樣,沒人見過。
未來怎么樣,我看不見。
此刻,被群山倒影
遮住的水面上,清幽寂靜地,
這條船應需而生
我等的,就是這艘船嗎?它是否預先
也構思了我?若僅是意識產物,
為何,它不是一艘新船?
河面空空蕩蕩。云扯著三角旗
馭風而行。我獨自站在河邊
看船徑直駛來,像發現了一位水手
巨鹿回夢
巨鹿懶洋洋,黠向山坡、
深谷和草場,一晃兒一上午光景。
拂略之美,幾乎粉碎了來意。
或是轉移,左傾右傾;
或是反對,無是無非。
它不很乖,但你可以命它,
挾持它,左右相搏般
數次謀殺它——以秒鐘為限。你甚至
可以乘興墜下,在借以安身的
谷底,替它植上適宜隱居的
螢火蟲草皮。你看,夜晚
就要升起來了——橘皮加
薄荷味的迷蹤正在加深!它迅速擴張的
半徑,象征著我們的困惑
晨曦中荷塘
三徑就荒[1]三徑:指家園,或喻歸隱。陶淵明《歸去來辭》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取直而行即可
抵達荷塘。你悸動于語言內部
那神秘關聯?此刻,物與物
相互俯就,奇妙對壘
有人絞盡腦汁,將苦味的詞
在荷塘未醒之時,提前寫出
荷塘蓬勃成一個人口大省,
嫩黃細蕊的巨型花朵,自成星球
龍蝦舉著紅色螯鉗低空潛行。青脊的
魚隊未盡其意,灑下宇宙墨點
你愿耽于此刻:這趨近肉欲的美,
愿能隨物賦形,無所禁忌
荷塘深處,淤泥涌動,仿佛白云回音
此刻,連居所未卜,亦已不是難事
純粹寫作
如今我是在用手指寫作。
我是說,從前,我用過
稿紙、用過電腦、用過心,
如今只能用手指寫。
當一個看不見的人
給我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
分別涂抹上一種特殊材料時,我知道
可以寫了,于是照辦。
此時,我不過仍是那具血肉之軀,
但終歸不同,與以往
跟朋友們跑步時不一樣,跟上司們
匯報工作時不一樣,跟丈夫談生活預算時
不一樣,但略微相似于
與貓咪嬉戲時。“嬉戲”一詞
并不準確,當我面對那團絨球
跟他眼睛對著眼睛時,
總感覺到內心升起一種
嚴謹的歡樂。
寫作即是
快樂之一剎,因而不能
訂立盟約,不能量化他、
優化他、帶著急于求成的
功利心,敗壞他。
人不能規范力不能及之事,
于是只好、也總是
聽天由命地,呆在深淵般的自我之中,
等待被指認、被顯現,
乃至被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