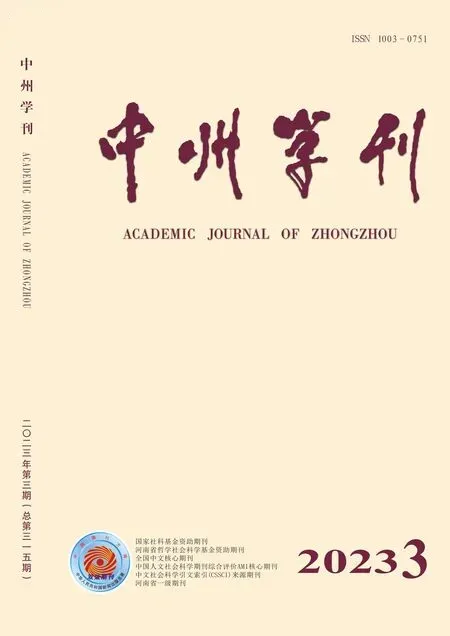數字時代的積極自由
李 石
在西方思想史中,積極自由理論因英國政治思想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的演講《兩種自由概念》[1]而名聲大噪。伯林在這篇演講中深入剖析了積極自由的理論結構,并對斯賓諾莎、盧梭、康德、黑格爾等思想家所闡發的自由理論進行了抨擊。從伯林的闡述中我們可以分析出積極自由理論的兩大特征:一是對自我進行劃分。區分出“較高自我”和“較低自我”,或“理性自我”和“欲望自我”,或“真實自我”和“虛假自我”等,并將“較高自我”“理性自我”或“真實自我”的實現當作自由。例如,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早系統闡發積極自由理論的哲學家愛比克泰德就認為,自由是理性自我的實現,而不是欲望自我的實現。他的精辟論斷是:自由不是通過滿足人們的欲望而獲得的,而是通過消除人們的欲望而獲得的[2]。二是將自由與特定的價值觀念聯系起來。在積極自由理論看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是自由,只有那些符合某種價值觀念的行為才是自由的。例如,偷竊顯然不是自由的實現。由此,在積極自由理論中,自由通常與道德相聯系,只有道德的行為才是自由的。例如,盧梭曾論述道:“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類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因為僅只有嗜欲的沖動便是奴隸狀態,而唯有服從人們自己為自己所規定的法律,才是自由。”[3]26由此,積極自由理論家經常將自由歸結為“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而所謂“真正想做的事”就是符合某種價值觀念的行為。
伯林在1958年對積極自由理論做出了精辟的分析。然而,隨著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的“自我”“真實欲望”“理性”這些概念都有了新的含義。這使得對積極自由理論的分析也有了新的可能。本文將在傳統積極自由理論的基礎上,分析數字技術對積極自由理論的影響,并討論伯林指出的積極自由的悖論可能呈現出的新形態。
一、人機混合體
積極自由理論要求對“自我”進行劃分,因此對積極自由的準確理解是以對“自我”的構建為基礎的。在數字時代,人類“自我”的最大轉變就是人類對人工智能的依賴以及所謂“人機混合體”的形成。
1960年,克萊因斯(Manfred Clynes)和克萊恩(Nathan Kline)在《航天學》(Astronautics)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賽博格與空間》的論文。作者在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賽博格的概念[4]。英文“cyborg”是“cybernetic organism”的結合,又稱電子人,指的是以機器作為人類身體的一部分,以增強人類能力,而形成的人機混合體。此概念提出后80多年來,人類一直朝著“人機混合體”方向飛奔。尤其是移動智能設備的普遍應用,更是加速了這一進程。而正在嘗試使用或已開始普及應用的可穿戴智能設備、植入式智能設備以及腦機接口等設備,更是使人成為名副其實的“人機混合體”。
數字時代的人從根本上來說,是數字設備與生物體的復合體。近20年來,移動智能設備得到普遍應用。依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國移動電話用戶總數達16.43億戶,其中5G移動電話用戶達3.55億戶[5]。可以說,人人都有手機,未成年人則有電話手表等智能設備。數字治理、數字經濟、數字交通……數字時代的來臨意味著一個人沒有數字設備就沒有合法身份,同時也將喪失許多生存所必需的決策能力。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沒有智能手機就無法出示“健康碼”“行程碼”,而這意味著你無法乘坐公共交通,無法進入商場、超市等公共空間。人與機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合在一起,而這一進程就像時間一樣,是不可逆轉的。
智能手機是外在于人體的智能設備,人們還可將其看作是外在于人的工具。然而,一些更貼近人體甚至進入人體的智能設備正在被發明出來,并以空前的速度與人體融合在一起。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智能穿戴設備、智能植入設備和腦機接口設備。這些設備最開始在醫療領域得到應用。例如,可穿戴的智能設備被用于檢測人們的各種生物學指標,體溫、心跳、血壓、血糖等。并將這些數據傳送給相關人員,如當事人的主治醫生或是當事人購買保險的保險公司,以監測當事人的健康狀況。穿戴式和植入式智能設備的應用,一方面使得數字設備與人體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數字設備能夠比行為者自己更清楚地了解自身,更好地調節身體狀況。例如,數字設備通過血壓血糖的監控,可能比行為者自己更早地預測到疾病發作,并提醒行為者或醫生提前做好防范。植入身體的心臟電子起搏器與人工肺已經能夠實現在人不自覺的情況下維持有機體的正常運作。智能假肢可以通過植入的智能芯片給佩戴者提供觸覺反饋;人造視網膜或視覺神經芯片能夠為失明者恢復部分視覺;智能神經裝置可以為神經損傷的病人恢復部分運動能力;等等。這些智能設備能夠比當事人更清楚地預知其身體狀況,為保險公司提供更準確的預測,幫助保險公司獲利。而腦機接口則可以將人腦與外部設備連接起來,實現大腦與外部設備之間的信息互通。例如,通過腦機接口,一個人只要憑借意念就可以打開家里聯網的空調等。這些“侵入”人體的數字設備,就像一個新的自我,而且是一個更聰明、更準確的自我。那么這個新的自我與那個原有的生物體自我之間是什么關系呢?
二、數字自我與生物自我
數字設備深入而廣泛的應用,最終將在人的生物自我中植入一個“數字自我”。這個數字自我雖然不是我們傳統上所理解的“生命”,但它與生物自我在本質上卻可能是同質的。因為,它們都可以歸結為算法。所謂“算法”,指的是“進行計算、解決問題、做出決定的一套有條理的步驟。所以,算法并不是單指某次計算,而是計算時采用的方法”[6]75。依照這個定義,人類大腦的工作原理確實可以歸結為一套做出決定的有條理的方法。一個人在做出決策時會考慮哪些因素,如何處理他接收到的信息,又會受到哪些環境因素的影響,受到什么價值觀念的影響?只要搞清楚這些機理,那么我們只需將這些相關數據輸入“人類大腦”這個處理器,就會得到特定的輸出。這不正是數字設備處理數據的方式嗎?由此看來,人類的大腦就像一個數據處理器,而人們為人處世的方式就是某種特定的算法。如是觀之,數字設備則是一個比人類大腦更高級的算法。因為,數字設備可以讀取更多的信息,并在短時間內進行更多更復雜的計算。谷歌等數字巨頭新近推出的人工智能產品還可以進行自主學習,高效率地學習人類大腦無法企及的海量知識。“阿爾法狗”和“阿爾法零”擊敗人類頂尖圍棋手的例子就生動體現了人工智能對人腦的超越。2016年,機器人“阿爾法狗”在學習了數百萬人類圍棋專家的棋譜之后第一次擊敗了人類棋手,而2017年擊敗人類頂尖棋手的“阿爾法零”則擯棄了人類棋譜,只靠深度學習就從完全不會圍棋到擊敗頂尖棋手,并且只用了四個小時的學習時間。這足以展示人工智能的超強能力。如果我們將數字自我和生物自我都看作是算法,那么數字自我就是比生物自我更為強大的算法。
如上所述,在傳統的積極自由理論中通常存在著兩個自我。例如,愛比克泰德所說的“理性自我”和“欲望自我”;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兩種快樂理論中包含的“較高自我”和“較低自我”[7];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理解的自由就是“自我實現”中的“真實自我”以及與之對立的“虛假自我”[8];等等。而在數字時代,這個理性的、較高的、真實的自我卻有被數字自我取代的危險。在傳統的積極自由理論中,較高自我對較低自我的指引被看作是自由的實現。而在數字時代,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兩個自我之間的關系呢?數字自我與生物自我之間到底誰聽誰的呢?
在數字設備和生物體組成的“人機混合體”中,兩個自我之間可能存在著下述三種關系:一是數字自我是生物自我實現自身目的的工具,數字自我聽命于生物自我;二是數字自我對生物自我的命令提出挑戰,違背生物自我的命令;三是數字自我反對生物自我的意志,并試圖改變生物自我的意志。
在第一種情況下,兩個自我之間是“下命令”和“去實現”的關系,就像皇帝和他的大臣一樣:生物自我給出“命令”,而數字自我則想辦法去實現。生物自我借助數字自我的幫助,最終實現自己的意志。例如,行為者借助導航找到目的地。當然,導航有可能出錯,這時生物自我可能聽從數字自我的錯誤指示,無法到達目的地,自由受挫;生物自我也可能忽略導航的錯誤指示,自己找出正確路徑,同時實現自由。但不管怎樣,數字自我依然是生物自我的工具,而工具好不好用則可能關系到行為者的自由是否能夠實現。然而,工具有時候會反客為主,這就涉及下面要討論的數字自我違背或試圖改變生物自我之“意志”的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況。
在第二種情況下,生物自我給出命令,數字自我反對生物自我的命令,使其意志無法達成。例如,一個人坐在自動駕駛的汽車中,并將目的地設為某風月場所。這時,智能設備報警,不建議車主人去該場所,并擅自做主將車開回家了。人工智能要做到這一點并不難,只需要在自動駕駛的程序中將某些目的地設定為“黑名單”即可。那么在這一過程中,數字自我顯然成了發號施令的那個自我。那么這兩個自我——生物自我和數字自我——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自我”呢?如果我們將生物自我當作“真正的自我”,那么我真正想做的事就是去風月場所,所以當自動駕駛汽車將我帶回家的時候,我的自由并沒有得到實現。但是,如果將數字自我(這個更理性、更道德的自我)當作“真正的自我”,那么我真正想做的就是回家而不是去風月場所,而正是自動駕駛汽車使我做到了這一點,所以人工智能幫助我實現了自由。在數字時代來臨之際,我們應采用上述哪種方式來理解自由呢?
在第三種情況下,當數字自我反對生物自我的意志時,它并非直接違背生物自我的意志,而是通過某些操作來改變它認為不恰當的意志。例如,一個人想吃糖,但數字自我在檢測了生物自我體內的所有生物指標之后認為此刻不適合吃糖,于是向其發出警告。但此時生物自我仍然想吃糖,并認為人生如果不能享用美食,就沒有意義。于是,數字自我可能通過某種“賄賂”來改變生物自我的意志。例如,給出“不吃糖就可以在游戲積分里獲得獎勵”這樣的提示等。在這樣的情形下,數字自我和生物自我雖然沒有發生直接的沖突,但生物自我真正想做的事情被修改了。那么,到底哪個意志才體現出行為者“真正想做的事”呢?是原先沒有被修改的意志,還是被數字自我修改之后的意志?而聽從數字自我勸告的行為者是否做了他真正想做的事,是否實現了積極意義上的自由呢?
三、誰是主人
人因為擁有自己的意志并能夠借助工具實現自己的意志而被尊為萬物之靈。人類也因此而自認為是自由的。由此,積極自由的核心含義也經常被理解為自主(autonomy),亦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自己是自己的主人(self-mastery)。例如,站在積極自由立場對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做出批評的拉茲就將自由理解為“自主”,理解為自己成為自己人生的“作者”(author)。在他看來,自主是一種自我創造的理想,“個人自主的理想就是人們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把握自己的命運,在他的整個人生中通過一系列的決定來塑造它”[9]。
相比于人們過去對工具和機械的應用,數字時代人類與機器的關系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在計算機被發明出來之前,機器是人類體力的延伸;而在數字技術普遍應用之后,智能設備是人類大腦的延伸。它們能代替人思考、判斷、做出決策,甚至幫助人們形成新的意志。因此,數字自我的植入讓自由的含義模糊了。在“人機混合體”中到底誰是“主”,是數字自我還是生物自我?而自由又是什么,是數字自我做主還是生物自我做主?
為了更好地理解自主的自由,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孩子逐步成長的過程。有經驗的家長都知道,要培養孩子的獨立人格,一定要有意識地讓孩子在一些事情上自己做決定。例如,四五歲的時候,可以讓孩子自己選擇玩具、衣服;七八歲的時候,開始讓孩子選擇自己喜歡閱讀的書;等到了十幾歲,就需要孩子自己選擇要學的專業;成年以后,則要自己選擇結婚的對象;等等。這正是一個人的“自主性”(autonomy)的形成過程。在不斷選擇的過程中,一個人逐漸成長為一個有主見的人,成為自己生命的作者,自己生活的主人。相反,如果家長處處越俎代庖,那么孩子即便成年也毫無主見、任人宰割,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而喪失了“自主性”的人生必然是不自由的,他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是“真實自我”,無法實現自由。
然而,在數字時代,這套理論變得含混其詞。因為,即使是很有主見的成年人,在做出選擇的時候也需要咨詢一下“谷歌”或者“百度”,或者是ChatGPT。這其中不僅包括買什么樣的衣服、玩具、書籍這類無關緊要的選擇,也包括考大學報什么專業、成年后選擇什么職業,甚至是和誰結婚這類重大選擇。人工智能、大數據,各種算法無時無刻不在為人們出謀劃策,并且給出讓人難以拒絕的選項。這就像一個非常強勢的家長,為孩子的方方面面做出了周密的安排,而且完全不允許孩子有第二種選擇,因為一切都計算好了,孰優孰劣都擺在眼前。就像導航系統已經精確地規劃好用時最短的路線,人們就沒有理由再選擇第二條路一樣。而人類呢,則是被慣壞了的孩子,各方面的能力都在退化。各種機械的應用已經使得人類的四肢大大退化了,而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則必會導致人類大腦各種功能的退化,這其中包括計算能力、溝通能力、判斷力等。正如《終極算法》一書的作者所說:“當前的一些公司想擁有數碼的你,谷歌就是其中一個。謝爾蓋·布林(谷歌創建者)說:‘我們想讓谷歌成為你大腦的第三個組成部分。’”[10]總之,有了處處為人類著想、為人類做主的人工智能,人類將毫無懸念地成為無主見的“巨嬰”。
四、強迫自由與數字獨裁
1958年,當伯林討論積極自由理論時,他抨擊的是積極自由理論隱含的強迫自由悖論,以及這一悖論將導致的專制和獨裁。積極自由理論確實有這樣的危險。如果我們將積極自由所推崇的“真實自我”外化成一個政治權威或道德權威,并且將對這個權威的服從當作是自由,那么,積極自由就可能推導出“強迫自由”悖論,而在政治現實中則可能導致極權統治。在伯林看來,盧梭的自由理論正是做了類似的推演。盧梭認為,所謂自由就是自己的行為聽從自己的意志。在《山中書簡》中,盧梭對自由做出這樣的論述:“與其說自由是按自己的意愿做事,不如說,自由是使自己的意志不屈服于他人的意志,也不使他人的意志屈服于自己的意志。”[11]盧梭認為,在人們締結社會契約之時,人們的意志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新的意志——“公意”。因此,在締結社會契約之后,每個人的自由就轉變為聽從公意的指揮,而公意就代表著每個人的“真實自我”。盧梭論述道:“任何人不服從公意的,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恰好就是說,人們要迫使他自由。”[3]24伯林對這種以“真實自我”之名行強迫之實的做法極為反感,這也是他批評盧梭的原因。
防止“強迫自由”以及極權統治的關鍵在于不要將“真實自我”外化成任何道德權威、宗教權威或政治權威。“真實自我”是屬于行為者自己的,誰也不能代替行為者自己說出他“真正想做什么”。只要堅守這一點,就不可能出現強迫自由的情形。筆者曾經提出一種“新積極自由”理論,試圖通過否認“他者猜想”而阻止內在權威的外化,以防止產生“強迫自由”的悖論[12]。然而,這一策略在已然到來的數字時代卻徹底失敗了。因為,數字自我和生物自我,哪一個才是真實的自我,這一點是不清晰的。伯林在分析積極自由理論時反對強迫人們自由的外在權威,而現在這個強迫自由的權威卻可能就在每個人體內,或者以網絡形式格式化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身體內的各種感應元件以及生活中的各種數字設備隨時可能向人們發出指令,這是一個更理性更智慧的聲音,不服從“它”就無法實現真正的自由(例如,不能獲得健康),但如果服從它那就是自由嗎?強迫他人自由悖論又一次浮出水面,而且是以更難以拒斥的方式。
前文說到,積極自由理論的第二個特征是將自由與道德聯系起來。這一點與積極自由的理論結構息息相關。積極自由理論首先將自我分為“較高”和“較低”兩個自我。對于這兩個“自我”孰優孰劣,只有通過特定的價值判斷,才可能進行挑選,并最終實現自由。例如,每天早晨當我在睡夢中聽到鬧鐘響起的時候,都會產生兩個自我,一個“想繼續睡覺的自我”和一個“理性起床的自我”。那么,實現哪一個自我才是自由呢?積極自由理論家通常認為,實現那個符合正確的價值觀念的自我才是自由。因此,如果我偷懶沒有起床,那我并沒有實現自由;相反,如果我掙扎著起床,按時到單位上班,那我就實現了自由。由此,自由就與特定的價值觀念聯系在一起。只有道德的人才是自由的,而惡人永遠不可能獲得自由。正如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家愛比克泰德所言:“沒有一個惡人能夠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所以沒有一個惡人是自由人。”[2]457因此,在積極自由理論家看來,人們做的事情必須是道德的、符合主流價值觀念的,才可能是自由的。
在數字時代,價值觀念對個人行為的規訓可能以更深入、更直接的方式發生。人們時時刻刻依賴的數字系統不僅能幫助人們做出更為理性的決策,還可能在倫理、道德甚至政治上對人們進行系統的指導。在數字自我和生物自我這兩個自我中,數字自我以其優越的數據處理能力充當了那個指引人們獲得自由的內在權威,而它同時還是一個道德權威。由此,在數字時代,為了幫助人們更好地實現自由,就完全可以在植入人體的生化設備中裝上一個倫理軟件,以控制人們的價值觀念。就如上文提到的例子,如果我乘坐一輛自動駕駛的汽車,并設定目的地為某風月場所或賭場。這輛裝載了某種嚴苛的道德軟件的車可能會向我發出警告,告訴我去那里是不道德的,它甚至可能拒絕我的請求,將目的地直接改為回家。如此一來,林林總總的智能設備不僅是幫我實現自由的助手,還將成為塑造三觀的人生導師。在數字時代,福柯所說的“規訓”與硅谷企業家們所說的“自由”并非背道而馳。準確地說,它們就是同一件事。
類似地,我們還可以在這些數字設備中裝載政治軟件。如果智能設備的使用者產生了某些不利于統治權力的想法或行為,那么這套系統就會發揮作用,將這些想法和念頭扼殺在搖籃之中。再以自動駕駛的汽車為例,如果我將目的地設為正在發生游行示威的地點,那么這輛汽車可能又將我帶回家。或者是,我如果想在網絡上發表抱怨某一政策的言論,而我的輸入系統就會自動報警。可以預見的是,這個數字自我最開始是以“健康”的名義指導行為者的各種行動,后面就可能以各種其他名義如安全、效率、道德、正義等,指導行為者的各種行動。我們是否能避免,在不斷演化的過程中,這個“超級自我”演變成一個內在于我的“數字獨裁者”?如果在我的身體中,或者在全方位包裹我的數字環境中,出現了一個這樣的獨裁者,那么我是更自由了還是完全喪失了自由?伯林要是能活到今天,他會撕心裂肺地吶喊“這不是自由,這是強迫”嗎?看看下面兩個真實的數字產品,大家可能會對數字時代的“強迫自由”有更為真切的理解。美國科創公司研制出的一款名為Pavelok的電擊手環,手環與智能手機相關聯,如果手機用戶未能完成之前自己設定的目標如戒煙、停止咬指甲、早睡等,那么手環就會釋放電流電擊用戶。另一款智能耳機則可以根據分析用戶頜部的運動和聲音,推算出其進食的速度、吞咽下的食品數量和攝入的卡路里。一旦攝入量超過之前規定的數量,智能耳機就會對用戶進行懲罰[13]。
當伯林批評積極自由理論時,他所批評的獨裁者是外在的,他們無法進入每個人的大腦中直接對人的意志進行操作。然而,在數字時代,科技賦予了人類這樣的力量:對人的意念進行監控、改寫,或者通過數字設備的設置來避免人們不符合某一價值觀念的行為。這樣一來,伯林所抨擊的“極權統治”就可能進入人們的頭腦,直接作用于每個人的決策機制,將所有的非道德行為和不利于統治權力的行為扼殺在搖籃之中。如果數字技術最終導向“數字獨裁”的話,這種獨裁統治的形態會更加隱蔽、更為高效,也更徹底。尤瓦爾·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論述道:“在未來,可能所有公民都會被要求佩戴生物統計手環,不僅監控他們的一言一行,還掌握他們的血壓和大腦活動。而且,隨著科學越來越了解大腦,并運用機器學習的龐大力量,該國政權可能會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知道每個公民在每個時刻想些什么。”[6]60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德國成功洗腦德國人民,使他們成為極權統治下的戰爭機器人。數字獨裁可能不需要像希特勒那么費勁地進行意識形態宣傳,而只需通過人機接口,再裝幾個意識形態軟件,就把所有公民變成了馴服的臣民。然后,再生產出成千上萬無所畏懼的機器人戰士,大概就能擁有希特勒所夢想的征服世界的力量。
另一方面,從數字系統的設計來看,數字技術在價值學說與社會現實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聯系。人們能夠將不同學者闡發的道德學說或政治學說數字化,并加載到諸多軟件當中。例如,在自動駕駛系統中裝載“即使車毀人亡也不能撞倒行人”的軟件,或者裝上“遇到危機情況首先保護車內乘客”的軟件,而這樣的自動駕駛汽車就成了一輛有著自己獨特的價值判斷的汽車。道德學說和政治哲學說可能被設計成軟件,裝載到每個人的決策機制中。這將是哲學與現實最直接的關聯。哲學家第一次擁有了直接改變現實的力量,而哲學家是否該為此負責呢?例如,那個裝載了拒絕將人們帶到風月場所軟件的汽車,是否會收到用戶的投訴?而這樣的投訴是對康德的投訴,還是對汽車公司的投訴呢?如赫拉利所言:“歷史上第一次,可能會有哲學家因其所提出的理論造成不幸結果而被告上法庭,因為這也是歷史上第一次能夠證明哲學概念與現實生活中的實踐有直接因果關系。”[6]56在思想史上,有許多政治思想家的學說都曾被認為導致了很糟糕的政治現實。例如,許多人認為盧梭的政治思想導致了法國大革命中的血腥屠殺;尼采的超人哲學引發了希特勒的極權統治;等等。但是,沒有人能夠真正起訴這些大思想家,因為思想與現實之間的因果鏈條是不清晰的。但是,在數字技術得到普遍應用之后,道德學說、政治學說等價值學說通過程序設計而被加載到數字系統中,由此而規范各種社會現實。數字技術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間建立了直接的關聯。哲學家們做好準備為自己的學說擔負直接責任了嗎?
綜上所述,數字技術的普遍應用讓人類變得更加強大。在數字時代,人們能夠更清晰地認識自己,高效而快速地實現自己的意志。然而,數字技術在增強人類自由的同時,也使得人類的自由變得含混不清。因為,在數字時代人類以“人機混合體”的方式存在,每個人的自我中都包含著一個“數字自我”。這個數字自我比原有的生物自我更理性、更強大。數字自我能夠為生物自我出謀劃策,甚至對生物自我的意志指手畫腳。而如果我們應用傳統的積極自由理論,則很可能將這個“數字自我”的實現闡釋為自由。由此,傳統的積極自由理論與新興數字技術的結合則可能發展出一個精確控制每個人的“數字獨裁者”,而政治現實則演變為數字極權。到了那時,人類的自由可能就真的岌岌可危了。人類社會想要避免數字極權,只能加快現有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使得更多的人能夠對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數字產品的應用(尤其是數字治理方面的應用)發表意見,防止形成專斷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