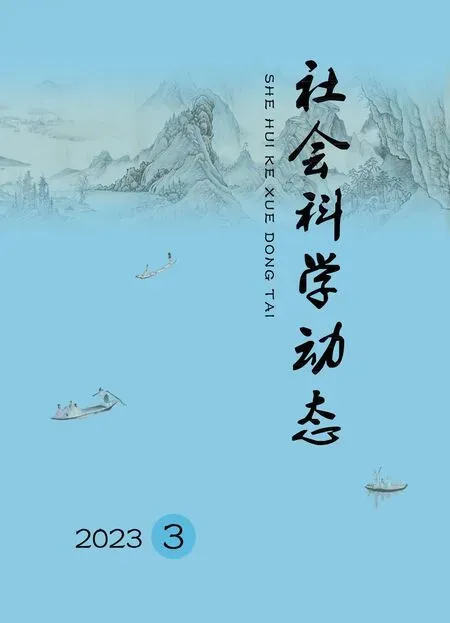唐代監察制度研究述評
黃開心 張衛東
傳統史料對唐代監察制度的記述,多載于史書、政書和類書中,如《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鑒》等史書中的職官志或散見于全書的相關記載,如《唐六典》《唐會要》《唐律疏議》《貞觀政要》《全唐文》《全唐詩》《通志》《通典》《文獻通考》《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和《文苑英華》等,還有一些出土文獻如敦煌文書和墓志碑刻等,這些都可以作為基本史料經考證后使用,這里不作詳細介紹。對唐代監察制度的研究,學界已有大量成果,主要集中在對御史臺、地方監察制度、唐代監察制度歷史經驗教訓和監察制度在唐代政治體制中的運作及變遷等方面的討論,囊括了學術論著、碩博論文、學術期刊和報紙文章等各類成果,涉及的專業主要有隋唐史和法律史,也有歷史文獻學、政治學和古代文學等學科的參與。本文主要從歷史學視角重點梳理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唐代監察制度研究的學術史梳理
清季民國時期由于西方學術理論的持續傳入和國內變革的不斷影響,學界開始批評傳統史學并尋找歷史研究的新理論和新路徑,梁啟超首先在《中國之舊史》一文中指斥傳統史學的編撰體例和論述形式有“四蔽”“二病”,認為“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①,主張“政治史”內涵應是其批評的“傳統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政治史”,由此把傳統史學歸入政治史的概念中②,并提倡進行社會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等新史學研究。學界隨之掀起新史學革命并發生多次論戰③,對新史料的發掘更甚于對傳統史學的堅守,古代史研究更加向下探視社會底層面貌和倡導疑古傾向,甚至在史學研究中出現“史料的廣泛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這兩種傾向并存的詭論現象④,使得政治史研究遭遇困境。在這一大背景下,監察制度史作為政治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深受影響而日益邊緣化。目前可見較早涉及唐代監察制度史的現代史學研究成果是高一涵《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1926)和徐式圭《中國監察史略》(1937)。高書按沿革體例研究了中國古代御史制度的發展變化⑤;徐書則以動態發展的視角論述監察制度在唐代的鼎盛和在五代十國時期的衰落,這一觀點到今天也還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⑥。
20世紀40年代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論述稿》兩部著述的問世,深刻影響了中古政治史研究,以事件、集團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范式流行開來并影響其他斷代研究,唐代監察制度研究領域也受到了影響,但由于政治史研究的困境和國內形勢變動的影響,長期以來專門運用這種研究范式討論唐代監察制度的學術成果在數量上相對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如部分學者注意到武周時期御史臺的變化,并用“集團”或“事件”的分析思路討論了武周政權的社會基礎和御史“進狀”“關白”現象。這其中,有關唐代“進狀”“關白”的討論最早是由日本學者八重津洋平提到的,中國一些學者后來又進行了補充和總結性的討論。⑦大體而言,這一時期學界對唐代監察制度的研究仍然集中在對官制設置和變遷的討論,只是在具體討論上有借助這種研究范式。
值得注意的是,白鋼、侯旭東和孫正軍等人對“制度史”研究進行了系統性的回顧和反思。白鋼認為,20世紀的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是以專史形式“自立”,很多論著實際是“從純官制史研究到向規范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轉化”;侯旭東則認為在20世紀20年代制度史就已經大致成型;孫正軍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出現多種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理路。學者們大致認為,制度史自20世紀以來已逐漸從政治史中“走出來”,在20年代“作為一門專史,已經大致成型”,并最終在80年代自成門戶。⑧在這個基礎上,學界形成了多條制度史研究路徑,如閻步克主張一種發軔于梁啟超的“制度史觀”⑨;鄧小南提出“活的制度史”和“制度文化”視角⑩;侯旭東提出“日常統治史”的理論與方法?;李里峰倡導“新政治史”;吳宗國等人主張推行“實際運行的制度”和“政府的運行機制”等概念下的“政務運行機制”研究?,等等。唐代監察制度史研究也跟隨這種變化趨勢,出現了許多新特點。在研究內容上,既有對唐代中央監察體系和地方監察體系的繼續關注,也有對監察制度的整體梳理、對歷史經驗的分析和監察制度在唐代政治體制中的運作和變遷的研究等。在研究分期上,既有對唐代監察制度的斷代考察,又有在通史視角下對唐代監察制度的概括性分析,還有把唐代監察制度置于漢唐時期、唐代前后分期、五代或唐宋時段等的嘗試。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引入多學科如法學、文學、歷史文獻學、社會史和文化史等綜合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更多探討具體官制變化和監察機制的實際運行等問題,并使用了更廣泛的史料如墓志碑刻和文學作品等嘗試進行新的分析。隨著研究范圍的擴展和研究視角的轉變,有關唐代監察制度的研究不斷深入,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亮點。
二、總體性研究
對唐代監察制度的總體性研究是唐代監察制度研究領域的重點,有很多有代表性的論著。徐連達、馬長林的《唐代監察制度述論》是目前學界公認最早專門討論唐代監察制度的著述,詳細論述了唐代監察制度的內容和特點。?陳仲安、王素的《漢唐職官制度研究》有一節專講漢唐時期“中央行政監察機構的演變”,以長時段的眼光總結漢唐中央監察機構的變化特點。?陳仲安還另外撰文討論了這一時段下的監察權力的分配調整。?胡滄澤亦在相同視角下考察了監察制度的變革。?以通史專題為視角,涉及唐代監察制度研究的著作也有很多,較具代表性的有前述民國時期徐式圭的《中國監察史略》、彭勃和龔飛蒼合著的《中國監察制度史》、胡滄澤的《中國監察制度史綱》、賈玉英的《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發展史》、李孔懷的《中國古代行政制度史》、邱永明的《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史》、胡滄澤的《中國監察史論》、曾哲的《中國監察制度史》、張晉藩的《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史》等等。?胡寶華的《唐代監察制度研究》是目前很具有代表性的斷代專題著作,他對唐代監察制度的研究視野更寬廣深入,還涉及到了對諫官制度的考察,書中大量運用了計量分析方法,更加直觀地反映了唐代監察體系的運行情況,也討論了“唐宋變革論”、唐代士族發展狀況和唐后期地方監察的兩種不同形式等問題,學術價值較高。
三、御史及相關研究
御史臺和御史制度是另一個研究重點,歷來就有很多學者高度關注并持續推進。御史臺的核心職能是彈劾與糾察,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監察御史等職官分使對三省六部、京官和地方要員的監察權。前述八重津洋平、胡寶華、霍志軍和林曉煒等人對唐代“進狀”“關白”的討論就涉及對唐代御史彈劾權力的研究。胡滄澤以列表分析的形式,從兩唐書和《資治通鑒》等史籍中發現,在德宗貞元年間御史大夫“官不常置”而“實際上以中丞為縣臺之長”的現象,繼而展開對唐代御史大夫在具體工作內容上的變化分析,認為盡管形勢多變,但御史大夫終唐一代始終是御史臺最高長官,位高權重,地位非凡,對肅清朝政有著重要的作用,唐代御史臺對一般事件的彈劾以臺院為主,對重大事件的彈劾則以御史大夫為主,彈劾的對象、依據、程序、儀式、效果和作用都有明確體現。?他還探討過御史臺在財政經濟工作上的監督作用,明確指出御史臺對唐后期經濟發展和政權穩定作出的貢獻。?吳曉豐具體討論了唐代奏彈制度的運作、書式、內容結構、功能轉變和禮制意義。?萬寶璋從經濟史的角度分析了唐代御史在財經上的監督作用,認為皇帝在監察過程中有決定性的地位,皇帝的態度對監察效果有著重大的影響,皇帝若“不問”“不窮其事”或“原之”,監察的案件很可能會不了了之,而御史本人也會因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及個人素質的制約,對相關案件處理的效果有著微妙的差異,尤其是武則天時期和安史之亂以后,御史受當時政治氛圍的影響更為明顯,表現得相對懈怠。?王素考察了唐代御史臺獄的置廢時間、建設原因、構成規模和職掌權力等具體內容。?杜文玉考察了五代時期的御史臺設置情況和變化。?胡寶華認為唐代御史在官僚制與社會輿論中表現出兩種不同的形象,這導致了唐前后期御史地位的升降變化。?賴瑞和的《唐代中層文官》討論了御史制度和錄事參軍,認為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是“極清貴的官職”、皇帝的“耳目”,也指出唐中葉以后方鎮使府中的文官幕佐可能帶御史臺虛銜而沒有執行御史的職權等現象。?王孫盈政針對唐后期御史臺的情況提出了“政務官化”的觀點。?張雨則參考“政務運行機制”研究方法分析了唐前期御史臺的行政特點和其在法律運作和政治運行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目前對唐代御史制度考察最詳實完備的論著還屬胡滄澤的《唐代御史制度研究》,該書以專題斷代形式對唐代御史制度進行了系統考察,尤其附錄和附表部分學術參考價值很高,對御史制度研究有很好的示范性。?黎蕓對《唐會要·御史臺》部分進行了整理與研究,考證了其版本源流,并對《唐會要》中記載的御史臺內設置的主簿、錄事二人進行了考辨。?
四、地方監察制度研究
唐代地方監察制度研究越來越引起重視,較早且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何汝泉對唐代前期的地方監察制度的考察。?隨著研究的不斷推進,對唐代地方監察制度的考察也越來越具體,既有采用長時段法的宏觀研究,也有具體到某一官職或監察現象的碎片化研究,如寧欣論述了唐后期巡院的出現給地方監察制度帶來的變化、巡院監察職能的逐步擴大、巡院維系中央統治和財政運轉的作用等問題。?齊濤則注意到了巡院監察制度的發展反映了唐宋時期官僚體制的巨大變革。?賈玉英認為唐宋兩朝完成了地方監察體制向固定型、多元化、多層面的變革,是我國封建社會地方監察體制前后兩期的分界線,在安史之亂及以后的諸多戰爭帶來的巨大影響、賦役制度變更和財政式國家體系形成的影響下,唐后期及以后出現新的地方監察體制如郎官出使制、轉運使制和巡院系統等推動了兩宋通判制的形成和發展。?杜文玉主張唐宋變革的關鍵時期在五代十國,不斷嘗試以唐五代十國時段探討唐宋問題,提出“宋承五代”說,并運用這種觀點,以唐五代十國時期為時間范圍考察地方監察情況,探討了州縣及藩鎮使府內部的監察面貌和勾檢制的監察作用。?他也對錄事參軍予以關注,建議將這一官職放在唐宋州僚佐體制變遷的大背景下來考察。?楊孟哲討論了唐代錄事參軍問題,指出州府錄事參軍是唐代地方監察體系的核心,但這一職位屬于清要而不得高位,“曾任錄事參軍者的終身仕途并不能達到一個較高位置”。?汪慶紅則從法學視角探討了唐宋錄事參軍法定職能的演變。?另有一些碩博論文對這一領域進行了專題研究,如袁岳系統梳理了唐以前及唐代地方監察體制主要內容,并針對現代社會發展形勢給出許多具體建議,例如提高監察人員素質,完善巡視制度,強化現場監督等?;肖光偉從歷史文獻學研究法出發,把唐代地方監察制度發展歷程分為六個階段詳細論述,認為相關制度的優點即體制完備、持法監察、選任嚴格和震懾地方?;李聞東在扎實論述的基礎上試圖對其進行評價,采用了傳統的進步性和局限性評價模式?;周石磊對唐代地方監察體系的局限性評價更加深入,他認為唐代地方監察官員只設置到道一級,一旦中央放縱了對這些官吏的管理,他們便會爭相轉變成行政官,奪取地方政治權力,給政治穩定帶來巨大的傷害,加速了唐王朝的覆滅?;劉娟以歷史學的研究方法,重點分析地方監察使的變化,指出“分道巡察”方式對后世的深遠影響?,等等。
還有一些學者關注唐代中央對地方的監察問題,如胡寶華對唐代的朝集使做了初步的整理研究。?于賡哲對朝集使和進奏院的區別做了探討,并對一些史料進行了辨析運用。?謝元魯對唐代京官和宦官出使制度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并探討了宦官出使在唐后期對地方監察的破壞。?虞云國、張玲突破朝代分期限制,討論了唐宋時期使職差遣制度下觀察使的職能變化。?宋平從司法實踐的角度,選用新史料敦煌寫本《河西節度觀察使判牒集》,結合唐五代典籍、詔敕、筆記小說、碑刻等材料,討論了節度觀察使司法權的具體內容和判官等僚屬的執行情況。?張達志論述了唐前期十道遣史的監察意義和更廣泛的制度影響。?趙一鳴討論了唐代采訪處置使的置廢問題。?王義康討論了唐代中央監督“蕃州”的方式和制度設計對穩定唐代邊疆地區的實際影響。?可以看出,唐代地方監察制度研究越來越深入,學者們討論具體而有深度的問題,但仍聚焦于官職制度,仍有深入討論的必要。
五、諫官制度研究
唐代諫官和諫諍制度也受到了很多學者的關注,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內容主要分三大部分:一是考察某一兩人或某時間段諫官的活動,研究他們的思想內核和制度運作特征,多涉及文學性的考察;二是考察諫諍制下群臣與皇權的關系和矛盾,研究其中的制度內容和文化影響;三是總體考察諫諍制度的內容和變化,歸納相關的影響與歷史經驗,為當代監察制度的發展提供思考借鑒。如胡寶華考證了唐代諫官補闕、拾遺定員等問題,對諫官制度的結構與功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胡滄澤討論了唐代諫諍制度對皇帝的制約和監督作用;李瑋認為唐代的五諫是“中國古代諫諍制度中五諫的集大成者”,等等。傅紹良則致力于對唐代諫官與文學的系統研究,他從文學角度出發,分析了杜甫在向皇帝諫言時的思想基礎,認為杜甫的憂君思想源于其憂道憂民思想,絕非現在人們理解的“愚忠”,且有傳承自儒道思想的君子內核在,又從文學理論上闡釋諫官活動是在“君權有限”的思想理論基礎之上進行的。并且指導多位學生研究“唐代××與文學”問題,形成了一派風格獨特的研究格局,其中與監察制度相關的研究成果當屬霍志軍對唐代御史與文學的持續研究。馬自力也運用這一研究范式討論唐代諫官與文學的關系。
還有一些結合唐代監察制度討論具體問題的論著,也值得關注。如毛陽光把唐代報災制度和相關監察制度聯系起來,討論了二者的關系和運作形式;張春海討論了御史臺在執行罰俸時擔任的角色及帶來的諸多影響;王保民從法學角度用“盔甲”形容唐代監察制度并總結出對當代社會的啟示;黃永年、岑仲勉、黃炳琛、吳河青和陳可等人對廳壁記的研究;等等。一些學者在做與監察制度關系較密切的研究時,也對唐代監察制度進行了一定的論述,如胡戟等人對20世紀唐史研究的學術史梳理中有一小節內容提到了監察制度的研究狀況;夏炎在研究唐代地方行政體系時也給予了唐代地方監察體系一定的關注與分析;梁瑞仔細研究了流貶官的具體狀況,分析了監察機構起到的作用及流貶官對監察官的特殊態度;李志剛討論了唐代監察運行機制的相對獨立性和內部獨立和多層次多維度的制衡體系;等等。
六、結語
綜上,可以看出唐代監察制度研究在時代變遷和學科演變的影響下,出現了很多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有一批學者對唐代監察制度有比較系統的研究,如徐連達、陳仲安、胡滄澤、胡寶華、杜文玉和楊孟哲等人,且各自有研究重點,這樣有利于推進對某些問題的研究,推動理論和方法的不斷突破。唐代監察制度在研究內容、研究分期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多推進,但總體上還限制在對官制的考察和對制度演變的討論上,在具體論述中又有陷入碎片化研究的傾向,還需要在理論和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從制度史研究的宏觀角度來看,走出傳統政治制度研究范式的窠臼是目前唐代監察制度研究的一個可能的突破點,無論是閻步克、鄧小南、侯旭東、李里峰和吳宗國等人提出的政治制度史研究最新理論,還是多學科綜合研究、新出史料論證等方法,都是具體而可行的嘗試,相信未來隨著學術研究的不斷推進,唐代監察制度研究會更加深入和拓寬。
注釋:
①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國之舊史》,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1—6頁。
②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史學之界說》,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7—11頁。
③ 謝保成:《增訂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69—89頁。
④ 羅志田:《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民國新史學的一個詭論現象》,《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⑤ 高一涵:《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第26—38頁。
⑥ 徐式圭:《中國監察史略》,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56—71頁。
⑦ [日]八重津洋平:《唐代御史制度について》,《法と政治》1970年第3期;胡寶華:《唐代“進狀”、“關白”考》,《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1期;霍志軍:《唐代的“進狀”、“關白”與唐代彈劾規范——兼與胡寶華先生商榷》,《天水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胡寶華:《唐代監察制度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70—95頁;林曉煒:《唐代御史“進狀”“關白”制度之研究》,《閩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⑧ 白鋼:《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歷史研究》1996年第6期;侯旭東:《“制度”如何成為了“制度史”》,《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1期;孫正軍:《何為制度——中國政治制度研究的三種理路》,《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4期。
⑨ 閻步克:《一般與個別:論中外歷史的會通》,《文史哲》2015年第1期。
⑩ 鄧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為例的點滴思考》,《浙江學刊》2003年第3期;鄧小南:《再談走向“活”的制度史》,《史學月刊》2022年第1期。
? 侯旭東:《什么是日常統治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225頁。
? 閻步克:《一般與個別:論中外歷史的會通》,《文史哲》2015年第1期;侯旭東:《什么是日常統治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225頁;吳宗國:《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劉后濱:《漢唐政治制度史中政務運行機制研究述評》,《史學月刊》2012年第8期。
? 徐連達、馬長林:《唐代監察制度述論》,《歷史研究》1981年第5期。
? 陳仲安、王素:《漢唐職官制度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37頁。
? 陳仲安:《漢唐間中央行政監察權力的分合》,載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史料》第11輯,第1—6頁。
? 胡滄澤:《漢唐監察制度的變革》,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9輯,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65頁。
? 彭勃、龔飛蒼:《中國監察制度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88—129頁;胡滄澤:《中國監察制度史綱》,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頁;賈玉英:《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發展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52頁;李孔懷:《中國古代行政制度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160頁;邱永明:《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294頁;胡滄澤:《中國監察史論》,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6頁;曾哲:《中國監察制度史》,光明日報出版社2019年版,第87—131頁;張晉藩:《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史》,中國方正出版社2019年版,第130—179頁。
? 胡滄澤:《唐代御史臺對官吏的彈劾》,《福建學刊》1989年第3期。
? 胡滄澤:《唐代御史臺對財政經濟工作的監督》,《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4期。
? 吳曉豐:《唐代的奏彈及其運作》,《中華文史論叢》2020年第4期。
? 萬寶璋:《試論唐代御史在財經上的監督作用——兼談唐代御史監察中的幾個問題》,《北京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
? 王素:《唐代的御史臺獄》,載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史料》第11輯,第138—144頁。
? 杜文玉:《五代御史臺職能的發展與變化》,《文史哲》2005年第1期。
? 胡寶華:《唐代御史地位演變考》,《南開學報》2005年第4期。
? 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9—92頁,第298—364頁。
? 王孫盈政、盧向前:《論唐代后期御史臺的政務官化》,《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 參見張雨:《御史臺、奏彈式與唐前期中央司法政務運行》,參見張雨主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13輯,第157頁。
? 胡滄澤:《唐代御史制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283頁。
? 黎蕓:《〈唐會要·御史臺〉整理與研究》,武漢大學2019年碩士學位論文。
? 何汝泉:《唐代前期的地方監察制度》,《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2期。
? 寧欣:《唐朝巡院及其在唐后期監察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北京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6期。
? 齊濤:《巡院與唐宋地方政體的轉化》,《文史哲》1991年第5期。
? 賈玉英:《唐宋地方監察體制變革初探》,《史學月刊》2004年第11期。
? 杜文玉:《唐宋時期社會階層內部結構的變化》,《江漢論壇》2006年第3期;杜文玉:《“婚姻不問閥閱”應始自五代十國時期:對學術界“宋代說”的糾正》,《南國學術》2015年第4期;杜文玉:《宋承唐制還是五代之制》,《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杜文玉:《唐五代州縣內部監察機制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杜文玉:《唐代地方州縣勾檢制度研究》,《唐史論叢》2013年第1期;杜文玉:《論唐五代藩鎮使府內部的監察體制》,《文史哲》2014年第5期;
? 賈玉英:《唐宋時期州僚佐體制變遷初探》,《中州學刊》2012年第6期。
? 楊孟哲:《唐代地方監察體系的核心:州府錄事參軍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16年第2期;楊孟哲:《唐代錄事參軍的籍貫分布及遷轉路徑研究》,《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楊孟哲:《位卑而權重:錄事參軍設置考》,《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 汪慶紅:《唐宋錄事參軍法定職能演變探究》,《寧波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 袁岳:《唐代地方監察制度探析》,云南師范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
? 肖光偉:《唐代地方監察制度的演變及其特點》,上海師范大學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
? 李聞東:《唐代地方監察制度研究》,貴州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
? 周石磊:《唐代地方監察制度研究》,江蘇大學2017年碩士學位論文。
? 劉娟:《唐代地方監察使的產生及流變研究》,天津師范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
? 胡寶華:《唐代朝集制度初探》,《河北學刊》1986年第3期。
? 于賡哲:《從朝集使到進奏院》,《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
? 謝元魯:《唐代出使監察制度與中央決策的關系初探》,《社會科學家》1988年第3期。
? 虞云國、張玲:《唐宋時期“觀察使”職權的演變》,姜錫東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7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0—69頁。
? 宋平:《唐中后期節度觀察使的司法權及運作問題研究——以敦煌寫本〈河西節度觀察使判牒集〉為起點的考察》,《敦煌研究》2018年第5期。
? 張達志:《唐十道遣使芻議——貞觀至天授》,參見《紀念岑仲勉先生誕辰13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委會編:《紀念岑仲勉先生誕辰13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29頁。
? 趙一鳴:《“坐而為使”:唐代地方監察制度變遷中的采訪處置使研究》,《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 王義康:《唐代“蕃州”監察制度試探》,《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