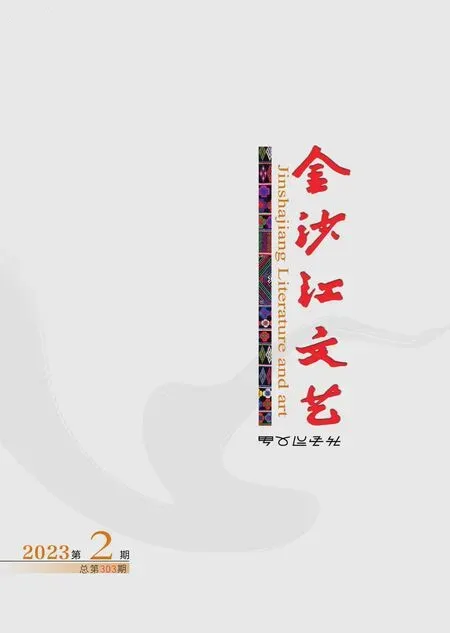大院里的歲月
◎李靜(白族)
下午五點半,太陽的光開始變得柔和,眼睛望向它的時候不再需要伸出手擋在額前。頭頂的天空是四方形的,有幾絲白云輕飄飄地浮在那里。對面張嬸嬸家屋頂的瓦片縫隙間生了許多草,他們從大院里搬出去兩三年了,六月的雨水給了雜草放肆的理由。一只不知從哪兒飛來的麻雀落在院子里,自如地啄食完全沒把院子里的兩個人放在眼里。小女孩完全被麻雀迷住了,起初她還乖乖地坐在板凳上只是用眼睛望著它,到后來頭也跟著轉來轉去,完全不顧正在給她編辮子的孃孃。
“別動,好好坐著,快編完了。”
她趕緊把頭轉正,閉上眼睛不去理那麻雀,配合著孃孃的工作。
孃孃大我六歲,當時正在讀初中。孃孃擁有一雙巧手,一有空我總會纏著她給我梳好看的辮子。用梳子將頭發輕輕地梳順,扎一束馬尾,再將那馬尾大致均勻地分成十二份,分別扎上皮筋。接著,耐心地編十二個小辮子,在辮子臨近收尾處依次扎上不同顏色的皮筋。從頭到尾大概花了十分鐘。我側過頭,看到了鏡子里夢寐以求的麻花辮,感到無比的滿足。明早我要穿好看的衣裳配上這麻花辮,昂著頭去升國旗。
大院和我們家只離著三四分鐘的腳程,從我出生起,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聽爸爸說,大院建成已經八九十年了。大院原本是白族民居里典型的四合五天井設計,青磚白瓦,很有徽派建筑的韻味,但一場意外,西邊的房子在火中燒為灰燼,只留下北南東三邊的廂房。
在我小時候,大院總是熱熱鬧鬧的,七奶奶一家、大爺爺一家,還有張嬸嬸一家,給大院平添了生氣。他們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瑣碎里歡笑、拌嘴;在蛙聲一片的農忙時節插秧,頂著夜色抹黑回家;在雨水連綿的七月里打牌閑聊。黃昏時分各家煙囪里升起的炊煙,帶有淡淡的柴火的香味;大風狂掃之后偶爾從屋頂掉落的瓦片,是碎開的青黛色。院子角落里青磚上長出的苔蘚,頑固地扎根。當然,大院給我的記憶不僅僅是這些,它給我的記憶更具體更細致,與實實際際的人聯系在一起。
我還沒上學之前,爸媽白天很忙,壓根沒空照顧家里。于是把我寄養到大院里,請大爺爺照看我一兩天,又讓七奶奶照看我幾天。大爺爺家的彩色電視買的很早,他和大奶奶都很愛看電視劇。大奶奶是漢族,和我們說漢話,剛開始不習慣到后來也愛跟著她玩。大奶奶的耳朵很背,眼睛也有點不好使,她總是坐在一張稍微有些高的藤椅上,而大爺爺坐在緊鄰著她的矮矮的草墩上。每逢看電視的時候,大爺爺總要時不時地轉頭側過身大聲告訴大奶奶電視里發生了什么,妙善被誰誣陷為災星,濟公又把哪個狗腿子的腳鑲滿了銅錢。于是,我斷斷續續地跟著他們看完了或者說聽完了濟公,但是我一點兒也搞不懂為什么濟公在新婚當天拋棄新娘,放著好好的生活不過要去當一個窮苦和尚,而 《觀音傳》 里常穿一身黑的張牙舞爪的女妖怪則成了我的童年噩夢之一。大爺爺家的樓梯很陡,但我愛跟著他上二樓,從窗戶里俯瞰院子,要是看到院子里有人,我就鉚足力氣大喊一聲想嚇唬住他。下午六點多鐘,爸媽來接我回家吃飯,日復一日。
七奶奶家每年都會種很多玉米,等把玉米收回家晾干了,就得把它剝了碾成玉米面。我小時候酷愛剝玉米,說不清為什么就是喜歡剝玉米的感覺。每年到七奶奶家剝玉米的那段時間,我往大院里跑得尤其勤快。下午放學寫完作業、星期六星期天,只要一得空就往大院跑。一年級剛接觸算術的時候,總覺得有些難算不過來,院里的叔叔讓我帶著玉米粒去學校,說是遇到難算的就用玉米粒數數。臨放學最后幾分鐘,老師提問了我一道兩位數的加法,我從文具盒里拿出玉米粒一顆顆演算。鈴聲一響同學們急著回家,同桌的手肘一碰玉米掉地下了,我蹲下去撿,透過桌腳凳腳,我看到了同學們魚貫而出的雜亂的腳,他們趕著回家而我蹲在地上,這樣的我不屬于他們。回家和爸媽撒氣,再也不帶玉米了,我一定要把數學學好。
我讀三年級那會,妹妹剛上幼兒園,下午放學回家,家里的門鎖著,我們沒有帶鑰匙,大門底下的空隙很窄,鉆進去也是行不通的了。七奶奶從家門口路過,把我們倆領到大院里,去灶房給我們燙了兩碗飯,往里加了白糖。我還記得,我和妹妹一人坐了一個草墩,把碗放在一長條板凳上,在堂屋旁用勺舀著有滋有味地吃著。吃完飯,我們拿出課本和練習冊,坐正身子認認真真寫作業。
站在七奶奶家二樓樓梯口,剛好可以看見我家大門,門前的一切一覽無遺。嬢嬢讀初中,放學時間比我們小學晚兩個小時,有時候吃完飯之后她會上樓梯口看看,如果我和妹妹恰好在門口玩,就喊我們過去大院里找她。但更多時候,是我領著妹妹早早地守在院子里等她,我們留心聽到的任何聲音,自行車的鈴鐺聲一在大院門外響起,我們就知道這是嬢嬢放學回來了,妹妹總要搶著跑朝前去迎接她。在很小的時候,我們就切身明白了等待和翹首以盼。
我們看著她把車推進大門再用手抓緊車身把它抬過二進門的石階,我們跟著她走進灶房守著她吃飯。她涮完碗把我們領進她的房間,拿給我們圖畫書,然后拉開書包上的扣子拿出我看不懂的書開始一篇一篇寫字。有時候,嬢嬢會給我看全是字的書,遇到不懂的字我就停下來問她。慢慢地我在她那里讀完了安徒生童話全集,讀她的語文課本,實在沒書了就去看叔叔的高中語文課本,接觸了朱自清、老舍。那會我最愛童話故事,其他只是我識字的工具,字里行間的意思暈叨叨的,我一點兒也不能明白。
逢年過節,是大院里最熱鬧的時候。兩張四方桌拼在一起,各家拿出來幾個板凳,老人坐主位,其他人挨著落座。平日里舍不得吃的菜在這時候都能吃得著,這家端出來蘿卜燉排骨,那家整一盤生皮。炸乳扇、油炸花生米、青菜湯、干煸洋芋絲……,空蕩蕩的飯桌在短短幾分鐘內被填滿。大人們往碗里倒白酒,觥籌交錯,小孩子喝百事可樂或者青梅爽,大一點的女娃娃也不準喝酒,這是約定俗成的規矩。我們家有時候會參與到大院的大聚餐里,很多時候會把大院里的人請到家里吃飯。我和妹妹吃一小會就吃好了,我們退到飯桌外,坐在堂屋門前的石階上,看著他們喝酒聊天。他們笑著,大聲嚷著,過一會兒臉色變紅。天黑下來不要緊,也不往院里格外拉燈,就讓灶房里透出的昏黃燈光配上月色,為他們照明。
到后來,大爺爺家添了個大胖小子,又過了幾年,添了個孫女,大院里越發熱鬧了。我和妹妹開始接過爺爺奶奶叔叔嬢嬢們手中的接力棒,成為照看小孩的主力軍。這倆弟弟妹妹特別愛跟著我和妹妹玩,一口一個“大姐姐” “二姐姐”。嬸嬸會在白天把他們倆寄養到我們家里來,于是我們帶著他們看電視、玩躲貓貓,等小妹妹再長大一點,她就能參加我們的跳皮筋活動。
在流動的光陰里,大院里的人來來去去,有人離開也有新生命降臨。大奶奶臨終前我和家人去病榻前看望了她,眼睛混濁;大爺爺生病了走路顫顫巍巍說話慢吞吞的,我和妹妹去給他送了晚飯,他客氣地道謝看著我們走出大門,再過了兩個月他溘然長逝。我眼看著嬢嬢去讀高中讀大學到后來成家,成為小時候我最想成為的大人;小妹妹一天天長大,到后來話變得越來越少轉眼竟然已經讀初三了。在單向的時間坐標軸上,每個人都在往前,帶著從前的記憶往前。
現在每逢春節,我們仍然去大院里吃飯,在外求學工作的人通通回歸到大院,坐在一塊談笑風生。年夜飯的原則是盡可能地拋開電器選用柴火燒菜,媽媽去生火煮魚,七奶奶切生皮,叔叔燒水,我和妹妹幫著洗菜洗碗,七爺爺和爸爸在院子的一角下象棋,各司其職。炊煙升起來的時候,仿佛回到了小時候,回到了有那些舊面孔的小時候。毫無疑問,在流動的光陰里,大院成了一個聯結,我們的出走是為了更好地回歸,以更好的身份出現在院子里,出現在和親戚朋友們相聚的飯桌上。我們逼迫自個兒努力向上,因為只有出落得有本事,才能更坦蕩地懷念那些消逝的身影。
像是系了一根線,高飛的風箏樂意受這繩線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