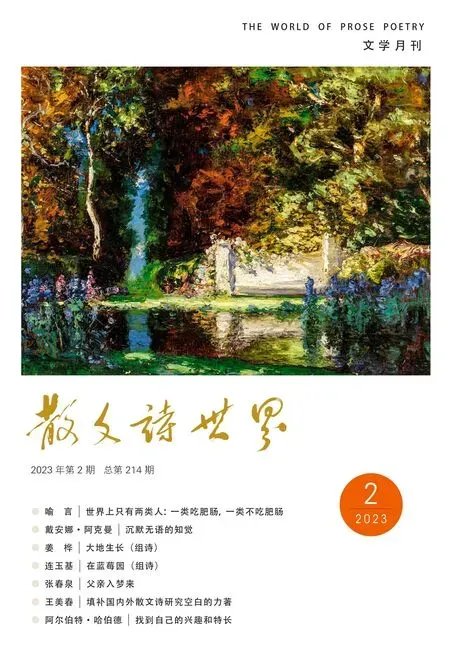白居易是否背自己年輕時寫下的詩?
2023-04-15 08:58:14王智勇廣東
散文詩世界 2023年2期
關(guān)鍵詞:小說
王智勇(廣東)
白居易會不會背自己的詩?
16 歲時他為了求取功名,
寫了首《賦得古原草送別》,
送給朝中大臣求過目。
想不到一千多年來一直在折磨后人。
就像某一日早晨,他喝了一碗米粥,
非要問無數(shù)后代碗里有幾粒米,
每一粒米代表什么意思?
白居易很長壽,一輩子喝了很多粥,
寫了幾千首詩。如果每一首都背下來,
純粹吃飽了撐的。
與專門折磨后代的詩人不同,
曹雪芹是專門給人留飯碗的。
看小說、評小說、分析小說就能成專家、教授。
至于分析得對不對?無論考證。
因為作者已死。
74 歲的老人至死好色,
71 卷《白氏長慶集》我第一次聽說。
一個貴族日漸沒落,
批刪十年,寫下一千字定有一萬字要說。
每一個字《紅樓夢》小孩子確實(shí)看了,
而且不止一遍,而是好幾遍。
然而這并不值得家長夸耀。
究竟理解了多少?吸收了多少?
別人的東西何時變成我的?
如果一個人非常有創(chuàng)造力,
他不會迷戀于往日的腳窩,
一遍遍重復(fù)很多年前的創(chuàng)作。
作為敲門磚的送別詩,
所體現(xiàn)的成熟,顯示一開始就成熟了,
余下的只是完善。
比如英國詩人奧登。
中外詩歌史上很多名詩都作于作者十幾二十
歲左右。
25 歲歌德寫下《少年維特之煩惱》,
19 歲王蒙寫下《青春萬歲》。
語感,還是語感!
幾乎與生俱來,
就像踢球的腳感。
那種流暢,細(xì)膩的感覺,不脫不懈的韌性,
揮灑自如的放松,旁若無人的沉醉,
自我愉悅的同時予人美感。
閱讀不是數(shù)量的疊加,
而是語言感覺敏銳度的喚醒,
深度的心靈參與,身居其境的置換,
當(dāng)然催眠也算,至少它讓人放松。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7:06
文苑(2020年11期)2020-11-19 11:45:11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作品(2017年4期)2017-05-17 01:14:32
中學(xué)語文(2015年18期)2015-03-01 03:51:29
西南學(xué)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小說月刊(2014年8期)2014-04-19 02: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