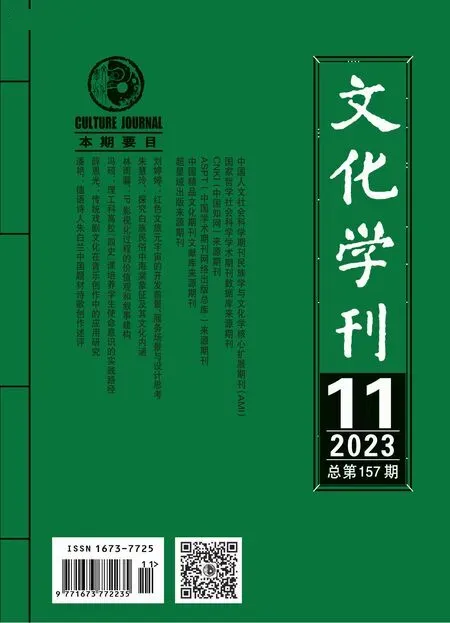對阿諾德·湯因比史學觀的認識
張嘉瑤
被譽為“近世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的阿諾德·湯因比曾撰寫了大量的歷史著作,包括《歷史研究》《人類與大地母親》以及《文明經受著考驗》等。湯因比窮其一生思慮著人類文明的歸路,尤其是提出一整套史學理論的《歷史研究》一書讓湯因比名滿天下,也同時將他的史學觀推向人類社會發展的研究視野中。
一、阿諾德·湯因比史學觀的形成與發展
阿諾德·湯因比是“文化形態史學觀”的代表人物,他的的史學理論集中反映在他那長達12卷的《歷史研究》書中。他在關注人類文明的同時也將“文明”作為一種“具有生長盛衰與發展階段的有機體”[1]。他還在此基礎上將當今世界劃分為五個文明體,試圖比較不同文明體的興衰歷史來追尋人類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史觀”是一個綜合體,在《歷史研究》這本書當中能夠看出,湯因比所描述的探索歷史的基本單位都是大于國家的文明,不僅有羅馬以及古希臘等學者因素,又有近現代美國以及俄國等國家學者的因素。
湯因比從小接觸的教育是極為嚴格的西方古典教育,幼年時期就學習雙語,在大學時期就接觸了很多拉丁以及希臘的古典著作。西方古典教育為湯因比奠定了歷史觀的基礎。湯因比史學觀的最初形成是受到古典史家對“文化”理念的劃分的啟迪,其中中古時期阿拉伯著名的史家伊本·卡爾敦的文化理念對湯因比影響很深。卡爾敦有“阿拉伯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之稱[2],他主張將文化事置于歷史學研究對象中,這種文化和文明的現象既包括物質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卡爾敦的觀點對湯因比文化形態史學觀的形成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近代發展以來人們逐漸認識到社會文明對于國家和社會的影響作用,所以,文明或者文化變成了當前歷史的重點研究對象。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隨著思想啟蒙以及文藝復興時代的推進,福爾泰將文化融入到了歷史學研究當中,提出了“文化史觀”[3]。伏爾泰否定了西方政治軍事史的編纂傳統,將文化和文明引入史學領域,并對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進行歷史描述。伏爾泰描述的這些地區就是湯因比文明體系的雛形。湯因比從他的研究理論當中吸取了總體史觀等概念,他提出歷史的探究單位并不是人類整體,也不是國家民族,應當是我們一個社會當中的人們的某一群體[4]。在《歷史研究》中,湯因比就將中華文明作為一種極為關鍵的文明形態探究,并極力追捧中華文明,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福爾泰文化史觀的影響。他提出,商人們和歐洲王公得知了東方的存在,追求的也僅是限于財富,但哲學家在東方所探究的是全新的物質以及精神事業[5]。湯因比不會中文,但是他卻被中華文明的魅力所吸引,想要來到中國一探究竟,與此同時,他歷史探究的視角也推動其在探究流程中更多的接觸了中國文明,對中國的了解一般是來源于相關歷史參考文獻,同時他幼年階段也受到身邊人熏陶的作用,聽到了很多關于東方的故事,這對他之后對于東方文明的向往有著一定的影響作用,他的視角認為中國不管是在治理還是道德層面都是全球最好的[6]。
如果說古典史家的論述是湯因比文化史學觀形成的啟蒙老師,啟蒙時期的近代史家的“文化”激情是湯因比文化形態史學觀的養分,那么現代歷史學家的“文化理論”則是他史學觀最終形成的推動力。步入近代社會之后,歷史學家在已有的文獻研究基礎之上建構了很多文化理論,用文明或者文化來探索歷史的發展脈絡不將目光局限于民族或者國家,而是用更加系統的史觀來探索人類歷史發展。 其中顯得尤為重要的是德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論”。
斯賓格(1880—1936年)在其著作《西方的沒落》中提出“文明形態史觀”并認為西方文明必將逐漸走向沒落,摒棄了西方中心論。湯因比的史學觀與斯賓格勒一脈相承,但是不同的是,在西方文明走向問題上,湯因比強調人類自身的能力,他認為文明走向沒落是文明自身發展的規律。也由此將城市文明引入到研究中。“湯因比在參考斯賓格勒的背景之上研究了西方文明是否沒落,同時也對城市問題加以探索[7]。”
二、阿諾德·湯因比文化形態史學觀
(一)城市文明發展的“四階段論”
湯因比在探究分析文化形態時,注重從多個方面進行研究,不僅表現在將“文明”作為單位進行研究,“城市” 文明作為一種文化形態也作為湯因比的研究對象,并成為湯因比晚年較多思考的一種文化形態。湯因比的城市文明觀并沒有離開他的文化形態視角,相比于以文明為單位進行的歷史研究,城市觀是以城市為單位的歷史研究的形態劃分,并不是大塊大塊的空間實體。湯因比在他的史學研究體系中提出了“文明循環”這樣的概念,他認為人類社會文明是循環發展的,天才、富有天賦等少數人的創造促使了歷史的發展,只有他們的創造才能決定歷史是向前發展的[8]。但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善于解決社會問題,有可能那些“富有天賦的少數人”就會成為“無產者”奮起反抗統治,于是一種文明就會發生分裂,甚至被摧毀。動亂中,舊文明在被破壞的同時,會有新的文明產生,開始文明發展的新周期,“文明循環”就會由此演進下去。
湯因比把“文明”劃分為四個階段,包括混亂階段、大一統帝國階段、間歇階段、蠻族大遷徙階段。以西方古史作為例子,認為古羅馬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意義。他將古羅馬的政治史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古羅馬在經歷了百年動蕩后,從一個區區小城成為了擁有廣袤土地的霸國,建立起統一帝國,為羅馬國未來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第二階段:公元161—180年,“黃金時代”告終后,出現了一個名為“間歇時期”的階段;第三階段:基督教在羅馬帝國興起并廣泛傳播,形成教會;第四階段:日耳曼等民族涌入羅馬帝國,導致了“蠻族”的大遷徙。這便是湯因比關于文明發展的“四階段論”,他認為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需經歷這四個階段。而后他也曾用“四階段論”理論解釋過中國歷史,春秋戰國是“混亂階段”,群雄竟起,列國紛爭;秦漢時期是大一統帝國階段;魏晉是間歇階段;五代十國是蠻族大遷徙階段。這是他的一家之言,不盡符合中國實際,但用這個觀點解釋某些西方歷史也并非全無道理。
(二)城市文明的“挑戰”與“應戰”
“挑戰”與“應戰”對湯因比文明的研究具有較大意義,同時,其也是湯因比文明形態理論具體闡述文明發展過程的一個重要條件。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回答了成功的應戰和挑戰的結果,歷史的發展過程表現在挑戰和應戰的相互作用之中。湯因比承襲了西方實用主義的理論,認為有用才是真理。他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就是“借古明智”,用以往的經驗來解決當代社會中存在的問題。他表示,一種能夠誕生出文明的環境并非是恬靜安逸的,而是必然存在著種種困難,這種充滿困難的環境對存活于其中的人形成了某種壓力,人們為應對這種壓力并在這種環境中存活,展現出較為強大的努力意志,因此,在應對與挑戰壓力的過程中一種文明由此誕生,而文明恰恰于應戰和挑戰中產生并發展[9]。湯因比把當前社會面臨的重大事件或重大危機稱為“挑戰”(challenge),而能夠解決此類問題,化解危機的人恰恰是先前提到的天才和富有天賦等少數人,湯因比把他們挽救危機的舉動稱為“應戰”(response)。如果這些人無法“應戰”成功,不能挽救危機,這個國家的文明就會崩潰甚至毀滅,如果“應戰”成功,文明就會存續下去。
經過對文明內在機制進行深入分析,面對“挑戰”,能否“應戰”成功,湯因比認為是最終導致歷史文明興衰的根本性原因。這個實用主義色彩濃厚的理論來自于《浮士德》中一個神話的啟示,開篇《天堂序曲》講的是一個關于上帝與魔鬼之間抗衡的故事,他由此受到啟發,感悟文明起源的動力和契機,創造出“挑戰—應戰”理論從而能從理論上闡述人類文明的產生、發展歷史。湯比因表示,大多數社會成員由于長期處于悄無聲息停滯不前的狀態,而不具備應對挑戰的能力,應當是少部分具有創造性的人。“挑戰—應對”理論的提出對湯因比來說具有深遠意義,他想提供一劑良藥來挽救沒落中的西方文明。湯因害怕共產主義的精神力量打敗基督教文明,因此,他在惶惶不可終日,憂心忡忡的情況下創造了此理論。湯比因所提出的文明興衰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是對“文化形態史觀”的發展與繼承。
(三)文化是城市文明之根
湯因比在其研究體系中也將城市作為載體。通過對文明形態史觀的分析與研究,湯比因觀察闡述了城市由產生至解體的全部過程,并且嘗試分析研究城市發展變化的具體規律。湯因比認為,城市的起源在于蘇美爾人在開發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下游盆地的過程中,創造出“地區文明”的人類社會的形態[10]。人類在經歷農業生產、階級分化、宗教信仰的過程中,文明程度愈見加深。其中,宗教和文化成為了城市生生不息的源泉。宗教信仰促進了蘇美爾城邦的誕生,蘇美爾人采取宗教中的祭祀活動,利用神的力量來維持蘇美爾城邦全體民眾一致的行動,宗教成為了集聚人類凝聚力方式的智慧。
湯因比的城市文明觀是從城市與文化的角度闡述的,他認為文化決定著城市的走向,城市的發展必須依靠文化對人心靈的影響來實現,尤其宗教是城市文化中的核心力量。而天才和有著獨特稟賦的人將是城市文化中的精英,他們將成為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動力和支柱。這些文化精英運用宗教的力量掌控城市文化,保持城市民眾的凝聚力和統一方向,在不致使城市走向衰落的基本保障下,促使城市的發展欣欣向榮。
當然,湯因比城市文明觀也存在著局限性,如湯因比在研究城市多具有的功能時,僅僅看到了城市的“精神化”,忽視了其“物質化”。而無論是精神還是物質都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對城市的發展來說,二者不可偏廢。
三、阿諾德·湯因比史學觀的局限
從城市文明發展的“四階段論”到“挑戰”與“應戰”理論形成,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史學觀對人類文明起源、發展、衰落至解體給予了宏觀的把握,旨在追溯城市文明興衰的客觀規律,然而,湯因比的史學觀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湯因比對于“文明”這一概念并未闡釋出較為清晰的定義,并且在劃分文明的過程中也存在較大的主觀性,在很多方面難以找到與現實相契合的地方。他指出促進社會歷史發展重點依靠少部分人,同樣這部分人也掌握著歷史的走向與發展,并未正確認識廣大群眾的貢獻。湯因比的唯心主義英雄史觀與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相反,他沒有看到在社會發展中所有文明均需要依靠廣大群眾來創造,如果沒有廣大群眾作為基礎,人類文明難以獲得發展。
湯因比表示“人文領域中非創造性的、靜態性的文化,往往會推動產生技術性較高的工具或手段;而文化所具有的較高創造性可以把潛能轉換為精準細密的形式;從而使得技術發展成品逐漸失去本身的物質形態,重量、體積也在逐漸降低,機理與設計不斷獲得簡化”[11]。從上述中可以看出湯因比將城市文明發展的主要內容和形式歸納為“靈妙化”。過分注重這一方面使湯因比的史學觀呈現出“非物質化”的特點,對社會過程的物質化比較忽略。然而事實是,湯因比所認為的“靈妙”的東西,包括文化、信仰、價值觀念等都需要物質形態的承載。比如宗教信仰的傳播需要依賴教堂堅固的石料得以維持。但是不管怎樣,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史學觀將留待后世繼續探索。
四、結語
作為 20世紀西方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湯因比畢生致力于史學研究,他從“文明”的新角度分析了世界歷史及人類文明發展的整個過程。他在其著作《歷史研究》中創立了博大精深的史學體系,對西方城市文明的發展過程展開了詳細的研究。其中城市發展的四階段論以及“挑戰”和“應戰”的理論成為西方史學體系中的閃光點,為當代和未來的史學家提供了參考。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阿諾德·湯因比對文明發展“靈妙化”的非物質方面過于重視,他將宗教的解救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