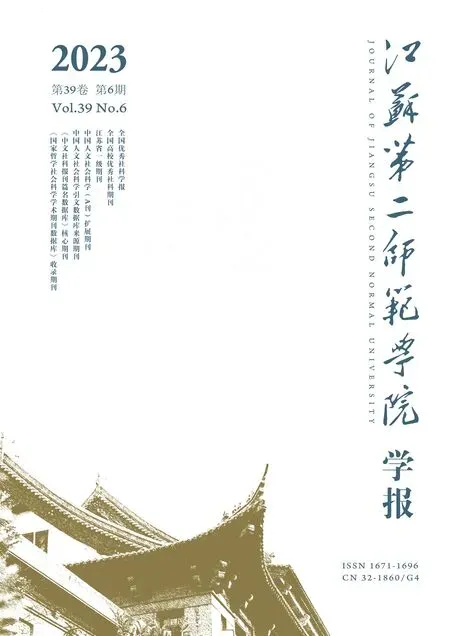教育數字化背景下我國教師在線教學態度量表修訂與實證研究
宋 雅 姜欣悅 徐新萍
(1. 江蘇第二師范學院教務處, 江蘇南京 211200;2. 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 江蘇南京 210093;3. 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南京衛生分院, 江蘇南京 210000;4. 江蘇第二師范學院數學科學學院, 江蘇南京 211200)
在線教學(online education)又稱電子教學(e-learning)、在線學習(online learning)、移動學習(mobile learning)、網絡學習(internet learning)等。在線教學指的是通過電子信息設備支持教學,教師與學生通過網絡進行互動的教學過程。早在2016年,教育部印發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規劃》中,已把“提升教師信息化能力、學生信息素養、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的深度融合”列入教育信息化的三大發展目標之一。2018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明確要求,教師應主動適應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變革,積極有效開展教育教學。2022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實施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一些研究認為,傳統的教學方式已經無法滿足信息化時代學生的需求,但不少教師仍習慣傳統課堂教學,從區域和學科的視角出發對在線教學持存疑態度,真正有效利用在線課程教學資源開展教育教學并不普遍[1-3]。然而,隨著在線教學理念的內化、相關技術的成熟、教師專業素養結構的重構[4],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的深度融合已逐步成為各類學校進行課堂教學改革的突破點和著力點。
“態度”是一個人基于認知、情感和行為經驗,對事物的一種辨別[5]。教師對在線教學的態度可能影響其是否愿意且勝任在線教學工作。同時,有各種各樣的因素影響教師對在線教學的態度,如知識、學習欲望、在線教學經歷、其感知到的在線教學易用性、信念和外部環境等[6-7]。當前研究中,存在多種教師在線教學態度測評量表,但多為歐美國家開發,如Kisanga和Ireson開發并驗證了《在線教學相關態度測驗量表》評估教師的在線學習態度[8];Teo基于導師質量、感知有用性和便利條件3個因素構建了《E-learning接受度量表》[9]等。鑒于歐美國家信息化水平較高,相關量表未必適宜中國本土教師使用,印度Punia團隊曾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開發了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教師在線教學態度量表,由于中國與印度同為發展中國家,信息化水平較為類似,國情也存在相似之處,因此,有理由假設這套量表的中文修訂版同樣適用于中國教師群體。
本文旨在通過對Punia團隊編制的《教師在線教學態度量表》進行翻譯和修訂,形成一套適宜本土樣本的測評工具。并通過對施測樣本的分析,考察分析不同教師群體對在線教學的態度差異及影響因素。
一、研究設計
1.研究對象
采用方便取樣,選取江蘇省不同類型、不同區域的學校教師發放電子問卷266份,通過測謊題剔除無效數據后,獲得有效問卷254份,有效率為95.49%。樣本年齡范圍為22~57歲,平均年齡為37.24±8.07歲。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n=254)
2.研究工具
(1)教師在線教學態度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Attitude Scale Towards 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ASOTL-CV)
對Punia團隊編制的《教師在線教學態度量表》進行翻譯和修訂,原量表包含30個條目4個因子:欣賞在線教學10個條目,對在線教育的響應性7個條目,對在線教學操作的掌握程度8個條目,技術革新知識5個條目[10]。該量表由Punia團隊在印度新冠肺炎疫情隔離期間發放,在687名高校教師樣本中施測。量表由教師自評,采取Likert5點評分,其中10個條目為反向計分題。總分越高,表示教師對在線教學態度越積極。英文版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88,分半信度為0.82,4個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布為0.77、0.79、0.78和0.75。
(2)人口學變量問卷。
主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職稱、子女情況、教齡、學校類型、學校所在區域等內容。對于教師原生家庭背景的考察參考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理論,通過家庭經濟收入、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職業類型三方面考察教師原生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根據周菲、余秀蘭等人的研究[11],每個條目均采用Likert7點評分,得分越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高。
(3)其他影響教師在線教學態度的因素問卷。
通過設置“在你任教的學科中,涉及操作練習內容”“當線上教學遇到阻礙的時候,能很便捷地獲得信息中心或其他部門的技術支持”“單位對教師從事在線教學有一定程度的政策支持”“周圍的同事都很愿意使用在線教學”幾個條目,考察可能影響教師在線教學態度的因素,幾個條目均采用Likert5點評分,得分越高,表示對條目陳述越認可。
3.研究方法
在獲得量表原作者Punia授權后,對初稿進行逐條修訂,確保中英文內涵一致的前提下對文化差異的部分進行文化調適,并增加1題測謊題。經課題組反復討論后,最終形成定稿。此后,將定稿問卷錄入問卷星,針對目標樣本發放問卷進行預測驗,預測驗數據初步檢驗后,進一步補充樣本,獲取最終數據。采用SPSS 20.0軟件進行正態性檢驗、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均值檢驗、卡方檢驗、相關分析等。
二、《教師在線教學態度量表》的中文版修訂
1.條目分析
計算被試的量表得分并從高到低排列,得分排名前27%為高分組,排名后27%為低分組。對高、低分組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條目15、20、22的決斷值不顯著(p>0.05),條目3的決斷值在p<0.05水平上臨界顯著,其余條目決斷值均顯著(p<0.001),表明相關條目具有較高的鑒別能力。
此后,將每個條目與量表總分進行Pearson相關,條目3與總分相關不顯著,其余條目與總分相關均顯著。除條目15在p<0.05水平顯著,其余條目均在p<0.01水平顯著。據此,剔除3、15、20、22這4個條目,保留剩余26個條目進行分析。觀察題項,此4題均為反向計分題,可能對被試答題造成了認知困擾,導致指標不佳。
2.信度分析
對保留26個條目的量表總分進行正態性檢驗,可知樣本數據符合高斯分布,正態性良好。使用SPSS 20.0軟件對ASOTL-CV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Cronbach’s α系數為0.91。此后,進行分半信度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ASOTL-CV的分半信度檢驗(n=254)
在小學教師、中學教師、高校教師3個樣本中分別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樣本中ASOTL-CV的信度檢驗(n=254)
3.探索性因子分析
對數據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所得KMO值為0.897,Bartlett球形檢驗χ2=3428.34,p<0.001,表明該量表條目適合探索性因子分析。不限定因子個數的情況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以最大方差法進行旋轉。結果顯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5個。
由于主成分分析中按特征根大于1進行分析,對因子數目的確定不夠精確,可能出現因子數過多的情況,因此使用SPSS 20.0軟件插件進行平行分析,幫助確定因子個數。平行分析顯示,根據PA的特征值分位數值,建議提取4個因子。前4個因子的特征根分別為9.00、2.80、2.00和1.51,分別解釋了總方差的34.6%、10.8%、7.5%和5.8%,總方差解釋率為58.7%。所有條目的因子載荷均在0.4以上,范圍在0.436~0.813之間,如表4所示。

表4 因子載荷分析
因子1共有8個題項,因子2共有7個題項,因子3共有6個題項,因子4共有5個題項。條目的因子分布與原作者在印度高校樣本中的數據有所不同。根據中文樣本中的數據,考察每個因子包含的題項后為因子命名,每個因子與總分的相關系數均在p<0.01水平上顯著,Cronbach’s α系數范圍在0.82~0.88之間,如表5所示。

表5 各因子的信度分析
具體來說,因子1的8個條目表現了教師對在線教學效果積極樂觀的預判,是教師對在線教學持欣賞、樂觀態度的體現,將這些條目命名為“對在線教學的認可”;因子2的7個條目體現的是教師認為信息化能力是其應該具備的專業素養,或作為教師希望且愿意在此方向努力,將這些條目命名為“提升自身信息素養”;因子3全部為反向計分題,體現的是教師在線教學過程中感知到的困境及壓力,將這些條目命名為“感知的困境與壓力”;因子4是教師先驗的信息化知識與能力,將這些條目命名為“先驗的知識與技能”,這一因子與原量表構成完全一致。
4.百分比常模構建
由于樣本符合正態分布,可以用百分比常模的方式構建該量表的常模。以十分位數、二十五分位數、五十分位數、七十五分位數、九十分位數劃分,該量表常模分值如表6所示。

表6 ASOTL-CV的百分比常模
三、我國教師在線教學態度的影響因素分析
1.三類教師群體在線教學態度整體表現
在小學、中學、高校教師3個樣本中分別進行描述性統計。全部樣本在ASOTL-CV上的得分均值為93.34±14.54,不同教師群體在ASOTL-CV總分及4個因子上分別的得分如表7所示。使用方差分析,LSD事后比較顯示,三類教師群體無論在總分上、還是在因子得分上,均無顯著差異。

表7 不同教師群體在ASOTL-CV得分的描述性統計
將總分與表6中的常模進行對照,三類教師群體對在線教學均持中立態度。根據常模細分三類群體對在線教學的態度,總體來說,對在線教學持非常積極態度的教師占11.40%,積極態度占15.40%,中立態度48.00%,消極態度13.80%,非常消極11.40%,不同教師群體中的占比情況如表8所示。

表8 不同教師群體對在線教學的態度占比
對三類群體的在線教學態度比率進行百分比同構卡方檢驗,卡方2=d10.04,p=0.26>0.05,不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可以認為三類群體對在線教學的態度較為同質,后續的數據處理中將合并進行。
2.人口學變量上的差異分析
一是地區方面,以學校所在區域作為分組變量,考察不同地區教師是否存在ASOTL-CV得分差異,方差分析結果如表9所示。在ASOTL-CV的總分上,城市教師與其他地區均無差異,郊區與鄉村地區教師存在顯著差異,鄉村地區教師對在線教學持更積極的態度。在“對在線教學的認可”維度上,鄉村教師與城市、郊區教師均有差異,鄉村教師更認可在線教學,“提升教師自身信息素養”維度上亦是如此。在“感知的困境與壓力”維度,郊區教師與城市、鄉村教師相比,感受到的困境和壓力最大,且有顯著差異;在“先驗的知識與技能”上,不同地區的教師均無顯著差異。

表9 不同區域教師ASOTL-CV的比較
二是性別方面,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考察男女教師在ASOTL-CV得分上的差異,結果顯示p=0.26>0.05,說明教師性別對在線教學態度無顯著影響。細分性別在ASOTL-CV的4個維度上的差異,發現“對在線教學的認可”“提升自身信息素養”“感知的困境與壓力”3個因子無顯著性別差異,但“先驗的知識與技能”因子上,男性均值為20.08±4.00,女性均值為18.71±1.33,t值-2.88,p=0.04<0.05。說明男性信息化方面的知識和技能高于女性信息化方面的知識和技能。
三是其他方面,使用方差分析考察受教育程度對ASOTL-CV得分的影響,除在“先驗的知識與技能”維度上,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存在顯著差異(p=0.04<0.05),各組間均無顯著差異;使用方差分析考察職稱、子女情況、婚姻情況對ASOTL-CV得分的影響,無論在總分還是4個因子的得分上,各組間均無顯著差異。說明教師職稱、是否育有子女、婚姻情況在各維度上都不影響教師在線教學的態度;考察家庭經濟社會地位與ASOTL-CV得分的相關性發現,教師父母的文化水平、職業類型及家庭收入與教師本人對線上教學的態度并無顯著相關。
3.其他影響因素的相關分析
用Pearson相關考察任教課程類型,學校技術支持、政策支持,其他同事對在線教學的態度與ASOTL-CV得分的相關性,如表10所示。任教課程類型與教師先驗的信息化知識與技能有顯著相關,學校在技術上、政策上的支持,周圍同事對在線教學的態度,與教師在線教學態度總分及各維度均顯著正相關。
四、結論與討論
通過修訂《教師在線教學態度量表》(ASOTL-CV),形成了一份可在中國高校、中小學使用的測評工具。在本文涉及的樣本中,該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較好;在結構分析上,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了與印度樣本不同的量表結構,析出的4個因子更適用于中國教師樣本且內部一致性信度均較好。同時,本文構建了教師在線教學態度量表的百分比常模。
在此量表的基礎上,本文分析了教師在線教學態度在學校類型、所在區域、性別、受教育程度、原生家庭及現家庭情況上的差異,并對影響教師在線教學態度的主要因素進行了探析。發現如下:
一是學校類型對教師在線教學態度無顯著影響,無論是高校還是中小學教師群體,對在線教學基本持中立態度,極其積極和消極態度者均較少,群體間無顯著差異。
二是鄉村教師對在線教學有效性認可的表現更積極,顯著高于城市和郊區教師,可能是在線教學對教育公平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這在鄉村體現得更為明顯。在線教學對教師個人成長的意義上,亦是鄉村教師得分顯著高于城市、郊區教師群體,可能是鄉村信息化教學基礎水平有待提高,對鄉村教師而言,在線教學對其個人成長幫助更明顯。對在線教學的困境感知上,郊區教師顯著高于鄉村與城市教師,這可能與城市學校對信息化教學本身較為重視,相應的培訓也較多,呈現“高要求,高支持”的特點,而鄉村學校需要使用信息化教學的情境并不多,呈現“低要求,低支持”特點。因此,鄉村教師對在線教學的困境感受并不明顯,故而“高要求,低支持”的郊區教師反而成為對在線教學困境最敏感的人群。
三是在先驗的信息化知識與技能上,男性評分高于女性。這與社會對男性擅長信息技術的刻板印象較為吻合,但究竟是男性的相關能力確實優于女性,還是男性接受了社會角色期待,導致測評出現社會期許效應,值得進一步考量。并且有研究發現,性別并不影響在線教學行為[12]。Lateef和Alab的研究認為,女性教師對在線教育表現出更有利的反應[13]。
四是在教師受教育程度差異上,只有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在信息化知識與技能上存在顯著差異,說明博士期間的科研訓練,對教師信息化能力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教師的原生家庭情況與教師對待在線教學的態度均無關聯,可見教師在職前和職后接受到的信息化知識培訓更為重要。教師本身的婚姻情況、子女關系也對其在線教學態度無影響,可能因為教師的家庭情況與在線教學工作并無關聯。
五是對教師在線教學態度影響比較顯著的因素是學校支持,這里的支持既包括教師在線教學中遇到困境時信息中心的幫助,也包括學校提供的政策鼓勵。因此,呼吁學校管理部門,在政策上和技術上為教師實施在線教學提供更多幫助,以鼓勵教師個體參與和投入到在線教學中。周圍同事的態度亦對教師在線教學有顯著的積極影響,這可能與從眾心理有關。班杜拉(Bandura)的觀察學習理論認為,通過觀察榜樣的行為進行間接學習比直接進行學習更加快捷[14]。因此,學校應營造良好的氛圍,讓更多教師對在線教學持積極樂觀的態度,以形成良性循環。
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進一步補充和細化樣本,考察研究型院校、應用型院校以及高職院校教師在線教學態度的差異,也可以進一步考察高中、初中、中職校教師在線教學態度的差異。可增加重測信度的測量,尋找合適的效標量表,進行效標關聯效度的檢定,補充樣本后用新樣本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同時,亦可考察教師在線教學態度,與實際在線教學開展效果的相關性。
五、建議
1. 構建“政策支持+培訓指導+評價激勵”管理服務體系
數據分析發現,教師對在線教學總體持中立態度,且對教師在線教學態度影響較為顯著的因素為學校政策鼓勵、信息技術中心的支持幫助等。可以認識到,學校的支持系統和管理體系還不夠完善,教師對在線教學的認識還不全面。基于此,學校應從頂層設計出發,構建“政策支持+培訓指導+評價激勵”管理服務體系。一是出臺完善的政策制度,鼓勵教師嘗試各種在線教學,開展教學模式的創新和實踐。同時,管理部門應提升管理服務能力和水平,在新型教學模式與原有教學秩序發生沖突時,提供更有創造性的支持和幫助。二是重視教師在線教學培訓指導,并將培訓重點逐步從技術層面的保障轉向內涵性建設的課程教學設計,如在線教學輸入環節的課程資源收集與制作、在線教學實施環節的組織與管理、在線教學輸出環節的學生知識能力素質評價等。三是優化在線教學考核、評價和激勵機制,關注不同類型學校、不同學科教師的需求差異,調動教師從事在線教學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2. 打造“優秀引領+同伴互助”在線教學研究共同體
充分發揮優秀教師的引領和示范作用,鼓勵并支持教師構建在線教學研究共同體,開展優秀案例展示、經驗分享、專題講座等有組織的教研活動,針對在線教學中遇到的各種問題進行交流和研討。調查數據顯示,周圍同事的態度亦對教師在線教學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因此,共同體建設中,注意充分發揮同伴互助的作用,在互相教學觀摩中提升對在線教學的認識,從而促使教師更加從容地適應在線教學“新常態”,樹立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新的教育觀念,提升教師運用信息技術改革教育教學方法的應用能力。
3. 加強鄉村教師在線教學支持和幫扶力度
正如前文分析,鄉村學校的信息化教學呈現“低要求,低支持”特點,且優質的培訓資源和課程資源較少。調查結果顯示,與城市教師相比,鄉村教師對在線教學表現出更積極的態度,并認為在線教學對個人專業發展更有幫助。這也表明,鄉村教師信息化教學基礎水平有待提高。未來,政府應加大對鄉村教師在線教學的技術和資金援助,實現城市帶動鄉村,并利用在線教學的優勢來促進教育公平,縮小鄉村教師與城市教師之間信息化能力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