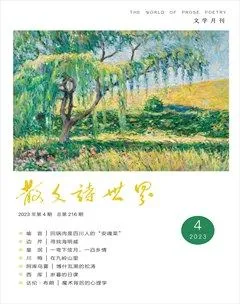以詩性的內(nèi)核開啟散文空間的神秘多維
紫藤晴兒
雨的神秘化、經(jīng)驗化是我第一次在陳文東的散文中發(fā)現(xiàn)的。它關聯(lián)的物象超出了我對現(xiàn)實語境的思考。雨和窯拉開的緯度寬泛到我的感知之外。我讀過許多次《窯》。雨線拉開的天空,我在獲取著一個詩性的空間,這讓一個讀者在閱讀中去定義語言的多種可能,打探著一座精妙的迷宮,并延伸著對時間接點的追問。
今天也在下雨,實際上雨從昨夜開始下的,秋天的雨會讓人間更為清晰,雨聲梳理了事物的在場與時間的關系。我從這場雨去向了佩索阿的雨,帕斯的雨,博爾赫斯的雨和陳文東的雨,而實際上又是在一場虛無之中的一次抽身和辨識。當然不僅是今天,無數(shù)次地走向雨的幻象都如詩歌建立的語言視界,我被那一場場雨圈定。這可以說是詩性的召喚精神,永不會倦意的閱讀,而每一次的進入又會覺得是不同的一場雨在契合一個詩人的及物能力。對于我來講永遠都是趨于感應的對答。
我不確定散文和詩歌的明確界限,但我確定《窯》是具有詩性的內(nèi)核,從雨中開啟著一場精神盛宴。在錯覺之中我也把今天的雨當成了佩索阿的雨,帕斯的雨,博爾赫斯的雨和陳文東的雨。共通于雨的寂靜,遙遠和不再遙遠的事物也如都在眼前。人間的低語我想寫點什么,一定是心靈上最明亮的句式了。它不會刻意地越出,自然于一場雨的造勢,語言也順從了心。我從開始第一次閱讀就確定《窯》的現(xiàn)代性,它不是散文的平鋪敘述,更多的時候具有詩性的柔韌度和爆發(fā)力,跳躍的個人經(jīng)驗。趨緩于自然的感應有了一片平原,有了一片曠野,也有了一片棉花地。張力打開的天空,時間切換的不同年代,柔軟展開的無序纏繞,空間展開的魔幻,這都讓我時常懷疑《窯》是關于一個詩人的行走和詩意棲居。也是荷爾德林的詩意歸鄉(xiāng)。雖然一再謙遜在自我之外,以散文的命題書寫。“雨從午后就開始下了,在雨聲中睡去,從雨聲中醒來。”我每每會被這句話送遠,隱秘聯(lián)系于一場雨的時空,但細讀雨霧也在向著另一個空間跨越,它有朦朧的指向,語言的秩序沉穩(wěn)著一個精神呼應。我一再地讀,又一再地被折服。我很難對一篇小說或散文放下更多的耐心,也很難向一篇作品反復闖入。用闖入是我無論在什么樣的心境之下在這里釋然的都如安寧。在這里識別到語言的常態(tài)是自然的密碼,和現(xiàn)實的質(zhì)樸。但又帶著魔力羈絆,當泥土也有了永恒的燃燒,光會在暗處照耀,反射。從一場雨到一個磚窯,從天空到大地的深層切換,我更多的時候覺得是心靈的遨游。被物象包圍的可以是一片烈焰,也可以是莫大的潮氣涌向現(xiàn)代化的喧囂中,心靈被那些寂靜頓悟,我也會想我們時常缺失的究竟會是什么呢。
《窯》再現(xiàn)了一個天空的秘境和歷史的蹤影。小小的切口卻關聯(lián)了一個龐大的精神體系。“燒窯人低矮的窩棚蹤影全無。”這句話輕拿輕放地落下,卻以詩性的延展挖掘,剖析向歷史的碎片。農(nóng)耕文明也躍然在字里行間,精神的救贖往往不是為自己似乎也是在為一個時代。我記得我們鎮(zhèn)上也曾有一個窯場,那里有一個高大的煙囪冒著黑煙。從沒有走過去,只知道窯場燒磚,但它確屬于一個時代的標志。紅色的磚在那個年代時常會被馬車或拖拉機運到村子,我知道泥土燒紅了就是磚。但不知道窯洞會在地下。我也不知道鎮(zhèn)上的那個窯場從那里什么時候也消失不見了。好多風物來不及回頭看它時,它又有了變數(shù)。還好有這篇 《窯》,我的鄉(xiāng)愁也可以在此找到出口。
歷史也會隱匿不見,只有文字以存在主義讓世事保留著完整,《窯》的引入像一個時間的懸秘,它具有可塑性。我相信它的真實,但它可以取代我們思想中所曾存在的一個窯場。不是我,也不是某個人,而是一個時代。我時常也會感嘆文學的魅力,寫作似乎又不是個人的事性,它是一個最為客觀的現(xiàn)實呈現(xiàn)。語言還原歷史,萬物仿佛又在當下鮮活。我沿著《窯》去向一個現(xiàn)實和虛無之間的審美。心靈的放牧你不能不說它是愜意的。鄉(xiāng)土的綸理我需要一些更為細微的語言彌合,大地的鏡像舒緩于生命的喘息,我再次被折服了。《窯》也在引發(fā)一場美學發(fā)現(xiàn)和詩意彌漫。那么多細膩的物象:秧子草、巴根草、蒺藜、牽牛花、蘆草、紫荊、薺薺菜……所容納的種類也是一個龐大的博物學。藏棣有一本詩集《詩歌植物學》,是人中有物,物我兩忘的。作家根系大地,回歸自然,這是我讀到的驚喜,同時我也攫取到自然的屋宇,與那些草木默察著種子和花蕊般的火焰。精神的共振我在這里找到,也從這里帶走并記憶。尋求與萬物一致的心。沒有界定的熱愛都皈依于自然,囊括于一個《窯》的成立和一個《窯》的消失。萬物有序,自然在它的規(guī)律中循環(huán)。開花結(jié)果。這些當然只是在《窯》的外部世界。介入它的內(nèi)部,也像是另一個天空,天空的陷落也在《窯》中。
去向《窯》的內(nèi)部,我便想起了馬爾克斯他寫過的《百年孤獨》,好像這一座窯也是一個小鎮(zhèn),不被世人通曉的奇異之地,需要坐著飛毯抵達,越過世人的視線。大膽的試探都帶著冒險精神,我想偉大的作家都需要如此的。“我忽然感到有些暈眩,恍惚間有了小時候看井的感覺,有些好奇,有些膽怯,可又仿佛有著抵抗不了的誘惑。”我當然也跟著這句話進入了《窯》中,可能我會比陳文東還急切。我不會掩飾自己的狂喜,如果可以跳,我是一下子跳了進去的。世間的熱愛我不想有任何耽擱和間歇。“那一刻,我的心還是突突地跳起來了,里面暗暗的、幽幽的……”神秘的力量也在發(fā)出巨大的召引,語言的撕裂在矛盾中對峙,我閱讀到是的一種快感。這也是一次靈魂的拷問。我們一直探索的究竟是什么?驀然于孤獨的又是什么?茫茫間能抵達的都屬于心靈的部分。我確信這是陳文東建立的精神家園。并以詩性的隱秘埋伏著巨大的張力。“我的喘息都有放大的回聲……可是靜靜中有什么東西使我緘口。” 詩性的對碰和錯位是我也在散文中找到寫作借鑒。語言的終極在無限漫過心靈。“我說過我還沒有見過土丘一樣的小山,卻感覺像孤身一人呆在大山深處的山洞里……松濤與野響從四面?zhèn)鱽怼痹娨獾纳仙灤┲粋€窯的立體。這不僅是語言經(jīng)驗,而是生命的體驗真實在一個時空的緯度。而我又獲取了更多的思想緯度。
寫到這里我已不關心一場秋雨停了沒有。文學的魔力往往是讓我忘我的。會有更多的情感發(fā)現(xiàn)讓我在關于《窯》思考。也合乎了“僅僅因為它是一座窯,或者是說一座廢圮的窯么?”答案是無疑的。精神的在場是永遠的現(xiàn)實關照,永遠的心靈回歸。隱忍克制的自我追問讓文本更具力量。未知的誘惑力遠比已知更為強烈。
而雨始終是去向窯的一個切入點。
雨好像也停了,停在了《窯》的詩性空間。從一場雨中探秘,一座窯安慰了人心。一場雨封存了塵世和多維的時空。縱然去表達都不及再次去閱讀。反復地去閱讀。語言的饋贈和詩性的新智重啟著《窯》的神秘性,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