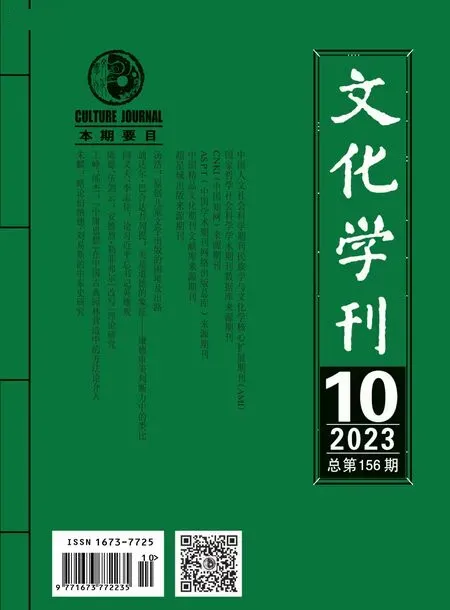作為社交媒體的宗祠
——以閩南地區宗祠為中心的考察
王志豪 雷玉璽
福建擁有數量龐大的宗祠,它廣泛存在于在鄉村聚落的集體生活中。 作為中國傳統鄉土社會最重要的特殊組織,它介于國家與基層社會之間,一定程度上扮演鄉村社會治理者的角色。 能夠實現其鄉村治理這一目標的前提,一方面是由宗祠形成本身的內在邏輯決定的,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方面則是宗祠作為一村一落的傳播中心,它總是能夠通過信息的流動,將居民相互聯結在一起。[1]除了信息溝通的職能外,宗祠還承擔著祭祀、禮儀慶典、儀式表演、娛樂等功能。 以往對宗祠的研究多從社會學的視角對其歷史、文化、功能等展開論述。 本研究在調研中發現從傳播學角度來考察宗祠的研究相對較少,尤其是在網絡社交媒體日漸發達的今天,它與網絡社交媒體有諸多相似之處。 本研究所選取的研究視角使用了社交媒體的名稱,但無意將當下主流對社交媒體的定義比附于宗祠的概念中,而更多從社會交往的角度來考察宗祠這一基本社會單元具有的傳播特性。
一、對宗祠的再理解
溫鐵軍對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有著這樣的總結: “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1]。” 這樣的總結將整個社會結構分為縣以上的國家權力部分,以及縣以下的宗族部分。 作為一個基本的社會單元,宗族具有相當完善的功能,對孝道傳承、促進宗親互助、維護鄉村秩序具有積極意義,其體現特點恰能反映哈貝馬斯關于社會交往理論的觀點。 哈貝馬斯強調以溝通為取向的交往行為是合理行為,認為社會交往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并且理性在其中有不可更替的重要性。 宗祠恰恰提供了傳統鄉村社會的這種社會交往功能,并且以信息的流動來聯結其中的居民。
宗祠也稱祠堂,是漢民族供奉祖先神主牌位并進行祭祀場所,是宗族組織存在的象征。 宗祠往往是一座村莊里的中心,在宗祠附近大多會有城隍廟和戲臺等配套設施。 福建擁有數量龐大的宗祠,多數宗祠新中國成立前便已修建。 據調查,福建省宗祠總數約13272 座,平均每萬人擁有3.59 座,每個縣、市、區擁有156 座宗祠。 其中漳州地區總數為2436 座,每萬人宗祠擁有量為4.9 座;泉州地區擁有宗祠總數約2219,平均每萬人擁有3.1 座。 廈門地區,總數為517 座,每萬人宗祠擁有量為2.45座[2]。 可以說,宗祠幾乎零星分布在每個村莊中,更有甚者,部分規模較大的村莊或存在多姓氏混居的情況,會有多個祠堂同時存在。 作為最基本的社會單元,宗祠在傳統鄉村社會中不僅是一個非官方的 “行政單元” ,還是一村一落的信息集散地,以此為傳播的中心節點,它讓信息在宗族之間流動起來。
傳統的宗祠往往是興辦公共事業的地方,一些實力雄厚宗祠會在宗祠開辦學堂接收學子入學,這些學子不完全都來自本村,也可能會來自周圍村莊。 并且一些有實力的宗族人士也會捐資助學。除了學堂,一些宗祠還會增設圖書、報刊供人取閱,有些村鎮甚至會將新建的圖書館設置在宗祠里面。教育無疑讓知識以信息的形式得以傳播起來,早期的宗祠學堂雖以簡單的識字為目標,但是一些觀念和倫常在潛移默化中亦得到相應傳承。
一所宗祠往往是一座村莊的核心,它提供了商討事務的場所。 從宗祠祭祀的經費收集與支出到修橋補路的集資等等,所有與村落息息相關的事務的討論與執行無一不是先在宗祠當中商討后完成的。 這意味宗祠在村莊集體生活中的權威性,因此,宗祠活動一般由一群比較有威望的老人主持,有些宗祠則干脆掛上 “老人會” 的招牌來主持宗祠的各項事務。 他們除商討事務,在必要的時候也會居中去調節村民之間的各項矛盾。 村民通常礙于 “老人會” 的權威而選擇各退一步,從某種程度看,老人會更像是一個村莊當中的 “意見領袖” ,從言行上影響個人的觀點和行動,而在撰修族譜這一件事情上,他們所擁有的話語權則要更大。
除了莊重的議事,宗祠還是一個重要的社交舞臺,有些宗祠會設置棋牌桌、茶桌等供人娛樂歇息,這也在無意中形成了一個信息交流的地方。 此外,每逢宗祠有各項祭祀時,宗祠也儼然成為一個社交的平臺。 通常情況下,閩南地區祠堂的活動可以分為常祭、專祭、大祭三種。 常祭指日常祭祀,是貫穿在一年中的每個月里面的祭祀活動,通常在每月的朔日(初一)和望日(十五)兩個固定的日期,由各分支或各家委派代表前往祠堂進行祭拜。 專祭指專門的祭祀,逢族人嫁娶、生子、考取功名等喜事,會舉行專門儀式祭告祖先。 大祭指宗族合族之祭,也是最重要的祭祀活動,不同地區甚至同一地區的不同村落在大祭的時間上會有所不同,一般包括祖先誕辰日(俗稱 “祖公生” )、宗祠修成進主以及其他特定重要活動的祭祀行為。 每逢有祭祀行為,不少村民便聚集在宗祠里相互攀談、交換信息,宗祠在這時候儼然成為八卦交流所。 大家會將日常瑣事加以分享、相互交流,以熟絡感情。
在宗祠的外圍,通常還會有一個布告欄,張貼著公示信息、重要事項通知等。 然而并不是每一個村民都會參加會議,因此,宗祠里還會有類似于傳話人的角色,傳話人是信息傳播出去的渠道,而且是穩固的渠道。 事實上,即便不參加宗祠的會議活動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因為信息總是流動的。 借由布告欄可以將信息告及父老鄉親,通過村民之間的人際傳播,用不了多久也會傳遍多數村民的耳朵,如果碰上特別重要的事項, “老人會” 還會派人挨家挨戶地通知。
二、宗祠的視覺傳播
宗祠除了作為一座村莊的信息中心,本身也作為一個實體的存在,它承載著一定文化信息,是信息傳播的 “媒介” ,以 “物” 為存在而為人感知。 作為實體,宗祠通過外在的、直觀的視覺呈現作為媒介來傳播信息。
首先,宗祠的建筑本身能夠成為一個傳播的重要符號。 閩南地區的宗祠往往追求形制豐富、裝飾考究、雕刻精美。 平面形制多以三開間兩落為主,建筑追求對稱的特點。 建筑的華美程度往往能夠說明一個宗祠的實力,在一些社交場合當中,宗祠是一張能夠迅速讓人認識的名片或社交標簽,一個宗祠總是代表著一個村子普遍的財務狀況、身份和面子。
除了建筑本身,宗祠內的楹聯、匾額、碑刻以語言符號或非語言符號的形式呈現,這些傳播內容隱含教化的意義。 楹聯的內容常常是歌功頌德、彰顯祖業、鼓勵耕讀、講述家風的主題。 匾額有的標示宗祠名稱,有的彰顯祖宗功名,有的敦親睦鄰。 至于碑刻,有創建重修的記事碑、記述家族世系源流的世系碑、寫祠規和家訓的碑、記載德行的懿行碑以及記載功名的碑等。 從語言符號看這些內容蘊含豐富的文化內涵,將傳統文化中的忠、孝、仁、義等主題融入其中,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著一村一落的居民。
祭祀同樣以視覺化的呈現來傳播,祠堂最基礎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祭祀祖先,每年都會定期舉行祭祀活動。 如前所述,在宗祠里的祭祀可以分成常祭、專祭、大祭三種,這些祭祀組成了一個宗祠最重要的活動, “節日和儀式定期重復,保證了鞏固認同的知識的傳達與傳承”[3]。 祭祀過程要遵循一定程序和儀式,在整套的儀式下,確認族人對祖先的追思,增強族人的凝聚力與認同感。
與祭祀相輔的是社廟游神,一般在較為重大的祭祀活動中會出現。 游神活動一般在春節期間,是整個春節期間娛神活動的高潮,也是節日氛圍最為濃厚的一項活動。 游神通常與境域祭祀圈聯系在一起,境域祭祀圈是一種在東南沿海地區常見的地域和信仰緊密結合的最基層的祭祀系統,其基本要素是以某個約定俗成的境域為神圣空間,以宮廟寺院為核心,以共同的宗教信仰為紐帶,以境域內的信眾為祭祀主體[4]。
作為一年一度最為盛大的娛神活動,游神既是一種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活動,也是能夠將此文化特色演繹并呈現的舞臺。 這種文化具有濃厚的鄉土情節以及宗族一體的觀念,而游神活動恰恰是最能體現這一人文特征的活動。 借由游神活動,激發了同宗同源的宗族意識、凝聚了宗族認同。 這一過程并不是通過文字來傳播的過程,而是以 “傳播的儀式觀” 來形塑認同。 傳播的儀式觀是詹姆斯·凱瑞在著作《作為文化的傳播—— “媒介與社會” 論文集》中所提出的概念,他認為 “傳播” 這一行為不是一種傳遞信息或影響的行為,而是對共同信仰的創造、表征與慶典。 他把傳播看作是創造、修改和改造一個共享文化的過程[5]。
綜上,與今天網絡社交媒體所呈現的景觀類似,許多傳播本身在內容的重要性和顯著性并不算突出,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其所營造出的儀式觀卻有著內容本身無法傳遞的價值。 如作為建筑實體的宗祠,以及在宗祠內所能見到的楹聯、匾額、碑刻等非語言傳播符號。 這其中尤其以祭祀和游神為代表,這種有著一定程序和煩瑣過程的活動恰恰成為了一個文化共享的過程。 在這樣一整套的審美、生活和祭祀規則傳播下,成為一種激發宗族意識、凝聚宗族精神并實現宗族教化的力量。
三、宗祠是否為公共領域
在前面部分的論述中,本研究重點描述了宗祠本身所具備的傳播屬性,它作為一個村莊信息傳播的中心,作為一個社交舞臺的存在,其所營造出來的鄉村這一基本社會單元的信息傳播網絡。 在這一傳播網絡中有作為 “意見領袖” 的鄉紳,有參與到信息傳播節點的個體。 并且宗祠的傳播方式里不僅包含了口耳相傳的人際傳播,也包含了布告欄這種組織傳播的形式,以及建筑、祭祀和游神等非語言符號的形式。 從傳播的議題看,宗祠所討論話題,主要是一些和宗族相關的話題,或是家長里短的 “八卦” ,較少有關乎政治的話題。 在最后一節的討論中,本研究將主要選取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關于公共領域的論說來展開,雖然關于公共領域的理論有許多,但以哈貝馬斯所提出的較為成熟,是目前國內學界引用和解釋最多的[6]。
如果按照哈貝馬斯對 “公共領域” 的定義,那么宗祠顯然與此謬之千里,但本研究無意將西方概念比附于中國經驗。 因為哈貝馬斯 “公共領域” 理論的提出是基于對西方的歷史、環境所生產出的理論,未必能夠解釋中國的情況。 不過,公共領域的理論同樣存在一個重新解釋與適用的過程。 如溝口雄三提出了辛亥革命中之所以能夠成為各省獨立的局面,乃是因為當時成熟的 “一省之力” 影響的結果。 溝口雄三進一步指出 “省” 的概念,指的是貫穿于鄉、鎮、縣、府的網絡,這一網絡以同心圓或放射線狀在同一平面上縱橫流動,形成了一省的 “鄉里空間” ,也就是能夠實現鄉鄉聯合的政治社會空間。 “鄉里空間” 這一概念是 “地方自治” 的觀念,形成了官、紳、民共襄共舉的局面[7]。
四、結語
筆者重點描述了作為社交媒體的宗祠,并重點討論了宗祠與哈貝馬斯 “公共領域” 概念的區別。盡管二者之間不能簡單地畫上等號,不過借由此概念,本研究認為宗祠具備成為一個社會交往的公共空間的可能,與哈貝馬斯強調的精英化的公共領域不同,宗祠是一種側向于中國鄉村公共空間的范疇,它的重點不在于為了去影響國家政治決策,而是維系宗族團體的一股力量。
筆者對社交媒體的理解,有別于時下對社交媒體的定義,而更強調其社會交往層面上的功能與內涵。 以此出發,可以看到在中國社會的基層里宗祠是一個重要的社交媒體。 在這個社交媒體當中有承擔著道德教化的作為意見領袖的鄉紳,有維護鄉村社會秩序的一群人,有參與信息流動的人群等等。 不論是哪一種形式,宗祠作為中國基層社會最基礎的一個單元,無疑在社會格局當中承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社會交往中所發揮出的功能以及創建出來信息傳播結構,構成了中國特色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