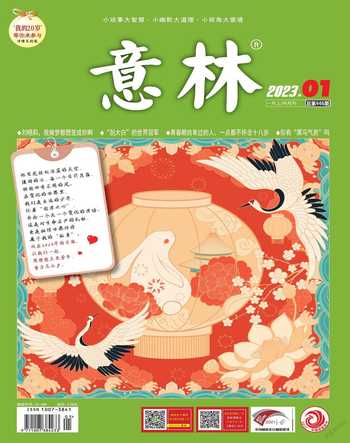辭職回老家后,我減少了不必要的消費
Cy
前兩天我刷微博,看到關注的博主發布了一條雙“十一”攻略,詢問大家都要買什么。這才恍然發覺,一年一度瘋狂剁手的日子又要來到了。
我順手打開購物軟件,想著添補點東西,卻驚訝地發現里面只有零星幾件商品,大部分還都因為加購的時間太久而下架了。實在不甘心又想了一會兒,愣是沒想到要買啥。
放在幾年前,我絕對不會想到,有朝一日自己會面臨這種“有錢沒處花”的消費困境。
前兩年我在北京工作,遵奉著“享樂主義至上”的生活原則。前腳工資卡打的錢,后腳就花了出去。根本不用發愁買什么,滿天飛的廣告和琳瑯滿目的商品,早就將“草單”種成了一片森林。
后來我辭職了,居住地從一線轉到了三四線小城市,消費欲望直線下跌。不僅打開購物軟件的次數屈指可數,連每月總花費都不超四位數。
回過頭來不禁感慨,苦練已久的縮減開支,竟是通過一場辭職來實現的。
消費減少是全方位的,先從“吃”顯露端倪。作為一個懶人,我在北京幾乎不下廚做飯。如果點外賣,一頓要二十多塊,再加上水果、飲料,一個月要吃進去兩千塊錢。工作日再買一杯咖啡,周末約個下午茶,逛個街,恩格爾系數就這么漲上去了。
辭職回了家,就是截然不同的光景,很多不必要的花費被節省下來。每天父母做好飯,根本不用花錢買菜。常去的餐館,也從“網紅”打卡地變成了路邊的蒼蠅館子,人均不超一百塊錢。昔日那些成本高昂的光鮮日常,在一個連星巴克都沒有的小城市里,成為稀有的生活方式。
說到“住”,才是消費的大頭。不舍得犧牲自己的睡眠品質,我租了北京一間有獨立衛生間的主臥,房子寬敞明亮,房租也很給力,一個月高達四千塊。我還在附近辦了一張健身卡,林林總總算下來,每個月可支配的收入縮水了一半。
要是問剩下的一半呢?那就是花在“衣”上了。
以前手機使用時長最久的App就是購物軟件,每天耗上幾個小時不足為奇,沒有經濟危機意識之前,我下單的隨機性很強。
這個東西做活動真劃算,買!
這個博主推薦的衣服不錯,怎么搭配呢?算了,成套下單!
偶爾出趟差回來,門口未拆封的快遞堆成了小山,很多東西當時又懶得拆,就塵封在柜子里。等到年終大掃除時,清理出一堆過時的全新衣服,心就疼得猶如刀割。

直到辭職后,我一時沒有找到心儀的工作,也不知道何時才能有穩定的收入,才下定決心,給自己立了一個“只買剛需”的flag。
剛開始消費慣性還未消散,遇上喜歡的東西還是會動心,只能瘋狂加購,把購物車塞得滿滿當當。久而久之,新的習慣成型,慢慢就打消了買東西的心思,日子也過得細水長流起來。大半年后我做起了副業,可支配收入變多了,腦袋里的那根弦也始終沒有放松。
“最近汽油又漲價了,買輛電動車騎騎吧!還沒有早晚高峰擁堵的煩惱。”
“去健身房?健身房教練能比劉畊宏專業嗎?還是對著抖音直播跳操吧。”
一次次自我說服之后,我成了“極簡生活”的推廣大使,銀行卡上的余額也慢慢漲了上去。
我漸漸發現,大部分不必要的消費其實都能找到相應的替代品,并不影響生活質量。真正產生影響的,是我們原本對高消費賦予的心理意義——把自己和物品等價類比,仿佛消費低了,自己就掉價了似的。
社會里存在著這樣的價值觀:消費體現了個人的品位與階級,對各種品牌的討論等同于社交貨幣,你不得不付出一定的成本去融入職場環境。而辭職讓我擺脫人際包袱,讓我不用再為多余的品牌溢價買單,在“低欲望”生活里找到了舒服的節奏。
曾經看過一組調查數據,2022屆畢業生平均簽約月薪達6507元,比去年下降了12%,可能還有虛高的成分。這個數字放在北上廣,甚至二線城市,根本無法支付房租開外的“精致生活”,這也是為什么現在的年輕人漸趨理性,紛紛叫囂著“拼夕夕真香”了。
仔細想想,減少不必要消費代表了一種成熟的消費態度,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丟棄華而不實的部分,為自己的需求瘦身。從心態上說,這何嘗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消費升級”呢?
當然了,抑制物欲不是杜絕消費,把自己關進孤獨的小黑屋。如果一件東西,令你開心,令你幸福,帶來的效益可以大概率達到預期目標,那就勇敢去買。對生活的掌控感,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從而在合理范圍內滿足欲望和日常所需。
生活千人千面,快樂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花錢也是,攢錢也是。希望每個人都能在物欲橫流的社會健康生活,成為消費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