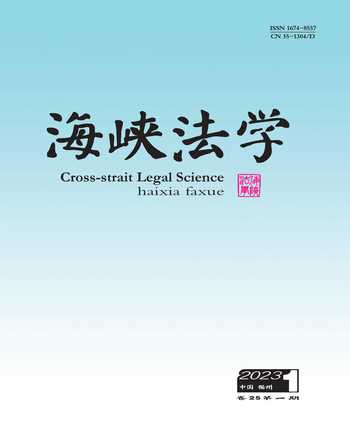《TBT協定》框架下的技術法規研究
摘 要:技術法規是世界各國實現國家治理通行的立法實踐,因其可能造成國際貿易壁壘而受《TBT協定》規則的約束。如何把握《TBT協定》對WTO成員技術法規的適用范圍與規則有待理論研究進一步明確。《TBT協定》認定技術法規是適用相關規則的前提,需要借助技術規范屬性與強制性效力兩個核心要件,結合相關爭議案件勾勒技術法規的輪廓。《TBT協定》要求WTO成員技術法規內容上以國際標準為基礎,在技術法規制定和通過程序中及時告知其他成員以便就分歧進行溝通。
關鍵詞:技術規范;強制性;國際標準;透明性
中圖分類號:? D99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4-8557(2023)01-0056-11
引言
技術法規是各個國家或區域借助技術要求實現國家治理的通行的立法實踐。美國在法律、法規中引用納入技術標準,通過賦予這些技術標準以強制性來明確履行相關法律義務的技術要求。[1]歐盟在條例、指令等形式的措施中規定基本技術要求,并委托三大歐洲標準化組織制定相關標準,為公眾提供一個被推定符合技術要求的路徑。[2]俄羅斯適用與實施歐亞經濟聯盟制定的技術法規,其中規定了產品強制性技術要求,同時又公布了其認定符合技術法規要求的標準清單。[3]在我國,既有法律法規等法律性文件規定相關技術標準或要求,也有通過強制性標準來規定需要強制遵守的技術要求。有鑒于此,ISO與IEC在一份關于標準化活動基礎術語的指南中指出了技術法規可能的多種形式,并將技術法規界定為“規定技術要求的法規”。[4]
然而,各國技術法規之間存在差異。除上述的法規形式迥異外,技術要求更可能是大相徑庭。例如在同一類產品玩具上,中俄技術法規的主要技術要求就存在著七個方面的差異,俄法規的技術要求中既有在國際標準基礎上提高水平的,也有其獨創的。[5]各國技術法規的不一致提高了國際貿易的成本,阻礙了商品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通與交易。為協調各國技術法規、促進全球共同市場,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成員間簽訂了《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以下簡稱為《TBT協定》),圍繞各成員制定、通過和適用技術法規制定了國際貿易規則。《TBT協定》所承載的規則約束著WTO成員的技術法規,其在多大范圍內以及何種程度上影響著各成員技術法規的內容與制定程序是本文致力于探討的問題,對于我們今后構建與《TBT協定》恰當銜接的技術法規體系起著重要的理論支撐。WTO《TBT協定》作為國際經貿規則體系的一部分,正由于世界各國之間力量博弈均衡的改變而面臨改革壓力,如何在改革中爭取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話語權是當前值得關注的問題。[6]因此,本文也將啟示我國如何在標準與技術法規領域提高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
一、技術法規國際規則的產生
技術法規是規定技術要求的法律規范,是國家或地區實現監管職能的重要手段,對于提升產品質量、保護國民健康和生命安全、保護消費者權益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技術法規往往基于本國或本區域政策考量制定,因而忽略了對國際貿易的影響,顯著增加國際經貿參與者獲取、適應他國法律與政策要求的成本,大大削弱其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限制了國際貿易活動的發展。[7]因此,在上世紀70年代,國際社會逐漸形成共識,認為技術法規、標準與認證等國家措施屬于一類技術性的貿易壁壘,需要由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組織(GATT)形成國際規則來約束。
在東京回合(1973-1979年)談判階段,GATT認識到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形成根源在于世界各國在監管層面缺乏跨國合作。各國政府都有保護本國國家利益的傾向,然而在國際貿易政策制定過程中,他們逐漸認識到國際標準的效益。國際標準的優勢是標準本身具有可兼容性,如果國際標準是被廣泛接受的,一方面降低了生產投入成本,另一方面也降低交易成本,不僅有益于跨國產品生產者,也有益于各國的消費者。[8]因此,GATT于1979年形成了《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1979)(又稱為《東京回合標準守則》),其中對制定、采納和實施技術法規、標準以及合格評定程序做出了原則性的規定,希望借助國際標準來協調各國法規以促進國際貿易。[9]盡管《東京回合標準守則》是自愿簽署的條約,它對于消除國際貿易壁壘仍然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美國、歐盟所有成員國等國家均簽署了該守則,該守則鼓勵各國政府審查技術法規方面的政策,提高其對這項工作的承諾;同時促進國際標準更廣泛和更有效地實施,以協調各國在技術法規方面的分歧。[10]
為了進一步明晰關于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規則,增強對各國制定技術法規等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約束,在烏拉圭回合談判(1986-1993年)時最終達成了一項更清晰、更具可操作性的國際條約《TBT協定》,其中堅持了以通過國際標準協調成員法規要求為主的解決方案,而強化了透明性義務的規則。自WTO正式運行之時始,《TBT協定》就包含在其一攬子協定之中,WTO的164個成員均須遵守。
《TBT協定》對技術法規的適用在很多情況下是并非明確的,在解釋上有一定的空間。一方面是因為《TBT協定》需要在國內監管權與國際貿易自由之間進行平衡,而有賴于WTO爭議解決機構的解釋。《TBT協定》約束各成員技術法規、標準與認證等措施,以避免其構成對國際貿易自由的不當限制,是在尊重各成員基于合法的非貿易監管目標而提出對產品的要求的這一前提下。正如《TBT協定》序言中說明,“不應阻止任何國家在其認為的水平上采取必要措施確保其出口質量,或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環境,或防止欺詐行為適當,但條件是它們的適用方式不會在條件相同的國家之間構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視的手段或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而在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提出,《TBT協定》對于技術法規立法更像是一種基于外交而非法律義務的國際協調。[11]WTO成員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會訴諸爭議解決方式,多數情況下是通過TBT委員會對其他成員提出“特別貿易問題”(Specific Trade Concerns)以溝通對其可能造成的不必要的貿易阻礙。由此帶來的規則內涵的不確定性使得理解《TBT協定》的適用范圍和規則變得更為復雜,描繪《TBT協定》框架下技術法規的輪廓需要借助相關爭議案件對這些問題的探討。
二、構成技術法規的技術規范屬性要件
《TBT協定》對各成員技術法規產生約束力的范圍取決于《TBT協定》對于技術法規的界定。一項措施如果落入《TBT協定》技術法規的范疇內,則將受相應規則的約束。根據《TBT協定》附件1.1的定義,技術法規是“規定強制遵守的產品特性或其相關過程和生產方法、包括適用的管理規定在內的文件。該文件還可包括或專門關于適用于產品、工藝或生產方法的專業術語、符號、包裝、標志或標簽要求。”在《TBT協定》中,技術法規不拘泥于特定的法律形式,只需要包含一定的規范性內容,因而“文件”可以囊括WTO成員所有的措施。技術法規的內容范圍不僅包括針對產品特性或其相關過程和生產方法的規定,還包括涉及這些內容的管理規定。
盡管《TBT協定》的定義模糊了技術法規的法律形式,以適應不同國家的形式的不同,但是它同時也強調了兩個實質性要件:一是具有技術規范屬性,即規定了產品特性或其相關的過程和生產方法;二是具有強制性效力,即“強制遵守的”,這是技術法規與標準區分的關鍵要件。這兩個要件在早前較為原則性的1979年《東京回合標準守則》中已有規定,定義技術法規為“規定強制遵守的技術規范,包括適用的管理規定”,并且將“技術規范”解釋為“在文件中包含的規范,其規定了產品特性,如質量、性能、安全或尺寸。它可能包括或專門關于適用于產品的專業術語、符號、測試和測試方法、包裝、標記或標簽要求。”[12]現行《TBT協定》雖然在文字上有所變動,但這兩個實質性要件仍然保留了下來。除上述兩者外,在涉及《TBT協定》的爭議案件中,WTO爭議解決機構通常對一項措施進行的“三層審查”[13]還會考察爭議措施是否適用于“可識別的”產品,認為如果不適用于“可識別的”產品則該措施喪失了可執行性。當然,一項措施并非必須在文字上體現其針對任何產品,而只需要在實施過程中能夠識別出其規制對象。[14]
需要注意的是,《TBT協定》對技術法規的界定不同于各WTO成員對于技術法規的界定。從這一方面來看,辨析《TBT協定》技術法規適用范圍具有必要性。我國標準化相關法在1980年就使用了技術法規的概念,但《TBT協定》中的技術法規是在國際法語境下的界定,與我國法律體系中的技術法規的語境和面向是不同的。[15]我國現行法律中雖未提及技術法規,但可以確認的是我國技術法規的范圍超過《TBT協定》的范圍。[16]歐盟在2015年《關于提供有關技術法規和“信息社會”服務規則等信息的程序的指令》中定義歐盟成員之間所協調的技術法規為“關于服務的技術規格和其他要求或規則,包括相關的行政規定,在營銷、提供服務、建立服務經營者或在成員國或其主要部分使用的情況下,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強制遵守這些規定,以及成員國禁止制造、進口、營銷或使用產品或禁止提供或使用服務或建立服務提供者的法律、法規或行政規定,第7條規定的除外。”[17]歐盟技術法規涵蓋范圍廣,涉及產品與服務,將事實上強制遵守的規定也納入進來。而美國雖未在法律中作出明確界定,但以引用納入標準的行政法規為主,其范圍與《TBT協定》語境下的范圍也是不相同的。《TBT協定》與各WTO成員對于技術法規的界定相互區別又有關聯,《TBT協定》將影響各國對于技術法規的界定。
(一)“產品特性”
構成技術法規的技術規范屬性體現在相關措施是否規定了“產品特性或其相關的過程和生產方法”。關于何為“產品特性”,WTO爭議解決的上訴機構曾在2001年歐共體石棉案、2014年歐盟海豹案中作過探討。在歐共體石棉案中,上訴機構指出“產品特性”包括“產品客觀可定義的‘特征、‘質量、‘屬性或其他‘顯著標志。……可能是與產品的成分、尺寸、形狀、顏色、質地、硬度、拉伸強度、可燃性、導電性、密度或粘度等有關。”“產品特性”都是“產品本身固有的特性和品質”。一項措施可以規定一個或多個“產品特性”。[18]這種產品特性可能是以肯定方式規定,也可能是否定的。[19]
如果一項措施僅僅是禁止自然狀態下的產品,則不能構成對“產品特性”的規定,因而不屬于技術法規。比如在石棉案中,上訴機構認為簡單地禁止自然狀態下的石棉纖維(純石棉產品)的措施,是不構成技術法規的。但爭議措施規定了禁止含有石棉的產品(混合產品),則具有技術規范屬性,因為它以否定形式規定了一種產品特性。[20]在歐盟海豹案中,爭議措施規定了禁止完全由海豹組成的產品(純海豹產品)不構成技術法規。
措施中規定產品的生產來源(例如生產商或制造商身份)、制造類型或目的、銷售方式不屬于“產品特性”。在歐盟海豹案中,上訴機構通過結合對禁止海豹產品的例外規定的分析認定,歐盟有關海豹產品的爭議措施,整體而言并不是基于產品特性而實施禁止或許可規定,而是基于“捕撈者身份”或者“產品來源的捕撈類型或目的”或“產品銷售方式”。[21]由于這些規定并不影響在市場上流通的含有海豹產品的“固有特性和品質”,因此不屬于“產品特性”的規定。
此外,判斷某成員的措施是否規定了“產品特性”需要根據具體措施的特點進行個案分析,只有對爭議措施整體進行綜合權衡和分析才能確定其法律性質。例如上訴機構比較上述兩個案件中規定了混合產品的措施的重要性后提出,相較于石棉案中主要是針對混合產品的規定,歐盟海豹案中有關混合產品的規定不那么明確且重要。[22]
(二)“過程和生產方法”
除了規定“產品特性”,一項措施僅對“過程和生產方法”(也稱為PPM)作出要求也可能構成技術法規。在歐盟海豹案中,上訴機構通過對技術法規的定義第一句“產品特性或其相關過程和生產方法”中的關聯詞“相關”的分析認為,一項措施所規定的過程和生產方法必須是與產品特性有“充分聯系的”,[23]而這種聯系程度是需要對措施進行個案具體審查的,其界限有待未來爭議案件的辨析。但可以明確的是,與產品特性無關的PPM不屬于技術法規,因而不受《TBT協定》的約束。在上述歐盟海豹制度案中,挪威和加拿大曾對于捕撈方式、來源方面的規定是否屬于PPM提出討論,但是由于專家組與上訴機構認為這是個新穎的問題因而并未進行探討并得出任何結論,[24]給這一問題留下了開放性的解釋空間。
然而,如果一項措施規定了“術語、符號、包裝、標志或標簽要求”,當其中有與產品特性無關的PPM時這項措施是否構成技術法規?這一問題存在爭議。[25]在技術法規定義的第二句“該文件還可包括或專門關于適用于產品、工藝或生產方法的專業術語、符號、包裝、標志或標簽要求”中并未明確PPM與產品之間存在“相關”聯系,那么規定與產品特性無關的產品標簽要求的措施受《TBT協定》約束嗎?與產品特性無關的PPM的法律地位一直是WTO發達成員與發展中成員之間博弈的過程,發達成員希望這類PPM構成《TBT協定》中的技術法規從而擴大《TBT協定》適用范圍、增加各成員措施的透明度。[26]因此發達國家支持的立場是技術法規定義的第二句是第一句的“補充”而非“舉例說明”,那么一項措施如果規定與產品特性無關的PPM的“術語、符號、包裝、標志或標簽要求”,將獨立于第一句所要求的與產品特性相關的PPM而構成技術法規。與產品特性無關的PPM的典型標簽措施是2012年美國金槍魚案(II)的爭議措施海豚安全標簽制度,該措施對于金槍魚捕撈地點、捕撈工具與捕撈技術能否貼上海豚安全標簽作出規定。在該案中,專家組與上訴機構一致認為,基于上述“補充”的邏輯,這類措施規定了《TBT協定》所適用的技術規范。[27]
技術法規之所以成為《TBT協定》規制的重點,正是由于其具備技術規范的屬性。一個國家可以通過這種看似中立的技術要求水平的提高或額外限制的施加,達到歧視、排除國際競爭者的目的,有別于關稅和一般的法律法規而成為阻礙國際貿易的一類特殊的貿易措施。“產品特性或其相關過程和生產方法”的構成要件就體現了技術法規的這種技術規范屬性。判定一項措施是否落入《TBT協定》適用范圍就需要審視是否具備技術規范的屬性,即意味著考察該措施的規范內容是如何對產品作出要求的——是否有針對產品的固有特性和品質或者相關的過程和生產方法作出允許或禁止的規定。
三、構成技術法規的強制性效力要件
強制性效力(又稱“強制性”)是構成技術法規的核心要件之一,它將《TBT協定》規制的兩大措施技術法規與標準區分開來。
(一)作為爭議中區分技術法規與標準的要件
從《TBT協定》附件1的定義來看,技術法規容易與標準相混淆。兩者都規定有產品特性或相關過程和生產方法的技術規范,并且兩者均“可包括或專門處理適用于產品、過程或生產方法的專業術語、符號、包裝、標記或標簽要求”。但附件1.2解釋性說明提示了兩者的區別,技術法規是強制遵守的,而標準則是自愿性的。兩者對于國際貿易的影響完全不同。進口產品可以選擇不同于該國標準的標準實施而在一國自由銷售,盡管會有一定市場競爭力的差異,但仍然屬于企業自主決定的范疇;而進口產品如果不符合該國技術法規則會被禁止銷售,這是法律強制性規定的要求,違反這一技術法規可能會導致相應的法律責任。與標準相比,技術法規具有更強的約束力而更可能(不當地)造成貿易壁壘。因此也不難理解,《TBT協定》對于WTO成員技術法規提出更高的要求。
WTO上訴機構在金槍魚案(II)中從字義上解釋了“強制性”,即“受命令規則要求的、必須遵守的”(obligatory in consequence of a command, compulsory)[28]或者“在法律上受約束的”(obligatory)[29]。[30]一般而言,按照上述字義理解能夠通過考察相關措施是否是強制性的,相關方是否必須遵守,來區分技術法規與標準。
然而,如果一項措施規定了“標簽要求”,則它可能構成標準,也可能被認定為技術法規。因為無論是技術法規還是標準,均可能“包括或專門處理適用于產品、過程或生產方法的專業術語、符號、包裝、標記或標簽要求”。從字義上理解,“要求”本身也是強制遵守的,但規定這類要求的措施卻不一定都具有《TBT協定》技術法規的“強制性”。構成技術法規的“強制性”含義充分體現在美國金槍魚案(II)對于海豚安全標簽措施的探討中。該案的爭議措施是美國政府對金槍魚產品能否貼有海豚安全標簽、涉及“海洋哺乳動物”、“海豚”等標簽作出規定,只有滿足了關于捕撈方式、地點和船只等特定條件才可使用標簽。貼有這類標簽的金槍魚產品更受市場青睞,但美國并未禁止其他未貼有該標簽的產品在美國市場上銷售。美國據此主張,其措施雖然禁止在不符合其條件的情況下使用海豚安全標簽等相關名詞的標簽,但并未禁止不含該標簽的產品在市場上銷售,因此不具有強制性。但上訴機構反駁了美國的主張并指出,技術法規在標簽要求上的強制性不體現在對于市場流通的限制,其強制性也可能是相關措施“構成處理特定事項唯一手段的具體要求”。[31]它在本案中就體現在,美國的爭議措施使得所有從事金槍魚的商業組織必須遵守該措施才能主張其產品是“海豚安全的”或相關表達。[32]除了排他性,上訴機構還考慮過相關措施是否出自成員頒布的法律法規而非私人行為,或者措施是否可執行的。但單獨分析這兩個檢驗標準,上訴機構發現它們都不能影響一項標簽相關的措施是否構成技術法規。因為從這兩個角度來看,標簽要求作為一項要求都可以被理解為是強制的,而并未體現出區分標準和技術法規的“強制性”含義。[33]因此,關鍵的問題是當一項措施將標簽限定為唯一、排他的,則該措施具有法律上約束力的、并非任意性的,才更可能意味構成著技術法規的強制性效力要件。
(二)理解強制性標準的法律性質
至此,《TBT協定》中技術法規與標準的區分似乎明朗,技術法規是規定強制遵守的技術規范的文件,而標準是規定非強制遵守的技術規范的文件。然而這一區分標準仍然沒有解決我國強制性標準的法律性質問題。
一方面,在《TBT協定》實際適用中,強制性標準被歸類為技術法規。1979年《東京回合標準守則》在技術法規定義的說明中明確了強制性標準屬于技術法規:如果在一般法律中賦予了某些標準以強制力,而并未在單獨法規中賦予特定標準以強制實施效力,則該類標準也屬于技術法規。[34]現行《TBT協定》刪除了這一解釋,避免了標準與技術法規概念混亂。然而結合《TBT協定》區分技術法規與標準這兩種技術性壁壘措施的目的和其強調的實質性區別“強制性”來理解,即使現行《TBT協定》在文本上并未將強制性標準歸入技術法規,也應當將強制性標準理解為技術法規。在我國入世談判期間,入世工作組成員就曾指出我國許多名為“標準”而實際具有強制性而應屬于“技術法規”的問題。[35]在面對工作組成員標準與技術法規混淆的質疑時,我國代表在入世工作組報告中表示我們會按照《TBT協定》對于“技術法規”與“標準”的界定來理解和遵守國際義務。[36]因此,我國標準談判組最后決定將我國強制性標準作為技術法規向各成員國通知,這一實踐受其他成員的認可。[37]當前,強制性標準仍然是我國履行《TBT協定》下通知義務的主要技術法規類型。
而另一方面,法學理論難以接受強制性標準與技術法規相等同。首先,作為一項標準,其性質、制定主體及制定程序與技術法規有明顯的區別。[38]其次,強制性標準制定權源為《標準化法》《強制性國家標準管理辦法》,有別于《立法法》中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等法規的制定權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強制性標準雖然與法律規范同樣具有規范性和強制實施效力,但不具有法律規則的所有必備要素。學界通常認為,法律規則的結構包括假定條件、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39]一般而言,強制性標準中包含假定條件與行為模式的要素。強制性標準文本中通常規定有該標準的適用范圍,規定了適用整體標準內容的前提條件,在具體規定中也有相應的適用條件。例如在國家標準《社會生活環境噪聲排放標準》(GB 22337-2008)中規定其適用對象為營業性文化娛樂場所、商業經營活動中使用的向環境排放噪聲的設備、設施,對這些對象進行管理、評價和控制時才由該標準的規則進行調整。其中4.1條區分了晝間與夜間不同功能區類別下社會生活噪聲排放源邊界噪聲不得超過的排放限值。同時,行為模式在強制性標準的規則中也必然存在。標準中的“指示”“要求”[40]表述了對于實施標準者應當如何行為的內容,例如上述規定不得超過邊界噪聲排放限值的要求。然而,強制性標準文本中缺失了一項法律規則的要素——法律后果。因為實施標準所帶來的科學技術性或社會性的效果并非法律后果,法律后果應該是法律對于實施該規范內容而進行法律評價的結果。因此,不能將強制性標準與技術法規混為一談。
那么解決《TBT協定》適用與法學理論之間概念分歧,還需厘清技術法規與強制性標準之間的關系。技術法規的法律規范屬性是法學界與標準化界的共識。正如國內外標準化界通用的概念——ISO和IEC對技術法規的定義,技術法規是指“規定技術要求的法規”,其中“法規”是指“由權力機關通過的有約束力的法律性文件。”[41]強制性標準僅有技術要求的內容,而缺失了構成一項法律規范的法律制定的權源及“法律后果”的必備要素。從這一意義上理解,技術法規與強制性標準的關系是:技術法規中的法律規范要求相關法律關系主體遵守特定義務,并借助強制性標準將這項義務具體化為特定技術規范內容,賦予強制性標準以強制實施效力,規定了遵守或違反強制性標準的法律后果來保障其技術規范內容的實施。
強制性標準與賦予其強制實施效力、規定有關法律后果的法律規范之結合,才是技術法規。在現行《標準化法》第2條中規定了“強制性標準必須執行”。這一條款規定了遵守強制性標準的義務,賦予“強制性標準”以強制實施效力。第25條規定“不符合強制性標準的產品、服務,不得生產、銷售、進口或者提供。”該條款表明了違反遵守強制性標準義務將不得生產、銷售、進口或者提供。在具體部門法中也規定了特定主體需要遵守相關標準的義務以及違反該項義務的法律后果。例如《食品安全法》第4條規定,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依照法律、法規和食品安全標準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第25條規定,食品安全標準是強制執行的標準。而在第63條、第64條等條款以及第九章法律責任中規定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將會承擔的民事、行政或刑事的法律后果。
強制性標準是具有強制實施效力的技術規范,而其效力來源于法律法規對于這類標準強制力的賦予。在《TBT協定》語境中將強制性標準理解為技術法規,仍需結合賦予其強制實施效力的法律規范。如果沒有法律規范中對于違反強制性標準法律后果的規定,其約束力便無從談起。由此看來,當各WTO成員通知其他成員這類受一般性法律賦予強制力的標準作為一類技術法規時,其實隱含了標準背后賦予強制力的法律法規。
四、影響成員技術法規內容的要求——基于相關國際標準制定
如上所述,《TBT協定》并非希望通過直接指定技術法規的內容以協調一致各成員的技術法規,而是希望在尊重各成員監管主權的情況下減少成員法規之間的差異。具體而言,《TBT協定》是借助第2條規定的三個方面的“倡導”和三項有約束力的“要求”使成員之間技術法規的內容更協調,避免成員不當地制造貿易壁壘和歧視;使成員技術法規的制定、實施過程更透明,便于成員就相關技術法規的爭議進行及時、有效的溝通。
《TBT協定》中“倡導”分別是:第一,成員充分參與技術法規所針對產品的國際標準的制定;第二,積極考慮其他成員的等效技術法規;第三,基于性能要求制定技術法規,而不是基于設計特征或描述性特征。這三方面的“倡導”對應了《TBT協定》第2.6-2.8條。盡管在理想化情況下,各WTO成員之間技術法規的相互承認(或者基本的技術要求的相互承認)是對國際貿易最友好的一種方式,但是這需要較大范圍地讓渡主權而顯然是不現實的。這三個條款的適用與否均取決于各成員自己的判斷,爭議解決機構不在這些方面考察其動機,因而這些條款是倡導性的,不具有強制約束力。
對成員技術法規具有約束力的三項“要求”包括:第一,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第二,不對國際貿易造成不必要限制,其中包括兩小項的要求:合法目的所必要、以國際標準為基礎;第三,透明性義務。這三者對WTO成員均有約束力,其他成員如果認為一成員違反這些要求可能會提出“特別貿易問題”,或者訴諸WTO爭議解決組織來解決。其中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合法目的所必要是《GATT協定》中就已經存在的要求。作為《TBT協定》的創新,正如上文關于《TBT協定》產生背景的闡述,技術法規以國際標準為基礎的義務以及透明性義務是理解《TBT協定》如何影響技術成員法規內容和制定程序的關鍵。其中,對成員技術法規的內容制定提出要求的是以國際標準為基礎的義務。
(一)要求成員技術法規以國際標準為基礎
通常而言,各成員自主制定或選擇采用技術法規中的技術規范內容,技術規范直接決定了技術法規立法目標的保護水平高低,也就決定著商品市場的經濟活力。如何選擇或制定技術規范一直屬于各成員域內監管權的決策范圍。然而,如果各成員選擇的技術規范異質性強,將帶來許多不利影響,因此《TBT協定》意圖通過國際標準的推行來解決各成員技術法規的不協調問題。國際標準是各類國際性的標準化組織在國際社會廣泛代表和參與下制定的,在技術方面形成國際統一標準。《TBT協定》推行國際標準將避免一成員因強制遵守或推行國際接受度低、難以兼容的標準而阻礙自由貿易、降低效率。[42]正如《TBT協定》序言中提到,“認識到國際標準和合格評定系統可以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和促進國際貿易的開展在這方面做出重要貢獻。”
《TBT協定》對成員制定的技術法規內容提出以下三方面的要求,這些要求促使成員在制定技術法規時將相關國際標準納入考慮范圍,乃至以此為首要選擇:
第一,要求成員技術法規以已經存在或即將擬就的國際標準為基礎。《TBT協定》第2.4條要求成員在制定技術法規時不僅要考慮已經存在的國際標準,還需要考慮正在協商中的國際標準。在新的國際標準出現或修改之后,成員也需要評估、修改已發布的技術法規中的技術標準。WTO上訴機構認為新制定的國際標準對已有的技術法規具有追溯力,這樣更有利于廣泛地統一各國國家標準,并且從該協定上下文來看:各成員在“制定、通過和適用”技術法規的全程(第2.5條)均需要遵守;如果一成員參與了國際標準化活動(2.6條)則意味著其對新國際標準是認可的。[43]
第二,技術法規如果符合相關國際標準則被推定為不會對國際貿易造成不必要限制。《TBT協定》第2.5條規定技術法規如果是為了第2.2條明確提及的合法目的之一制定、通過或適用,并且符合相關的國際標準,將推定不會對國際貿易造成不必要障礙。這一規定使得各成員為避免受到質疑而更愿意基于國際標準制定技術法規,因為這項推定在相關爭議中起著關鍵的作用。
第三,如果相關國際標準不存在,或者技術法規不符合相關國際標準的技術內容,則該成員負有通知其他成員、考慮其意見并為其留有足夠時間實施的義務,這些方面的要求屬于透明性義務的一部分。雖然《TBT協定》允許在成員認為國際標準對于其達到所追求的合法目標無效或不適當時適用其他標準,但通過增加上述透明性義務促使其更加謹慎地作出評估與選擇。
在《TBT協定》中,“國際標準”的概念沒有確定的范圍,在附件1中也沒有進行準確的定義。TBT委員會在2000年提出了符合“國際標準”制定的六項原則(透明、開放、中立和協商一致、有效和相關、統一、發展中國家利益關切),以此來確定該標準組織制定的標準是否屬于“國際標準”。[44]然而在歐共體沙丁魚案中,上訴機構否認TBT委員會提出的六項原則是有約束力的,認為這六項原則只是TBT委員會的“政策偏好的聲明”。結合上訴機構在歐共體沙丁魚案和美國金槍魚案(II)的觀點,可以得出:國際標準是以“在非歧視性的基礎上”向其他所有成員開放的從事標準化活動的機構所采用的標準,[45]但并不要求必須是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制定。上訴機構在沙丁魚案中的觀點與附件1.2的解釋保持一致,認為協商一致是并不總是能夠達成。即使沒有通過協商一致的方式達成,如果是國際標準化界公認的機構采用的標準也可以構成“國際標準”。[46]
(二)以國際標準為基礎的規則實效性和爭議
盡管上述規則具有一定約束力,但并不是絕對的。它仍然允許成員選擇或高于或低于國際標準的技術規范,只要相關國際標準對于技術法規所追求的目標是無效的或不適當的,留給成員自主選擇的空間。此外,由于國際標準的相對有限,在一些情況下沒有對應的國際標準可供參照和協調,自主制定的國家標準更有可能成為該國技術法規的技術規范內容。但國際標準作為協調成員技術法規的重要工具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TBT協定》所期望的效果。歐洲共同體委員會曾在《對外貿易政策與標準的通訊》中提到:“在一些領域難以偏離國際制定的規則和標準,即使存在這樣做的技術原因。”[47]
盡管以國際標準為基礎在WTO成員制定技術法規過程中占有重要的權重中,但它作為一種協調技術法規的解決方案仍然存在不少爭議。這些爭議圍繞的核心在于國際標準是否有正當性來解決各成員在法規層面協調的問題。國際標準無法充分代表各成員的利益,國際性標準化組織存在“民主赤字”,由于技術專家的“俱樂部心態”而缺少公共利益的代表。[48]TBT委員會試圖通過上述國際標準制定的六項原則解決這些問題,《TBT協定》第2.6條也建議各成員在資源允許的情況下充分參與與其技術法規相關產品的國際標準制定活動,通過在國際標準化中充分地獲取信息與積極參與,增強對相關國際標準的認可從而夯實其民主基礎。
五、貫穿技術法規制定與實施過程的要求——透明性義務
透明性義務是《TBT協定》的“基石”。透明性降低了國際貿易中進口國法規與政策信息的獲取與熟悉的成本和難度,有助于形成對于他國法律法規的合理、穩定的預期,[49]便于其他成員就涉及的問題進行溝通和協作。透明性有助于監督《TBT協定》義務的履行,充分信息為爭議解決建立了證據基礎,促進爭議解決機會的均等化。[50]透明性義務是WTO爭議解決機制的替代方案,因為成員之間如果能夠通過“特別貿易問題”就技術法規更充分地溝通和協商,就會避免多數問題成為正式爭議。[51]
透明性相關的規則要求WTO成員在制定、修訂技術法規的程序中,分別在法規制定期間和法規生效后,及時通知其他成員,其內容包括法規文本、制定目標與理由的說明、法規與國際標準偏離的信息等。
技術法規制定期間的透明性義務要求各成員在制定技術法規的最終決策完成之前,通知其他成員其技術法規措施草案,為其他成員政府開放了解、關注以及溝通的渠道,這也被稱為事前透明性義務。《TBT協定》第2.9-2.10條規定,當一成員制定技術法規,相關國際標準不存在或者與相關國際標準不符合,并且對其他成員貿易產生重大影響時,該成員應在制定早期通知各成員,簡要說明其目標和理由,盡可能提供實質上偏離國際標準的信息,并考慮其他成員的書面意見。如遇緊急問題則這一通知程序相對簡化,但仍然需要告知并考慮其他成員的意見。《TBT協定》不僅要求提供充分的法規信息,還要求技術法規的通知留給其他成員足夠的時間進行評論,如果供評論的時間有限將會削弱其他成員的利益。TBT委員會也提醒道,提交評論的時間不足可能會妨礙成員充分行使其提交評論的權利。因此委員會認為,對技術法規和合格評定程序提出意見的正常期限應為60天,并且應鼓勵任何能夠提供更長的提出意見期限(例如90天)。[52]事前透明性義務保證了受影響的國際貿易商可以通過其所在的政府在制定法規期間向對方政府提出意見,可供磋商的機制避免了未來可能產生的爭議。
法規生效后的透明性義務要求各成員在制定技術法規決策作出后,向其他成員提供法規要求、標準與合格評定認證的可用信息,以降低出口商在國際貿易中的獲取法律與政策的成本和難度,避免由信息不充分帶來的寒蟬效應,這也被稱為事后透明性義務。[53]《TBT協定》第2.5條、2.11-12條提供了法規信息公開的框架:一成員制定、通過或適用可能對其他成員的貿易產生重大影響的技術法規,應另一成員的要求,應根據第2至第4款的規定解釋該技術法規的理由;所有已通過的技術法規及時公布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以使其他成員的相關方能夠熟悉它們,在技術法規的公布與生效之間留出合理的間隔。透明性要求的信息充分通知與公布不能由法律法規的國內公布方式替代。美國曾在唯一的涉及《TBT協定》透明度義務上訴爭議案件——美國丁香煙案中辯稱其法律法規均是公開的,已經履行了相關透明性義務,但專家組否定了該意見并解釋第2.9.2條稱,公開信息不能替代“通過WTO秘書處告知其他成員其產品覆蓋范圍、目標和擬議技術法規的理由”。[54]上述事前事后的透明性義務均有助于各方在《TBT協定》建立的機制下進行充分信息溝通和就相關問題的磋商。
(責任編輯:周? 宇)
【基金項目】2021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基于法治、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技術法規研究”(項目編號:21&ZD192)。
【作者簡介】陳媛媛: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比較法學博士研究生。
[1]劉春青:《技術法規與自愿性標準的融合——美國政府高度重視利用標準化成果的啟示》,載《世界標準化與質量管理》2008年第
10期,第16~19頁。
[2]李玫:《歐盟技術法規體系的建設及對中國的啟示》,載《河北法學》2008年第4期,第160~162頁。
[3]《歐亞經濟聯盟條約》第51條第1款第3項、附件9第4條。
[4] ISO/IEC Guide 2:2004, 3.6.1.
[5]歐陽雨等:《中俄玩具技術法規比較分析》,載《檢驗檢疫學刊》2018年第2期,第35~36頁。
[6] 沈偉、秦真、蘆心玥:《霸權之后的大轉型:霸權之后的大轉型:中美貿易摩擦中的國際經貿規則分歧和重構》,載《海峽法學》20
22年第3期,第61~73頁。
[7] OECD/WTO,Facilitating Trade through Regulatory Co-operation:The Case of the WTOs TBT/SPS Agreements and Committees,
Paris:OECD(2019),p.9.
[8] Jacques Nusbaumer,The GATT Standards Code in Operation,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18:6(1984),pp. 549-552.
[9]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LT/TR/A/5,Apr.14,1979.
[10] R.W.Middleton,The GATT Standards Code,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14:3(1980),pp. 201-204.
[11] Rodolphe Muoz,TheTBT‘Agreement:A Perfect Tool to Monitor Regulatory Activities Worldwide,Cambridge Yearbook of
European Legal Studies 4,2001,pp. 273-292.
[12]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Apr.14,1979,LT/TR/A/5,ANNEX 1.1-1.2.
[13] WTO爭議解決機構的專家組通常會就是否構成《TBT協定》中“技術法規”的問題進行“三層審查”(three-tier test),上訴機構
也肯定了這一審查的合理性。“三層審查”分別是:1. 爭議措施是否適用于“可識別的”產品或產品組;2. 爭議措施規定了技術規范,即“產品特性或相關過程和生產方法”或者“關于適用于產品、工藝或生產方法的專業術語、符號、包裝、標志或標簽要求”。3. 爭議措施中的技術規范是否為強制性的。Report of Appellate Body, European Communities – Measures Affecting Asbestos and
Asbestos-Containing Products,WT/DS135/AB/R,12 March 2001,paras. 67-70;Report of Appellate Body,European Communities – Measures Prohibiting the Importation and Marketing of Seal Products, WT/DS400/AB/R, 22 May 2014, para.5.1.1.
[14]Report of Appellate Body,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Affecting Asbestos and Asbestos-Containing Products,WT/DS135/AB/R,
12 March 2001,para. 70.
[15]楊凱:《技術法規的基本觀念反思》,載《北方法學》2014年第4期,第99~102頁。
[16]郭濟環:《技術法規概念芻議》,載《科技與法律》2010年第2期,第10~13頁。
[17] DIRECTIVE(EU)2015/1535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9 September 2015 laying downa
procedure for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technical regulations and of rules on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OJL 214,17.9.2015,Article 1,1(f).
[18] Report of Appellate Body,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Affecting Asbestos and Asbestos-Containing Products,WT/DS135/AB/R,
12 March 2001,para. 67.
[19] Id.,para. 69.
[20] Id.,para. 71.
[21] Report of Appellate Body,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Prohibiting the Importation and Marketing of Seal Products,WT/
DS400/AB/R,22 May 2014,paras. 5.41,5.54-55.
[22] Id. para.5.42.
[23] Id.,para.5.12.
[24] Id.,paras.5.66-67.
[25]Jan McDonald,Domestic Regulation,International Standards,and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World Trade Review Vol.4:2(2005),
p. 256-257.
[26] 李冬冬:《TBT協定技術法規判定中的PPM問題研究》,載《國際經濟法學刊》2016年第3期,第36~37頁。
[27] Report of Appellate Body,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Concerning the Importation,Marketing and Sale of Tuna and Tuna
Products,16 May 2012,WT/DS381/AB/R,paras.183,199.
[28]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6th edn,A. Stevenson(ed.),Vol. 1,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 1694.
[29] Merriam Webster's Dictionary of Law, L.p.Wood (ed.)(Merriam-Webster Inc.), 1996, p. 304.
[30] Appellate Body Report,United States–Measures Concerning the Importation,Marketing and Sale of Tuna and Tuna Products,
WT/DS381/AB/R,13 June 2012, para. 185.
[31] Appellate Body Report,United States – Measures Concerning the Importation,Marketing and Sale of Tuna and Tuna Products,
WT/DS381/AB/R,13 June 2012,para. 188.
[32] Id.,para. 196.
[33] Arwel Davies,Technical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under the WTO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Legal Issu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Vol.41:1 (2014), p. 58–62.
[34]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LT/TR/A/5, Apr.14,1979,Annex 1,2.
[35] WTO Working Party report ON ACCESSION OF CHINA IN WTO,WT/ACC/CHN/49,1 October 2001,para. 181,https://www.
wto.org/english/thewto_e/acc_e/completeacc_e.htm.
[36] Id, para. 182.
[37]中國標準化研究院著:《標準是這樣煉成的:當代中國標準化的口述歷史》,中國質檢出版社、中國標準出版社2014年版,第87~88頁。
[38]劉春青等著:《國外強制性標準與技術法規研究》,中國質檢出版社、中國標準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5頁;另見何鷹:《強制
性標準的法律地位——司法裁判中的表達》,載《政法論壇》2010年第2期,第180~181、184~185頁。
[39] 付子堂主編:《法理學初階(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145頁。
[40] 根據GB 20000.1-2014,“指示”是指“表達應執行的行動的條款”;“要求”是指“表達需要滿足準則的條款”。
[41]上述國際標準ISO/IEC Guide 2:2004以及采用了該國際標準的國家標準GB 20000.1-2014均使用這一表述。
[42] Chairperson to the TBT Committee,TBT Committee Workshop 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19 March 2009, pp. 2-6.
[43] Michael M.Du,Reducing Product Standards Heterogeneity throug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the WTO:How Far across the River?,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44:2 (2010), pp. 299-300.
[44]TBT Committee,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on Principl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Guides and Recommendations
with Relation to Articles 2,5 and Annex 3 of the Agreement (2000),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bt_e/principles_standards_tbt_e.htm.
[45] Report of Appellate Body,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Concerning the Importation,Marketing and Sale of Tuna and
Tuna Products,WT/DS381/AB/R,16 May 2012,paras. 354-364,374-375.
[46] Appellate Body Report,European Communities–Trade Description of Sardines,WT/DS231/AB/R,26 September 2002,paras. 222-
223,227.
[47]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on Community External Trade Policy in the Field of Standards and ConformityAssessment,COM(96)
564,para. 19,referred from Michael M.Du,Reducing Product Standards Heterogeneity throug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the WTO:How Far across the River?,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44:2(2010),p. 312.
[48] Rob Van Gestel And Hans-W.Micklitz,European integration through standardization:How judicial review is breaking down the club
house of private standardization bodies,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Vol.50 (2013),pp. 148–150.
[49] OECD/WTO,Facilitating Trade through Regulatory Cooperation:The Case of the WTO's TBT/SPS Agreements and Committees,
OECD Publishing, Paris/WTO, Geneva, 2019, pp. 36-39.
[50] Marriana B. Karttunen,Transparency in the WTO SPS and TBT Agreements-The Real Jewel in the Crow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pp. 247-249.
[51] 根據WTO/TBT委員會的統計,自1995年至2022年4月28日,成員通過WTO秘書處完成的通知有45412項,成員提出的特別貿易
問題有746項。針對這些特別貿易問題提出的爭議57項,說明99%以上的問題已經通過特別貿易問題的溝通機制解決。參見WTO官網,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bt_e/tbt_e.htm,訪問時間:2022年9月30日。
[52]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Second Triennial Review of the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G/TBT/9,13 November 2000,para. 13,p. 22.
[53] Denise Prévost,Transparency obligations under the TBT Agreement,in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WTO and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3,pp.140-152.
[54] Panel Report,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Clove Cigarettes,WT/ DS406/R,adopted 24 April2012,
as modified by Appellate Body Report WT/DS406/AB/R,DSR 2012:XI,p.5865, at para. 7.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