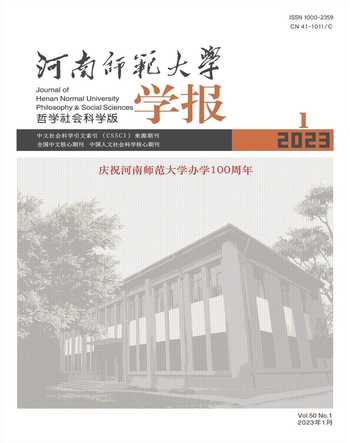論委任統治時期英國的巴勒斯坦猶太政策
李方恩 王皖強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3.01.12
摘要:對猶太人政策是英國在巴勒斯坦委任統治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該政策變遷過程中,丘吉爾發揮了重要作用。出任殖民大臣后,丘吉爾將英國在巴勒斯坦推行的“扶猶排阿”的政策進行了部分調整,減少了對猶太人的扶助。1922年,丘吉爾又通過政策白皮書將“扶猶排阿”政策調整為“抑猶壓阿”政策。二戰前夕,張伯倫政府在巴勒斯坦推行“限猶拉阿”的政策,該政策遭到丘吉爾的強烈抨擊。然而,丘吉爾出任首相后,卻大體上沿襲了他曾經強烈反對的政策。這些政策調整體現出英國在該地區強烈的功利性動機和突出的投機性策略。
關鍵詞:委任統治;英國巴勒斯坦猶太政策;丘吉爾
中圖分類號:K15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359(2023)01-0086-07收稿日期:2021-02-03
一戰之后,英國獲得了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權,從而在巴勒斯坦形成了互相博弈的三方:英國委任統治當局、猶太人、阿拉伯人。對于巴勒斯坦未來的發展,三方各有不同的甚至是沖突的計劃。英國委任統治當局為了維持自身的統治,不斷對該地區的政策進行調整。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對該地區政策的調整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丘吉爾一向以猶太文化的欣賞者、猶太民族不幸遭遇的同情者的形象示人,在現實之中,也一直和猶太方面保持著良好的溝通與交流,所以猶太方面對他進行了大力爭取,希望他能夠從政策層面給予猶太人更多的扶助。但是,丘吉爾對該政策的影響卻較為復雜。本文試圖在已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探索這一問題 Oskar K. Rabinowicz:Winston Churchill on Jewish Problem,Thomas Yoseloff LTD,1960;Martin Gilbert:Churchill and the Jews—a lifelong friendship,Newyork:2007;Michael Makovsky:Churchills Promised Land:Zionism and Statecraf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Cohen J Michael:Churchill And The Jews,London:Frank Cass,2003;岳昕燦:《丘吉爾與一戰后英國中東殖民政策研究》,北京大學歷史學系2018年碩士論文。。
一、丘吉爾對“扶猶排阿”政策的調整
勞合·喬治(Lloyd George)政府通過《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在巴勒斯坦推行“扶猶排阿” 肖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97頁。的政策。該政策在幫助英國在巴勒斯坦站穩腳跟的同時,也加劇了當地的混亂。丘吉爾則從實踐出發,認為“扶猶”應設限,“排阿”不可取,他試圖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阿猶雙方都能接受的政治框架,實現阿拉伯-猶太共存共生 Warren Dockter, Churchill and the Islamic World, London:I.B.Tauis & Co.Ltd, 2015, p144.。
1917年,英國政府發布《貝爾福宣言》,表示“英國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家園,并要盡力促使這個目標的實現,但是必須要清楚的是,絕對不能使目前巴勒斯坦非猶太人社團的公民權利或者宗教權利受到損害,也不能損害其他國家猶太人所享有的權利和地位” 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Palestine Mandate,London:1939,p7.。這是世界主要大國首次正式表示支持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標志著英國將要在巴勒斯坦推行“扶猶排阿”政策。該宣言發布前,英方并沒有與阿拉伯方面進行協商,并且一度不允許該宣言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中傳播。為了在支持猶太人的同時給自己留下回旋余地,《貝爾福宣言》對于一些關鍵問題,如巴勒斯坦的主權問題 一戰時期,英國為了鼓動阿拉伯人的政教領袖侯賽因·伊本·阿里反抗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答應他在戰后建立一個獨立的阿拉伯國家。1915年7月14日,侯賽因致信英國駐開羅高級專員麥克馬洪,提出了這個阿拉伯國家的范圍,其中包括巴勒斯坦。麥克馬洪在對侯賽因提出的疆界進行了措辭模糊的修正后接受。然而,就在阿拉伯人與奧斯曼土耳其進行激烈戰斗之際,1916年5月,英國卻和法國簽署了瓜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領土的《賽克斯—皮科協議》,其中規定巴勒斯坦屬于國際共管地區。在《貝爾福宣言》之中,英方又向猶太方面許諾,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猶太民族家園”。和兩個民族的地位問題,或回避或語焉不詳,這就為后來巴勒斯坦的混亂局勢埋下了伏筆。之后,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力量迅速發展壯大,阿拉伯人則對此非常不滿。1920年2月27日,耶路撒冷爆發了第一次阿拉伯人反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大規模游行。此后,阿拉伯人方面又進行了多次示威游行。
丘吉爾于1921年2月出任喬治政府的英國殖民大臣。雖然丘吉爾與喬治私交甚篤,但是兩人在許多問題上都有不同意見,其中包括對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政策問題。《貝爾福宣言》頒布后,丘吉爾沒有發表過公開的評論。但是在1919年10月提交給喬治的一份備忘錄中,丘吉爾認為,英國贊助猶太復國主義將會帶來麻煩,因為猶太人將會認為英國在巴勒斯坦扶助他們是理所應當的。1920年6月,丘吉爾又對喬治表示在巴勒斯坦的冒險恐怕會得不償失,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將會引發持續的摩擦 Michael J. Cohen,Palestine to Israel : from Mandate to Independence,London, F. Cass, 1988,p1.。出任殖民大臣后,在考慮到當時巴勒斯坦的形勢與一戰后英國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后,丘吉爾認為必須對《貝爾福宣言》所確定的“扶猶排阿”政策進行調整,目的是減輕使阿拉伯方面對《貝爾福宣言》的敵意,保持巴勒斯坦的穩定,以便使英國能夠減少在當地的駐軍,節省開支。
丘吉爾對英國巴勒斯坦猶太政策的調整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丘吉爾對巴勒斯坦實施分而治之的策略。1921年3月12日,丘吉爾在開羅組織了一次會議,匯集了40位英國中東政策的專家,并戲稱他們為“四十大盜” Michael Makovsky,Churchills Promised Land Zionism and Statecraf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p111.。會議主要討論削減英國在中東地區的駐軍、扶植阿拉伯領導人等問題。丘吉爾等人所主張的是“謝里夫解決方案”(Sherifian Solution) Commons Sitting of 14 June 1921 Series 5 Vol. 143 HANSARD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921/jun/14/middle-eastern-services 2021.6.6.,該方案的目的是將英國的直接統治轉換為扶植親英政權,將權力授予哈希姆家族(Banu Hashim) 哈希姆家族是中東地區的名門望族之一,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便是出自這個家族。該家族世代居住于伊斯蘭教圣地麥加,擁有“謝里夫”(阿拉伯語“圣裔”“貴人”的含義)的稱號。一戰前后,英國對該家族進行了大力爭取,使之出現了親英的傾向。,哈希姆家族的族長謝里夫·侯賽因(Sharif Hussein)將成為漢志國王,并將駐扎在麥加;扶植他的兒子費薩爾·伊本·侯賽因(Faisal Ibn Hussein)在美索不達米亞,也就是后來的伊拉克建立統治;另一個兒子阿卜杜拉·伊本·侯賽因(Abdullah lbn Hussein)則控制約旦河以東的巴勒斯坦,也就是外約旦,英國提供一定的援助。約旦河以西則由英國統治,逐漸落實《貝爾福宣言》,建立“猶太民族家園”。這一方案將巴勒斯坦75%的區域劃歸了阿拉伯方面。
其次,丘吉爾只是對《貝爾福宣言》的適用范圍作出了調整,對其基本內容則加以維護。1921年3月28日,丘吉爾收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領袖穆薩·卡茲姆·侯賽尼(Musa Kazem al-Husseini)遞交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對《貝爾福宣言》進行了強烈批判并提出:“第一,取消猶太人民族家園;第二,建立一個民選政府,該政府要向巴勒斯坦人民選出的議會負責;第三,在民選政府成立之前,禁止猶太移民;第四,英國巴勒斯坦當局應當執行一戰前當地的法律和條例,廢除所有其他的法律和條例,在民選政府成立之前,不得制定新的法律;第五,不能將巴勒斯坦從他的阿拉伯兄弟之中分離出去。” Official Reports of Deputation of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Haifa Congress, CHAR/8/260 Page77-82,The Churchill Archive.在回復中,對于阿拉伯方面否認《貝爾福宣言》,取消“猶太民族家園”的要求,丘吉爾表示:“我無權這樣做,這一宣言已得到勝利的盟國的批準。因此,它必須被視為一個由偉大戰爭的勝利所確定的事實。”丘吉爾提醒穆薩“注意宣言第二部分,該部分莊嚴而明確地向巴勒斯坦居民承諾,他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將得到最充分的保護”。此外,丘吉爾還特意向阿拉伯人強調英國為巴勒斯坦付出的代價:“我聽到你的發言,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似乎推翻了土耳其政府,那與事實相反。是英國軍隊解放了這些地區。你在路上可以看到2000多名英國士兵的墓地。” Reply by Mr. Churchill,CHAR/8/260 Page82,The Churchill Archive.丘吉爾認為,英國人作為巴勒斯坦的“解放者”,有資格對巴勒斯坦的發展方向進行干預。丘吉爾在給同時送來的猶太方面備忘錄的回復中,也保證英國將繼續落實《貝爾福宣言》 Mr. Churchills Reply, CHAR/8/260 Page84,The Churchill Archive.。英國人在一戰后,正是打著扶助猶太人的旗號進入巴勒斯坦的,所以,英方決不能放棄該宣言。
再次,丘吉爾對《貝爾福宣言》之中一些措辭模糊的核心概念進行了初步的界定,對阿拉伯方面的一些擔心和要求也開始作出回應。關于“猶太民族家園”的性質,丘吉爾表示:“巴勒斯坦將包含一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并不意味著它將不再是其他人的家園,也不意味著將建立一個猶太政府來統治阿拉伯人民。” Reply by Mr. Churchill,CHAR/8/260 Page82,The Churchill Archive.在給猶太方面備忘錄的回應中,丘吉爾也表示,英方將確保對各方的公平。在回應阿拉伯方面對于猶太人的發展會影響他們的利益時,丘吉爾表示英國政府將會力保公平公正,同時,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發展將會對整個地區都有好處。關于阿拉伯人建立民選政府的要求,丘吉爾的回應是:“目前的政府形式將持續多年,我們將逐步發展代表性機構,直至完全自治。”最后,丘吉爾倡導雙方的合作:“猶太人在每一個階段都需要阿拉伯人的幫助,我認為你們應該給予他們幫助和指導,并鼓勵他們克服困難。這種成功將增進巴勒斯坦所有居民的財富和福祉。” Reply by Mr. Churchill,CHAR/8/260 Page83,The Churchill Archive.同時,丘吉爾也希望猶太方面與阿拉伯方面多進行溝通,打消他們的恐懼與疑慮。
總之,在開羅會議上,丘吉爾對英國“扶猶排阿”的政策作出了調整,將猶太人發展限制在約旦河以西,同時,其執行《貝爾福宣言》的態度又是比較明確的。所以,在約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猶太移民不斷增加,“猶太民族家園”也有了較大的發展。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方面對丘吉爾的政策調整非常不滿意,他們不打算做出任何讓步。1921年5月1日,在雅法爆發了阿拉伯人反對猶太移民的暴力活動,雙方發生了激烈的沖突,造成95人死亡,220人受傷。此后,暴力活動蔓延到整個巴勒斯坦地區,又造成了更多的傷亡 Martin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Ⅳ,Boston : Houghton Mifflin Co.,1971—1975,p.585.。壓力之下,英國當局暫時停止執行《貝爾福宣言》。對此,猶太方面進行了強烈譴責,一些極端分子開始組織非法移民,巴勒斯坦的形勢日趨惡化。與此同時,阿拉伯和猶太雙方都派出代表團來到倫敦,不斷向英國政府陳述己見,這使得英國政府感到有必要推出新的政策,以穩定形勢。
二、《丘吉爾白皮書》確定“抑猶壓阿”的政策
1922年7月1日,丘吉爾發布了一項政策聲明,就是后來通稱的《丘吉爾白皮書》。《丘吉爾白皮書》是英國進入巴勒斯坦地區之后所發布的第一份全面的政策宣言。在《貝爾福宣言》和《丘吉爾白皮書》的基礎上,7月24日,國聯正式通過了確認英國在巴勒斯坦進行委任統治的條款。《丘吉爾白皮書》正式將“扶猶排阿”政策調整為“抑猶壓阿”的平衡政策。
該白皮書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白皮書對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各自最主要的關切進行回應,可以看作“抑猶壓阿”政策出臺的背景。當時,阿拉伯方面主要擔心將來巴勒斯坦會被猶太人控制,而猶太人則擔憂英國將放棄《貝爾福宣言》。白皮書首先表示阿拉伯方面沒有很好地理解《貝爾福宣言》:“就阿拉伯人而言,這些擔憂部分是基于對1917年11月2日宣言的含義的夸張解釋。有人發表了未經授權的聲明,大意是建立一個完全猶太化的巴勒斯坦。英國政府認為任何這樣的期望都是不切實際的,也沒有這樣的目標。”對猶太方面的擔心,白皮書明確表示:“就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而言,其中有些人似乎擔心國王陛下的政府可能會背離1917年《宣言》所體現的政策。因此,有必要再次申明,這些擔心是沒有根據的。”
白皮書的第二部分是主體,對一些核心概念與關鍵問題進行正式闡述,為“抑猶壓阿”的平衡政策奠定基礎。白皮書首先解釋了“猶太民族家園”的必要性:“猶太民族家園在巴勒斯坦是理所當然的,而不是被容忍的。”白皮書認為猶太人天然具有在巴勒斯坦存在的合法性,而不是要靠哪一方的恩賜。這實際上是要壓阿拉伯人接受既定事實。關于“猶太民族家園”的含義,白皮書表示它“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猶太人的幫助下,進一步發展現有的猶太社區,以便使它成為一個中心,使這里的猶太人民能夠因其宗教和種族而感到驕傲” The Churchill White Paper,https://www.un.org/unispal/document/auto-insert-202945/2021.6.6.。也就是說,“猶太民族家園”不是一個猶太國家,只是一個文化宗教中心。這與猶太方面的期待有很大的不同,也和勞合·喬治、貝爾福等人的設想不同。其次,猶太移民數量的問題。對于該問題,白皮書表示:“移民的數量不能大到超過該地區當時吸收新移民的經濟能力。必須確保移民不應成為整個巴勒斯坦人民的負擔,他們不應剝奪目前人口的任何部分的就業機會……還必須確保將政治上不受歡迎的人排除在巴勒斯坦之外,行政當局已經并將為此采取一切預防措施。”這種表態可以視作對阿拉伯人的一種承諾,對猶太人的一種限制,即猶太移民不能超過當地的容納能力,不能影響阿拉伯人的就業。不過,這種許諾仍然比較模糊,沒有設定猶太移民的上限。再次,關于猶太人機構的地位問題,白皮書表示:“巴勒斯坦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不應該擁有該國一般行政管理的任何份額……本組織可以協助該國的總體發展,但無權在任何程度上參與其政府。”巴勒斯坦猶太人的各種機構都只是自治機構。相應的,阿拉伯方面也將具備類似的機構,“現政府已經將穆斯林宗教基金和穆斯林宗教法庭的全部控制權移交給由巴勒斯坦穆斯林社區選出的最高委員會”。最后,關于阿猶兩個民族的法律地位,白皮書的表述是:“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所有巴勒斯坦公民的地位都是巴勒斯坦人,從來沒有打算讓他們或他們的任何部分擁有任何其他法律地位。”也就是說,兩個民族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表面公平的言辭下,暗含了對阿拉伯方面的壓制,即讓世代居住于此,且人口處于絕對優勢的阿拉伯人與移居此地時間較短且處于人口絕對劣勢的猶太人處于法律上相同的地位。
白皮書的第三部分,展望了這種“抑猶壓阿”平衡政策的前景。白皮書首先解釋了沒有將巴勒斯坦全部交給阿拉伯方面的原因,即約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不包括在侯賽因-麥克馬洪通信(Hussein-McMahon Correspondence)之中:“這一陳述主要基于1915年10月24日亨利·麥克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給麥加謝里夫(Sharif of Mecca)的一封信。這封信被看作一個承諾,承認并支持阿拉伯人在他提議的領土內的獨立。但這一承諾是在同一封信中作出保留的前提下作出的。約旦河以西的整個巴勒斯坦被排除在麥克馬洪爵士的承諾之外。”因此,“國王陛下政府的意圖是促進在巴勒斯坦建立全面的自治政府”。其次,白皮書給出了這個自治政府的發展路線圖:全面的自治政府“應逐步完成,而不是突然完成。第一步是在民政管理體制方面,設立了目前已經存在的被提名咨詢委員會。第二步,即建立一個立法委員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成員是在廣泛的選舉中選出的。屆時,立法會將由高級專員擔任主席,12名當選議員和10名正式議員組成。在進一步的自治措施擴大到巴勒斯坦和議會控制的行政當局之前,明智的做法是留出一段時間。幾年后,情況將再次得到審查,如果狀況很好,那么將把更大的權力分配給民選代表”。不過,白皮書沒有給出自治政府建立的時間表。再次,關于英國政府所起作用的問題,按照白皮書的表述,英國政府將起到一種仲裁者的作用,成為巴勒斯坦委任統治當局之上的最終決策者。
對于這份白皮書,猶太方面比較失望。相比于《貝爾福宣言》,《丘吉爾白皮書》對猶太人的承諾大大縮水了。白皮書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指出了猶太民族家園的含義,即只能是一個文化與宗教中心,而他們的最終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國家。白皮書之中移民不能超過當地吸收移民能力的說法也將成為阿拉伯人反對猶太移民的有力武器。對于白皮書建立民選代表組成議會的建議,他們也表示反對,因為顯而易見,如果按照人口比例進行選舉,在這個議會之中,阿拉伯人會占明顯的優勢。不過,在這個白皮書出臺后,猶太人團體的合法地位被再次確認,猶太移民又可以合法地進行了,這實際上是繼續推行《貝爾福宣言》,并要求阿拉伯人接受之。從實踐上看,發展到后來,“無論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方面看,還是從武裝力量方面看,猶太民族家園完全是一個國家的雛形” 李平民:《英國的分而治之與阿以沖突的根源》,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第220頁。。再者,英國當局所面臨的阿拉伯人的壓力也是顯而易見的。早在1921年9月,魏茲曼就曾經在一次會議上表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目前處于困境,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與阿拉伯人和解。” Bernard Wasserstein,The British in Palestine : the mandatory government and Arab-Jewish conflict, 1917-1929 ,Oxford,B. Blackwell,p135.也就是說,《丘吉爾白皮書》已經是英方在當時的條件下所能夠給猶太方面最好的方案了。所以,猶太方面在進行了激辯之后接受了這項新政策。
阿拉伯方面對《丘吉爾白皮書》則是一種明確拒絕的態度。他們否定《貝爾福宣言》,不準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設“民族家園”,不打算接受任何以《貝爾福宣言》為基礎的方案。對于白皮書關于巴勒斯坦地區不應該劃歸阿拉伯人的解釋,阿拉伯方面認為英方是在進行狡辯。阿拉伯人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獨立完整的阿拉伯國家,猶太人在其中只能算作一個少數民族,沒有任何特殊權利。當然,阿拉伯方面也很清楚,在己方的壓力之下,《丘吉爾白皮書》對猶太人勢力的擴張已經進行了限制,這是對英國傾向于扶助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政策的明顯調整,說明英國人已經無法繼續回避對巴勒斯坦地區“非猶太人”的責任,必須作出公開的回應與保證。
雖然雙方都對該白皮書不滿意,但是從實踐來看,在《丘吉爾白皮書》的影響下,之后的幾年內阿猶雙方的沖突暫時得到了緩解。此后,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移民人數大為增加。據統計,1919年至1923年的猶太移民人數是34183人,而1924至1926年的猶太移民人數就達到了62133人 W. Preuss,The Economic Effects of Jewish Immigration in Palestine,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64,(Nov. 1932):pp108-115.。相形之下,該白皮書對猶太方面更為有利。事實上,“抑猶壓阿”的政策之中,“抑猶”只是意味著英方對猶太方面的扶助不再大張旗鼓,而“壓阿”則是實實在在的。
總體而言,《丘吉爾白皮書》對于緊張局勢的緩解產生了一定的作用。該白皮書回答了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其宗旨是要以“抑猶壓阿”的政策實現阿猶分治之下的平衡發展。這樣的政策既是為了平息巴勒斯坦地區阿拉伯人的憤怒情緒、化解猶太方面的不安心理,也是為了英國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能夠順利地進行。但是《丘吉爾白皮書》的弊端也十分明顯:首先,該白皮書“權宜之計”的色彩明顯,并沒有打算解決引發雙方矛盾沖突的移民問題與雙方政治關系問題,所給出的巴勒斯坦的全面自治也遙遙無期。其次,從實施后果看,在這種政策的作用之下,巴勒斯坦地區逐漸形成了英國統治之下兩個互相疏離的集團,且兩個集團都對英國當局的政策不滿意,這就為雙方矛盾的繼續發展和英國委任統治的最終崩潰,乃至后來委任統治結束后巴勒斯坦地區的亂局埋下了伏筆。再次,在白皮書的影響之下,此后英國在該地區歷次的政策調整,大都帶有“權宜之計”的特點。也就是說,英國從未打算在詳細研究當地的歷史與現狀的基礎上,為巴勒斯坦地區設計一個可持續的發展框架,而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通過投機性的策略,對巴勒斯坦的各派進行拉攏或壓制,維持一種殖民地色彩濃厚的英式平衡。其結果則進一步造成各派對英國統治的離心力,使得英國維持委任統治的難度日益加大。
在該政策推行的過程中,丘吉爾的個人傾向也發揮了一些作用。從丘吉爾個人來說,他對巴勒斯坦阿猶雙方的感受差別明顯。除了文化方面的好感之外,他還認為,猶太人定居點的發展繁榮,推動了當地文明的發展,在一段時間內對英帝國有利,所以他樂見猶太方面的力量在巴勒斯坦的增長,但是他不能公開這些態度。在1921年5月騷亂之后,巴勒斯坦猶太人的地下武裝“哈加納”(Haganah)迅速發展了起來,丘吉爾曾經對魏茲曼說:“我們不反對它,但也不談論它。” 李平民:《英國的分而治之與阿以沖突的根源》,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第220頁。丘吉爾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態度則比較消極,在他的眼中,大部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區貧瘠落后,與猶太人定居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此外,作為一個典型的歐洲政治家,丘吉爾很善于做多方面的協調工作,講究讓步與妥協。然而他在和巴勒斯坦阿拉伯方面打交道的過程中,卻發現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打算做出任何讓步,這令丘吉爾既惱火又無奈。
三、丘吉爾對“限猶拉阿”政策的反對與執行
1937年5月,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成為英國首相。當時的世界形勢日趨緊張,張伯倫政府出于種種考慮,對外推行綏靖政策。在巴勒斯坦地區,這種綏靖政策表現為“限猶拉阿” 劉中民:《從阿拉伯民族主義到巴勒斯坦民族主義:20世紀上半葉巴勒斯坦地區民族主義的發展與轉型》,《西亞非洲》,2011年第7期。。丘吉爾對此進行了激烈的抨擊。
20世紀30年代后期,在全球和平遭遇嚴重挑戰之下,巴勒斯坦的局勢讓英國政府非常憂心。巴勒斯坦的戰略地位重要,能夠直接影響到埃及的安全,而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巴勒斯坦地區阿猶沖突頻繁發生,令英國頗感頭疼。而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勢力已經在利用英阿矛盾來爭取阿拉伯人。因此,英國當局對之前“抑猶壓阿”的政策進行了較大的調整。1939年5月17日,英國殖民大臣麥克唐納(Malcolm MacDonald)發布了《關于巴勒斯坦問題的白皮書》,史稱《麥克唐納白皮書》。白皮書聲稱,在未來的10年之中,英王陛下政府將要在巴勒斯坦成立一個雙民族的、與英國有聯系的政府。未來的5年之中只允許75000名猶太移民進入巴勒斯坦。這之后,猶太方面再向該地區移民必須經過阿拉伯人的同意。關于巴勒斯坦的土地問題,白皮書規定,某些地區完全不得建立新的猶太人居住區,其他地方則進行嚴格的審查和限制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ummary of British White Paper,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 Vol. 16, No. 11 (Jun. 3, 1939):pp7-10.。該白皮書標志著英國政府正式放棄“抑猶壓阿”,轉而實行“限猶拉阿”政策。
丘吉爾在1939年5月23日的議會辯論中對此進行了激烈的抨擊。首先,丘吉爾在《麥克唐納白皮書》中明顯看出來英國針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綏靖政策的傾向。他表示:“我們的潛在敵人會怎么想呢?那些煽動阿拉伯人的人會怎么想?他們會不會忍不住說:‘他們又在逃亡了。這是另一個慕尼黑。”丘吉爾認為,對阿拉伯人的退讓不僅不會讓他們滿意,反而會促使他們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當地的猶太人也會進行激烈的反對,這將會導致英國付出更大的代價。
其次,丘吉爾認為這是對《貝爾福宣言》的違背。丘吉爾說:“《貝爾福宣言》不是給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的,它是給世界猶太人的。正是由于這一承諾,并在此基礎上,我們在戰爭中得到了重要的幫助。也正因為如此,在戰爭結束后,我們得到了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權。” Commons Sitting of 23 May 1939 Series 5 Vol. 347,HANSARD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939/may/23/palestine 2019-10-10.這就是說,《貝爾福宣言》不僅僅是對猶太人的一種許諾,更是一戰之后,英國獲得巴勒斯坦委任統治權的一個重要基礎,如果拋開《貝爾福宣言》,則英國在巴勒斯坦的統治合法性就出了問題,其統治將會遭遇更多的挑戰。
再次,丘吉爾認為這個白皮書只顧爭取阿拉伯人,忽視了猶太人在建設巴勒斯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早在1921年6月,丘吉爾在參訪過巴勒斯坦地區后就公開表示:“任何一個目睹過巴勒斯坦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所建立的定居點的人,都會被他們豐富的成就所震驚,在看到這么多成果之后,無論誰說英國政府可以無視它,允許它被阿拉伯居民摧毀,我都不能同意。” Anne Murray,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and the Middle East:discourse and disside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151.在這次議會發言中,丘吉爾進一步表示:“他們已經開始了幾十個蓬勃發展的行業。他們在貧瘠的海岸上建立了一座大城市。他們治理約旦河,把約旦河的電力分散到全國各地。阿拉伯人非但沒有受到迫害,反而蜂擁而至,成倍增長。”而按照《麥克唐納白皮書》的限制,丘吉爾認為這一切將會中止,中東地區文明的發展會因此而緩慢下來,這是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最后,基于丘吉爾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一向的同情,以及他對英帝國顏面的考慮,他認為這樣做道義上也是說不過去的,這種背信棄義的做法將會使得英國在全世界面前丟臉。他直接引用張伯倫的原話來表達自己的憤怒:“我尊敬的朋友(張伯倫)在20年前曾說過這樣激動人心的話:‘猶太復國主義者將承擔更大的責任,他們不久將懷著喜悅的心情前往他們人民的古老之地。他們的任務是在長期被忽視和被暴政所統治的古老圣地建設一個新的繁榮昌盛的巴勒斯坦。他們正朝著他們的希望前進。我們怎么能夠給這種可貴的精神以沉重一擊呢?” Commons Sitting of 23 May 1939 Series 5 Vol. 347,HANSARD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939/may/23/palestine 2019-10-10.
丘吉爾對《麥克唐納白皮書》的批判非常契合猶太方面的理念。魏茲曼致信丘吉爾,對他表示了感謝:“您精彩的言論足以摧毀這項政策。任何言語都不足以表達我對您的感激之情。” Chaim Weizmann,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Series A: Letters,vol 19,London:Oxford U.P,1968-1980,p88.當然,這種表態也暗含著對丘吉爾的一種期望:等到丘吉爾有足夠的力量時,應廢除這份白皮書。猶太方面認為這一期許“變現”的可能性極大。然而,英國政府之所以作出這種完全背離之前政策的調整,自然有其利益考量。英國當局認為,在巴勒斯坦的局勢日益緊張之際,不列顛更加需要阿拉伯人的友誼,而不是猶太人一以貫之的善意。與更具“議價”資質的阿拉伯人不一樣,猶太人絕無可能選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此外,英國還希望以此緩和巴勒斯坦的局勢,以便能從巴勒斯坦抽調出部分力量來應對歐洲的局勢。基于以上的考慮,《麥克唐納白皮書》的出臺,對于英國方面而言就順理成章了。
該白皮書的用意在于削弱巴勒斯坦猶太人的地位,緩和阿拉伯人的敵意。所以,它甫一公布,立刻引起了猶太人的強烈反對。對這一點,麥克唐納本人早有預料。1939年白皮書發表后不久,記者杜德爾夫人(Mrs Dugdale)在采訪了麥克唐納之后談道:“我說他摧毀了我們對猶太人的忠誠,毀了英國公正的名字時,他把胳膊放在桌子上,囁嚅著說:‘我都想到了。” Cohen J Michael,Palestine to Israel:From Mandate to Independence,Totowa,N.J,F.Cass,c1988.p49.這個白皮書實際上是對《貝爾福宣言》和《丘吉爾白皮書》的否定。這對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是個沉重的打擊。此外,當時法西斯正在歐洲瘋狂地迫害猶太人,許多猶太人都在想方設法,希望能逃出歐洲前往巴勒斯坦,而這個白皮書一出,就基本上把歐洲猶太人逃往巴勒斯坦的大門關閉了起來。
1940年5月10日,丘吉爾出任英國首相。猶太方面立即呼吁丘吉爾進行干預,廢除這個白皮書。當時魏茲曼曾經就此多方爭取丘吉爾 Norman Rose,Chaim Weizmann:A Biography, New York:Viking Penguin inc,1986,p357.。然而,令猶太方面失望的是,丘吉爾并沒有呼應猶太方面的要求。其中包含著他的政治邏輯:在成為英國的首相之后,他所要考慮的問題,與最初他單純作為政策的批評者是不一樣的。在當時的情況下,“限猶拉阿”的政策最符合英國的戰略利益,因此,不論誰出任英國首相,也不管他是不是同情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都不可能對這個政策作出大的調整。如果丘吉爾僅從道義出發,對《麥克唐納白皮書》進行修改,那將會激怒阿拉伯人,他們或許會倒向軸心國陣營,英國就會面臨失去中東的危險。因此,當他受到了來自猶太人團體不斷的批評時,一向能言善辯的丘吉爾卻沒有進行過公開的辯護。由此可見,當他僅僅處于旁觀者的角度對英國政府的巴勒斯坦猶太人政策進行評判時,其個人傾向體現得非常明顯。然而當他再次進入政治實踐領域,能夠對巴勒斯坦的局勢發揮實質性影響之時,他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以英國利益為出發點,沒有明顯受到其個人喜好的影響。
1943年4月,魏茲曼在給丘吉爾的一封信中非常失望地談道:“在議會關于巴勒斯坦的東歐猶太人的討論中,斯坦利先生(Oliver Stanley,時任殖民大臣)和克蘭伯恩勛爵(Lord Cranborne,時任外交副大臣)都認為1939年白皮書是國王陛下的政府在巴勒斯坦牢固樹立的政策。” Chaim Weizmann,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Series A: Letters,vol 21,London:Oxford U.P,1968-1980,p19.對此,丘吉爾還是沒有直接地回應,而是在不久后給斯坦利的信中談道:“關于1939年白皮書是政府牢固樹立的政策的說法我不能同意,我認為他是前任留下來的政策。在此問題上,將不宣布新的聲明,它將運行到被替代為止。我個人的立場還是此前我在議會辯論時所闡明的那樣。” Oskar K. Rabinowicz,Winston Churchill on Jewish Problem. New York and London:Thomas Yoseloff LTD, 1960,p110.從這一表態之中不難看出,最初丘吉爾對于《麥克唐納白皮書》的激烈抨擊,是主要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和道義上的考量,還夾雜著不少個人感情因素。當時,丘吉爾只是一個下院議員,所以,在他發表這些見解時不用考慮太多,并且,這種反對也只是停留在口頭上。一旦進入實踐,作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丘吉爾又開始自動地尋求英帝國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猶太方面非常失望而且憤怒地發現,在整個二戰時期,英國當局一直都在執行《麥克唐納白皮書》所確定的“限猶拉阿”的政策。這就為二戰之后猶太方面和英國決裂埋下了伏筆。
相比之下,阿拉伯方面則對《麥克唐納白皮書》持歡迎態度。一些阿拉伯政治家,如阿拉伯獨立黨的領導人阿卜杜勒·哈迪和艾哈邁德·希勒米甚至公開呼吁阿拉伯最高委員會接受這一白皮書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139頁。。英方為了進一步拉攏阿拉伯人,還將一些被英方拘禁的阿拉伯政治家釋放。一時間,原本非常緊張的英阿關系得到了明顯的改善。然而,當1940年6月伊拉克首相拉希德·阿里提議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阿拉伯國家時,卻被丘吉爾政府斷然拒絕。
二戰時期,猶太人在嘗試推動丘吉爾修改“限猶拉阿”政策的同時,還希望丘吉爾能夠正式宣布一個方案,為二戰后的巴勒斯坦猶太人明確地位。事實上,丘吉爾心中對此也有想法,即巴以分治計劃。于是二戰期間,猶太人在反復地追問一個問題:既然如此,那為什么他不通過一個明確的政策,來為猶太人將來的地位奠定基礎呢?這樣一來,各方面也就沒有必要再對猶太移民進行限制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將免遭納粹的迫害。可是,丘吉爾始終沒有這樣做。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在丘吉爾看來,那必然會影響主要目的的達成。由此看來,當時丘吉爾的巴勒斯坦猶太政策由三個因素決定:他只專注于快速贏得戰爭的勝利;他堅持不承諾關于未來的任何明確的措施;因為戰爭正在進行,所以無法充分處理戰后問題。出于這些考慮,丘吉爾擱置了猶太人建國的要求。
丘吉爾所堅持的“限猶拉阿”政策對確保其實現主要戰略目標作出了貢獻,但是也造成英猶關系的日益緊張。猶太方面的一些極端分子開始不斷策劃針對英國人的恐怖活動,其登峰造極的標志就是1944年11月6日,丘吉爾的密友、英國中東事務大臣莫因勛爵在開羅街頭被猶太極端分子暗殺。丘吉爾對此非常憤怒,他表示:“如果我們的猶太復國主義夢想在刺客手槍的戰爭硝煙中告終,如果我們的努力只產生一批類似于納粹的新黑幫分子,那么像我這樣的許多人將不得不重新考慮我們一貫和長期保持的立場。” Michael Makovsky,Churchills Promised Land Zionism and Statecraf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p217.此后,英國巴勒斯坦委任統治當局不再履行任何扶助猶太人的義務,英猶關系逐步走向破裂。二戰之后,英國對巴勒斯坦亂局越來越力不從心,再加之美國、蘇聯等的介入,最終,英國退出了巴勒斯坦。
從丘吉爾對政策調整的角度來看英國委任統治時期巴勒斯坦猶太政策,我們不難看清該政策強烈的功利性動機和突出的投機性策略,巴勒斯坦英國委任統治當局在“扶猶”“限猶”“壓阿”“拉阿”之間搖擺不定,前后矛盾,導致猶太方面與英方漸行漸遠,甚至到最后兵戎相見。而阿拉伯方面,則始終對英國無法信任:英國人為了換取阿拉伯人的支持,在一戰前許諾要讓阿拉伯人建立統一獨立的國家,結果戰后英國人將敘利亞給了法國,又將巴勒斯坦許給了猶太人。當他們提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阿拉伯國家時,卻被英國政府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在他們的心目中,英國人的信譽早就破產了。總之,英方希望通過投機性的策略,對阿猶雙方時壓時拉,既不讓猶太人建國,也不讓阿拉伯人達成目的,從而確保自己對巴勒斯坦的控制。雖然這種政策曾短時間內奏效,但卻使得本就有著復雜的歷史與現實的巴勒斯坦的局勢更加錯綜復雜,英國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也逐漸陷入泥淖之中無法自拔,最終不得不狼狽地退出了巴勒斯坦。
On Britains Palestinian Jewish Policy During the Mandate Perio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urchills Policy Adjustment
Li Fangen,Wang Wanqia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policy towards Jew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ritish mandate policy in Palestine. Churchil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is policy change. After assuming the post of colonial minister, Churchill partially adjusted the British policy of “supporting Jews and limiting Arabs” in Palestine, reducing the support to Jews. In 1922, Churchill adjusted the policy of “supporting Jews and limiting Arabs” to the policy of “restricting Jews and suppressing Arabs” through the policy white paper.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 the Chamberlain government carried out the policy of “restricting Jews to attract Arabs” in Palestine. This policy was strongly criticized by Churchill. However, after Churchill became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he generally followed the policy he had strongly opposed.These adjustments reflect the strong utilitarian motivation and prominent speculative strategy of British policy in the region.
Key words:mandate;British Palestinian Jewish policy;Winston Churchill[責任編校王記錄]
作者簡介:李方恩(1975—),男,河南新鄉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王皖強(1966—),男,江蘇常熟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世界近現代史研究和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7BSS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