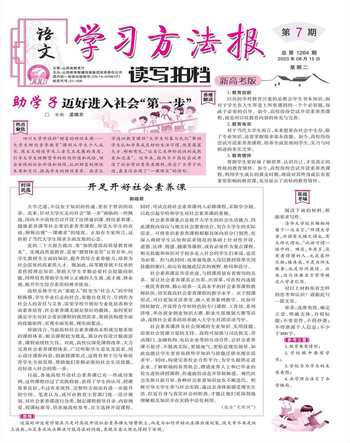心之所向(1)
張詩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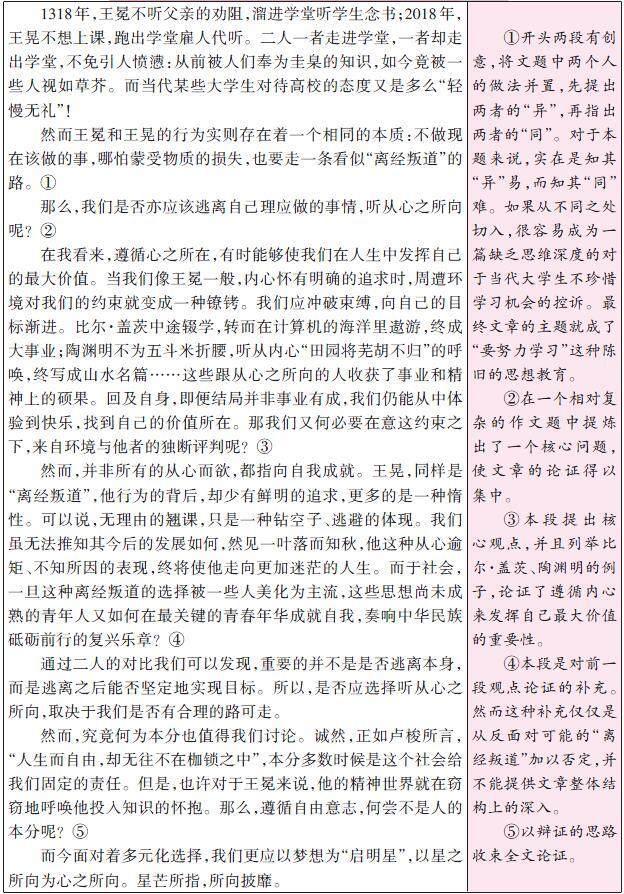
1318年,王冕不聽父親的勸阻,溜進學堂聽學生念書;2018年,王晃不想上課,跑出學堂雇人代聽。二人一者走進學堂,一者卻走出學堂,不免引人憤懣:從前被人們奉為圭臬的知識,如今竟被一些人視如草芥。而當代某些大學生對待高校的態度又是多么“輕慢無禮”!
然而王冕和王晃的行為實則存在著一個相同的本質:不做現在該做的事,哪怕蒙受物質的損失,也要走一條看似“離經叛道”的路。①
那么,我們是否亦應該逃離自己理應做的事情,聽從心之所向呢?②
在我看來,遵循心之所在,有時能夠使我們在人生中發揮自己的最大價值。當我們像王冕一般,內心懷有明確的追求時,周遭環境對我們的約束就變成一種鐐銬。我們應沖破束縛,向自己的目標漸進。比爾·蓋茨中途輟學,轉而在計算機的海洋里遨游,終成大事業;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聽從內心“田園將蕪胡不歸”的呼喚,終寫成山水名篇……這些跟從心之所向的人收獲了事業和精神上的碩果。回及自身,即便結局并非事業有成,我們仍能從中體驗到快樂,找到自己的價值所在。那我們又何必要在意這約束之下,來自環境與他者的獨斷評判呢?③
然而,并非所有的從心而欲,都指向自我成就。王晃,同樣是“離經叛道”,他行為的背后,卻少有鮮明的追求,更多的是一種惰性。可以說,無理由的翹課,只是一種鉆空子、逃避的體現。我們雖無法推知其今后的發展如何,然見一葉落而知秋,他這種從心逾矩、不知所因的表現,終將使他走向更加迷茫的人生。而于社會,一旦這種離經叛道的選擇被一些人美化為主流,這些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年人又如何在最關鍵的青春年華成就自我,奏響中華民族砥礪前行的復興樂章?④
通過二人的對比我們可以發現,重要的并不是是否逃離本身,而是逃離之后能否堅定地實現目標。所以,是否應選擇聽從心之所向,取決于我們是否有合理的路可走。
然而,究竟何為本分也值得我們討論。誠然,正如盧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本分多數時候是這個社會給我們固定的責任。但是,也許對于王冕來說,他的精神世界就在竊竊地呼喚他投入知識的懷抱。那么,遵循自由意志,何嘗不是人的本分呢?⑤
而今面對著多元化選擇,我們更應以夢想為“啟明星”,以星之所向為心之所向。星芒所指,所向披靡。
望聞問切
本文在進入題目時并不是簡單地選擇贊揚王冕而批評王晃,而是從他們二人行為的相同點入手來分析——兩人在各自的時代都是離經叛道、特立獨行的。由此出發展開論述可以確保中心突出,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割裂感。在具體的論述方面,本文將“離經叛道”的行為解釋為“逃離”。在逃離這一做法上,王冕和王晃實際上并沒有差別。但要叩問逃離背后的原因,就要分析他們分別去往哪里。而本文在對觀點進行論述之后,第五段僅僅提供了反面補充。從整體的論證結構上看,這種“一正一反”的論證形式,使得全文僅有一個論證層次。如果能使用層進式論證結構,那么文章便可以在內容和邏輯上更顯深刻。
- 《學習方法報》讀寫拍檔新高考版的其它文章
- “千金”原指出類拔萃的男子
- 高考作文高頻主題:審美
- 古人如何為不同朝代冠名
- 墨子的科學成就
- 真正的美,美在精神
- 愛美之心,求美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