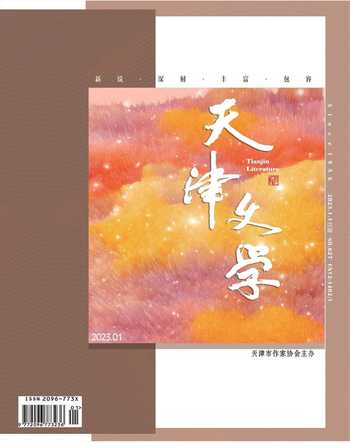飛翔的紅棗林
1
夜很黑,睜不睜眼都一樣。我仍向前摸索著,像個(gè)倔強(qiáng)的幽靈。
一周以來(lái),班長(zhǎng)每晚都要給我們幾個(gè)新兵搞上十次緊急集合,往往才閉眼,夢(mèng)的小船兒還在腦海邊緣漂蕩起伏,他的食指關(guān)節(jié)就敲響了床板:“緊急集合!”聲音不大,卻極瘆人。我條件反射般從床上彈起,慌亂中打好背包,傘兵一樣從上鋪跳到地上,腳塞進(jìn)棉鞋,來(lái)不及提,氣喘吁吁跑到班長(zhǎng)面前。
“報(bào)告!”
“六分鐘……”班長(zhǎng)嘬了嘬牙花兒,像我裹去的風(fēng)刺了他的牙齦,“太慢了,比樹(shù)懶還慢……”
我不知樹(shù)懶是啥,但有個(gè)“懶”字就夠了。我的確夠慢,全班倒數(shù)第一。
“解背包就寢!”班長(zhǎng)的眼珠在黑夜里閃爍著奇怪而狡黠的光。
我們迅速執(zhí)行命令。
忙碌過(guò)后,我直挺挺躺在冰涼的被窩里,夢(mèng)的小船兒仍在腦海漂浮,沒(méi)靠近,也沒(méi)消失。我知道,五分鐘,十分鐘或者半小時(shí)后……只要天不亮,班長(zhǎng)的“緊急集合”隨時(shí)會(huì)響起。一個(gè)星期,夜夜如此,幾個(gè)新戰(zhàn)友都麻木了。唯有我在悄悄期盼,哪天有什么意外發(fā)生,好讓我實(shí)施計(jì)劃。
今晚,機(jī)會(huì)來(lái)了。
下午,幾個(gè)老兵和我們一起跑五公里,班長(zhǎng)也參加了,鬧出一身汗,之后去水房沖澡,大家都用涼水,以顯示身體強(qiáng)壯,腎氣正足。班長(zhǎng)卻猶豫了,想擦一擦了事。我當(dāng)著他的面,將一盆涼水兜頭潑在自己身上。
“班長(zhǎng),爽啊!”我磕著后槽牙,望向班長(zhǎng)。
班長(zhǎng)瞪我一眼,也端起了臉盆。晚飯后,他開(kāi)始流鼻涕、打噴嚏,嘴巴張得老大,能看到他憤怒的喉嚨眼兒。熄燈前,我一臉關(guān)心地湊過(guò)去,將從衛(wèi)生隊(duì)取來(lái)的感冒藥獻(xiàn)給了班長(zhǎng)。前半夜,班長(zhǎng)還在床上翻騰了幾回,大概想掙扎著起身,繼續(xù)錘煉我們的反應(yīng)能力,過(guò)了十二點(diǎn),他沉沉地睡去了,我第一次聽(tīng)到他的鼾聲,毫無(wú)規(guī)律,忽長(zhǎng)忽短,忽高忽低,間或戛然而止,憋上二三十秒,才長(zhǎng)長(zhǎng)地吁出一口氣——我都有點(diǎn)兒擔(dān)心他會(huì)窒息。他是個(gè)不錯(cuò)的班長(zhǎng),盡管對(duì)我們有些苛刻。
今夜,不會(huì)再有緊急集合,不會(huì)再有突發(fā)事件。確定除我之外,全班都陷入了深深的夢(mèng)境,我輕手輕腳而又麻利地穿好衣服,下了床,像個(gè)自由主義的幽靈,閃出宿舍。直到如今,我仍記得自己躡手躡腳推開(kāi)房門(mén)時(shí),還不忘回頭掃了一眼班長(zhǎng)。他就在緊挨房門(mén)的下鋪,正在與下一口氣殊死搏斗。
夜,黑得黏稠。
我抬頭望了望天。哪怕有一顆星也好,起碼讓人安心些。但沒(méi)有。天上什么都沒(méi)有,四周也什么都沒(méi)有,黑色已將一切吞噬。那我也要前進(jìn),朝著廁所的方向摸索前進(jìn)。到部隊(duì)兩個(gè)多星期了,從第三天起,我?guī)缀趺刻於荚谘芯窟@個(gè)旱廁,尤其是它后面五米開(kāi)外的那堵南北走向的院墻。當(dāng)然,我有被換崗的老兵或查鋪查哨的連隊(duì)干部碰到的可能,但對(duì)我而言,他們都不可怕,我最忌憚的人,此刻正躺在床上跟感冒病毒和感冒藥糾纏。我想好了,萬(wàn)一被人碰見(jiàn),我會(huì)捂著肚子說(shuō):“疼,上廁所。”
大約十分鐘后,我摸到了廁所后面。若在白天,或是打了手電筒,這段路用不了多久,所以班長(zhǎng)才會(huì)有“大解五分鐘,小解三分鐘”的命令,但今晚,一來(lái)我極為緊張,二來(lái)實(shí)在太黑,每邁一步,都必須先用腳尖兒試探一下,唯恐撞上路邊某棵呆傻的楊樹(shù)。
現(xiàn)在,我的計(jì)劃已完成一半。
只要我順利爬上這堵黑乎乎三米高的圍墻,縱身一躍,跳到外面黑黢黢的果園,我的計(jì)劃就大功告成。我只是想趁班長(zhǎng)生病、趁長(zhǎng)夜漫漫跑回楊元帥營(yíng),我心里向班長(zhǎng)保證只這一次見(jiàn)崔芷若,就一夜的工夫,黎明前一定回來(lái),不露任何破綻。
對(duì)了,我叫高自攀,是個(gè)入伍不到一個(gè)月的新兵。
2
楊元帥營(yíng)是我的老家。
那個(gè)時(shí)候,我們村里很多人家都養(yǎng)牛,用來(lái)耕地。我喜歡牛,它們的眼里總是汪著善良與溫順,讓人看了心疼。崔芷若家里就有牛。
崔芷若的父親是我們村小學(xué)的校長(zhǎng),一個(gè)高高瘦瘦滿臉嚴(yán)肅的男人,我怕他那張黑臉,但不怕崔芷若。每次見(jiàn)到我,崔芷若總先微微一笑,露出兩顆晶瑩的虎牙——我迷死那兩顆小虎牙了,認(rèn)為那是世上最漂亮的兩顆牙,以至于常常拿鏡子照自己的嘴,希望也長(zhǎng)出這么兩顆來(lái)。令人失望的是,我的牙平平整整,普普通通,毫無(wú)個(gè)性。
好在,我沒(méi)個(gè)性,我們家的牛有。
我十三歲那年的春天,父親不知從哪兒牽回來(lái)一頭半大黑牛,短腿兒,大肚兒,牛頭正面有片菱形白毛,四個(gè)蹄子上方以及尾巴尖,也各有一截白,其余純黑。在此之前,我家養(yǎng)過(guò)雞,養(yǎng)過(guò)鵝,養(yǎng)過(guò)豬,從未養(yǎng)過(guò)大牲畜,這頭牛算不上大,沒(méi)到我胸脯高,但比鵝和豬大多了,關(guān)鍵是眼睛大,水汪汪的,從中能照到我纖瘦的身影。
“爸,這牛我來(lái)放!”我自告奮勇。
崔芷若家里有牛,我家也有了牛,我就可以堂而皇之約她一起去放牛了。琢磨半晌,我給這頭黑多白少的矮母牛起了個(gè)霸氣的名字——“梅超風(fēng)”。
選個(gè)星期天,吃過(guò)午飯,我牽著“梅超風(fēng)”去找崔芷若。
她家的牛是一頭有了年歲的大黃牛,走路四平八穩(wěn),像戲里的老忠臣,據(jù)說(shuō)耕地很好用。她父親對(duì)牛比對(duì)兒女親,從不讓淘氣的兒子去放。崔芷若是姐姐,聽(tīng)話,成了家里放牛的不二人選,她也樂(lè)意去。過(guò)去我家沒(méi)牛,不代表我不去北山坡,我家的棗樹(shù)行子在那兒,樹(shù)下還有幾分山坡地,我在地里幫大人干活時(shí),不止一次見(jiàn)過(guò)崔芷若牽著牛在山腳下晃悠,有時(shí),她會(huì)把韁繩繞在牛犄角上,任老牛漫山坡自由吃草,自己則躺在青石板上望天,一望就是很久。我一直想知道,空蕩蕩的天空,究竟有啥吸引了她。
我沒(méi)敢進(jìn)崔家院子,守在她家所在的胡同口耐心等待。“梅超風(fēng)”想吃路邊的草,左嗅嗅右聞聞,像只狗,還很挑吃,這個(gè)草不吃那個(gè)草不吃,拼命要往遠(yuǎn)處去,我只得使出渾身力氣將它往回拽,勉強(qiáng)保持位置不變。初夏的陽(yáng)光很燦爛,但不熱,我仍被“梅超風(fēng)”搞出一頭汗。
“早來(lái)啦?”崔芷若的聲音從我身后響起。
我急忙扭頭去看,同時(shí)扽了扽“梅超風(fēng)”的韁繩,它也就抬頭看。崔芷若穿了件杏黃色的長(zhǎng)裙,裙擺快將腳踝蓋住了,像是她媽媽的衣服,還穿著一雙白球鞋,抹鞋粉的那種白,風(fēng)一吹,衣袂飄飄,不像要去牧牛,更像織女牽著牛郎的牛出來(lái)散步。
“才到一會(huì)兒。”我答。
“去哪兒放?”崔芷若又問(wèn)。
“北坡。”我說(shuō)。
北坡就是北山坡。楊元帥營(yíng)坐落在燕山余脈的腳下,村北五里就是一座曲線渾圓的饅頭山。站在饅頭頂上,可以將楊元帥營(yíng)盡收眼底,還可以望向更遠(yuǎn)的地方,那里天地一線,莽莽蒼蒼,令人神往。
人在前,牛在后,我和崔芷若邊走邊聊,“梅超風(fēng)”和大黃牛邊走邊吃路邊草,和諧,完美,怪就怪我突發(fā)詩(shī)興,扯著尖嗓吼了起來(lái):“牛得自由騎,春風(fēng)細(xì)雨飛……”沒(méi)有細(xì)雨,只有我的吐沫星子。
崔芷若被我的樣子唬住了,投來(lái)仰慕的目光。我知道,這是因?yàn)樗恼Z(yǔ)文成績(jī)沒(méi)我的好,至于數(shù)學(xué),不提也罷。
“小若,知道嗎?”我大聲說(shuō)。
“知道什么?”
“我敢騎牛!”我拍了一下“梅超風(fēng)”的脊背,它朝我翻個(gè)白眼,又低頭去啃草。
“這可不是水牛,不好騎的。”
“是牛都可以騎!”我拍拍瘦胸脯,“你看著,我現(xiàn)在就騎上去——”嘴里說(shuō)著,我把韁繩交予左手,右手一摟“梅超風(fēng)”的脖子,像騎自行車(chē)那樣,翻身跨了上去。“梅超風(fēng)”沒(méi)料到我來(lái)這么一手,重點(diǎn)是它聽(tīng)不懂主人在吹牛,我明顯感覺(jué)它愣了一下,旋即像被烙鐵燙了牛腚,翻蹄亮掌朝前狂奔,脊背劇烈起伏,沒(méi)出十米,就將我掀了下來(lái),我的屁股正好剮在路旁棗樹(shù)棵子上,只聽(tīng)“刺啦”一聲,褲子撕了。
顧不得屁股上火辣辣的疼,我爬起來(lái)就去追陷入癲狂狀態(tài)的“梅超風(fēng)”。身后,傳來(lái)崔芷若的驚叫,接著又變成咯咯地笑。
最終,“梅超風(fēng)”被一簇鮮嫩的狗尾巴草吸引,停下了狂躁的腳步,準(zhǔn)備啃食。我瞅準(zhǔn)機(jī)會(huì),一個(gè)箭步竄過(guò)去,牢牢攥住了那條避免我倆都流浪的韁繩,也就在俯身的剎那,屁股上的火辣辣被涼颼颼取代,這使我猛然醒悟,迅速捂住屁股——正處于好面子的年齡啊,我那不算白的瘦臀被崔芷若瞧個(gè)穩(wěn)妥,心都快碎了。
很長(zhǎng)時(shí)間,我沒(méi)敢再去找崔芷若。
懷揣無(wú)限失落,我上了初中,學(xué)校在離楊元帥營(yíng)十幾里地的坨寺村,走著去有點(diǎn)兒遠(yuǎn)。父親咬咬牙,給我買(mǎi)了輛舊車(chē)子。一輛只有大架、車(chē)把、鏈條、腳蹬桿、車(chē)轱轆的簡(jiǎn)約版自行車(chē),騎起來(lái)風(fēng)阻低。
如今想來(lái),有車(chē)閘就好了。
3
更冷的一股寒氣襲來(lái),將我腦海中紛亂的追憶從耳朵鼻子嘴巴頂了出去,眼前一團(tuán)漆黑,但我能感覺(jué)到,自己距離高高的院墻不足三米遠(yuǎn)了。只要一個(gè)助跑,前腿蹬,后腿搭,以我的身高,加上新兵集訓(xùn)近三周的體能,我有信心順利騎上墻頭——這墻是死的,絕不會(huì)像當(dāng)年騎“梅超風(fēng)”那樣驚心動(dòng)魄。然而,就在我下定決心準(zhǔn)備行動(dòng),四肢也剛剛繃上勁兒時(shí),耳邊突然響起排長(zhǎng)的警告:
“小心墻根兒,有地雷!”
似有霹靂在心中炸開(kāi),我傻在了墨色中。
那是到部隊(duì)后的第一個(gè)傍晚,新兵排集合,我們被帶著熟悉營(yíng)區(qū),走到廁所附近時(shí),值班班長(zhǎng)下口令讓隊(duì)伍停住。新兵們雖不敢嘻嘻哈哈,但每個(gè)人還是很放松,很無(wú)所謂,很社會(huì)小青年。而那時(shí),班排長(zhǎng)對(duì)我們也是滿面春風(fēng)。
“上廁所,是每個(gè)人的自由,”凜冽北風(fēng)中,排長(zhǎng)頂著寒氣開(kāi)始訓(xùn)話,“但是,現(xiàn)在大家是軍人,是個(gè)當(dāng)兵的了,就要嚴(yán)格按照條令條例行動(dòng),上廁所也要跟班長(zhǎng)報(bào)告……”他依舊一臉慈祥,話語(yǔ)卻像一顆顆釘子,釘在我們略顯脆弱的身心上。
“介要四——鬧肚子,打完報(bào)告,早拉襠里了。”有個(gè)天津籍新兵在我身后嘀咕,滿口天津普通話逗得人想笑,但我忍住了。
“……同志們要特別注意,營(yíng)區(qū)院墻下,是埋有地雷的,”見(jiàn)幾個(gè)新兵瞪大了眼,排長(zhǎng)咧嘴笑了,臉上的兩條法令紋折射出關(guān)愛(ài),“主要是防止敵特搞破壞,你們不用緊張,別靠近就行了。”他接著說(shuō)。
我們只享受了一天一宿的遠(yuǎn)方來(lái)客待遇,第二天一起床,緊張的軍營(yíng)生活就迎面撲來(lái)。
出操、體能訓(xùn)練、整理內(nèi)務(wù)、洗漱、開(kāi)飯、操課,齊步、跑步、正步,拔軍姿——特別是拔軍姿,簡(jiǎn)直要人命。的確不用動(dòng),但隆冬季節(jié),北風(fēng)呼嘯,人站在塵土飛揚(yáng)的操場(chǎng)上一動(dòng)不動(dòng),想象自己是個(gè)雪人,可耳朵、鼻子、腮幫子不同意啊,寒冷讓血液流速減緩甚至停滯,裸露的皮膚就愈加感覺(jué)冷,到最后就剩麻木了。
我屬于又高又瘦的豆芽菜體形,忍耐力尚可,最怕緊張。新兵集訓(xùn)的這種緊張,會(huì)隨著時(shí)間流逝一分一秒逐漸累積,讓你覺(jué)得渾身累得像個(gè)秤砣,這種“累”感覺(jué)很疲憊。
到部隊(duì)后的第四天下午,我們正在訓(xùn)練場(chǎng)練習(xí)跑步走。本來(lái)大家都會(huì)跑,經(jīng)班長(zhǎng)細(xì)細(xì)講解,尤其一步一動(dòng),每個(gè)人又不知如何跑了,胳膊腿兒仿佛不是自己的,怎么也不協(xié)調(diào)。正當(dāng)我打算請(qǐng)假去廁所時(shí),班長(zhǎng)突然下達(dá)集合口令,接著整個(gè)新兵連都集合了。
“介四來(lái)大官了。”天津兵小聲嘀咕。
我用余光掃一下,見(jiàn)班長(zhǎng)、排長(zhǎng)、連長(zhǎng)都站得筆挺,看樣子比新兵還緊張。正覺(jué)好笑,卻見(jiàn)一個(gè)穿著風(fēng)衣,戴著大檐帽,肩膀上綴滿星星的人走到了隊(duì)伍前面。
然而,大官?zèng)]訓(xùn)話,僅是在隊(duì)伍前站了站,就走到了隊(duì)伍中間,邊走邊細(xì)看一個(gè)個(gè)新兵芽子,拍拍這個(gè)動(dòng)動(dòng)那個(gè),嘴里還磨叨著什么。我想側(cè)耳聽(tīng)聽(tīng),被班長(zhǎng)瞧見(jiàn),狠狠瞪了我一眼。我立即挺胸抬頭目視前方。
“喲,小同志軍姿很標(biāo)準(zhǔn)嘛!”一個(gè)男中音在我耳邊響起。
我一動(dòng)不動(dòng)。反正不是說(shuō)我。
“就是瘦了點(diǎn)。”男中音繼續(xù)說(shuō)。
“高自攀,首長(zhǎng)問(wèn)話呢。”班長(zhǎng)一聲低吼,將我從忘我中震了出來(lái)。這才看清,大官已走到我身旁,正笑瞇瞇望著我。
“首長(zhǎng)好!”這句話我說(shuō)對(duì)了,班長(zhǎng)嘴角擠出一絲笑。
“小伙子,為啥來(lái)當(dāng)兵啊?”首長(zhǎng)跟我那民兵連長(zhǎng)的父親年歲相近,但比他慈祥。
“報(bào)告首長(zhǎng),我當(dāng)兵是為了保家衛(wèi)國(guó)!”我?guī)缀跏呛俺鰜?lái)的。
“好!”首長(zhǎng)高興了,用力拍拍我的肩膀,“瘦是瘦了點(diǎn),練一練也就壯實(shí)了。”
班、排長(zhǎng)都笑了,跟在首長(zhǎng)身后的新兵連連長(zhǎng)沒(méi)笑,但向我投來(lái)贊許的目光。這天晚上班會(huì),班長(zhǎng)將我好好表?yè)P(yáng)了一通,說(shuō)我思想端正,要全班同志向我學(xué)習(xí)。
我來(lái)當(dāng)兵,首先是我從小的夢(mèng)想,同時(shí)也是為了把身體練得更結(jié)實(shí),等我復(fù)員回家,我更要讓崔芷若知道,我比那個(gè)滿臉青春痘的孫虎強(qiáng)得多,而且我能參軍,他卻因手腕上有用煙頭燙的肉梅花,部隊(duì)不可能要他……
此刻,我還是不敢靠近院墻,萬(wàn)一被地雷炸死,其實(shí)我最怕的是即便沒(méi)被人發(fā)現(xiàn),但在我內(nèi)心中還是萌生一種當(dāng)逃兵的恥辱,哪怕一夜都可能造成我終身悔恨。冷,再次順著耳朵鼻子嘴巴鉆進(jìn)體內(nèi),與血液結(jié)合,凝結(jié)成冰,嘎嘣嘎嘣,碎到了腹部,從里到外瞬間涼透,我不禁打了個(gè)哆嗦。
“高自攀,你還跳不跳?”
“高自攀,你還去不去?”
“高自攀,你還想不想見(jiàn)崔芷若?”
我感覺(jué)自己冰冷的腦海中,軍營(yíng)和崔芷若正發(fā)生碰撞,而崔芷若就像在軍營(yíng)上空泛起的一串串氣泡,躥出一個(gè),就被凍結(jié)一個(gè),變成透明堅(jiān)硬的冰疙瘩,浮在我的腦海里。
4
初中三年,那輛簡(jiǎn)約版自行車(chē)成為我的忠實(shí)助手,一天兩個(gè)來(lái)回,我騎著它奔馳在楊元帥營(yíng)到坨寺中學(xué)的路上。
是個(gè)周一的早晨,夜里下了大半宿的雨,上學(xué)路上,空氣清新,莊稼草木經(jīng)過(guò)雨水沖刷,在晨曦中閃著迷人的光澤。我喜歡這樣的場(chǎng)景。村村相通的主道上,鋪了層石子面,雨后騎行起來(lái),發(fā)出沙沙的聲響,潤(rùn)潤(rùn)的。出來(lái)得早,我車(chē)速并不快,還吹起了斷斷續(xù)續(xù)的口哨,是“依稀往夢(mèng)似曾見(jiàn),心內(nèi)波瀾現(xiàn)”的《射雕英雄傳》主題曲。
正當(dāng)我沉浸在自我世界時(shí),身后傳來(lái)一串清脆的車(chē)鈴聲。我下意識(shí)回了頭,后面的人距我有幾十米,從蹬車(chē)的姿勢(shì)看,是崔芷若,只有她,騎車(chē)時(shí)兩個(gè)膝蓋在大梁下挨得很近,像粘在一起,很嬌羞、很含蓄。想來(lái),她是在向我打招呼。估計(jì)是腦子抽了筋,我不但沒(méi)放緩車(chē)速,反而猛地抬起屁股,雙腿用力,將鏈條蹬得“咯吱吱”響,車(chē)子像闖出欄的瘋牛一般,“嗖”地沖了出去。
我是想證明什么。
多年以后,我仔細(xì)分析了一下,認(rèn)為那是青春期的荷爾蒙在搞鬼,是莫名其妙的自卑心在作祟,才導(dǎo)致我想在崔芷若面前顯擺一下,讓她知道,我是有力氣有速度的——我忽略了路面不平整,忽略了路面很濕滑。大概騎出去百十米,我的前面乍現(xiàn)一個(gè)小緩坡,確切地說(shuō),無(wú)非一個(gè)小突起、小鼓包,但是在加速度的作用下,我和我的簡(jiǎn)約范兒自行車(chē)同時(shí)騰空而起,完成人車(chē)分離后,重重地摔在一個(gè)水洼里。當(dāng)我暈頭轉(zhuǎn)向爬起來(lái)時(shí),先著地的右手掌火燒火燎疼起來(lái),再看,竟有無(wú)數(shù)小石子搓進(jìn)肉里,血,紅色瑪瑙般冒了出來(lái)。
崔芷若趕了上來(lái)。
“怎么樣,摔壞了沒(méi)?”她下車(chē)湊到了我面前,我能聞到她身上散發(fā)出的萬(wàn)紫千紅擦臉油的淡淡香氣。
“沒(méi)事。”我急忙將傷手背到身后。
“我看看……”她一把攥住我的右手,“出血了都!”她輕聲驚叫。
“小意思。”我訕笑。
“不敢馬虎,會(huì)感染的。”崔芷若說(shuō)著,從兜里摸出一塊粉色的手帕,“給,用它裹上。”
我想拒絕,奈何她已經(jīng)幫我包扎起來(lái)。由于低頭,她的發(fā)梢垂到了我的胳膊上,癢癢的,柔柔的,像有溫水滑過(guò)。
我的心怦怦亂跳。
我沒(méi)理由回避崔芷若了。
那塊我搓紅了手也洗不凈的手帕,她沒(méi)收回,說(shuō)是送我了。從這以后,幾乎每次上學(xué)放學(xué),我都會(huì)等崔芷若一起走。
早晚有些涼了,北山坡的棗樹(shù)行子里,彌散出棗子成熟的香氣。這兩年,紅棗價(jià)錢(qián)還不錯(cuò),為提防有人披星戴月去偷棗,棗子剛紅圈時(shí),父親就每晚去山坡上睡。到了周末,就換成我。父親是村里的民兵連長(zhǎng),很會(huì)利用現(xiàn)有地形地物,為節(jié)省材料,他將窩棚直接搭在了兩座墳包中間,很矮,進(jìn)去只能躺著。這個(gè)位置正處于視野開(kāi)闊地,可以將我家這片棗樹(shù)林一覽無(wú)余。
我喜歡夜里在棗樹(shù)行子待著,盡管這里埋葬著楊元帥營(yíng)祖祖輩輩的先人。
用父親的話說(shuō):“死人不可怕,可怕的是活人。”
靜夜里,我可以聽(tīng)聽(tīng)收音機(jī),可以望望天上的星星。那時(shí)的夜空,純凈,清澈,密密麻麻的星星像是鑲嵌在巨大的弧形黑水晶上,金色與純黑完美映襯,璀璨極了。尤其銀河,我真是被它迷住了。我曾久久地盯著銀河看,想象那里面到底有多少顆像地球這樣的星體,上面有多少個(gè)如我這樣仰望蒼穹的生命,無(wú)邊無(wú)際到底是個(gè)什么概念……想著想著,我會(huì)進(jìn)入癡迷狀態(tài),以為自己不存在了,與蒼茫合而為一了。
周六傍晚,吃過(guò)飯,天尚未完全黑下來(lái),我就拿著手電筒朝北山坡出發(fā)了。出村北時(shí),我發(fā)現(xiàn)有兩三個(gè)村里的混混在朝北坡望,見(jiàn)我過(guò)來(lái),要么低頭干別的,要么轉(zhuǎn)身閃開(kāi),引起我的懷疑。他們一定是想等天黑了去偷棗。從我們村往北山坡有三條溝,均是山洪長(zhǎng)年累月沖擊形成,我家的棗樹(shù)行子在中間那條溝的頂端,再往上走,就是山根了。崔芷若家的棗林與我家只隔了一戶的樹(shù)行子,路過(guò)時(shí),我放慢腳步,朝她家的窩棚掃了幾眼,今天是她弟弟在,正在樹(shù)下捉知了猴。我有點(diǎn)小失望。崔芷若是不來(lái)看棗的,都是她爹和她弟來(lái)。這樣也好,晚上我可以安心望夜空了。
黑幕很快拉了下來(lái)。
星星漸次在夜空中點(diǎn)亮,越來(lái)越多,越來(lái)越密。今晚我沒(méi)拿收音機(jī),主要是沒(méi)啥可聽(tīng)的。百無(wú)聊賴中,我打開(kāi)手電筒,將光柱直直地射向蒼穹,可惜沒(méi)爬多高,光的盡頭就被黑暗吞噬。怕費(fèi)電,我沒(méi)敢將這個(gè)游戲進(jìn)行太久,關(guān)掉電筒,也沒(méi)立即鉆進(jìn)窩棚,而是坐在旁邊的一塊石頭上,那里仍是暖暖的,白天被吸收的熱能,正緩慢釋放出來(lái)。
蟲(chóng)鳴在棗樹(shù)林中響起,高高低低,此起彼伏,有的清脆,有的低沉,不知在表達(dá)著什么。我從身旁垂下來(lái)的棗枝上拽了個(gè)大棗,扔進(jìn)嘴里,又脆又甜。我家的棗子是長(zhǎng)的,最大的有拇指長(zhǎng),很甜。崔芷若家的棗子是橢圓的,不知味道如何,經(jīng)常從她家樹(shù)下路過(guò),我從未摘過(guò)一顆——君子樹(shù)下不正冠,我不是君子,但樹(shù)是她家的,我肯定不摘。良久,秋蟲(chóng)的叫聲漸漸被夜色覆蓋,我有些犯困了,望向銀河的眼睛開(kāi)始酸澀,打算起身進(jìn)窩棚,伴著旁邊的兩位先人睡去。
突然,一聲尖叫劃破了夜的寧?kù)o。
是從崔芷若家的棗樹(shù)行子傳來(lái)的?
又一聲尖叫,像女人踩到蛇。我聽(tīng)出來(lái)了,的確是崔芷若。她今晚來(lái)北坡了?我急忙打開(kāi)手電筒,野兔般朝她家窩棚跑去。
5
我終究沒(méi)有,或者說(shuō)沒(méi)有勇氣敢去見(jiàn)崔芷若。
返回途中,我的腿有些發(fā)軟,被地面絆了一下,右腳大腳趾像被揭掉指甲,鉆心疼。來(lái)到宿舍門(mén)口,我猶豫片刻,輕輕推開(kāi)了門(mén),一股暖氣,一股帶著男人體味的暖氣迎面撲來(lái),我差點(diǎn)兒沒(méi)落下淚疙瘩。然而,當(dāng)我的視線掃向班長(zhǎng)的床鋪時(shí),所有矯情瞬間不翼而飛。
班長(zhǎng)正一動(dòng)不動(dòng)地端坐在床上。
他的眼睛竟然能在如此黑的夜里閃出光亮。
“回來(lái)啦?”他開(kāi)口說(shuō)話了,聲音不像從他嘴里發(fā)出的,而是從我頭頂某個(gè)很高很遠(yuǎn)的地方緩緩砸下來(lái)。我差點(diǎn)兒尿了褲子。
“班長(zhǎng),我肚子疼。”我磕著牙,戰(zhàn)戰(zhàn)兢兢說(shuō)。
“班用柜上不是有手電嘛,下次再出去,記得拿上。”班長(zhǎng)仍直直地坐著,像一尊深色塑像。
“班長(zhǎng),你……”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安心睡吧,明早還要出操呢。”
班長(zhǎng)似乎笑了,我看見(jiàn)雕像嘴部有微弱的白光閃過(guò)。他不是感冒了嗎?我溜出去的時(shí)候,他不是在打呼嚕嗎?難道,他跟著我去了?我的腦袋里嗡嗡作響。
“回來(lái)就好,去睡吧。”班長(zhǎng)又說(shuō)。
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又什么都不確定。膽戰(zhàn)心驚地上了床,一宿未睡,恰如當(dāng)年在北山坡的棗樹(shù)林里陪崔芷若。
那天夜里,當(dāng)我跑到崔家的窩棚前,見(jiàn)到崔芷若時(shí),她正縮在一棵棗樹(shù)下瑟瑟發(fā)抖,而我的到來(lái),讓她愈加受到驚嚇。
“是我,高自攀!”我將電筒的光打在自己身上。我沒(méi)敢朝臉上打,這種環(huán)境下,光線若從下巴往上照,別說(shuō)一個(gè)女孩子,就是我那當(dāng)民兵連長(zhǎng)的爹,也會(huì)心驚肉跳。
崔芷若瞪著我看了足有幾秒鐘,才說(shuō):“是你呀,你怎么來(lái)樹(shù)行了?”
“你怎么來(lái)了?剛才還是你弟弟在呢。”
“他……有點(diǎn)兒不舒服,讓我替他……”
“你爸呢?”
“我爸媽去姥姥家了。”崔芷若好了許多,我伸出手去,想她拉起來(lái)。她猶豫一下,攥住了我的手,卻沒(méi)起來(lái)。“高自攀,你也來(lái)看棗樹(shù)啊?”她的手冰涼,還在抖。
“我每個(gè)星期都來(lái)。”我嘿嘿笑了。
崔芷若咧了咧嘴,兩顆小虎牙在星光下閃了閃,像星星飛進(jìn)她嘴里。
我四下看看,沒(méi)啥異常,問(wèn):“剛才是你叫的嗎,怎么啦?”
“鬼火……”崔芷若仍在輕輕磕牙,“有鬼火……”
“哪里?”
崔芷若伸手朝右邊指了指。我急忙望去,黑黢黢一片,哪有什么鬼火。
“沒(méi)啥呀?”
“剛才我還看見(jiàn)呢,還往我這兒飄呢。”
“螢火蟲(chóng)吧?”我笑了。
“你家螢火蟲(chóng)秋天還出來(lái)啊。”崔芷若也“撲哧”一聲笑了,手不抖了。
“我聽(tīng)說(shuō),有些螢火蟲(chóng)夏天沒(méi)有找到另一半,會(huì)撐到秋天,堅(jiān)信自己能見(jiàn)到另一半,就有了秋天的螢火蟲(chóng)。”我絞盡腦汁道。
“胡編。”說(shuō)著,崔芷若自己站了起來(lái),朝那團(tuán)黑黢黢又掃了一眼,“今晚不會(huì)有人偷棗子吧?”
“這可說(shuō)不準(zhǔn)。”
“那你……”
“沒(méi)事,先跟你待會(huì)兒,這么近,有動(dòng)靜我能聽(tīng)到。”
我倆并肩坐在她家的窩棚前,我想說(shuō)點(diǎn)什么,可一旦靜下來(lái),發(fā)現(xiàn)再打破這種寧?kù)o很難。其實(shí),能跟崔芷若坐一會(huì)兒,我就很知足了。我很感謝今晚老天爺賜給我這個(gè)機(jī)會(huì),大概剛才我仰望星空的時(shí)候很虔誠(chéng),那些亮晶晶的恒星一起發(fā)了善心吧。
約莫過(guò)去十幾分鐘,不遠(yuǎn)處,幾棵挨得很近的棗樹(shù)下,突然有亮光閃了閃。我倆都看見(jiàn)了,我頓感有股涼氣順著后脖頸“嗖”地鉆進(jìn)了衣服里。
崔芷若再次驚叫起來(lái):“你看,鬼火!”
“磷火好不。”不知哪兒來(lái)的勇氣,我忽地站起身,大踏步趕過(guò)去,打開(kāi)了電筒。的確是鬼火,有三簇,在一個(gè)土包四周懸浮著。我知道,這里到處是墳頭,有磷火正常,但說(shuō)實(shí)話,我也是第一次見(jiàn)。
“就是鬼火!”崔芷若在我身后喊道。
“化學(xué)課上,老師不是講過(guò)嘛,這是正常現(xiàn)象。”說(shuō)著,我朝鬼火走了幾步,它們竟然讓開(kāi)了,我退回,它們又跟了上來(lái),“空氣流動(dòng),它們就被擾動(dòng)了。”我用學(xué)到的知識(shí)壯著膽子。
“你說(shuō)的有道理。”崔芷若的情緒稍稍緩和。
“要不,你回家去吧,我替你看著棗樹(shù)行。”我對(duì)她說(shuō)。
“還是跟你一起待著吧,回去的路也是黑。”崔芷若低聲說(shuō)。
我豪氣地點(diǎn)了點(diǎn)頭。就在這時(shí),那三簇鬼火消失了。
這一宿,我倆幾乎把一輩子的話都說(shuō)完了。
6
又一個(gè)夏天過(guò)去,我和崔芷若上了鎮(zhèn)高中,離家更遠(yuǎn)了。楊元帥營(yíng)這次考上三個(gè)人,還有一位是老楊家的楊苗苗。這個(gè)楊苗苗,學(xué)習(xí)一直不咋地,也考上了高中,讓人詫異。后來(lái)有人說(shuō),是判卷老師看錯(cuò)了卷子。
父親給我買(mǎi)了輛新自行車(chē)。
我卻高興不起來(lái)。高一分兩個(gè)班,我和楊苗苗分在一班,崔芷若分到了二班,僅一墻之隔,我還是少了跟她接觸的機(jī)會(huì)。我是個(gè)時(shí)而靦腆時(shí)而張狂的人,可氣的是,在對(duì)待崔芷若的事情上,我的靦腆會(huì)升級(jí)。
鎮(zhèn)里比楊元帥營(yíng)和坨寺都大多了,房子多,人多,街道寬,熱鬧,校門(mén)口的小痞子也多。楊苗苗和崔芷若選擇了住校。我也想。父親掃了一眼我的新自行車(chē),說(shuō):“那還買(mǎi)它干啥?”
這讓我無(wú)話可說(shuō)。
高中的學(xué)業(yè)更緊張,而這時(shí),我迷上了看小說(shuō),古龍、梁羽生、臥龍生、上官青云、金庸……看著看著,我忘了翻課本,忘了自己是個(gè)學(xué)生,忘了隔壁教室的崔芷若。忽然有一天,同學(xué)珍藏的瓊瑤的書(shū)傳到我手里,看了幾頁(yè)后,我又什么都記起來(lái)了。這才發(fā)現(xiàn),自己已是高二的學(xué)生了,再想想,有三個(gè)多月的時(shí)間,我僅在去飯?zhí)玫穆飞弦?jiàn)過(guò)崔芷若幾面。
中午時(shí)間短,我也在飯?zhí)么蝻埢亟淌页浴`l(xiāng)鎮(zhèn)中學(xué)的飯?zhí)脹](méi)那么講究,餐桌都沒(méi)有,學(xué)生們?cè)趦蓚€(gè)窗口打了飯,要么蹲在飯?zhí)贸裕椿亟淌遥偸莵y糟糟的。基本的秩序也有,只在窗口前,列上兩隊(duì)歪歪扭扭的長(zhǎng)蛇陣,一般也沒(méi)人插隊(duì),高中生了,荷爾蒙的確充沛,要面子懂規(guī)矩的心還是有的。我發(fā)現(xiàn),我們班的比二班的人要老實(shí)。
二班有幾個(gè)刺頭。
這天中午,二班的幾個(gè)男生來(lái)得有些晚,不想排隊(duì),在隊(duì)伍中鉆來(lái)鉆去,很放肆。我在隊(duì)尾前后左右看了看,崔芷若還沒(méi)來(lái),正想要不要去二班教室找她,前面突然一陣騷亂,接著聽(tīng)到楊苗苗在喊:“有沒(méi)有個(gè)先來(lái)后到?”
我探身一瞧,是二班一個(gè)留著小分頭滿臉青春痘的家伙想插隊(duì),跟楊苗苗吵了起來(lái),看情形,他還滿不在乎。這不是欺負(fù)人嘛,我走了過(guò)去,我比他高出半頭,即便打起來(lái),也不會(huì)吃大虧,雖然他長(zhǎng)得比我壯實(shí)。
“嗨,哥們兒……”一張嘴,我把自己嚇了一跳,這分明是校門(mén)口混混們的腔調(diào),“不能插隊(duì)啊!”我裝腔作勢(shì)道。
小分頭朝后捋了一下頭發(fā),瞪著小眼珠看了看我:“你誰(shuí)呀?”
“你誰(shuí)呀?”我反問(wèn)。說(shuō)話間,二班那幾個(gè)男生圍了上來(lái),一個(gè)個(gè)虎著臉。我用余光掃了掃,我們班男生沒(méi)一個(gè)過(guò)來(lái)支援的,都遠(yuǎn)遠(yuǎn)地站著觀望,有的還趁機(jī)朝窗口擠了擠,打了飯就走。這讓我很傷心,很沮喪,很惱火。
“你出來(lái)!”小分頭咧嘴笑了笑,牙很白,“到外面我告訴你!”那白牙分明咬了咬,聲音聽(tīng)起來(lái)透著狠勁。
我不想出去,飯?zhí)美锶硕啵瑳](méi)人幫忙心里也踏實(shí),若到外面,情況就未知了。但我不能不去,楊苗苗等女生正在看著我,我們班的男生也在靜觀其變,若想在班里待下去,我絕不能認(rèn)。我昂首挺胸地朝外走。楊苗苗拽了一下我的衣角,沒(méi)拽住,于是也跟了出來(lái),把飯缸子反手攥了,做出要拼命的樣子。她的堅(jiān)毅鼓勵(lì)了我。在飯?zhí)们暗囊豢门萃?shù)下,雙方站定。
“想怎么著?”我問(wèn)。
“你說(shuō)呢?”小分頭又撩了一下頭發(fā)。
那幾個(gè)男生將我和楊苗苗圍了起來(lái)。我對(duì)楊苗苗說(shuō):“你去打飯,別管了。”輕輕推她一下,將她推出了包圍圈。
“喲,英雄救美啊?”小分頭嘿嘿一笑,伸手要抓我的衣領(lǐng)。
這種情形下,只能盯準(zhǔn)一個(gè)往死里磕,我心一橫,抬腿就踹在了他的肚子上,小分頭沒(méi)想到我會(huì)先下手,“哎喲”一聲,手上松了勁兒。那幾個(gè)小子立即撲了上來(lái)。我沒(méi)搭理他們,一個(gè)餓虎撲食,與小分頭糾纏在一起。有拳頭砸在我后背上,有腳板踹在我屁股上,我全然不顧,雙手胡亂揮舞著,誤打誤撞將手指塞進(jìn)了小分頭的嘴角,用力一扯,將他的嘴角撕出了血。見(jiàn)了血,大家都愣了。
就在這時(shí),崔芷若不知從哪兒冒了出來(lái),喊道:“孫虎,干啥呢?高自攀是我們村的!”
我的心像被箭“砰”地射中,是一支穿心箭,很疼很要命的那種。從崔芷若的叫喊中,我能聽(tīng)出她跟這個(gè)小分頭關(guān)系不一般。
“我想早點(diǎn)兒給你打飯,被他攔了。”孫虎抹了一下嘴角,朝崔芷若笑。
“晚點(diǎn)兒能餓死啊?”崔芷若說(shuō)。
7
新兵集訓(xùn)那三個(gè)月,啥時(shí)候想起來(lái),都是刻骨銘心的。其實(shí),最累人的就兩樣:隊(duì)列訓(xùn)練,體能訓(xùn)練。至于射擊、投彈啥的,簡(jiǎn)直是上學(xué)時(shí)的體育課、音樂(lè)課。尤其走鴨子步,直到如今,我也搞不懂人學(xué)鴨子走路能鍛煉哪部分肌肉,而它的實(shí)戰(zhàn)價(jià)值,更無(wú)法確定。
日子太累,也太枯燥,看個(gè)電視都要手放膝蓋,上身挺直。好在,時(shí)不時(shí)地會(huì)有書(shū)信像一只只小白鴿“撲棱棱”飛進(jìn)宿舍來(lái),每周六晚上的自由活動(dòng)時(shí)間,就成了新兵們最渴望的時(shí)刻——晚七點(diǎn)半到九點(diǎn)半,兩個(gè)小時(shí),是屬于我們的。哦,不,是屬于我們自由心靈的。
這期間崔芷若沒(méi)給我寫(xiě)過(guò)信。我收到的,除去父親的革命教育信外,剩下都是楊苗苗寫(xiě)的。
事實(shí)上,我沒(méi)參軍前收過(guò)崔芷若的信,一張紙條,三指寬,用的是筆記本里的橫格紙,上面寫(xiě)了一句話:我沒(méi)你想的那么好。
當(dāng)時(shí),我已經(jīng)離開(kāi)學(xué)校,正跟父親冷戰(zhàn),他非要我去村小當(dāng)老師,從此成為孩子頭,而我卻想逃離家鄉(xiāng),到廣闊天地遨游一番,哪怕淹死于人生大海也在所不惜。那段日子,若不是母親在中間周旋,估計(jì)父親會(huì)將我趕出家門(mén)。他沒(méi)想到我會(huì)輟學(xué)。我也沒(méi)想到我會(huì)輟學(xué),尤其在還差二十天就高考的關(guān)鍵時(shí)刻。直到現(xiàn)在,我還認(rèn)為自己輟學(xué)是由于考學(xué)無(wú)望。
偶爾,也會(huì)有個(gè)沉悶的聲音在我心底緩緩響起——你是因?yàn)榇捃迫簟?/p>
高三上學(xué)期,孫虎就輟學(xué)了,聽(tīng)說(shuō)他家里開(kāi)了個(gè)什么廠子,正缺人手,見(jiàn)他無(wú)心學(xué)業(yè),讓他提前融入了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孫虎離開(kāi)學(xué)校,最高興的是我。這之前,飯?zhí)猛獾谝淮谓皇趾螅辽僬疫^(guò)我三次麻煩,前兩次我倆單對(duì)單,沒(méi)動(dòng)手,光動(dòng)嘴了。最后一次,他在一個(gè)傍晚將我叫到了男生宿舍,我是不住校的,也知道此行兇多吉少,不想去。可是,上晚自習(xí)的楊苗苗發(fā)現(xiàn)孫虎在教室門(mén)口示意我出去,急忙跑過(guò)來(lái)對(duì)我說(shuō),高自攀你千萬(wàn)別跟他走,他沒(méi)安好心!還用她說(shuō)嘛,我知道。她這么一摻和,我想不出去都不可能了。揣著一顆視死如歸的心,我跟孫虎進(jìn)了男生宿舍,才進(jìn)去,就后悔了。
屋子里至少坐了七八個(gè)人,都不像學(xué)生。有個(gè)唇上長(zhǎng)了黑乎乎小胡子的家伙,手里還握著根鋼管,我進(jìn)屋時(shí),他正右手倒左手、左手倒右手地玩那根管子,像剛從煉鋼爐里偷出來(lái)似的。
我知道,這種情形下不動(dòng)點(diǎn)兒腦筋,有被打死的可能。
我先是“嘿嘿”一笑,而后一屁股坐在了最近的下鋪上,還翹了二郎腿,說(shuō):“哥兒幾個(gè),鬧這么大動(dòng)靜啊?”
“少?gòu)U話,你不是狂嗎?”孫虎眼都不眨地說(shuō),“打他!”
“打我簡(jiǎn)單,今下午我那當(dāng)民兵連長(zhǎng)的爹可來(lái)鎮(zhèn)里了,說(shuō)等我下自習(xí)課后一起回家的。”我不緊不慢地說(shuō)。
“你爹來(lái)了也救不了你。”小黑胡子惡狠狠地說(shuō)。
“他是救不了,但你們也走不了,他是來(lái)鎮(zhèn)里修槍的。”我面無(wú)表情地說(shuō)。
“扯淡,你爹能有槍?”小黑胡子說(shuō)著,瞟了一眼孫虎。
“我爹是民兵連長(zhǎng),別說(shuō)槍了,家里還有炸藥和雷管哩,大哥你要用嗎?用的話,我可以讓他送你點(diǎn)兒。”我繼續(xù)胡謅。
“別聽(tīng)他瞎說(shuō),要有槍,他爹早被派出所抓了。”孫虎對(duì)小黑胡子說(shuō)。
“瞎說(shuō)?你見(jiàn)過(guò)手槍嗎?我可在我爹抽屜里見(jiàn)過(guò),他打槍能讓兩顆子彈穿過(guò)同一個(gè)窟窿……”天助我也,說(shuō)到這里,外面突然有人悶聲悶氣地喊了我一聲。
“高自攀,來(lái)我辦公室一趟!”是班主任。
幾個(gè)家伙愣愣地看著我走出了宿舍。事后得知,是楊苗苗在關(guān)鍵時(shí)刻找的班主任。從這以后,我盡量不單獨(dú)行動(dòng)了,上學(xué)放學(xué)變換著路線走,每次都將車(chē)子騎得飛快。直到我離開(kāi)學(xué)校,再?zèng)]出現(xiàn)被人圍困的局面。
這件事消停后,楊苗苗認(rèn)為自己立了功,有事沒(méi)事就在我面前晃悠,并且跟我說(shuō),這個(gè)孫虎,現(xiàn)在是崔芷若的對(duì)象。我當(dāng)時(shí)就惱了,說(shuō)你怎能亂講?楊苗苗臉紅了一下,解釋說(shuō)整個(gè)年級(jí)都知道,不知道的也就你和老師了,否則,孫虎有毛病啊,總替她打飯,倆人在教室里吃,就差相互喂了。
我的腦袋“嗡”的一聲。
距高考還有兩個(gè)月的時(shí)候,一個(gè)周末的傍晚,我剛走出教室,就見(jiàn)孫虎騎著一輛摩托車(chē)從遠(yuǎn)處駛來(lái),我以為他又要找我麻煩,誰(shuí)知他在我面前停下后,居然朝我笑了笑。
“今天放學(xué)早啊。”他說(shuō)。
我沒(méi)搭理他。
孫虎又嘿嘿笑了,而后朝二班的教室門(mén)口張望。“我來(lái)接崔芷若,帶她去轉(zhuǎn)轉(zhuǎn)。”
“她沒(méi)空!”我愣愣地接話道。
這時(shí),崔芷若已經(jīng)走了出來(lái),也朝我笑笑,動(dòng)作輕盈地上了孫虎的摩托車(chē),像小鳥(niǎo)躍上枝頭。
我給崔芷若寫(xiě)了一封信,托楊苗苗捎給她。
在信中,我說(shuō)了一大堆冠冕堂皇而又彎彎繞的話,最后一句才是重點(diǎn):我想跟你一起努力,考上大學(xué)!三天后,我收到了那封回信。沒(méi)等我反應(yīng)過(guò)來(lái),又過(guò)去一周,崔芷若也離開(kāi)了校園。
我的世界分崩離析,甚至能聽(tīng)到碎裂的聲響。
8
我以為,部隊(duì)的生活無(wú)非是緊張,緊張就緊張吧,沒(méi)見(jiàn)哪個(gè)老兵一臉愁容,說(shuō)明這種緊張還能適應(yīng)。但我怎么也沒(méi)料到,新兵下連這天,竟然沒(méi)老兵來(lái)認(rèn)領(lǐng)我——這跟一棵棗樹(shù)長(zhǎng)滿紅棗卻沒(méi)人來(lái)摘有啥區(qū)別?
難道,我高自攀還不如一棵七扭八歪的棗樹(shù)?
哦,是的,棗子還有人吃,還有營(yíng)養(yǎng)的,我呢?長(zhǎng)得倒像一顆好棗,但五公里跑不快,單雙杠湊合及格,投彈、射擊成績(jī)不僅平平,還凹下去一點(diǎn)兒,老兵的眼珠兒多毒啊,你是好兵是孬兵,人家掃一眼就知道,可不管你長(zhǎng)啥樣,哪怕賽過(guò)潘安,軍事素質(zhì)軟塌塌,在部隊(duì)里照樣沒(méi)人瞧得上。
曾經(jīng)住了十個(gè)人的宿舍,如今人去鋪空,只剩下我獨(dú)自坐在班長(zhǎng)的那張下鋪,靠著打好的背包望房頂,心情不爽令我覺(jué)得屋里更顯空蕩,喘氣都有回音。
快中午了,仍沒(méi)老兵過(guò)來(lái),我心里開(kāi)始發(fā)慌。這時(shí),門(mén)開(kāi)了,班長(zhǎng)一臉慈祥地走了進(jìn)來(lái)。他也要回老連隊(duì)報(bào)到了,估計(jì)是來(lái)跟我道別的。
“班長(zhǎng)……”像看到了救星,我“騰”地站起來(lái)。
“等急了吧?”班長(zhǎng)只比我大四歲,此刻看起來(lái),他比我那民兵連長(zhǎng)的父親還像個(gè)父親。
“沒(méi)……是。”
“下午,咱倆去靶場(chǎng)報(bào)到。”班長(zhǎng)說(shuō)著,坐下來(lái),遞給我一支煙。
我簡(jiǎn)直震驚——新兵集訓(xùn)期間,天津兵在廁所偷著抽煙,被班長(zhǎng)發(fā)現(xiàn)后,給他搞了兩個(gè)多小時(shí)的思想課,全班都跟著提心吊膽,唯恐夜里緊急集合次數(shù)翻番,況且,我從未見(jiàn)過(guò)班長(zhǎng)吸煙,他也不知道我吸煙啊?我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臉和手都僵住了。
“接著吧。”班長(zhǎng)淡然一笑,那口白牙在我眼前一閃。
“我……嘿嘿,”我果斷搖頭,“不會(huì)。”
“你可拉倒吧!”班長(zhǎng)將煙叼在自己嘴里,熟練地從兜中摸出打火機(jī),點(diǎn)著,吸了一口,“廁所里你也抽過(guò)。”
我后脖頸的汗毛挺了起來(lái),不亞于那個(gè)夜里見(jiàn)他坐在床上等我。
“沒(méi)事,從現(xiàn)在開(kāi)始,你樂(lè)意抽就抽。”班長(zhǎng)說(shuō)完,將視線投向了窗外。營(yíng)區(qū)里,楊樹(shù)上已經(jīng)掛滿樹(shù)吊,在春風(fēng)的吹拂下,像無(wú)數(shù)蠕動(dòng)的毛毛蟲(chóng)。
我哪兒有心思抽煙啊。聽(tīng)話聽(tīng)音,想來(lái),班長(zhǎng)什么事都了如指掌,這是件多么恐怖的事啊!直到現(xiàn)在,我不敢想更不敢問(wèn),那天夜里,我準(zhǔn)備跳墻時(shí),班長(zhǎng)到底知不知道?
“不抽也罷,吸煙終歸是不好的。”見(jiàn)我發(fā)愣,班長(zhǎng)輕輕嘆了口氣,接著說(shuō),“高自攀,你在部隊(duì)的日子還長(zhǎng)著呢。”
我點(diǎn)了點(diǎn)頭。
心里被各種念頭填滿時(shí),反而是空的。揣著一顆空蕩蕩的心,我和班長(zhǎng)去靶場(chǎng)報(bào)到了。說(shuō)著簡(jiǎn)單,實(shí)際上,我們足足坐了半天的東風(fēng)牽引車(chē),抵達(dá)時(shí),天色已晚。我們團(tuán)是高炮團(tuán),每年夏季都要進(jìn)行實(shí)彈射擊。打炮嘛,當(dāng)然不能在駐地,郊區(qū)也不行,萬(wàn)一炮彈落到老百姓院里,就是大事故。不知從哪年起,在上級(jí)的統(tǒng)一安排下,我們?cè)诖蠛_呥x了這么一塊灘涂地,建起了靶場(chǎng)。面朝大海,萬(wàn)彈齊發(fā),全落到海里充其量炸上幾條魚(yú)來(lái),多么理想的練兵場(chǎng)。為了保證靶場(chǎng)隨時(shí)能用,團(tuán)里從每個(gè)連各抽兩名戰(zhàn)士負(fù)責(zé)日常維護(hù),加上場(chǎng)部的人,方圓百十多里的偌大灘涂,只有不到三十人。若不是實(shí)彈射擊,誰(shuí)愿來(lái)這兒啊,想看個(gè)鮮面孔都費(fèi)勁。
我當(dāng)然也不愿守靶場(chǎng)。但是,班長(zhǎng)來(lái)了,我不得不緊隨其后,誰(shuí)讓其他老兵沒(méi)選我呢,指揮排,炮排,司機(jī)班……即便新兵們都不愿去的炊事班,也沒(méi)看上我,讓我這張已經(jīng)不白了的小臉往哪兒放?軍用卡車(chē)載著我駛?cè)氚袌?chǎng)邊緣時(shí),望著茫茫的鹽堿地,望著遠(yuǎn)處水天一色不知是泊是湖是海的遼闊,我想,自己來(lái)這里,或許真是最合適的。除了班長(zhǎng),我大概不需要見(jiàn)任何人。
人不見(jiàn)我,我不心煩。
然而,僅在靶場(chǎng)待了一個(gè)多星期,我就開(kāi)始渴望陌生人了,哪怕是棵陌生的樹(shù)也好。班長(zhǎng)也寂寞,否則,他不會(huì)帶著我去修整我們連的陣地——我已經(jīng)知道,陽(yáng)光下那些白花花的水面,是廢棄的鹽池,每一個(gè)都有半個(gè)楊元帥營(yíng)那么大,而那些同樣白花花的地面,似乎看不到邊的地面,就是我們團(tuán)各個(gè)連隊(duì)的炮陣地,至于大海,還要背向場(chǎng)部,再往東走十幾公里才能見(jiàn)到。在這樣的空間里,班長(zhǎng)帶著我,一人一把戰(zhàn)備鍬,誓將我們連的陣地用泥土圍出一個(gè)大大的框,說(shuō)白了就是泥墻,一米高,底寬半米,頂寬三十厘米,若有螞蟻從底下往上望,會(huì)以為金字塔成了精、連了線,若是從蛤蟆的視角看,這就是一道土長(zhǎng)城。
班長(zhǎng)說(shuō):“完工后,咱倆再用貝殼美化一下墻體。”
我腦袋暈暈的,四肢軟軟的,恨他都沒(méi)了力氣。
9
班長(zhǎng)說(shuō):“部隊(duì)的日子,不能論天數(shù),也不能論周論月,要論季度。”
有點(diǎn)自欺欺人,但切實(shí)可行。
仿佛真的只是眼珠一轉(zhuǎn),冬季就來(lái)了。場(chǎng)部封了門(mén)窗,我們各回各連。在連隊(duì),跟我接觸的人,掰著手指都能數(shù)過(guò)來(lái)。除去日常訓(xùn)練,大部分時(shí)間我都貓?jiān)谒奚峥磿?shū),日子過(guò)得快與慢,似乎與我無(wú)關(guān),直到這年的第一場(chǎng)雪將營(yíng)區(qū)染白,我才霍然發(fā)現(xiàn),班長(zhǎng)要退伍了。
掛了上等兵軍銜的我,第一次經(jīng)歷送老兵。
紅著眼圈,整理摘掉肩章、領(lǐng)花的舊軍裝,托運(yùn)包裹,出趟營(yíng)區(qū),買(mǎi)一雙早就看上過(guò)去不讓穿的新皮鞋或旅游鞋,懷揣復(fù)雜的情緒串串連隊(duì),告別一下老鄉(xiāng)、老戰(zhàn)友,參加一次歡送晚會(huì),唱上幾首軍歌,扯著嗓子盡情吼一吼,然后回到宿舍,吸著煙等天亮……老兵退伍的這些過(guò)程,我第一次接觸,卻感覺(jué)很平靜,好像自己不屬于這里,只是一個(gè)旁觀者。
我以為,即使班長(zhǎng)他們坐上火車(chē),在車(chē)窗內(nèi)莊嚴(yán)敬禮、拼命揮手,眼含熱淚、依依惜別,即使那冰冷的鐵軌將他們引向各自歸途,從此不會(huì)有交集,“再見(jiàn)”成為美好愿景,我也不至于感傷——鐵打營(yíng)盤(pán)流水兵嘛,老的不去,新的怎么來(lái)?
但我沒(méi)想到,那天夜里,班長(zhǎng)從俱樂(lè)部回到宿舍后,鄭重地交給我一個(gè)棕色硬殼筆記本:“要走了,沒(méi)啥送你的,這個(gè)筆記本留作紀(jì)念,心煩的時(shí)候,可以在上面寫(xiě)寫(xiě)畫(huà)畫(huà)……”說(shuō)罷,沒(méi)等我反應(yīng)過(guò)來(lái),他兀自上床睡了,很快打起標(biāo)志性的呼嚕,忽高忽低,時(shí)斷時(shí)續(xù),像是胸腔里有人在哽咽。
筆記本的扉頁(yè)上,寫(xiě)著這樣一句話:當(dāng)兵后悔三年,不當(dāng)兵后悔一輩子。
淚水,在我的眼中慢慢匯聚,逐漸滾燙,最終奪眶而出。這一夜,班長(zhǎng)睡得很沉,絲毫不像明早就要告別軍營(yíng)的樣子,而我,卻翻來(lái)覆去無(wú)法入夢(mèng),感覺(jué)睡了一年的硬床板很是硌得慌。這是短暫的夜,又是漫長(zhǎng)的夜,比我和崔芷若在紅棗林的那個(gè)夜晚更加短暫,更加漫長(zhǎng)。
翌日上午八點(diǎn),班長(zhǎng)那批退伍老兵坐上了火車(chē)。
車(chē)站里人來(lái)人往,卻因我們的存在,變得格外安靜。老兵們大都沉默,表情戚戚,與送行的戰(zhàn)友們不敢過(guò)多交流,唯恐失控。班長(zhǎng)也是如此,早早就帶著笑上了車(chē),步伐矯健,甚至虎虎生風(fēng)。然而,隔著車(chē)窗,我發(fā)現(xiàn)他坐到座位上后,目光有些空洞,愣了片刻,使勁摩挲幾下臉,扭頭看見(jiàn)了我。
“班長(zhǎng),有空常回來(lái)看看!”我說(shuō)了句自己都不信的話。
車(chē)玻璃很厚,但班長(zhǎng)顯然聽(tīng)到我的話了。他想笑,只是咧咧嘴,點(diǎn)了點(diǎn)頭。
我的鼻子有些酸,我知道,這時(shí)候那句話再不問(wèn),估計(jì)永遠(yuǎn)都沒(méi)機(jī)會(huì)了。“班長(zhǎng),那天夜里,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嗎?”我把憋了整整一年的話喊了出來(lái)。
班長(zhǎng)還是點(diǎn)點(diǎn)頭,靠近車(chē)窗,也大聲說(shuō)了三個(gè)字:“筆記本。”
像被誰(shuí)猛推一把,列車(chē)極不情愿地向前頓一下,待看清伸向遠(yuǎn)方的鐵軌后,撒起了歡。最后一節(jié)車(chē)廂駛過(guò)時(shí),我猛然仰起頭,想將洶涌的酸澀壓回體內(nèi),卻在這一瞬間發(fā)現(xiàn),天空又飄起了雪花。
一片,兩片,三四片……每片都顯得那么孤單,放眼望去又氣勢(shì)磅礴。
這個(gè)冬季最后一場(chǎng)雪融為液體復(fù)蘇了大地,營(yíng)區(qū)向陽(yáng)的墻根下,已有春草萌發(fā),我正在考慮今年干點(diǎn)啥時(shí),排長(zhǎng)找到了我。如今,排長(zhǎng)仍是排長(zhǎng),只不過(guò)不再帶新兵,而是炮一排的排長(zhǎng)了。
“高自攀,連長(zhǎng)讓我找你談?wù)劇!迸砰L(zhǎng)笑瞇瞇地坐到我對(duì)面,兩條深深的法令紋使他顯得比實(shí)際年齡大了許多。
我也笑,有點(diǎn)兒傻。
“是這樣,這不,新兵馬上下連嘛……”排長(zhǎng)看了看我,“但今年,咱們連的訓(xùn)練任務(wù)重,暫時(shí)沒(méi)找到合適的新兵接替你守靶場(chǎng),連隊(duì)考慮到你熟悉情況……”
“我去。”我直截了當(dāng)?shù)卣f(shuō)。
“好!”排長(zhǎng)站起身,很高興,“不過(guò),要有心理準(zhǔn)備,估計(jì)老兵也抽不出人來(lái)陪你。”
我愣了一下。
“當(dāng)然,若有意見(jiàn),可以提,我向連長(zhǎng)匯報(bào)。”排長(zhǎng)原地踱了幾步。
“我自己去。”我將視線甩向窗外。楊樹(shù)梢上,又掛滿了樹(shù)吊,像一個(gè)個(gè)倔強(qiáng)的問(wèn)號(hào)。
10
場(chǎng)部領(lǐng)導(dǎo)說(shuō),連隊(duì)派我一個(gè)人守本連靶場(chǎng),是對(duì)我的極大信任。
我承認(rèn)。
事實(shí)上,我也的確喜歡一個(gè)人守著幾排房子。出門(mén)是一望無(wú)際的遼闊,進(jìn)屋是一成不變的內(nèi)務(wù),在外可以吼幾嗓子,興致來(lái)了,鹽堿地上翻幾個(gè)跟頭,打幾套軍體拳,曬曬太陽(yáng)出出汗,沒(méi)啥不好的;回宿舍可以看看書(shū),發(fā)發(fā)呆,寫(xiě)寫(xiě)信,推算一下李白到底出生在國(guó)內(nèi)還是國(guó)外,也沒(méi)啥不好的。
只是我收到的信越來(lái)越少。
重新回到靶場(chǎng)后,直到外面的鹽池快被雨水填滿,我才收到本年度的第一封信,是楊苗苗寄來(lái)的,僅一頁(yè),沒(méi)寫(xiě)滿。她在信中說(shuō),孫虎自己到崔芷若家提親了,開(kāi)著小汽車(chē)來(lái)的,開(kāi)始崔父還不同意,架不住全家人都樂(lè)意,最終只得點(diǎn)頭,崔母在村里吹噓了好幾天準(zhǔn)姑爺,說(shuō)孫虎如何有出息,將來(lái)兒子可以跟著姑爺一起發(fā)財(cái)……楊苗苗還說(shuō),她去縣城一家罐頭廠上班了,工資還可以,就是有點(diǎn)累——我沒(méi)回信。
想來(lái),父親覺(jué)得我已穩(wěn)定,也不再給我寫(xiě)勵(lì)志的信。
沒(méi)有來(lái)信,就不必回信,倒少了件麻煩事。
我越來(lái)越寡言,去場(chǎng)部有事辦事,沒(méi)事就早早地回連隊(duì)靶場(chǎng)。去年跟班長(zhǎng)一起時(shí),我倆還每天去場(chǎng)部吃飯或者打飯回來(lái),如今,我干脆自己做,除非集合開(kāi)會(huì),或者想去場(chǎng)部服務(wù)社買(mǎi)日用品,我才步行幾公里趕過(guò)去一趟,碰到伙食不錯(cuò),偶爾也會(huì)吃上一頓兩頓。最初,場(chǎng)部領(lǐng)導(dǎo)還打電話過(guò)來(lái),命令我前去就餐,后來(lái)見(jiàn)我獨(dú)自開(kāi)伙并沒(méi)變瘦,且提醒一次管用幾天,不說(shuō)我又不去了,方圓百里也沒(méi)啥能讓人犯錯(cuò)的機(jī)會(huì),漸漸地放寬了對(duì)我的要求。
我當(dāng)然有事要忙。
及時(shí)修繕維護(hù)幾排屋舍,確保連隊(duì)來(lái)實(shí)彈射擊時(shí)能有地方居住,有情況了,要及時(shí)向場(chǎng)部、向連隊(duì)匯報(bào),小到換塊玻璃,大到換門(mén)換窗,均需報(bào)告……還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我自找的了——和班長(zhǎng)一起修的炮陣地,經(jīng)過(guò)去年的雨季,熬過(guò)寒冷的冬季,又被今年幾場(chǎng)雨沖來(lái)泡去,早不成了樣子,我打算在年度實(shí)彈訓(xùn)練前將它修葺一新。這么做,并不是想讓連隊(duì)表?yè)P(yáng)我,而是班長(zhǎng)退伍了,我不能讓他的精氣神也退伍。少了一半的戰(zhàn)力,干起活來(lái)還是蠻累的,好在那土長(zhǎng)城的坯子還在,我只需要修修補(bǔ)補(bǔ)就行。
唯一不足的,是我感到了孤獨(dú),那種渴望有人卻又不想接觸人的孤獨(dú)感。
入伍第三年的春天,連隊(duì)打算換我回去,我說(shuō)我已經(jīng)熟悉這里的一切,不想回去,考慮到在我的看守下,連隊(duì)靶場(chǎng)的基礎(chǔ)設(shè)施維護(hù)得很好,連隊(duì)領(lǐng)導(dǎo)也就同意了,并給我安排了一個(gè)新兵。這個(gè)家伙,比當(dāng)年的我還沉默寡言,基本上問(wèn)一句答一句,若非如此,他可以三天不說(shuō)話。
這恰恰符合我的選人標(biāo)準(zhǔn),我不喜歡鬧騰的。
這年冬季,以楊樹(shù)梢最后一批黃葉悄然落下被我們掃進(jìn)垃圾堆為標(biāo)志,毫無(wú)特點(diǎn)地到來(lái)了,就在同年兵開(kāi)始做退伍準(zhǔn)備的時(shí)候,我收到了一封來(lái)自老家的信,楊苗苗寫(xiě)的。信中,她告訴我,家鄉(xiāng)的縣城變化很快,但楊元帥營(yíng)似乎沉睡了,依舊老樣子,只是北山的泉水漸漸枯竭,還有那些棗樹(shù)行里的棗樹(shù),也都長(zhǎng)瘋了,只見(jiàn)葉子不見(jiàn)棗,被人們砍掉了一大批。最后,她談到了以往我最想知道的內(nèi)容:崔芷若在中秋節(jié)結(jié)婚了……很奇怪,楊苗苗所說(shuō)的一切,似乎與我無(wú)關(guān),沒(méi)在我心中激起一點(diǎn)兒波瀾。只不過(guò),這天夜里臨睡前,我從枕頭包摸出了那塊早已顏色變淺、薄如蟬翼的手帕,將它疊整齊,壓在了迷彩包的最底層。我想,自己再不會(huì)去觸碰它了。
再有一個(gè)多月,老兵就該退伍了,連隊(duì)的訓(xùn)練也轉(zhuǎn)為共同科目,每天走走隊(duì)列,跑跑步,安排一下教育,緊張的氛圍仿佛消失。其實(shí),所有涉及退伍或是留隊(duì)問(wèn)題的人,心里都踏實(shí)不下來(lái)。我反倒很坦然,還請(qǐng)?zhí)旖蚣畱?zhàn)友幫我熟悉了熟悉炮班專業(yè),練得很投入——我的想法很簡(jiǎn)單,退伍回去了,萬(wàn)一被老家人問(wèn)起來(lái),至少吹牛的時(shí)候不會(huì)露怯。
一周后,退伍工作將全面展開(kāi)。我沒(méi)想到,在這個(gè)關(guān)鍵時(shí)刻,老排長(zhǎng)也是現(xiàn)在的副連長(zhǎng)將我叫到了四百米障礙訓(xùn)練場(chǎng)。我一肚子不解地趕過(guò)去時(shí),先是發(fā)現(xiàn)他的兩道法令紋更深了,接著在他眼中看到了神秘的喜悅。
“考慮到這幾年你對(duì)連隊(duì)所做的貢獻(xiàn),指導(dǎo)員讓我問(wèn)問(wèn)你,想不想留隊(duì)?”副連長(zhǎng)說(shuō)。
我愣了一下,像是沒(méi)聽(tīng)清,很快又明白過(guò)來(lái)。“當(dāng)然!”我說(shuō)。
“行了,回去等消息吧。”副連長(zhǎng)說(shuō)完,微微一笑,轉(zhuǎn)身走了。
這個(gè)冬天,一場(chǎng)雪沒(méi)下。
好在,開(kāi)春后,尤其進(jìn)入初夏,雨一場(chǎng)比一場(chǎng)大,駐地才擺脫了干旱局面。這時(shí),我已經(jīng)是一名上士班長(zhǎng)了,卻是在炊事班。我認(rèn)為,炊事班的作用起碼頂?shù)蒙习雮€(gè)指導(dǎo)員,一天伙食的好壞,能直接影響到班排訓(xùn)練的效果。為此,我努力投入,干得風(fēng)生水起,每當(dāng)聽(tīng)到戰(zhàn)友們夸贊饅頭蒸得好、菜炒得香時(shí),我從內(nèi)心深處感到驕傲。
原來(lái),我高自攀最擅長(zhǎng)的是做飯。
哦,不,應(yīng)該說(shuō)是組織幾個(gè)人去做好飯。
在這種自我滿足的喜悅中,日子很快又過(guò)去了九個(gè)季度,我成功套改成了二級(jí)士官。就當(dāng)我認(rèn)為日子這么過(guò)下去也挺好時(shí),我那可愛(ài)的民兵連長(zhǎng)父親給我打來(lái)了電話,要我務(wù)必在一個(gè)月內(nèi)回家一趟。初始我嚇了一跳,擔(dān)心家里出了什么狀況,當(dāng)聽(tīng)清是要給我介紹對(duì)象后,我在電話這端連連搖頭。
“必須回來(lái)!你都六年沒(méi)探親了,村里人還以為你出了事!”父親下了死命令。
一個(gè)星期后,我風(fēng)塵仆仆地踏進(jìn)了家門(mén)。做夢(mèng)也沒(méi)想到,母親沒(méi)啥變化,父親卻仿佛一夜之間變老了——人,真的是瞬間變老的。他的兩鬢已經(jīng)斑白,走路的時(shí)候有些哈腰,腿也不那么直溜了。父親的變化,讓我懊悔不已,六年來(lái),我是有機(jī)會(huì)回家看看的,只是一直沒(méi)去面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罷了。
我太自私了。
意識(shí)到自身存在的問(wèn)題后,父母再說(shuō)什么,我都滿口答應(yīng)下來(lái)。
“后天下午,你跟女方見(jiàn)個(gè)面。”母親對(duì)我說(shuō)。
我點(diǎn)頭,盡管我反感這種拉郎配的方式。
女方?jīng)]來(lái)我家,也沒(méi)讓我去她家,而是選在了北山坡,說(shuō)那里環(huán)境好,適合慢慢聊。對(duì)此,我嗤之以鼻。但父母之命,還是要應(yīng)付一下的,大不了到時(shí)候找個(gè)理由推掉——我主要是覺(jué)得好笑,認(rèn)為這跟電影里特務(wù)接頭一樣,神秘兮兮的。
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
我如約而至。五分鐘后,一個(gè)時(shí)髦的女子出現(xiàn)在我的視線里。她穿了一件杏黃色的連衣裙,在綠色的天地里,格外扎眼。走近了,我被驚到。
是楊苗苗。
楊苗苗變了,頭發(fā)長(zhǎng)了,還燙了卷,臉蛋不那么圓了,整個(gè)人比當(dāng)年瘦了一圈兒,個(gè)子顯得高了許多。
“怎么,不認(rèn)識(shí)啦?”她笑瞇瞇地望著我。
我一陣慌亂,忙說(shuō):“你挺好的啊……”
簡(jiǎn)單介紹過(guò)彼此的近況后,楊苗苗讓我陪她走走,于是我倆并肩朝一座小山包走來(lái)。經(jīng)過(guò)崔芷若家的棗樹(shù)行子時(shí),我驚訝地停下了腳步。
“那些棗樹(shù)呢?”
“全瘋了,只長(zhǎng)葉子不開(kāi)花,誰(shuí)還留著……”楊苗苗解釋說(shuō)。
“都砍了?”
“都砍了。”
“……”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淌了下來(lái)。
楊苗苗看到后,先是一愣,接著輕輕地抱住了我。“還有我呢……”她喃喃地說(shuō)。
責(zé)任編輯: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