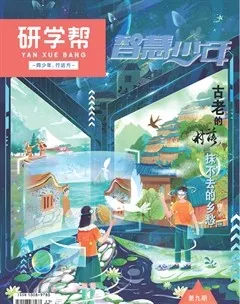古老的村落,抹不去的鄉愁

傳統村落是農耕文明的物態載體,也是人們守望精神家園的鮮活圖典。那些山水田園、民居街巷以及民俗禮儀,組合成一個個“各有其美”的小村莊。在現代化的浪潮里,保護村落的固有屬性,開發和深挖其在生態、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多元價值尤為重要。如何讓鄉村在走向振興的同時留住這份鄉愁呢?讓我們打開中國傳統古村落中的典型村落,探尋她們的蝶變之路——
蟳埔村的“海絲遺風”
福建泉州市蟳埔村(也叫潯埔村),是背山靠海的古老村落。這里的人世代以漁業捕撈、灘涂養殖為生。清晨出海撒網,日暮滿載而歸。捕魚是男人的活計,女人則手持小鉤,熟練地剝出一顆顆海蠣,留下一堆堆海蠣殼。她們身著青、藍色為主的大裾衫、寬腳褲,便于在海灘負重行走;頭發高高盤起,避免在俯身、低頭的瞬間松散開來遮擋視線,而簪滿發圍的花朵,則為扎實的日子平添幾分雅致。
勞作歸來,回到“蚵殼厝”,一家人圍坐桌前,吃一頓大海的饋贈:海蠣煎、紅蟹飯……飽腹之時,享受居室帶來的愜意。蚵殼厝是用海蠣殼建造的房屋,最早所用的蚵殼卻不是產自當地。宋元時期,滿載貨物的船只從蟳埔去往世界各地,自非洲東海岸返航時,船員用那里廢棄的蚵殼壓艙以維系空船平穩。再后來逢特殊年月,蟳埔人把這些蚵殼二次用于房建,要么與磚石混用,要么單獨嵌在墻壁、檐口……蚵殼墻堅固耐用,蚵殼厝冬暖夏涼,蚵殼疊加如同好看的魚鱗。
今日蟳埔主打文旅切入點。順濟宮,關帝廟,將軍祠……不少宮廟、祖厝、祠堂遺跡得以修復,傳統祭祀、巡香活動中,南音、什音的天籟古樂,火鼎公婆的踩街舞蹈傾情演繹。特別是蟳埔女的“簪花圍”,如今以“國潮”新屬性吸引八方愛好者。務實而開放、浪漫且包容的海絲遺風,為全新的蟳埔加滿油。
石門坎+控拜,兩個追夢苗寨
貴州威寧縣石門坎村,位于偏遠、蠻荒的烏蒙山區腹地,卻締生出當地近百年來罕見的“文化制高村”。石門坎村創制了苗文,開啟了苗漢雙語教學,開創了我國近代男女同校的先河;還創建了烏蒙山區首個西醫醫院、中國首所苗族醫院……系列巨變的推動者是英國傳教士柏格理。早年為方便磚瓦運送,他帶領鄉民打通村子與云南昭通間的一條巖路,修路取石時恰遇一扇天然石門,“石門坎”就此而來。石門坎的奇跡還有很多:每年校園體育運動會吸引學生、村民數萬人員,衍變為轟轟烈烈的民俗活動;良種種植、織紡染等的實業教育,為周邊乃至后世“經濟扶貧”提供可參閱樣本。
然而由于自然災害和歷史原因,石門坎在二十世紀50年代以后趨向落寞。近年來,國家加大扶持力度,促進當地松茸養殖等綠色產業;新一批公益人重拾柏格理的博愛事業,活躍在教育、農業等各個領域……萬眾一心,薪火相承,石門坎走在重現昔日繁榮的路上。
貴州雷山縣控拜村,就像與彩虹共生的仙境。村寨主體坐落在海拔近千米的山腰,山頂的杉木林與村寨四周的梯田相映成景,桿欄式吊腳樓群掩映其中。每個吊腳樓中堂前檐下皆建有美人靠,這個靠背欄桿的設計,既方便女子挑花刺繡,亦方便家人納涼觀景。控拜村有“中國銀匠村”之稱,苗銀鍛造技藝便圍繞“富養女兒”的傳說祖輩沿襲。昔日母親教待嫁女兒針線女紅與做人道理;父愛含蓄,父親希望在其嫁衣上縫點“銀子”作嫁妝。這些碎銀,慢慢演變成銀梳子、銀項圈、銀手鐲、銀腰帶……控拜銀飾多借鑒苗族刺繡,凸顯“大”“多”“重”的民族美感。
近年來,控拜村集企業、合作社、群眾之力,積極打造鄉村旅游與民族手工藝的結合模式。與此同時,控拜村陸續完善路面、路燈、消防、飲水工程等基礎設施,以“硬件”提升游客體驗。控拜苗寨,如其銀器,歷久彌新。
新生村,續延山的精魂
黑龍江黑河市新生村,是由神秘的鄂倫春族下山創建的村子。該村建于1953年,歷史年齡并不久遠,但就狩獵文化而言,卻是典型的“古村”。
鄂倫春族被譽為“北半球漁獵民族活化石”,遷入新村依然保留舊日習慣,專職狩獵、手工藝品制作、山產品采集等活動。這些活動塑造了鄂倫春人能歌善舞的性子,他們的歌舞多即興而起,其中“摩蘇昆”類似史詩講唱,基于“莫日根”英雄故事或自己的苦情身世,“說一段,唱一段,說唱結合”。“呂日格仁”是在狩獵歸來或喜慶節日,燃一堆篝火,人們圍著裊裊火苗唱歌踏步……而今,鄂倫春藝術團體不斷“走出去”,將本土民俗帶往全國乃至國際。
坐落在刺爾濱河與索爾其干河交匯處的新村,有如興安嶺一樣豐富的土地、森林和草原資源,在國家“興邊富民”行動中,它們得到合理的開發和利用。村民重新用樺樹皮、樺樹桿建造“斜仁柱”建筑,還原真實的游獵生活場景。瞧,他們吃著烤面圈,喝著稠李子粥,換一身狩獵皮衣穿梭在密林深處……新生村,是“興安嶺氣質”的繼續。
黃嶺西村,靜且美
北京門頭溝區黃嶺西村,迄今已有幾百年建村歷史。村落主要依東、西、北路分別通往齋堂、清水、柏峪村鎮的京西古道,承擔起交通及商貿往來功能,使該村空前繁盛。到1909年京張鐵路開通,古道的商業功能被逐步取代,黃嶺西村才轉化為“農業村”。
黃嶺西村農業元素突出:村落主體依托鳳凰山脈面北鋪陳,光照、溫度適宜,梯田、古柏錯落有致。鳳凰山周圍拱列九個山頭,是謂“九龍朝一鳳”的吉祥意象。山谷之中的排水體系遵循西高東低的地勢建成,確保村落具備有效的泄洪功能。村內尚存諸多清代及民國建筑,灰瓦屋頂的三合院、四合院以及院內外的磚雕、石礅,恍惚呢喃著舊日絮語。
近代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期間,門頭溝區是齋堂川抗日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當時僅有百戶人家的黃嶺西村組織全村青壯年組成“黃嶺西排”。這些男兒不懼艱險,奮勇殺敵,用熱血和生命捍衛尊嚴,鐫刻下紅色印記。
今天,勤勞聰慧的村民以生態文化和紅色文化助力“旅游村”:葡萄采摘園、花椒采摘園為主的觀光線路主打“怡情”;《山梆子》《蹦蹦戲》等戲種猶見淳樸;英雄墻、英烈雕像弘揚古村人的家國精神……自然景色與人文景觀并存的黃嶺西村,是大美入心脾的存在。
時代變遷,有人離開村落奔赴山海,有人留守村里呵守舊地。小村或繁華,或寂寥,或在兩者之間兜轉……而循著鄉村建設的步履,每一個村落,都將煥發新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