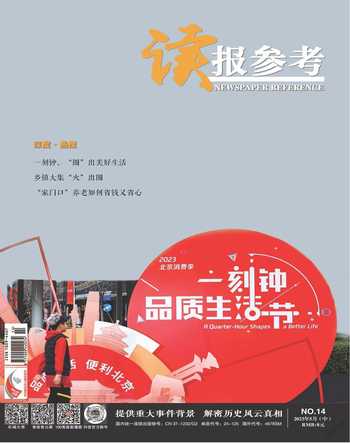“上海攤”有序回歸上海灘
晚上9點后,走在上海街頭,會看到一幅與白天全然不同的景象。
“這是我10年來第一次在上海看到炸串攤。”在青浦區住了10年的一位上海居民,一邊感嘆一邊將鏡頭對準炸串攤——這值得發一條朋友圈來紀念。
類似的景象也發生在數十公里外的閔行區。晚上9點后,虹梅路與東蘭路地鐵站相隔不過2公里的距離內,幾乎每個十字路口都有品類豐富的“上海攤”,年糕車、水果車、豬肘子車、炒飯攤,甚至是賣運動鞋的車。
去年9月23日,上海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上海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簡稱《管理條例》),其中對設攤不再“一禁了之”的內容最受關注,對設攤經營、占道經營從“全面禁止”改為“適度放開”“有序設攤”的消息沖上了微博熱搜。
今年2月20日,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發布公告,為進一步加強設攤經營活動管理,規范市民集市、創意夜市、分時步行街、超出門窗和外墻經營(簡稱“外擺位”)等新型設攤行為,相關部門研究擬定了《關于進一步規范新時期設攤經營活動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簡稱《指導意見》)。這也標志著“上海攤”在逐步規范。
信號
小雅和源源幾乎是同一時間開始擺攤的。去年9月,小雅來到上海最大的露天夜市——泗涇夜市時,攤位并不多,只有一些食品商家將攤位外擺在路邊。即使在后來圍滿了攤位的花壇四周,也只有包括小雅在內的兩家攤位。“攤位就在9月開始的3個月內迅速聚集了起來,慢慢形成了現在的規模。”小雅回憶。
源源也差不多在那時到泗涇夜市擺起了攤,賣梅花小蛋糕和冰湯圓。從事了十幾年美容行業的源源,2019年開了一家美容店,在疫情影響下關了門。2022年9月底,源源決定從江蘇到上海擺攤,賣小吃。
選擇到上海的原因有二:一是上海經濟好,擺攤能賺錢;二是上海將有序開放設攤的信號給了她信心,“新規一出,很多人都躍躍欲試”。
“95后”小雅原本在一家餐飲店做店長。2022年初的3個月封控期,住在集體宿舍里的員工們缺少食物,工資也被拖欠,所有重擔都壓在了小雅身上。解封后,小雅便辭了職。憑借之前在餐飲店工作的經驗,小雅來到泗涇夜市擺攤,她賣的烤苕皮和雞蛋仔接連成了夜市的人氣爆款。在小雅看來,她其實是被動地站到了風口之上,擺攤以來,每個月的收入比之前上班時翻了好幾倍。
夜市里“網紅”小吃“來個蛋堡”的攤主大彬是黑龍江人,從南京一所211高校的機械工程專業畢業后,他一直在大連一家半導體芯片企業工作。決定辭職擺攤后,大彬在老家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學習了5種小吃的制作方法,來到上海后,又花了一個多月考察擺攤地點,從各大夜市看到各類商務寫字樓周邊,最終在泗涇夜市支起了一個攤位賣雞蛋漢堡。
最初,父母對大彬的選擇非常不認可。現在,生意好時,一天能賣大幾百個雞蛋漢堡,收入比上班時翻倍了,大彬的媽媽也來到上海當幫手。“現在,幾乎每天都有不少年輕人到攤位前問我擺攤的事。”大彬說。
在泗涇夜市擺攤幾個月后,去年12月,大彬還是選擇花8000多元/月租下泗涇夜市的半張門面,在店鋪門前外擺賣雞蛋漢堡。“野攤并不穩定”,大彬解釋,夜市實際上也是自發聚集的“野市”,而且因為攤位不固定,經常會有攤販因為搶位而打架。夜市地面污水橫流、布滿油污,十分黏膩。夏天不可避免地有蒼蠅蚊蟲和揮之不去的異味。這也是小雅和源源這樣年輕的擺攤新人有些接受不了的。“雖然是擺攤,但我們都想擺干凈衛生的、合規穩定的攤。我們也想有回頭客哩!”源源說。
今年3月,相關部門全面整治泗涇夜市。夜市在3月1日臨時關閉,3月31日,經歷一個月重整,夜市重新開張。原本雜亂無序的夜市變了樣,夜幕降臨,上海松江泗涇地鐵站3號口的泗涇夜市迎來了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候,蚵仔煎、甑糕、肉夾饃、車輪餅、卷面皮、鐵板豆腐,這里匯聚了全國各地的小吃。重整后的夜市外擺攤位按照“準入制”管理,由市場監管局等職能部門審核從業者健康證明、身份信息、衛生許可證等,通過后再行營業。
大彬對泗涇夜市的變化如數家珍,過去地面上烏黑的油污不見了,有了自己的固定攤位后,大家對攤位環境更愛護了,收攤后自己會打理;晚上收攤后,也會有物業的人進行打掃。“過去夜市里幾乎看不到垃圾桶,吃完東西的包裝袋只能亂扔,現在垃圾桶都有幾十個。”
轉變
對老何這樣擺了6年多“野攤”的“老人”來說,一個顯著的感受是,路邊擺攤的人越來越多了。“各式各樣的都有。”老何說,原本擺攤的地鐵口只有他1家,今年陸續冒出了5家小吃攤。
一家福建的鞋廠甚至在上海各個區域設置了26個地攤點,用于清理上海倉庫的庫存。店鋪租金太高,一天也清不出去幾雙,而地攤清貨的效果不錯。近千雙運動鞋散落在地面上,幾個小伙子扯著嗓子喊著:“品牌運動鞋,通通60、60一雙!”因為城管晚上仍會對“野攤”進行管理,一晚上可能只能擺上一個多小時,但好的時候能賣出近百雙。該名攤販表示,去年12月份后,雖然城管也會管,有時候可能需要交數額不等的罰款,但至少不會把車拖走了。“城管來了,我們就走,那天不賣了就是。”
老何這幾個月再也沒有被城管連瓜帶車地拖走扣留了,老何戲稱之為“文明執法”。不過,老何十分清楚,即使“野攤”越來越多,執法也更加人性化了,但“野攤”仍然是不被允許的。“還是會有城管的,不可能所有地方都能擺攤。”城管工作人員告訴老何,會規劃出允許的地方進行擺攤,未來可以去指定的地方擺攤。
實際上,地攤正在上海有條件地回歸。2022年12月1日施行的新修訂版《管理條例》,對設攤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新版條例二十一條規定,“區人民政府會同市有關部門根據需要……可以劃定一定的公共區域用于從事經營活動”。這也給了《指導意見》的政策依據。《指導意見》在細化擺攤細則方面提出的“分類分區管理”是一大亮點。允許區級政府劃定設攤開放區,設置特色點、疏導點、管控點。
源源非常期待《指導意見》進一步落地,她的規劃是今年在上海開4-5個攤位。“不擺野攤,都要是正規的攤位。”源源和小雅剛剛合伙租下距離泗涇夜市40多公里的寶山區“香吧拉”夜市的一個攤位,那是一個經過政府備案的新開夜市。源源也會趁周末入駐一些美食集市、臨時夜市。“現在這類夜市比去年我剛來上海時多多了。”源源經常挑選不過來,這些美食集市的租金100-300元/天不等,有些夜市為了吸引人氣甚至會讓攤販免費入駐。
小雅也計劃著在上海擺更多攤。她不認為擺攤是生活所迫,年輕人選擇擺攤更多是為了賺錢和自由,大家都厭倦了每天擁擠的早高峰地鐵和格子間里寫PPT的枯燥與重復。
曾經,小雅覺得不可能一直擺攤,最終肯定要開個店,那樣才能“穩定下來”;但現在,她有了新想法,近兩年來,上海不斷鼓勵“人間煙火氣”的回歸,外灘楓徑、安義夜巷、凱田路夜市以及商業體沿街外擺位等具有特色的商業形式不斷涌現。擺攤也在逐漸正規化、合法化。“也許未來地攤也會成為一種正經營生,可以一直擺下去!”
(摘自《經濟觀察報》丁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