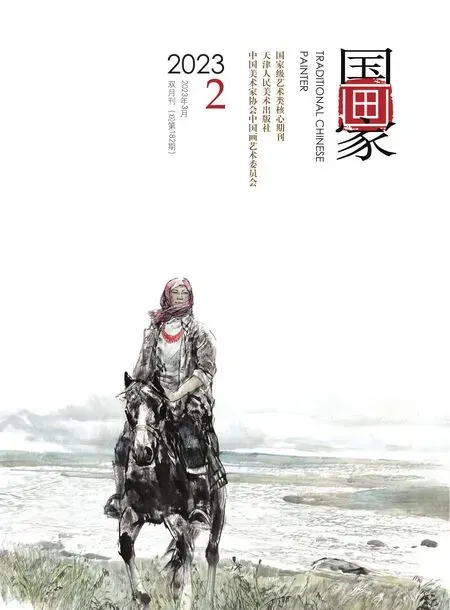中國畫革新的兩種途徑:以顧一塵與李碩卿為例
福建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葉璐
在中國畫的近現代進程中,自民國初年康有為提出“中國近世之畫衰敗極矣”,到新文化運動陳獨秀提出“美術革命”,批判舊藝術而提倡寫實主義后,關于中國畫的變革、發(fā)展及其途徑的問題,就成了民國畫壇和中國畫人討論和探索的一大焦點。許多美術家如徐悲鴻、林風眠、高劍父、汪亞塵等都在此問題上各抒己見并付出實踐努力,美術界也因此產生了形形色色的“新國畫”,反映著這一文化語境下中國畫人對革新中國畫的強烈愿望和探索進取精神。此種影響在時空上是廣闊且持久的,與之相呼應,出生于20世紀初、成長于民國中后期的福建泉州畫家顧一塵(1906—1963)和李碩卿(1908—1993),在持續(xù)著的中國畫革新變局之大時勢潮流當中,自然也著眼于同樣的繪畫歷史任務。他們各自對中國畫現代化進行了不同的探索,并發(fā)展出不同的藝術傾向,前者倡“中國畫的二重表現”,開文人畫一新途徑;后者中西兼學,以西畫寫實主義技法融入中國傳統筆墨,開中國畫一新生路。二者之才華與畫名在民國期間都已引人注目,于泉州畫界各有地位。
顧一塵和李碩卿兩人僅相差兩歲。查閱史料可以發(fā)現,他們在泉州的藝事活動中有著許多的交集,同時頗有意思的是,作為同一地域的同代畫家,其個體無論是在藝術還是性格方面,都有著鮮明的差異。但是,其現實中的個人性格、藝術感知和實踐活動方式是相統一的。“人物的性格不僅表現在他們做什么,而且表現在他們怎樣做。”[1]同時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共識中,也有“畫如其人”“書如其人”等觀念。對于畫家而言,其個體的藝術探索和現實個性的差異,很大程度上也對他們的藝術成就和個人命運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從而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美術的發(fā)展進程。
顧一塵,又名金治,字寶輥,別署慧癡、癡寅,泉州市后街彩筆巷人。他從小顯露出畫才,13歲前就以畫稿供人刺繡。1921年至1925年,他就讀于泉州中學,畢業(yè)后留校任教,教授圖畫等學科。21歲組織“桂花吟社”,22歲與林子白合刊出版《叢畫合集》,其時作品已可窺見大家風度。[2]1928年,顧一塵考入上海藝術大學,師從潘天壽。1929年,因父喪肄業(yè)回閩,此后一直在泉州、廈門的多所學校擔任教職,并從創(chuàng)作上致力于國畫現代化的努力,同時創(chuàng)作了大量舊體詩和新詩。1933年加入由孫福熙、徐悲鴻、汪亞塵等人組織,由孫福熙任社長,成立于杭州的“藝風社”美術社團,并成為該社的主要骨干人員之一。[3]顧一塵的國畫作品和詩文多次刊登在《藝風》月刊上,并參加了“藝風社”在上海、南京、廣東舉行的第一、二、三屆美術展覽會。[4]顧一塵擅畫山水、花鳥,文學造詣也精深,對史學、考古、佛學也頗有研究,還通英語、日語。他的博學多才,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蜚聲畫壇。《中國美術年鑒·1947》一書中載其作品《鴛鴦》和論文《中國畫的二重表現》,述其“畫風崇創(chuàng)造,重內容,尚革新”,“多畫燕子,作風簡徑獨特,時論重之”。[5]
李碩卿,原名松林,字云田,祖籍泉州惠安涂寨下樓村。由于家境貧寒,9歲才入私塾,其時已能臨摹“七十二賢人像”。1924年,考入陳家楫創(chuàng)辦的泉州唯一的美術學校——泉州溪亭美術專科師范學校。為謀生計,1925年曾在泮宮口開設“藝真美術社”,以賣畫為生。[6]1927年,李碩卿考入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插班就讀西畫系三年級,同時選修中國畫,師從潘天壽、陳宏、王個簃、諸聞韻等國畫名家,始學國畫海派畫風。1928年畢業(yè)后回閩,于泉州、廈門等地多所學校任美術教員,后兼任國立海疆大學美術講師,并致力于國畫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中國美術年鑒·1947》一書中載其多幅作品,可以看出他的國畫在20世紀30、4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中西結合的試驗,書中述其“因感國畫取材距離現實太遠,遂轉移方針,專以實際生活動態(tài)及一切有關復原工作等為題材”,“以畫潤所得雪廬一座,同道過從甚密”。[7]
一、早年求學及生活經歷的影響
顧一塵和李碩卿的出生年代,同處于20世紀初,是中國社會新舊交替、中西文化交匯的思想大變革時代。科舉制度的廢除與傳統美術教育的蛻變,使得他們同樣都接受了新式教育及專門的美術高等教育。因此在求學軌跡上,兩人的經歷基本類似。
他們在幼時都曾以“四書五經”為蒙養(yǎng)之學,接受舊式傳統文化教育。這是由于泉州民國初年時在一定程度上仍有相當數量的私塾存在,這樣的儒學啟蒙教育是他們文化結構中的基本成分。少年時期,他們在繪畫上的學習基本處于自然萌發(fā)的狀態(tài),嚴格來說還沒有經受過系統的專業(yè)教學訓練。至中學畢業(yè)后,他們往藝術方向發(fā)展的趨勢逐漸明確化。顧一塵身兼圖畫科教師的同時已有畫集面世,李碩卿則入泉州溪亭美術專科師范學校正式接受專門的美術教育,在這期間他已自立畫室,二人在繪畫上的發(fā)展都有較強的自我意識,以畫家身份立足于社會的理想已經初顯。隨后,他們又都進一步求學于上海的美術高等學校,雖然就學時間都較為短暫,但因在當時系統的新式美術高等教育中,他們得以充分吸收中、西文化藝術及理論等學識養(yǎng)分,受多位名師指導和同學器重,不僅打開了寬闊的藝術視野,外在的技藝和內在的學養(yǎng)也均得到了提高和發(fā)展。這些都促使他們能夠跳出傳統藝術的窠臼,順應時代發(fā)展的潮流,進而對他們個人藝術風格的選擇和探索,以及藝術目標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前導作用。
另一方面,家庭環(huán)境及童年經驗對他們的個人性格品質,乃至才識藝能同樣也都有著重要的影響。顧一塵和李碩卿幼時家境都較清貧,但家世卻不相同。顧父為清邑庠生,故能為兒子親授漢文詩詞,且“督課甚嚴”。[8]長期的古典文學的熏染,蒙養(yǎng)了他恬淡、超脫、溫良的性情。他善畫的同時也善作詩,既是畫家也是詩人,繪畫也極富詩情,文學修養(yǎng)頗高,學識廣博,情操高雅,這種純凈的文人性格,正是源于家庭教育的滋養(yǎng)。而李碩卿的父親和祖父皆是以種菜為生的農民,李碩卿自小隨父種菜賣菜,長期的勞作給他帶來的是對現實生活足夠深刻又切實的體會,從而形成他對于現實生活的情感底蘊。另外雖然李父并非文化人士,但他對制作傳統花燈工藝卻十分擅長,這對于聰敏好學的幼年李碩卿來說不可不謂是一種美育上的啟蒙與熏陶。
通過以上對比,我們對此二人個性與生活的異同有了一定的了解,進而對他們的個人藝術發(fā)展傾向及創(chuàng)作表現進行研究。
二、對于中國畫革新的思考與探索
在面對傳統中國畫如何突破舊的羈絆,即國畫的改良和革命、國畫現代化這個重要問題時,顧一塵在青年時代就有著鮮明的“革新”立場和深刻見解。他曾在1935年的《藝風》月刊雜志中發(fā)表《從新國畫談到我所理想的現代國畫》一文,對于“中國畫的改革,是否一定要西化”的問題,他認為這還是“一個疑問”。他說:“中國繪畫的窮盡,只是內容思想的窮盡,而不是畫法技巧的窮盡。國畫的記號式的畫法,雖然是古舊的,死板的,有窮盡的,但我們的意匠、思想卻是新穎的,多變化的,無窮盡的。”他用文學來打比方:“我們用的也不過那幾千字或幾萬字的記號在湊來湊去,然而古今天下的大哲理、大文章、大著述,還可以在百千萬年間繼續(xù)有新穎的產生。繪畫和文章所用的記號雖然不同,但應用它來傳達思想情感卻是一樣,然則國畫的窮盡又何必歸罪于呆板古舊的記號與畫法而必西化之呢。”[9]可見,比之國畫西化的改革方式,更讓他認同的,是應該對國畫自身的藝術語言進行改革,需要有新穎的思想,產生新穎的技巧,而不能是“西洋畫在國畫紙上的搬移”。
他繼而又發(fā)表《再談現代國畫和畫家應有的修養(yǎng)》一文于《藝風》月刊上,從積極方面表明畫家該如何追求藝術的進步和充實。他贊同孫福熙、汪亞塵諸先生提倡的“接近自然,觀察自然”,進一步提出了“改造自然”之法,即畫家的修養(yǎng)應著力于:第一,改造的能力涵養(yǎng)在于多讀書以鍛煉腦筋思想,求筆墨與胸襟兩大特色。第二,技巧的修養(yǎng)則須采取科學方法與精神。[10]在這兩點上,他又對中西畫的優(yōu)劣勢做出了分析,認為國畫比西畫之高明在于國畫家對待自然只是“利用它來表達自己的意匠”,下筆時自然是受其支配的,“寫其神”而非“描其質”。但西洋人知道分析自然,觀察出透視、解剖及光色的變化等道理,這是死守古法的畫家所缺的修養(yǎng)。他看到了中西畫之互補的地方,技術的提高應受科學的洗禮。第三,現代事物的入畫。“所以洋樓也好,汽車也好,車夫、小販、西裝、旗袍、電燈、煙卷……”都可畫起來,“以后它們在一般人的眼中也就有詩情畫意了”。[11]可見,對于現代國畫的理想,以及如何實現這個理想,顧一塵抱有非常大的熱情。他的這些觀點,也反映出了他對于中國畫現代化的前途認知和思想傾向,基本上是以傳統為本位,力求新的思想情感、新的技巧,畫新的事象,重視學養(yǎng),從而實現藝術、自然與人生的統一。
結合其個人藝術創(chuàng)作上的中國畫革新實踐,顧一塵還寫了《中國畫的二重表現》一文,此文載于《中國美術年鑒·1947》。顧一塵從中西方繪畫發(fā)展史來洞察中國畫特有的二重表現:西方繪畫到19世紀中葉后才發(fā)生了自“再現”到“表現”的革新趨勢,而中國繪畫自唐以后吳道子就開始了表現的畫風,11世紀的蘇東坡更進一步要求“于筆墨形象的表現以外,內容方面也要有深刻的表現,使人于感官的刺激以外,更要求一種詩的意境、詩的趣味,也就是繪畫的內在生命的充實豐滿,而給人以心靈上的刺激,這也就是中國畫特有的二重表現”[12]。顧一塵對中國畫,尤其是傳統文人畫的“畫中有詩,詩中有畫”的藝術境界給予了充分肯定,這也是對思想學問和筆墨胸襟的再次肯定。想要創(chuàng)造出有內在生命力的中國畫,一幅畫要表現什么?怎么表現?他認為表現的方法和作詩完全相同,這是他特別強調的,即繪畫和文學,尤其是和詩歌的相通的關系。“詩歌的最高表現的詩法是用象征、暗喻或擬人化,詩人常把自己的感情付于自然物”,“繪畫的表現也何嘗不應用這擬人化的感情移入呢”,[13]他自己嘗試使用擬人、象征、明喻、暗喻等多種詩化表現手法創(chuàng)作了許多繪畫作品,如《吊影》《追求》《寂寞中的不寂寞》《舞乎風》《希望》等,可以感受到,這些畫名也如同詩名一般充滿了清新夢幻般的文學色彩。他還批判了那些承繼宋元以后文人畫派余緒的國畫家,認為他們把文人畫最主要的表現問題給忘卻了,做的是棄本逐末的“不求形似”和“逸筆草草”,甚至攻擊一切技巧,使文人畫變得毫無生氣,變?yōu)椤傲髋筛袷降拿~”。[14]總的來說,中國畫的“二重表現”,是顧一塵對文人畫所采取的積極肯定的態(tài)度,也是他所認為的對國畫革新的一種努力。他的認識,深度地把握了藝術的情感與表現的本質,也奠定了他治藝的方向。
上述顧一塵在20世紀30、40年代發(fā)表的理論文章,反映了他對國畫革新這一問題從“理想”到找到明確的實踐方向的一個認識過程。同時期的李碩卿,卻對這一問題另有不同的探索過程。
李碩卿未曾發(fā)表過相關的理論探討文章,但這不代表他對自己的繪畫方向沒有理性的思考和選擇。應該注意到,在這一點上,他最主要的表現,一是對自己的繪畫類型做了因地而變的轉型,二是對自己的繪畫方針做了因時而變的調整。關于前一點,可追溯到他在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時主攻的是西畫方向,嚴格來說,國畫不是他的主科。作為西畫系畢業(yè)的學生,他從上海返回泉州后,起初也曾為某華僑畫過大幅油畫肖像,但終因西畫在當時的泉州并無很好的現實發(fā)展條件,不久便轉而攻研國畫,自此成為一名國畫家。關于后一點,首先,據《中國美術年鑒·1947》載,李碩卿為攻學國畫技法,“上窺唐宋諸大家,下及時下諸名賢,舉凡山水花卉各種繪法,無不融會貫通”,說的是他對國畫所下的苦功和所見的成效。但僅是如此顯然還不夠,因為令每一個國畫家都不能忽視的問題,是中國畫究竟該如何生存及發(fā)展的問題。創(chuàng)作者必須與時代的藝術觀念同步,才能正確地判斷出自己的藝術該走的道路。李碩卿學西畫出身,他對中國畫的改革之親身體驗,正來源于他的西畫素養(yǎng),即西畫所具有的寫實特點和技法,包括寫生等再現對象的繪畫方式。因此,李碩卿意識到當前的國畫“取材距離現實太遠”,他開始嘗試以現實生活為題材,并運用西畫寫生方法來進行國畫寫生。這一繪畫方針的調整對他的國畫創(chuàng)作傾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他在抗戰(zhàn)期間作了多幅寫生作品,如《厝前厝后》《拉杉排者》《捕蝦》《推稻桶過溪》等,從畫名便可知其畫面內容具有濃厚的現實生活氣息。抗戰(zhàn)勝利后他創(chuàng)作了不少富有閩南民間特色的作品,如《水圓湯》《洗衣女》等。[15]現存李碩卿早期的作品,可見于《中國美術年鑒·1947》中收錄的《水磨》(圖1)、《努力》(圖2)、《出發(fā)》、《侍御》(圖3)等,可以看出,他在保留中國畫傳統筆墨的同時,又運用了西方繪畫中的透視、比例、明暗的造型手法,以表現出一種更貼近于真實視角的效果。這雖是他早期的藝術探索,但他的這種“中西融合”的技法,以及重視寫生、重視取材和反映現實生活的精神,為他后來取得更高的藝術成就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圖2 李碩卿 努力

圖3 李碩卿 侍御
三、藝術風格成熟期的創(chuàng)作及特點
顧、李二者不同的藝術傾向,發(fā)展至20世紀50年代,他們各自的藝術創(chuàng)作都進入了黃金期。相比早期的探索性創(chuàng)作,這時候的藝術作品無論是在畫法還是風格上都已達至成熟,其中必然也包含著畫家主體的個性特征、創(chuàng)作環(huán)境、思想觀念等方面的典型性體現。
根據時人的傳頌和史料的描述,顧一塵最喜畫“燕子”,他作過多幅燕子圖,創(chuàng)作于20世紀50年代的《柳燕》(圖4)就是其中之一。從畫面中靈動灑脫的筆墨技巧、輕松有致的構圖布局,以及散發(fā)出的明快活潑的格調氣象,皆可看出他此時的技藝之精湛。我們甚至能夠感受到他畫燕子時創(chuàng)作心情的愉悅和真誠。顧一塵對燕子的喜愛,不僅見于其畫,他還曾寫過關于燕子的詩歌,這就為我們了解畫家和“燕子”這一主題之間的深度淵源提供了可信的參照。在《燕子》(外四章)的詩歌中,他深情地表達了對燕子自然形態(tài)、生命形態(tài)的觀察和贊美,還賦予燕子多種高潔的人格化品質,如他這樣寫道:“在鳥類當中,我最愛小燕子,它沒有雞鶩爭食的鄙俗,也沒有振翮摩云、英雄獨處的雄風,更不像那鴉子,聒得叫人討厭的叫唱。它只有努力地,追求那永恒的明麗溫暖。”“它的態(tài)度是積極的,它的意志是堅強的,雖然它曾經風雨,看過落花的飄零,它曾受折磨,聽過海濤的長嘯,可是它不傷春,也不悲秋,還是努力地剪斷橫風,掠過大洋,去追求那永恒的明麗溫暖。”[16]這是一首發(fā)表于1946年的散文詩,時值抗戰(zhàn)勝利后不久。詩中所寫燕子經風雨、受折磨的意象使我們聯想到人們剛經歷過的抗日戰(zhàn)爭,以及普遍意義上的人生之不可避免的逆境之時。而燕子所表現出的淡然的心境,追求希望的積極態(tài)度和堅強意志,以及它不同于其他鳥類的天然本性之平實可愛,則指示了顧一塵所真正喜愛、認同的一種內在品格,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這代表著他個人所期望、追求的一種人格和面對人生的態(tài)度。

圖4 顧一塵 柳燕
因此,藝術作品作為人的精神活動和情感態(tài)度的表現載體,顧一塵對燕子的特殊喜愛,呈現出了這一主題的特定人格化理念,某種意義上,這也正是他個人的一種“自我”人格意識的體現。回到《柳燕》這一畫面,我們已經知道他是力倡中國畫的“二重表現”的,“于筆墨形象的表現以外,……更要求一種詩的意境”[17],他還提出過“高明的繪畫作者,應該要和高明的詩歌作者一樣”[18],以上《燕子》之詩與《柳燕》之畫也是這一詩畫相通思想的實踐證明,而且在繪畫的表現上更達到了傳神精絕的藝術高度,顯示著他的藝術在內容與形式、形象與思想、詩情與畫意的“二重表現”上的統一性。
李碩卿創(chuàng)作于1958年的巨幅山水畫《移山填谷》(圖5),是該時期用藝術反映生活,描繪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題材的經典之作,此作品為他贏得了終生的名譽。前面我們已經闡述過李碩卿早期對“中西融合”技法的探索,以及他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他的這種藝術傾向,是從現實出發(fā),與實際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20世紀50年代,當新中國的政權把主要精力用在經濟建設上并通過新的組織方式(如合作社、人民公社)來向自然進軍,建設自然、改造自然的時候,也要求畫家去把這一過程反映出來。在這樣的形勢下,李碩卿如魚得水。

圖5 李碩卿 移山填谷 178.4cm×108cm
《移山填谷》取材于“鷹廈鐵路建設”的工地一角。該畫創(chuàng)作歷時半年多,經過多次修改才完善而成。它不是簡單地“如實”羅列現象,而是在題材、畫意上均有著刻意的經營,從而使之成為一幅主題明確、頗具匠心的新時代作品。童策曾這樣描述《移山填谷》的畫面:“群峰凌空,奇巖突兀,風展紅旗,云鎖峽谷,在懸崖峭壁之間,到處是機器轟鳴,人聲鼎沸,氣勢磅礴的勞動大軍與雄偉險峻的高山深谷,構成了多么壯麗動人的景象!”“作者通過它熱情地歌頌了人民向自然進軍的豪邁壯舉;而這種叫高山低頭、河水讓路的英雄氣概,正是我們時代精神的集中表現。”[19]在藝術表現上,《移山填谷》反映出了李碩卿深厚的傳統藝術修養(yǎng)和創(chuàng)新精神,“在位置經營上如此,在筆墨的運用上也是如此。從表現各種物象的神態(tài)來看,老畫家是很有筆墨功夫的”[20]。他根據不同的對象變化著筆法與墨的效果,最獨特的,是其中皴法的使用,它是李碩卿在寫生中摸索演變而來的,一種與傳統斧劈皴相似,但又并不完全相同的創(chuàng)造性皴法,為的是真實而生動地表現出鷹廈鐵路沿線山脈花崗巖的人工斷崖的形質。
總的來說,在當時的新形勢要求下,大部分畫家都投入了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自覺嘗試,但成功者非常少。原因是在國畫的創(chuàng)新性問題上,如何既能突破舊的傳統形式,又能表現新的生活內容,即如何解決舊形式與新內容的矛盾問題。大多數畫家還未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從這個方面來看,李碩卿的《移山填谷》就是“新內容與發(fā)展了的舊形式相結合得好的作品”,它說明了“發(fā)展了的舊形式不僅可以表現新內容,而且可以結合得很融洽很自然”,[21]這意味著中國畫迎來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和嶄新的面貌:《移山填谷》被譽為“中國畫的新聲”[22]及“中國畫新生的標志”[23]。
總結
綜上,顧一塵和李碩卿的兩種不同的藝術創(chuàng)作方向,為我們呈現了兩種不同的藝術思想與方法。我們無意于比較二者的藝術造詣之高低好壞,而是通過對同樣歷史條件下,在對國畫革新發(fā)展的追求下,這兩位同代同輩的泉州畫人各自的藝術實踐之途徑做一深入的觀察和分析,來認識泉州美術發(fā)展進程中的一個歷史截面。另外,綜合來說,顧、李二人也有著許多相同的地方,比如高度的藝術天分、出色的學習資質、較早的畫家身份意識、同樣求學于上海的經歷、對中國畫革新都抱有明確的立場和方向、對藝術與生活的積極態(tài)度等。最后,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兩人又有著迥異的性情,反映在對藝術的影響上,則是個體之個性、人格與藝術的高度融合的表現。
顧一塵對中國傳統文人畫的革新見解和創(chuàng)作實踐,拓展了文人畫的表現價值,富有學術力量。李碩卿融合中西藝術技法,推陳出新,準確把握時代脈搏,富有開創(chuàng)精神。他們二人對于中國繪畫前途的不同途徑的探索和成就,促進了泉州美術向現代化的轉型和發(fā)展。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44頁。轉引自胡波《歷史心理學》,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03頁。
[2]《顧一塵》收錄于泉州市鯉城區(qū)地方志編撰委員會編《鯉城人物傳稿(第二輯)》,1992年,第70頁。
[3]許志浩,《中國美術社團漫錄》,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年,第135頁。
[4]在石晶博士學位論文《〈藝風〉月刊(1933.1—1937.3)研究》一文中記載,藝風社舉辦了四屆美術展覽會,但第四屆美展情況不詳。其“附錄1:《藝風》月刊目錄(1933.1—1937.3)”和“附錄2:藝風社三屆美展作品、作者目錄”中均記載了顧一塵發(fā)表文章于《藝風》,并參與三屆美展。石晶,《藝風》月刊(1933.1—1937.3)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56、99—192頁。
[6]李碩卿國畫研究會《緬懷畫家李碩卿》,李碩卿國畫研究會編印,2003年,第128—129頁。
[7]同[5],第85頁。
[8]同[2],第70頁。
[9][10][11]顧一塵,《從新國畫談到我所理想的現代國畫》,《藝風》,1935年第7期,第3卷,第62—64頁。
[12][13][14]顧一塵,《中國畫的二重表現》,《集美周刊》,1944年第5—6期,第34卷,第1—3頁。
[15]李碩卿國畫研究會《緬懷畫家李碩卿》,李碩卿國畫研究會編印,2003年,第130—131頁。
[16]顧一塵,《燕子(外四章)》,《明日文藝》,1946年第2期,第12—14頁。
[17][18]顧一塵,《中國畫的二重表現》,《集美周刊》,1944年第5—6期,第34卷,第1—3頁。
[19][20]童策,《移山填谷》,《美術》,1959年第10期,第44頁。
[21]華夏,《“妙在似與不似之間”——談中國畫如何克服“如實描寫”的傾向》,《美術》,1959年第3期,第10頁。
[22]王朝聞先生在其文章《英雄的業(yè)績》中指出:“現在,用中國畫來反映現實的佳作出現了。以建設為題材的《梅山水庫》(張文俊作)和《移山填谷》(李碩卿作)等新作品,當成中國畫來看,特點鮮明;當成反映當前我國現實的作品來看,表現了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雄偉面貌。這是中國畫的新聲!”出自:簡平《王朝聞全集 第4卷 一以當十》,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72頁。
[23]“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蔡若虹在全國文藝創(chuàng)作三十年的總結時進一步指出:‘當看到第一幅反映現實革新的國畫(指《移山填谷》),我非常感動,這是中國畫新生的標志。’”出自:張吉昌《我國著名國畫家李碩卿事略》,《泉州文史資料(新十一輯)》,政協泉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