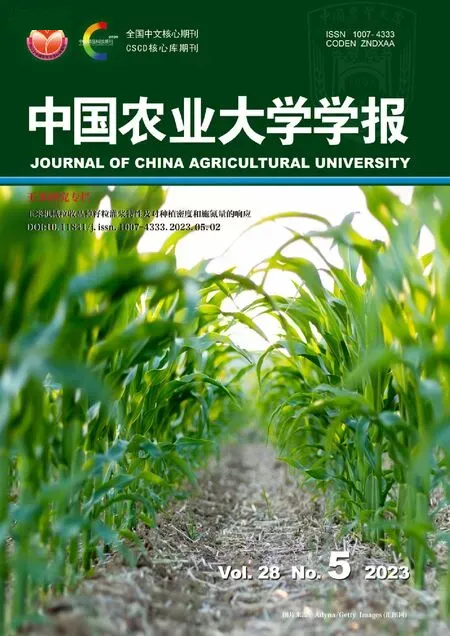1970s—2010s玉米品種產量及籽粒營養品質的分析
王利青 高聚林 王富貴 馬達靈 于曉芳* 郭懷懷
(1.內蒙古農業大學 農學院/內蒙古自治區作物栽培與遺傳改良重點實驗室,呼和浩特 010019;2.內蒙古農業大學 職業技術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109)
玉米具有較高的單位面積產量和巨大的增產潛力,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據統計,2011—2015年我國玉米種植面積占全國主要糧、油料作物種植面積的35.31%,在我國耕地面積剛性受限的條件下,提高玉米單位面積產量是滿足糧食需求的重要途徑[2]。玉米遺傳產量增益在總產量提升中作用顯著,優良品種的持續涌現是全球玉米產量大幅度提高的因素之一[3-4]。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玉米已不再作為主要的口糧作物,約有70%的玉米用作飼料,因此為了提高玉米的深加工能力和降低飼料成本,在保證高產的同時,還要提高玉米籽粒的營養品質[5]。關注不同時期代表性玉米品種籽粒產量及營養品質變化特征的研究,對提高玉米栽培技術水平,促進玉米產業良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玉米單產水平大幅提高。我國玉米單產從20世紀70年代的2 086.37 kg/hm2提高到了2019年的6 316.70 kg/hm2(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故為了探索玉米增產的途徑,許多農業科研人員回顧了玉米品種更替過程中形態特征、生理功能、產量性狀等的變化。Ci等[6]對1950—2000年中國玉米品種的研究發現,隨著品種的更替,葉片數相對穩定,葉面積以每年443 cm2/株的速率增加。Wang等[7]對1964—2001年的29個中國玉米品種進行測試也得出了相似的結果,葉長、葉寬均隨著品種更替而增加。穗位葉是對玉米果穗生長影響最直接的葉片,大量的研究結果證明新品種生育后期穗位葉同化CO2能力增強,光合速率增加,使其在灌漿期可保證籽粒吸收較多的同化產物,利于產量的形成[8-11]。Ma等[12]的研究表明,20世紀60年代—21世紀初,中國和美國雜交玉米在3個種植密度下,空桿率的下降,穗粒數和單位面積粒數顯著增加。同時董樹亭等[8]對1960s、1980s、2000s的中國玉米品種研究表明,新品種與老品種相比,穗長、穗粗均呈逐漸增加趨勢,且新品種具有較高的穗粒數。
鑒于玉米籽粒消費結構的優化,新品種在追求高產的同時,其籽粒的綠色、優質和安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就籽粒營養品質而言,粗蛋白、淀粉和粗脂肪都是評價玉米營養品質的重要指標[13]。生理成熟時玉米籽粒的貯藏成分中包括了60~72 g/100 g的淀粉、8~11 g/100 g的粗蛋白和4~6 g/100 g的粗脂肪[14],不同營養組分含量對玉米籽粒作為糧食、飼料、化工、醫藥原料的質量有很大影響。陳先敏等[15]的研究發現,品種更替過程中,千粒重和容重等產量性狀是中國玉米品種改良相對較快的性狀,而千粒重和容重的升高主要依賴于粗淀粉含量的迅速提升。白永新等[16]對1998—2001年國審玉米品種品質分析結果表明,品種間賴氨酸含量基本不變,平均含量為2.96 mg/g。楊書成等[17]發現“十一五”期間的普通玉米的粗脂肪含量有下降的趨勢,粗淀粉有微小的下降,粗蛋白的變化規律不明顯。也有學者對國內省級審定的玉米品種的品質變化進行了研究[18-20],發現玉米品質在遺傳特性調控的基礎上,也易受到氣象因子[21]、種植制度[22]和栽培措施[23]等多方面的影響。與此同時,孫琦等[24]研究還發現產量與籽粒淀粉含量顯著正相關,與脂肪、蛋白質含量呈負相關關系。籽粒營養品質也可以影響玉米商品品質,如籽粒容重。張麗等[25]就發現要想提高玉米籽粒容重,就必須著眼于籽粒總淀粉含量的提高。但是,目前關于不同年代玉米品種籽粒營養品質與冠層結構、干物質積累量與轉運量、產量及其構成因素等指標相互關系的研究鮮見報道。
本試驗以1970s—2010s 5個具有代表性的高產玉米品種為材料,分析了不同年代代表性玉米品種冠層結構、干物質積累量與轉運量、產量及其構成因素、籽粒營養品質等指標,旨在明確玉米產量提升過程中籽粒營養品質的變化規律,以期為今后優質玉米品種選育和栽培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區概況
試驗于2018—2020年在內蒙古包頭市土默特右旗溝門鎮北只圖村(40°33′ N,110°31′ E)試驗基地進行。土壤類型為沙壤土,0—30 cm耕層土壤基礎生產力及試驗期間主要氣象因子同文獻[26]。
1.2 試驗設計
試驗為單因素試驗,采用隨機區組試驗設計,利用5個1970s—2010s不同年代具有代表性的高產玉米品種:1970s的‘中單2號’(‘ZD 2’)、1980s的‘丹玉13’(‘DY 13’)、1990s的‘掖單13’(‘YD 13’)、2000s的‘先玉335’(‘XY 335’)、2010s的‘登海618’(‘DH 618’)進行試驗,每個處理3次重復。小區行長6 m,等行距種植,行間距為0.6 m,10行區,面積36 m2,種植密度為75 000株/hm2。肥料用量為純N、P2O5、K2O分別為465、210、202.5 kg/hm2。將氮肥溶于施肥罐,結合滴灌分別在拔節期、大喇叭口期、吐絲期按3∶6∶1比例追施,P2O5和K2O作基肥一次性施入。生育期內共灌水4次,分別為拔節期、大喇叭口期、吐絲期、灌漿期,灌水量均為750 m3/hm2。其他管理同一般大田。
1.3 測定項目及方法
1.3.1 冠層生理指標
葉綠素相對含量(SPAD):于吐絲期、乳熟期和成熟期采用日本美能達公司的手持式SPAD-502型葉綠素計,測定各株玉米穗位葉的葉綠素相對含量(SPAD),每葉測定10點,每個小區測定5株。
葉面積指數(LAI):每小區標定好5株具代表性植株,分別于播種后第70、85、105和145天,測量葉片長、寬,當葉片干枯一半以上時,被認定為死亡葉片。
單葉葉面積=長×寬×系數
式中:未展開葉片系數為0.5,展開葉片系數為0.75。
葉面積指數(LAI)=單株葉面積×
單位土地面積內株數/單位土地面積
光合勢(LAD)=[(L1+L2)/2]×(t2-t1),
式中:t1和t2為相鄰的生育時期持續時間,d;L1和L2為t1、t2生育時期葉面積指數。
凈光合速率(Pn):于吐絲期、吐絲后10、30、50和65 d,采用英國ADC BioScientific 公司生產的便攜式光合測定儀,測定各株玉米穗位葉中部的凈光合速率(Pn),每個小區測定5株。測定條件為大氣CO2濃度(360±5) μmol/mol,相對濕度為(60±5)%,氣體流速500 μmol/s,利用儀器的內置LED 光源,光量子通量密度設為1 600 μmol/(m2·s)。
1.3.2 單株干物質重和轉運量
于吐絲期和成熟期,選擇代表性植株3株,按葉片、莖稈、雌穗(苞葉、穗軸、籽粒)等分開,分別裝入紙袋,放入烘箱105 ℃殺青30 min,80 ℃恒溫烘干后稱重,單株干物質重等于各部分干重總和。
莖葉轉運量=吐絲期莖葉干物質重-
成熟期莖葉干物質重
莖葉轉運率=
莖葉轉運量/吐絲期莖葉干物質重×100%
1.3.3 產量及其構成因素
測產面積為每小區6 m2,統計各測產區內有效穗數,人工脫粒后測籽粒鮮重和含水率,并折算成含水率為14%的籽粒產量,隨后每小區留10穗代表性果穗風干后考種,測定穗粒數和百粒重(含水率14%)。
1.3.4 籽粒營養品質
于生理成熟期,選擇代表性果穗,取中部籽粒于烘箱105 ℃殺青后,60 ℃烘干至恒重,粉碎后進行測量。利用半微量凱氏定氮法測定籽粒全氮含量(粗蛋白含量=籽粒全氮含量×6.25);用索氏提取法-殘余法測定粗脂肪含量;蒽酮-硫酸比色法測定總淀粉及可溶性糖含量[27]。
1.4 數據處理及結果分析
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6進行數據處理,利用SAS 9.4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方差、通徑和相關性分析。采用LSD(least-significant different)法進行多因素方差分析,利用Duncan法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應用Pearson法作相關性分析。使用Sigmaplot 12.5與Origin 2021進行制圖。
2 結果與分析
2.1 產量提升過程中冠層生理特性變化規律
2.1.1 產量提升過程中LAI變化規律
由表1可知,播種后第70、85、105和145天的LAI在年份和品種間均有極顯著差異(P<0.01)。由圖1可知,播種后第70和85天時,各品種LAI均值以2019年為最高,較2018和2020年各品種LAI均值分別提高3.97%、16.45%和14.47%、4.79%;播種后第105和145天時,各品種LAI以2018年為最低,較2019和2020年各品種LAI均值分別降低16.91%、17.51%和8.04%、13.03%。播種后第70和85天時,1970s—1990s品種的LAI均顯著高于2000s、2010s的代表品種(P<0.05),于播種后第85天時,品種間差異最大,且差異達極顯著水平。播種后第105和145天時,品種間差異又逐漸變小。伴隨生育進程的推進,各年代品種的LAI均顯著降低(P<0.05)。相較于播種后第85天時,播種后第145天的1970s、1980s、1990s、2000s、2010s各品種LAI依次降低64.27%、61.10%、59.50%、47.41% 和57.05%(2018年),65.14%、62.45%、61.42%、52.34%和59.04%(2019年),69.70%、60.00%、53.61%、45.36%和47.55%(2020年)。可見,2000s、2010s品種(‘XY 335’和‘DH 618’)在播種后85~145 d的LAI降幅低于1970s—1990s品種,保證了植株在花后有較高的光合面積,在一定程度上延長了光合持續期。

表1 LAI的多因素方差分析Table 1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LAI

不同小寫字母表示處理間在0.05水平上差異顯著。下同。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reatments at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圖1 2018(a)、2019(b)和2020(c)年不同品種播種后的LAIFig.1 Changes of LAI after seeding of different varieties in 2018 (a), 2019 (b) and 2020 (c)
2.1.2 產量提升過程中群體LAD變化規律
由表2可知,花前和花后的群體LAD在年份和品種間均有極顯著差異(P<0.01)。由圖2可知,各品種花前、花后群體LAD均值均以2019年為最高,較2018年和2020年分別增加20.19%、11.46%和30.82%、2.40%。品種間群體LAD變化規律表現為1970s—1990s品種的花前群體LAD均顯著高于2000s—2010s品種,花后群體LAD在2018年,以1990s、2000s品種為最高;2019年,以1980s、1990s品種為最高;2020年,以1980s品種(‘DY 13’)為最高。對比1970s(‘ZD 2’)、1980s(‘DY 13’)、1990s(‘YD 13’)品種,2010s品種(‘DH 618’)花前LAD依次降低9.86%、12.80% 和19.12%(2018年),5.29%、1.27%和7.88%(2019年),21.20%、21.91% 和 14.15%(2020年)。

表2 群體LAD的多因素方差分析Table 2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population LAD

F1,花前,F2,花后。F1, before the flower, F2, after the flower.圖2 2018(a)、2019(b)和2020(c)年不同品種群體的LADFig.2 Changes of LAD in different breed populations in 2018 (a), 2019 (b) and 2020 (c)
2.1.3 產量提升過程中穗位葉SPAD變化規律
由表3可知,吐絲期、乳熟期和成熟期的穗位葉SPAD在年份和品種間均有極顯著差異(P<0.01)。由圖3可知,各品種吐絲期穗位葉SPAD以2018年為最大,乳熟期穗位葉SPAD以2020年為最大,成熟期穗位葉SPAD則以2019年為最大。生育進程推進過程中,各年代品種穗位葉SPAD均顯著降低(P<0.05)。由吐絲至成熟期,1970s、1980s、1990s、2000s、2010s各品種穗位葉SPAD分別降低80.49%、90.41%、86.33%、59.97% 和39.71%(2018年),62.38%、53.10%、46.12%、31.88% 和29.90%(2019年),76.36%、62.65%、47.63%、42.08%和39.02%(2020年)。生育進程的推進也導致了品種間差異在成熟期達到最大。2010s品種(‘DH 618’)成熟期穗位葉SPAD較1970s、1980s、1990s、2000s品種依次提高40.00%、42.66%、33.71%和19.10%(2018年),34.23%、26.02%、18.75%和8.96%(2019年),37.32%、26.10%、17.05%和8.22%(2020年)。由此可見,2010s品種(‘DH 618’)可有效緩解穗位葉SPAD在生育后期的降幅,在成熟期仍能保持較高的穗位葉SPAD。

表3 穗位葉SPAD的多因素方差分析Table 3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SPAD in spike position leaves

R1表示吐絲期,R3表示乳熟期,R6表示成熟期。下同。R1 represents silking stage, R3 represents milking stage, R6 represents maturity stage. The same below.圖3 2018(a)、2019(b)和2020(c)年不同品種穗位葉的SPADFig.3 Changes of SPAD in panicle leaves of different varieties in 2018 (a), 2019 (b) and 2020 (c)
2.1.4 產量提升過程中穗位葉Pn變化規律
由表4可知,吐絲期—吐絲后第50天的穗位葉Pn在年份和品種間均有極顯著差異(P<0.01),吐絲后65 d的穗位葉Pn僅在品種間有極顯著差異(P<0.01)。由圖4可知,2019年的各品種吐絲期和吐絲后10 d的穗位葉Pn均值較2018年分別提高35.28%和16.88%,2019年的各品種吐絲后第30—65天的穗位葉Pn均值較2018年分別改變-5.75%、-5.66%和0.95%。生育進程推進過程中,各年代品種穗位葉Pn均顯著降低(P<0.05)。吐絲期—吐絲后的第65天,1970s、1980s、1990s、2000s、2010s各品種穗位葉Pn分別降低85.14%、82.02%、78.79%、79.98%和72.63%(2018年),75.71%、76.23%、73.66%、73.74%和64.56%(2019年)。生育進程的推進也導致品種間差異在生育后期達顯著水平。2018年,品種間差異在吐絲后第65天時達到最大,其中2010s品種(‘DH 618’)較其他年代品種穗位葉Pn分別提高105.35%、68.73%、31.86%和41.66%;2019年,品種間差異在吐絲后第50天時達到最大,其中2010s品種(‘DH 618’)較其余年代品種穗位葉Pn提高89.97%、86.33%、27.47%和9.63%。可見,2010s的品種(‘DH 618’)在生育后期仍能保持較高的穗位葉Pn,保證了花后較高的光合生產力。

表4 穗位葉Pn的多因素方差分析Table 4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leaf Pn at ear position

圖4 2018(a)和2019(b)年不同品種穗位葉的PnFig.4 Changes of panicle leaf Pn of different varieties in 2018 (a) and 2019 (b)
2.2 產量提升過程中單株干物質重與轉運量變化規律
2.2.1 產量提升過程中單株干物質積累量變化規律
由表5可知,吐絲期和成熟期的單株干物質積累量在年份和品種間均有極顯著差異(P<0.01)。由圖5可知,品種間吐絲期單株干物質重在不同年份有較大的差異。2018年,1970s品種(‘ZD 2’)均顯著低于其他年代品種(P<0.05),較1980s、1990s、2000s、2010s品種分別降低18.41%、18.12%、17.75%和19.24%;2019和2020年,均以1990s品種(‘YD 13’)吐絲期單株干物質重為最大,較1970s、2000s和2010s品種分別增加了12.42%、22.42%、15.60%(2019年)和7.04%、12.26%、12.12%(2020年)。成熟期單株干物質重則表現為1970s品種(‘ZD 2’)顯著低于其他年代的代表品種(P<0.05)。對比1980s、1990s和2010s品種,1970s品種(‘ZD 2’)成熟期單株干物質重依次降低25.41%、24.44%和29.21%(2018年),10.59%、13.62%和10.93%(2019年),7.96%、14.99%和11.38%(2020年)。

表5 單株干物質重的多因素方差分析Table 5 Multi-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dry matter weight of per plants

圖5 2018(a)、2019(b)和2020(c)年不同品種單株干物質積累量變化規律Fig.5 Changes of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per plant of different varieties in 2018 (a), 2019 (b) and 2020 (c)
2.2.2 產量提升過程中單株花后干物質積累量與轉運量的變化規律
由表6可知,單株花后干物質重、單株轉運量在年份和品種間均有極顯著差異(P<0.01);單株轉運率在年份和品種間均有極顯著差異(P<0.01)。由表7可知,1970s品種(‘ZD 2’)單株花后干物質重較1980s、1990s、2000s、2010s品種分別降低21.58%、20.74%、24.40%和24.94%(2018年),13.22%、12.87%、15.90%和19.39%(2019年),11.59%、18.37%、19.96%和20.91%(2020年)(P<0.05)。單株轉運量表現為2010s品種(‘DH 618’)顯著高于1970s—2000s品種(P<0.05)。除2000s品種(‘XY 335’)外,單株轉運率的變化規律也表現為2010s品種(‘DH 618’)均顯著高于1970s—1990s品種(P<0.05),2018年分別依次提高10.31%、39.46%和39.61%,2019年依次提高42.42%、55.76% 和66.21%,2020年依次提高43.49%、51.77% 和59.50%。可見,2010s品種(‘DH 618’)可保證較高的花后單株干物質量,并提高單株轉運效率,有較強的物質供應能力。

表6 單株花后干物質重和轉運量的多因素方差分析Table 6 Multi-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dry weight per plant after anthesis and transshipment per plant

表7 不同品種單株花后干物質重和轉運量變化規律Table 7 Variation of dry matter mass and transfer volume per plant after anthesis of different varieties
2.3 產量提升過程中產量及其構成因素變化規律
由表8可知,產量、百粒重在年份和品種間均有極顯著差異,有效穗數和穗粒數僅在品種間有極顯著差異(P<0.01)。由圖6可知,對比1970s—2000s品種,2010s品種(‘DH 618’)的產量、有效穗數和百粒重均有顯著提高,但穗粒數則顯著低于2000s品種(‘XY 335’)(P<0.05)。對比1970s、1980s、1990s、2000s品種,2010s品種(‘DH 618’)的產量分別提高55.89%、24.02%、20.28%、9.37%(2018年),50.22%、34.56%、21.87%、18.12%(2019年)和51.68%、36.20%、26.57%、9.75%(2020年);收獲穗數分別提高10.48%、8.65%、5.96%、4.18%(2018年),7.09%、5.43%、6.25%、7.09%(2019年)和7.00%、4.51%、6.19%、8.18%(2020年);百粒重分別提高21.80%、17.66%、26.11%、9.85%(2018年),33.48%、26.18%、25.51%、11.82%(2019年)和22.91%、32.97%、33.48%、17.18%(2020年);穗粒數分別改變了-13.70%、-15.31%、-13.20%、-8.56%(2018年),2.15%、-3.03%、-3.74%、-11.44%(2019年)和0.96%、-3.96%、-6.28%、-10.97%(2020年)。

表8 產量及其構成因素的多因素方差分析Table 8 Multi-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yield and its components

(a)、(b)、(c)為2018—2020年各玉米品種單產;(d)、(e)、(f)為2018—2020年各玉米品種收獲穗數;(g)、(h)、(i)為2018—2020年各玉米品種穗粒數;(j)、(k)、(l)為2018—2020年各玉米品種百粒重(a), (b) and (c) are the yield per unit area of maize varieties from 2018 to 2020; (d), (e) and (f) are the number of ears harvested by each maize variety in 2018-2020; (g), (h) and (i) were the number of grains per ear of maize varieties in 2018-2020; (j), (k) and (l) are 100 grain weight of each corn variety from 2018 to 2020圖6 不同品種產量及其構成因素變化規律Fig.6 Variation of yield of different varieties and its constituent factors
2.4 產量提升過程中籽粒營養品質變化規律
由表9可知,籽粒粗蛋白含量、總淀粉含量、粗脂肪含量和可溶性總糖含量在年份和品種間均有極顯著差異(P<0.01)。由圖7可知,1970s—1990s品種籽粒粗蛋白含量顯著高于2000s—2010s品種,總淀粉含量以1990s品種(‘YD 13’)為最低,粗脂肪含量也以1990s品種(‘YD 13’)為最高,可溶性糖含量又表現為2000s—2010s品種顯著高于1970s—1990s品種(P<0.05)。相較于1970s、1980s、1990s品種,2000s品種(‘XY 335’)籽粒粗蛋白含量分別降低6.32%、2.85%、6.30%(2018年)和8.11%、8.52%、4.45%(2019年),籽粒可溶性糖含量分別增加8.88%、5.33%、11.84%(2018年)和13.25%、6.82%、18.29%(2019年);2010s品種(‘DH 618’)籽粒粗蛋白含量分別降低8.17%、4.77%、8.15%(2018年)和7.66%、8.07%、3.98%(2019年),籽粒可溶性糖含量分別增加6.56%、3.10%、9.46%(2018年)和11.52%、5.19%、16.48%(2019年)。1990s品種(‘YD 13’)籽粒總淀粉含量較2000s、2010s品種依次降低1.88%、1.99%(2018年)和2.34%、2.09%(2019年),其籽粒粗脂肪含量較1970s、1980s、2000s和2010s品種則依次增加9.74%、15.35%、24.70%、12.69%(2018年)和11.76%、9.78%、11.76%、6.47%(2019年)。

表9 籽粒營養品質的多因素方差分析Table 9 Multi-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nutritional quality of grains
2.5 單產及其構成因素的相關性分析
單產與其構成因素的相關性分析表明,產量構成因素中,有效穗數、百粒重與單產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0.775 6、0.800 7,P<0.05),而與穗粒數無顯著相關關系(0.155 3,P>0.05),見圖8。可見,提高有效穗數和百粒重是玉米增產的有效途徑之一。
2.6 百粒重與籽粒營養品質的通徑分析
由表10可知,4項營養品質組分中,籽粒總淀粉、可溶性糖含量均與百粒重呈極顯著正相關關系(0.585、0.573,P<0.01),籽粒粗蛋白含量與百粒重呈極顯著負相關關系(-0.704,P<0.01),籽粒粗脂肪含量與百粒重的相關關系較小(0.189,P>0.05)。籽粒總淀粉、粗脂肪和可溶性糖含量對百粒重均起正向的直接效應,籽粒粗蛋白含量則起負向的直接效應,正向的直接貢獻由大到小為籽粒可溶性糖含量>籽粒粗脂肪含量>籽粒總淀粉含量。各項營養品質組分中,籽粒可溶性糖含量對百粒重的正向直接作用最大(0.438),且其通過籽粒粗蛋白、總淀粉含量、可溶性糖含量對百粒重的間接作用也均為正值(0.070、0.041、0.024);籽粒粗脂肪含量對百粒重的正向直接作用次之(0.408),但其通過籽粒粗蛋白、總淀粉含量產生了較大的負向間接作用(-0.393、-0.230),導致籽粒粗脂肪含量與百粒重表現為負相關關系;籽粒總淀粉含量對百粒重的正向直接作用最小(0.293),但其通過籽粒粗蛋白、可溶性糖含量產生了較大正向間接作用(0.552、0.062),使其綜合間接作用最大(0.293),最終表現為同百粒重的極顯著正相關關系。籽粒粗蛋白含量與百粒重存在較大的負向直接作用(-0.656),且其綜合間接作用也表現為負向(-0.049)。可見,較高的籽粒可溶性糖、總淀粉含量有利于提高百粒重,同時鑒于籽粒粗脂肪含量同百粒重的復雜關系,故其在玉米產量構成中也不應被忽視。

表10 百粒重與籽粒營養品質的通徑分析Table 10 Passage analysis of 100 grain weight and nutritional quality of grains
2.7 冠層生理特性、干物質積累與轉運和籽粒營養品質的相關性
由圖9可知,籽粒可溶性糖含量與播種后85 d的LAI呈極顯著負相關關系,R2為-0.892(P<0.01),與播種后105 d的LAI呈顯著負相關關系,R2為-0.726(P<0.05),與花前、花后LAD呈極顯著負相關關系,R2分別為-0.883、-0.785(P<0.01),與吐絲期、吐絲后10 d的穗位葉Pn呈顯著正相關關系,R2分別為0.687、0.690(P<0.05),與單株干物質轉運量、單株花后干物質重也呈顯著正相關關系,R2分別為0.742、0.666(P<0.05);籽粒總淀粉含量與乳熟期穗位葉SPAD呈極顯著正相關關系,R2為0.786(P<0.01),與成熟期穗位葉SPAD呈顯著正相關關系,R2為0.728(P<0.05);籽粒粗蛋白含量與乳熟期和成熟期穗位葉SPAD均呈極顯著負相關關系,R2分別為-0.915、-0.909(P<0.01),與吐絲后30 d穗位葉Pn呈極顯著負相關關系,R2為-0.840(P<0.01),與吐絲后50 d穗位葉Pn呈顯著負相關關系,R2為-0.740(P<0.05),與單株干物質轉運量呈顯著負相關關系,R2為-0.655(P<0.05);籽粒粗脂肪含量僅與吐絲期穗位葉Pn呈顯著負相關關系,R2為-0.741(P<0.05)。

陰影部分為95%置信區間,**表示在0.01水平差異顯著。The shaded areas are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1 level.圖8 產量與其構成因素的相關分析Fig.8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yield and its constituent factors

X1~X3,吐絲期、乳熟期和成熟期穗位葉SPAD;X4~X7,播種后70~145 d的LAI;X8~X9,花前和花后LAD;X10,吐絲期單株干物質重;X11,成熟期單株干物質重;X12,單株干物質轉運量;X13,花后單株干物質積累量;X14~X18,吐絲期~吐絲后65 d的穗位葉Pn。X1-X3, SPAD of spike leaves in silking stage, milk ripe stage and mature stage; X4-X7, LAI of 70-145 d after seeding; X8-X9, LAD before and after flowering; X10, dry mattermass per plant in silking stage; X11, dry matter mass per plant in mature stage; X12, dry matter transfer volume per plant; X13,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per plant after anthesis; X14-X18, Pn of panicle-position leaves during the period of silking-65 d after silking.圖9 冠層生理、干物質積累與轉運和籽粒營養品質的相關分析Fig.9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anopy physiology,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and translocation and nutritional quality of grains
3 討 論
作物的產量性狀是由多基因控制的,品種演替過程中,玉米籽粒產量顯著增加[28],穗行數和百粒重隨著品種審定年份的增加顯著增加[29],其中百粒重對我國3個玉米主產區產量的遺傳增長都有貢獻[30]。試驗年份對不同年代玉米品種的產量也有影響,但由于遺傳效應在提高產量過程中的顯著作用,導致品種更替過程中,產量提升在不同試驗年份下變化較小,且已有在不同試驗年份下的研究結果均能證明以上觀點[31-33]。同一時代品種由于其遺傳效應間的變化較小,故試驗年份在產量及產量構成因素上的影響是巨大的,如Wang等[34]對黃土高原連續10年春玉米定位試驗研究表明,在不同降水年份下穗粒數差異顯著(P<0.05)。張元紅等[35]研究也發現,在干旱年,無論在任何密度條件下,單位面積穗數和穗粒數是影響產量的最主要因素;在平水年與豐水年,低密度條件下單位面積穗數是影響產量的主要因素,而高密度條件下,春玉米籽粒百粒重是影響產量的主要因素。本研究結果表明,對比1970s—2000s品種,2010s品種(‘DH 618’)的產量提高9.37%~55.89%。較高的收獲穗數和百粒重是2010s品種(‘DH 618’)高產的主要原因,其收獲穗數和百粒重較1970s、1990s和2000s品種提高4.18%~10.48%和9.85%~33.48%。
有效穗數受種植條件影響較大,而百粒重的高低則主要由遺傳因素控制[36]。粒重形成過程也是營養物質逐步積累的過程,營養物質的分配比例影響著玉米籽粒產量的高低和品質的優劣[27]。關于籽粒各營養組分間的關聯性,張曉芳[37]和袁亮等[38]研究認為,玉米籽粒中的淀粉含量與蛋白質含量、脂肪含量均為極顯著負相關關系。基于此,孫琦等[24]研究認為,二者的負相關是由于它們均儲存于胚乳中,作為光合作用的產物,一類物質的增加將導致另一類物質的減少,二者間的負相關是必然的。陳先敏等[15]也提出籽粒粗淀粉的快速積累對粗蛋白、粗脂肪等其他組分的積累產生了稀釋效應。但是Zhang等[39]又認為普通玉米通過育種材料的選擇及適宜的栽培措施,完全可以達到優質高產。本研究結果發現,2010s品種(‘DH 618’)籽粒粗蛋白含量比1970s—1990s品種降低8.17%~3.98%;籽粒粗脂肪含量比1990s品種降低6.07%~11.26%;籽粒可溶性糖和總淀粉含量則分別比1970s、1990s品種增加6.56%~16.48%和0.70%~2.14%。這部分研究結果與陳先敏等[15]的研究結果稍有不同,可能是由于所研究的年份和品種的選取不完全一致所導致。同時本研究關于百粒重與籽粒營養品質組分的分析發現,籽粒總淀粉、可溶性糖含量與粒重有積極的直接作用和極顯著正相關關系;籽粒粗脂肪含量與百粒重的關系較為復雜,雖然籽粒粗脂肪含量可以對百粒重產生較大的正向直接作用,但同時其通過其他品質組分產生的綜合間接作用更大,且為負向作用;較高的籽粒粗蛋白含量則不利于百粒重的進一步提升。
籽粒營養物質的合成主要由植株冠層光合作用提供,冠層光合能力的強弱及其對光合產物的積累運輸影響著籽粒營養物質的成分及比例[40-41]。Rajcan等[42]研究表明,玉米葉片衰老的延遲使植株有更長的光合作用時間。Tollenaar等[43]研究表明,與過去的品種相比,現代的品種干物質積累速率更快,光能利用率更高,這有利于當代玉米品種獲得更高的產量。王空軍等[44]的研究結果發現,現代的品種之所以可以獲得較高的籽粒產量就在于其能夠保證灌漿后期葉綠素含量及葉綠體功能的完整性。董樹亭等[8]也發現,在品種更替過程中,光合色素的組成比率沒有顯著變化,現代品種生育后期細胞間隙CO2濃度低的原因不是氣孔限制,而是葉片同化CO2能力增強的結果。本研究結果發現,2010s品種(‘DH 618’)穗位葉SPAD在生育后期的降幅較其他年代品種均小,從而保證較高的穗位葉Pn,成熟期穗位葉SPAD較其他年代品種高8.22%~42.66%,吐絲后65 d,穗位葉Pn較其他年代品種也提高31.86%~105.35%,同時2010s品種(‘DH 618’)生育后期的LAI下降也較為緩慢。2010s品種(‘DH 618’)花后單株干物質積累量和轉運量較1970s—2000s品種分別增加0.72%~33.22%和5.34%~43.77%。本研究結果發現,籽粒總淀粉含量主要受到乳熟期和成熟期穗位葉SPAD的正向調控,籽粒可溶性糖含量則受到吐絲期、吐絲后10 d的穗位葉Pn、單株干物質轉運量和單株花后干物質積累量的正向調控。由此可見,對比1970s—2000s品種,2010s品種(‘DH 618’)在保證較高的開花期穗位葉Pn和生育后期穗位葉SPAD的基礎上,有較高的單株花后干物質的積累量及向籽粒的轉運量,促進了籽粒可溶性糖和總淀粉含量的增加,最終實現了籽粒產量及營養品質的綜合提升。
4 結 論
與1970s—2000s的玉米代表品種相比,2010s品種(‘DH 618’)的產量提高9.37%~55.89%(P<0.05),‘DH 618’高產的主要原因是較高的有效穗數和百粒重。百粒重的進一步提升依賴于籽粒總淀粉和可溶性糖含量的顯著增加,且鑒于籽粒粗脂肪含量同百粒重的復雜關系,故其在玉米產量構成中也不應被忽視。相較于1970s、1990s的代表品種,‘DH 618’的籽粒可溶性糖、總淀粉含量均有顯著提高,但其籽粒粗蛋白含量則顯著降低。在保證花期較高的穗位葉Pn基礎上,進一步維持生育后期的穗位葉SPAD,同時顯著增加花后單株干物質積累量及轉運量則是‘DH 618’籽粒總淀粉和可溶性糖含量高于1970s—1990s品種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