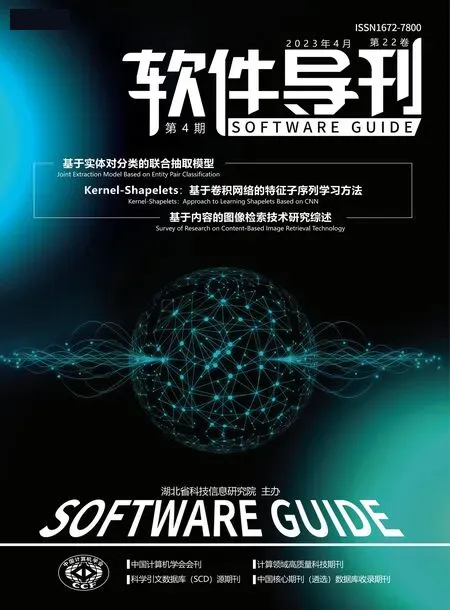精神分裂癥患者誘發態腦電信號特征提取研究
徐 琪,李 斌,朱 耿,李永康,王琦雯,李曉歐
(1.上海理工大學 健康科學與工程學院,上海 200093;2.上海健康醫學院 醫療器械學院,上海 201318;3.上海市楊浦區精神衛生中心,上海 200093)
0 引言
中國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2019-2020 年中國精神醫療行業報告》顯示,截至2017 年我國精神障礙疾病患病率為17.5%,居于全球首位,其中精神分裂癥(Schizophrenia,SCZ)患者占比最高[1]。SCZ 是一種嚴重的精神障礙疾病,患者多發于青少年時期和成年初期,并且具有復發率高、致病原因不明確和病程遷延的特點,不僅會對患者學習生活造成影響,還會給社會和家庭帶來沉重負擔[2]。由于SCZ 患病原因及病理機制尚未明確,因此傳統診斷方法主要通過臨床經驗對患者癥狀作出判斷[3],缺乏一定的客觀性。
近年來,研究人員嘗試多種技術獲取SCZ 患者的生物標志物,包括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fMRI)、腦電檢測技術、行為學采集技術等。其中,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m,EEG)具有時間分辨率高、成本低等優點受到廣泛使用[4]。
1 相關研究
臨床上,主要通過靜息態腦、誘發態腦電信號采集腦電信號。其中,靜息態EEG 是未施加特定刺激或任務的內源性或內在神經活動;誘發態EEG 是由外源性刺激或任務所誘發的神經活動。
目前,腦網絡研究大多關注兩通道時域幅值的同步性互相關、頻域幅度同步性相干性(Coherence,COH)[5]、相位同步性鎖相值(Phase Locking Value,PLV)[6]、相位滯后指數(Phase Lag Index,PLI)[7]等方面。其中,采用PLV、PLI 衡量腦部連通性居多。Douglass 等[8]研究SCZ 患者各腦區的平均功能連接性,發現患者額葉腦功能連接模式不同。Kim 等[9]采用PLV 對不同程度SCZ 患者的EEG 信號構建網絡,研究網絡屬性特征。Zhao 等[10]采用PLI 對SCZ患者誘發態信號構建網絡,分析腦功能網絡的拓撲結構和腦功能連通性,發現SCZ 患者Theta 腦網絡存在差異。Zhang 等[11]采用PLI 對重度抑郁癥患者靜息態EEG 信號構建網絡,發現Theta 節律的平均最短路徑長度、聚類系數及節點介數中心性可作為潛在生物學標志。
雖然,通過改變腦連接模式可提供信息區分SCZ 患者,但現存研究仍然較少。為此,本文主要基于PLI、COH構建腦網絡,分析學習任務過程中SCZ 患者和健康人腦網絡屬性在特定階段、頻段下的顯著性和腦功能連通性差異,探索患者在學習任務中的表現。此外,通過處理誘發態腦電信號特征,在精神分裂癥領域將兩種腦網絡構建方法進行比較分析。
2 數據集
本文數據來源于開放數據庫Zenodo[12]。該數據集共記錄71 名受試者(42 名SCZ 患者與29 健康人),包括32 個通道,256Hz采樣率的EEG 數據。
實驗建立了具有獎懲機制的任務,每次試驗金錢收益或損失設定為0.05 美元。任務要求將4 個簡單形狀以偽隨機方式呈現給受試者48 次(試驗次數共192 次),受試者則需要通過按下按鈕(Go)或停止回應(NoGo)獲得獎勵(Win)或避免懲罰(Avoid)。
因此,實驗將包含以下4 種刺激:Go-to-Win、Go-to-Avoid、NoGo-to-Win 和NoGo-to-Avoid。其中,設定刺激所獲得的獎懲概率為80%,要求受試者快速反應贏取更多獎勵。試驗開始時,屏幕上出現十字,持續0.4~0.6s;然后進入刺激階段,屏幕隨機呈現一幅刺激圖片停留1s;接下來進入0.25~2s 的無反應期和2.5s 的反應期;最后屏幕出現1s十字后顯示反饋圖像,并停留2s。
根據以上不同刺激可將反饋類型分為正反饋、負反饋和中性反饋[10]。本文僅對負反饋誘發事件的相關電位進行分析,將EEG 進行標準腦電預處理后選擇19 個腦電通道(FP1、FP2、Fz、F3、F4、F7、T7、T8、C3、C4、Cz、Pz、P4、P3、F8、P8、P7、O2、O1)進行分析。
3 評價指標
3.1 時頻功率
本文選用Morlet 小波變換對單次試驗數據計算時頻功率[13]。
其中,A 為高斯窗函數系數,n為小波循環次數,f為峰值頻率。本文將3.8~40Hz 峰值頻率均勻劃分為50 個點,設置小波變換循環次數為5,對每個試驗數據得到一個50(頻點)×768(時間點)的二維矩陣。
隨后,比較SCZ 患者和健康人的時頻功率圖,總共包括15 350 次比較(-0.2~1.0s 共307 個時間點,3.9~40Hz 共50 個頻點)[14]。為了簡化計算,本文通過一種基于聚類的非參數置換檢驗驗證實驗數據[15]。
3.2 相位滯后指數功能連接
EEG 信號產生于人體大腦皮層,是由大腦皮層下的神經活動導致的電活動。在無外界干擾情況下,每個電極記錄的電位信號均只反應對應位置下腦源的放電活動。但事實上,由于頭皮、腦內血液、顱骨等存在不同的電傳導特性,可將人的大腦看作一個容積導體。因此,腦源放電活動不僅能傳導至大腦正上方,還會傳導于頭皮周邊位置,導致一個腦源放電活動會被多個電極共同記錄[16]。為此,使用PLI 量化每個腦電信號通道間的功能連通性,假定兩個EEG 信號xn(t)、xm(t)在t時刻的相位差。
其中,i、j為整數,通常取均取1,φn(t)、φm(t)為兩個時間序列n、m的相位,當兩者間的相位差近似于一個常數時,稱n、m相位同步。x(t)的瞬時相位為:
定義相位同步指標PLI為:
其中,sign 為符號函數,PLI 在0-1 間變化,當PLI 為0時,兩個時間序列無相位同步;當PLI 為1 時,兩個時間序列完美相位同步。根據上式,可在每個時頻點處得到一個19×19的PLI函數連通性矩陣。
3.3 相干性功能連接
在同一頻率下,度量EEG 信號相位穩定性最經典的方法為頻譜分析,即將信號由時域轉為頻域,基于豐富的頻段信息對兩個信號的相互關系進行計算分析。
其中,f為m(t)、n(t)經過傅里葉變換后的頻率,Smn為信號m(t)、n(t)的互功率譜,Smm、Snn分別為m(t)、n(t)的自功率譜。COH 值在0~1 間變化,當COH 為0 時兩個信號在某頻率f上不相干;當COH 為1 時,表明兩個信號在某頻率f上完美相干。
3.4 精神分裂癥特征選擇
本文共獲得342 個特征,包括19×(19-1)/2=171 個PLI功能連通性特征和19×(19-1)/2=171 個COH 功能連通性特征。然而,特征中存在部分不相關或相關性較低的特征會影響分析結果,為此通過Fisher 評分法獲取SCZ 患者與健康人間具有顯著差異性的特征[17]。
4 實驗結果與分析
4.1 時域分析
Albrecht 等[12]發現SCZ 患者在兩種相同條件(Go-to-Win 和NoGo-to-Avoid)下的準確性相較于健康人準確性有所降低,存在一定的認知缺陷。在此基礎上,本文主要研究SCZ 患者與健康人的時域特征,如圖1 所示(彩圖掃OSID 可見,下同)。
圖1 為19 個電極的負反饋誘發事件電位的疊加平均。由此可見,在0.3~0.4s 間,SCZ 患者和健康人間存在顯著性差異(p=0.042)。

Fig.1 Time domain comparison of negative feedback between healthy people and SCZ patients圖1 健康人和SCZ患者的負反饋時域比較
4.2 時頻分析
圖2 為健康人和SCZ 患者的時頻功率,在F3、F4 通道上取平均值,并繪制的時間—頻率功率圖。由此可見,在刺激開始后約0.2s 時,SCZ 患者的θ、α頻段加強,健康人則在刺激開始后θ頻段立即增強,約0.2s后α、β頻段增強。
圖3 紅色區域表示兩組間差異顯著位置。由此可見,在刺激開始后0.1~0.8s 內,健康人θ頻段功率相較于精神分裂癥患者更強(p=0.003),證實了通過theta 頻段和時間段計算PLI和COH 腦連通性的合理性。

Fig.3 Difference area圖3 差異區域
4.3 腦功能連接分析
4.3.1 COH腦功能分析
本文選擇刺激開始后0.2~0.6s 的時間窗口和4~7Hz(θ頻段)的頻率范圍,得到每個受試者任務相關的加權功能連接矩陣,如圖4所示。
圖中橫縱坐標均為19 通道,矩陣值為相應兩通道間的EEG 信號關聯強度,顏色越深代表值越大,關聯強度越強。由此可見,健康人和SCZ 患者COH 腦功能連接差異較小。
根據腦功能連接矩陣對大腦連通性進行可視化操作,如圖5 所示。其中,不同顏色色條表示連接強度。由此可見,基于COH 建立的腦網絡SCZ 患者相較于健康人差異較小。
然后,使用Fisher評分進行分析,選取評分較高的前兩個特征進行比較,如表1 所示。由此可見,兩組均存在統計學差異,但差異并不明顯。

Fig.4 COH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atrix of healthy controls and SCZ patients圖4 健康人和SCZ患者的COH功能連接矩陣

Fig.5 COH brain network of healthy controls and SCZ patients圖5 健康人和SCZ患者的COH腦網絡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H between healthy people and SCZ patients表1 健康人與SCZ患者的COH比較
4.3.2 PLI腦功能分析
圖6 為健康人和SCZ 患者的PLI 平均功能連接性矩陣,矩陣值為相應兩通道間EEG 信號的關聯強度,顏色越深代表值越大,兩信號關聯強度越強。由此可見,相較于SCZ 患者,健康人在不同腦區間的功能連接更強。
根據平均功能連接矩陣對腦部連接矩陣進行可視化操作,如圖7 所示。由此可見,基于PLI 建立的腦網絡中SCZ 患者額葉/顳葉皮質與枕葉間的遠距離連接相較于健康人更少,連通性更弱。
然后,通過Fisher 選取評分較高的前10 個特征進行比較,如表2 所示。由此可見,10 個腦連通性特征在兩組間均存在統計學差異,SCZ 患者顳葉皮質與視皮層之間的連接強度相較于健康人顯著降低。
4.4 結果分析
在同等條件下構建的腦網絡,SCZ 患者和健康人的腦功能連接差異性較小,主要集中在額葉與顳葉間,而PLI腦功能連接存在顯著差異,主要集中在顳葉與枕葉間,這可能與PLI本身對共同源、噪聲等不敏感性相關。

Fig.6 PLI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atrix of healthy controls and SCZ patients圖6 健康人和SCZ患者的PLI功能連接矩陣

Fig.7 PLI brain network of healthy controls and SCZ patients圖7 健康人和SCZ患者的PLI腦網絡

Table 2 Statistical comparison of PLI results between healthy controls and SCZ patients表2 健康人與SCZ患者的PLI統計結果比較
實驗結果表明,SCZ 患者額葉、顳葉和枕葉均存在不同程度受損,與文獻[18]的研究報告相一致。
5 結語
本文對SCZ 患者和健康人誘發態EEG 信號進行研究,對3 種特征研究方法所獲取的腦電特征進行分析。實驗證明,SCZ 患者和健康人的EEG 信號存在顯著特征差異。然而,本文尚未進行多層網絡分析,后續將結合多種腦網絡結構,并引入深度學習方法分析SCZ 患者的腦網絡差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