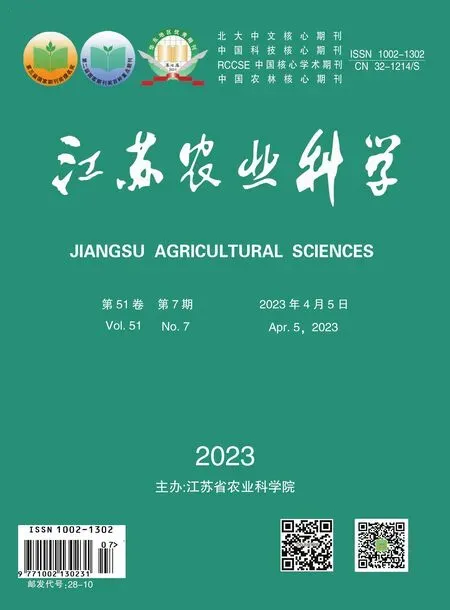不同凋落物水浸提液對杉木種子萌發(fā)和幼苗早期生長的化感作用
李夢琪, 趙 沖, 羅 航, 陳 杭, 劉 博, 王正寧
(1.福建農(nóng)林大學(xué)林學(xué)院,福建福州 350007; 2.曲阜師范大學(xué)生命科學(xué)學(xué)院,山東曲阜 273100; 3.莆田南門學(xué)校,福建莆田 351100)
凋落物是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一部分,參與了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物質(zhì)循環(huán),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森林的生長及天然更新[1]。凋落物層是植物種子脫落后的最初始階段接觸的物理環(huán)境,而在森林天然更新的過程中,種子萌發(fā)及早期生長階段最為敏感和脆弱,也明顯受到凋落物的影響[2-4]。目前,凋落物的水源涵養(yǎng)和水土保持功能、養(yǎng)分循環(huán)狀況及分解速率等一直是凋落物生態(tài)學(xué)方面研究的重點(diǎn),而目前尚少見將凋落物作為單獨(dú)的因子研究其對森林植被更新的影響[5-6]。
物理、化學(xué)和生物作用機(jī)制是凋落物影響種子萌發(fā)和早期生長的三大作用機(jī)制,其中化學(xué)作用,即化感作用具有重要影響[7]。研究發(fā)現(xiàn),森林凋落物可以通過雨水淋溶、腐爛分解或者微生物作用等途徑將化感物質(zhì)釋放入土壤環(huán)境中,影響種子休眠、萌發(fā)、幼苗生長等過程,進(jìn)而調(diào)節(jié)群落的物種組成,并進(jìn)一步影響種群的自然更新和群落演替等過程[8-9]。羅俠等的研究結(jié)果顯示,不同干質(zhì)量濃度(0.025、0.050、0.100、0.200、0.300 g/mL)的天山云杉(Piceaschrekiana)凋落物水浸提液對自身種子萌發(fā)和幼苗生長均起著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并且濃度越高,抑制作用越強(qiáng)[10]。晉夢然等為了研究格氏栲(Castanopsiskawakamii)天然林凋落物浸提液對杉木(Cunninghamialanceolata)種子萌發(fā)與胚根生長的影響,分別對不同分解層、不同濃度凋落物浸提液與種子萌發(fā)和生長相關(guān)指標(biāo)的相關(guān)性進(jìn)行分析,結(jié)果顯示,5種料液比(1 g ∶5 mL、1 g ∶10 mL、1 g ∶30 mL、1 g ∶50 mL、1 g ∶100 mL)的格氏栲天然林凋落物浸提液對杉木種子萌發(fā)總體表現(xiàn)出“低促高抑”的作用[11]。莊正等通過設(shè)置不同濃度(10、20、40 g/L)的杉木凋落物水浸提液,研究其對杉木種子萌發(fā)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過氧化物酶(POD)等相關(guān)酶活性的化感作用,結(jié)果表明,化感作用強(qiáng)度與浸提液濃度呈正相關(guān),對杉木種苗的抑制作用隨杉木凋落物浸提液濃度的增加而增強(qiáng)[12]。雷日平等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不同濃度華山松(Pinusarmandi)與銳齒櫟(Quercusacutissima)凋落物浸提液對油松(Pinustabulaeformis)種子發(fā)芽無顯著影響,但對油松幼苗的生長均有明顯的促進(jìn)作用[13]。眾多研究結(jié)果表明,化感物質(zhì)對植物生長會產(chǎn)生各種促進(jìn)或抑制作用,但是由于森林的樹種組成不同,各種林分差異明顯,不同類型的凋落物(如針葉和闊葉)在分解時(shí)產(chǎn)生的化感物質(zhì)也不相同,在不同濃度處理下植物的反應(yīng)也有所差異,因此會對種子萌發(fā)與幼苗生長產(chǎn)生不同影響[11,14-15]。
杉木是我國南方地區(qū)種植面積最大的經(jīng)濟(jì)樹種,在滿足我國木材需求和維持生態(tài)安全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但在長期的經(jīng)營過程中,杉木人工林因林分結(jié)構(gòu)簡單、林齡單一,引起了一系列種植障礙,如土壤板結(jié)、養(yǎng)分含量降低、有毒物質(zhì)積累及林木產(chǎn)量難以長期維持等,這些都會影響杉木林的可持續(xù)健康發(fā)展[16]。木荷(Schimasuperba)是我國常見的常綠闊葉樹,以其為優(yōu)勢種的常綠闊葉林群落在我國南方地區(qū)分布廣泛。何宗明等通過6年的觀測試驗(yàn)發(fā)現(xiàn),杉木的8種伴生植物中木荷對杉木株高的促進(jìn)效果最明顯[17]。曹光球也通過試驗(yàn)證實(shí),在種間生化物質(zhì)關(guān)系的研究中,木荷化感物質(zhì)對杉木化感物質(zhì)的毒性具有一定程度的降解作用[18]。因此,目前木荷也被當(dāng)作杉木的理想混交樹種廣泛用于營造針闊混交林分[19]。部分研究發(fā)現(xiàn),影響杉木種子萌發(fā)及幼苗生長的原因之一是林下不斷累積的凋落物產(chǎn)生的化感物質(zhì)抑制了杉木種子萌發(fā)及幼苗生長,但是目前尚不清楚杉木和木荷混交后會對杉木種子萌發(fā)和幼苗生長機(jī)制產(chǎn)生怎樣的影響[3]。并且,盡管目前已有關(guān)于凋落物浸提液對種子萌發(fā)和幼苗生長的研究,但是大部分研究都采用培養(yǎng)皿的試驗(yàn)方法[20],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試驗(yàn)采用盆栽方法,種子萌發(fā)與幼苗生長試驗(yàn)均在花盆中進(jìn)行,更有利于模擬自然環(huán)境。本試驗(yàn)設(shè)計(jì)參考前人的方法,設(shè)置3種凋落物類型(杉木、木荷、混合凋落物)和5種浸提液濃度(0與10、20、50、100 g/L 浸提液)[11-12,21],探究凋落物的化感作用對杉木種子萌發(fā)、幼苗存活、生物量累計(jì)和分配及幼苗葉片生理特性的影響,從而探明不同類型凋落物的不同濃度浸提液如何影響杉木種子的萌發(fā)及生長,為杉木人工林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提供依據(jù)。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yàn)材料的收集與處理
本試驗(yàn)所需的杉木種子于2017年11月下旬從福建省漳平五一國有林場(25°02′N,117°29′E)收集,本試驗(yàn)于福建農(nóng)林大學(xué)林學(xué)院實(shí)驗(yàn)室開展。試驗(yàn)開始前,先用0.3%高錳酸鉀(K2MnO4)對種子進(jìn)行消毒,30 min后用去離子水把種子清洗干凈,將種子靜置3 h后,去除浮在水面的種子,再把剩下的種子放置在45 ℃溫水中自然冷卻,浸泡時(shí)間為1 h,最后挑選自然下沉、形狀大小一致的種子備用[10]。
收集杉木、木荷的凋落物帶回實(shí)驗(yàn)室,等凋落物自然風(fēng)干后,將其放進(jìn)烘箱中烘至恒質(zhì)量,隨后用粉碎機(jī)粉碎,再用2 mm篩過篩。試驗(yàn)共設(shè)置3種凋落物類型(杉木、木荷及混合凋落物),每種類型的凋落物各稱取100 g裝入棕色瓶子中,注入 1 000 mL 蒸餾水,在室溫下避光浸提48 h,然后將溶液過濾,把提取的浸提液放入棕色瓶中,于2 ℃低溫保存。試驗(yàn)時(shí)將母液稀釋至10、20、50、100 g/L,經(jīng)高壓滅菌后儲存?zhèn)溆?以滅菌后的蒸餾水(0 g/L)作為對照。
本試驗(yàn)為盆栽試驗(yàn),以河沙為生長基質(zhì),每盆稱取3.2 kg清洗后經(jīng)高溫滅菌的河沙,每個(gè)處理設(shè)置5個(gè)重復(fù),每個(gè)重復(fù)均勻撒播50粒經(jīng)過處理的杉木種子。用3種不同類型的水浸提液進(jìn)行噴灑,每種類型的凋落物水浸提液設(shè)置5種濃度(0、10、20、50、100 g/L),第1次均噴灑100 mL水浸提液,對照噴施100 mL蒸餾水。之后每隔2 d噴灑50 mL水浸提液和蒸餾水。種子萌發(fā)結(jié)束后繼續(xù)進(jìn)行幼苗生長試驗(yàn),此時(shí)將澆灌時(shí)間延長至3 d 1次。
1.2 指標(biāo)測定內(nèi)容與方法
1.2.1 種子萌發(fā)指標(biāo)的測定 將種子播種后,每天記錄其萌發(fā)狀況,連續(xù)2周后沒有新種子萌發(fā)便結(jié)束觀測試驗(yàn),萌發(fā)時(shí)間大約為1個(gè)月。種子萌發(fā)的標(biāo)準(zhǔn)為出現(xiàn)第1張真葉;幼苗存活的標(biāo)準(zhǔn)為具有鮮活的根、莖、葉[22]。相關(guān)計(jì)算公式:
種子萌發(fā)率=(種子發(fā)芽數(shù)/種子數(shù))×100%;
幼苗存活率=(試驗(yàn)結(jié)束時(shí)存活的幼苗數(shù)/種子發(fā)芽數(shù))×100%[23]。
化感作用(RI)計(jì)算公式:
RI=1-C/T。
式中:T為處理值,C為對照值[11]。當(dāng)T≥C、RI>0時(shí)為促進(jìn)作用;當(dāng)T 1.2.2 幼苗形態(tài)指標(biāo)的測定 種子萌發(fā)試驗(yàn)結(jié)束后,不改變?nèi)魏苇h(huán)境條件繼續(xù)培養(yǎng)幼苗2個(gè)月,全部試驗(yàn)結(jié)束后,收回所有培養(yǎng)的幼苗,清洗干凈后每盆隨機(jī)選擇5株幼苗,分離其根、莖、葉,然后用毫米刻度尺測量杉木幼苗的根長、莖長和株高,記錄數(shù)據(jù)。 1.2.3 幼苗生物量積累及其分配測定 用信封將幼苗的根、莖、葉進(jìn)行分裝,裝好后置于80 ℃烘箱中,干燥48 h至恒質(zhì)量,用0.000 1 g電子分析天平稱質(zhì)量,分別計(jì)算根、莖、葉的生物量和總生物量與根生物量占比(根生物量/總生物量)、莖生物量占比(莖生物量/總生物量)、葉生物量占比(葉生物量/總生物量)、根冠比(根生物量/地上生物量)[3]。 1.2.4 幼苗葉片生理指標(biāo)的測定 試驗(yàn)時(shí)先將杉木幼苗葉片用純水沖洗干凈、擦干,從中稱取0.2 g放入提前預(yù)冷卻的研缽中,隨后加入1 mL pH值為7.8的磷酸緩沖液將其研磨成勻漿,再用4 mL磷酸緩沖液,多次少量地將勻漿沖洗到5 mL離心管中,用離心機(jī)冷凍離心(4 ℃、10 000 r/min)20 min后,用膠頭滴管吸取上清液到新離心管中,放入4 ℃冰箱中保存,作為待測酶液,可以用來測定SOD、POD、過氧化氫酶(CAT)活性及丙二醛(MDA)含量,每個(gè)指標(biāo)都需測定3次[12]。 本試驗(yàn)采用氮藍(lán)四唑法對SOD活性進(jìn)行測定[24],POD活性的測定選用愈創(chuàng)木酚法[25],CAT活性的測定采用紫外吸收法[26],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27]測定MDA含量。 本試驗(yàn)用Excel 2010對數(shù)據(jù)進(jìn)行整理,用SPSS 20.0軟件對整理后的數(shù)據(jù)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用Excel 2010、Origin 2018進(jìn)行圖表的繪制,采用雙因素方差分析法(Two-way ANOVA)分析不同類型、不同濃度凋落物水浸提液以及兩者交互作用是否對杉木種子萌發(fā)率、幼苗存活率、根長、莖長、苗高、根生物量、莖生物量、葉生物量、總生物量、根生物量占比、莖生物量占比、葉生物量占比、根冠比及SOD、POD、CAT活性、MDA含量產(chǎn)生顯著影響,用最小顯著性差異法(LSD)進(jìn)行顯著性檢驗(yàn)。 由表1可以看出,凋落物水浸提液的濃度對杉木種子萌發(fā)及幼苗存活存在極顯著影響,凋落物水浸提液類型及凋落物水浸提液的濃度與凋落物水浸提液類型的交互作用則對其無顯著影響。 圖1顯示,本試驗(yàn)所挑選的3種類型的凋落物中,隨著凋落物浸提液濃度不斷增高,杉木種子的萌發(fā)率和幼苗的存活率呈現(xiàn)出先升高后下降的趨勢。在3種凋落物水浸提液作用下,當(dāng)濃度為10、20 g/L時(shí),種子萌發(fā)及幼苗的存活都受到促進(jìn),當(dāng)水浸提液濃度提升至100 g/L時(shí),則會抑制種子萌發(fā)及幼苗的存活,且濃度越大,抑制作用越強(qiáng)。當(dāng)浸提液濃度為10 g/L時(shí),杉木、混合浸提液處理下種子的萌發(fā)率、幼苗的存活率均高于木荷凋落物浸提液處理,而當(dāng)浸提液濃度提升至20、50、100 g/L時(shí),木荷凋落物浸提液處理下種子的萌發(fā)率、幼苗的存活率反而高于杉木、混合浸提液處理。由此可以看出,在同樣的處理下,木荷浸提液對杉木種子萌發(fā)、幼苗存活的反應(yīng)與杉木和混合浸提液處理下的反應(yīng)有差異,但是杉木與混合凋落物浸提液處理下杉木種子的萌發(fā)率和幼苗的存活率差異很小。 由表1可知,凋落物水浸提液類型只對杉木幼苗根長起顯著影響,而對莖長、苗高無顯著作用,凋落物水浸提液濃度不僅影響杉木幼苗的根長,而且對其莖長、苗高都具有顯著影響,但凋落物水浸提液類型與凋落物水浸提液濃度的交互作用對三者均無顯著影響。 表1 不同凋落物水浸提液對杉木種子萌發(fā)率、幼苗存活率和生長及生理特征的雙因素方差分析 由圖2可知,隨著掉落物浸提液濃度的升高,杉木根長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且在10、20 g/L浸提液濃度下,根長均顯著高于對照,此時(shí)的濃度明顯是利于根系生長的;當(dāng)浸提液濃度為100 g/L時(shí),根長顯著低于對照,在杉木、木荷、混合浸提液處理下分別下降了約24.0%、19.2%、21.8%。在3種凋落物浸提液處理下,杉木幼苗的莖長、苗高整體上隨著濃度的提升而降低,除了在20 g/L濃度的混合浸提液下莖長高于對照,10 g/L濃度的杉木浸提液下苗高高于對照,其他濃度處理下的相應(yīng)指標(biāo)均低于對照。在3種浸提液處理下,幼苗莖長分別下降了14.0%、12.9%、12.9%,幼苗的苗高分別下降了13.1%、11.4%、20.3%。通過對比3種類型凋落物處理后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在杉木浸提液處理下,幼苗較高但根、莖長較短;在木荷浸提液處理下,幼苗根較長但莖長、苗高均受到抑制,而受混合浸提液的影響,杉木幼苗的苗高較低,根、莖較長。綜合比較分析得出,影響杉木幼苗根長、莖長和苗高的主要因素是浸提液濃度。 由表1可知,凋落物水浸提液濃度對幼苗根、莖、葉及總生物量均有極顯著影響,而凋落物水浸提液的類型以及凋落物水浸提液濃度與凋落物水浸提液的類型的交互作用則對杉木幼苗的葉生物量和總生物有顯著影響。 由圖3可知,在3種凋落物浸提液處理下,杉木幼苗的根、莖、葉和總生物量等指標(biāo)都呈現(xiàn)出先增后降的趨勢。在杉木浸提液和混合浸提液處理下,幼苗的根、莖、葉及總生物量都在10 g/L濃度時(shí)達(dá)到最高值,且高于對照,隨后便呈下降趨勢,在50、100 g/L濃度時(shí)均低于對照。在木荷浸提液處理下,幼苗的根、莖、葉及總生物量都在10、20 g/L濃度時(shí)高于對照,并且在20 g/L濃度時(shí)達(dá)到最高值,隨后在高濃度浸提液處理下,生物量顯著下降。在3種凋落物浸提液處理下,杉木幼苗的莖生物量在低濃度處理下顯著提高,而在高濃度處理下莖生物量與對照相比差異較小。幼苗的葉生物量與總生物量在不同浸提液處理下有幾乎相同的變化趨勢,在杉木浸提液處理下的幼苗根生物量低于木荷和混合浸提液處理下的根生物量。 由表1可以看出,不同凋落物水浸提液的類型對杉木幼苗的根生物量占比、葉生物量占比和根冠比影響顯著,而杉木幼苗的莖生物量占比受到凋落物水浸提液類型的影響并不顯著。不同凋落物水浸提液濃度對杉木幼苗莖生物量占比、葉生物量占比影響顯著,幼苗的根生物量占比、根冠比受浸提液濃度的影響甚微。凋落物水浸提液濃度與凋落物水浸提液類型的交互作用對幼苗生物量的分配無顯著影響。 由圖4可以看出,杉木幼苗的根生物量與根冠比的變化趨勢大致相同,隨著杉木凋落物浸提液濃度的提高,杉木幼苗的根生物量與根冠比下降,且均低于對照。在木荷浸提液處理下,幼苗的根生物量占比與根冠比在浸提液處理濃度為10、50 g/L時(shí)高于對照,而在100 g/L處理下低于對照。在混合凋落物浸取液濃度為10 g/L時(shí),杉木幼苗的根生物量占比與根冠比達(dá)到最大值,隨后隨著浸提液濃度的上升而降低,直至浸提液濃度為50、100 g/L時(shí)低于對照。杉木幼苗的莖生物量占比隨著凋落物浸提液濃度的提升呈現(xiàn)先降后升的趨勢。當(dāng)3種凋落物浸提液濃度為10 g/L時(shí),杉木幼苗莖生物量占比低于對照,而在50、100 g/L凋落物浸提液濃度下,幼苗莖生物量占比高于對照。隨著杉木浸提液濃度的提升,杉木幼苗的葉生物量占比呈現(xiàn)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趨勢,當(dāng)浸提液濃度為10、20 g/L時(shí),葉生物量占比高于對照,在浸提液濃度為50、100 g/L時(shí),幼苗葉生物量占比稍低于對照。在木荷浸提液處理下,只有當(dāng)浸提液濃度為20 g/L時(shí)幼苗的葉生物量占比高于對照,其余濃度處理下均低于對照。在不同濃度的混合凋落物浸提液處理下,杉木幼苗的葉生物量占比均小于對照。 由表1可以看出,凋落物水浸提液的類型會顯著影響幼苗葉片中的SOD、POD活性和MDA含量,而杉木幼苗葉片中的SOD、CAT、POD活性和MDA含量受浸取液濃度的影響較大,且效果極顯著,兩者的交互作用則會對幼苗葉片SOD、CAT活性及MDA含量產(chǎn)生顯著影響。 由圖5可以看出,隨著凋落物浸提濃度的提升,杉木幼苗的SOD活性表現(xiàn)出先升后降的變化,最終低于對照,而POD、CAT活性和MDA含量在3種凋落物浸提液處理下隨著浸提液濃度的上升有不同的變化,但最終都是顯著高于對照。當(dāng)杉木浸提液濃度為10 g/L時(shí),杉木幼苗葉片中的SOD活性比對照高,在其余浸提液濃度下,杉木幼苗葉片的SOD活性均低于對照。POD、CAT活性及MDA含量的變化趨勢則與SOD活性剛好相反,在浸提液濃度為 10 g/L 時(shí)低于對照,其余濃度下高于對照。在木荷浸提液處理下,幼苗葉片的SOD活性在浸提液濃度為20 g/L時(shí)達(dá)到最高值,在浸提液濃度為100 g/L時(shí)達(dá)到最低值且低于對照,其余均高于對照。杉木幼苗葉片的POD活性與MDA含量在木荷浸提液濃度為20 g/L時(shí)最低,在浸提液濃度為100 g/L時(shí)高于對照;CAT活性隨著浸提液濃度的上升而提升,且在每個(gè)梯度處理下都高于對照。在混合凋落物浸提液處理下,杉木幼苗葉片的SOD活性在浸提液濃度為10、20 g/L的處理下高于對照,在浸提液濃度為50、100 g/L的處理下低于對照;POD、CAT活性及MDA含量的變化趨勢與在杉木浸提液處理下的變化趨勢相同,表現(xiàn)為先降后升,差異在于各濃度之間的變化比例不同。在整個(gè)生理變化過程中,杉木與混合凋落物浸提液處理下杉木幼苗的酶活性反應(yīng)大致相同,與木荷凋落物水浸提液處理下的反應(yīng)有明顯差異。在高濃度浸提液處理下,杉木幼苗的生理結(jié)構(gòu)受到破壞,酶活性變化與對照相比具有顯著差異。 森林凋落物是化感物質(zhì)的重要來源之一,由凋落物分解產(chǎn)生的化感物質(zhì)進(jìn)入土壤中后,會影響土壤的理化性質(zhì)和微生物群落組成與結(jié)構(gòu),導(dǎo)致其周圍的微生態(tài)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從而影響林下植物的生長和林木自然更新,最終可能導(dǎo)致群落退化[28]。本試驗(yàn)結(jié)果顯示,在3種凋落物浸提液處理下,低濃度處理對杉木種子萌發(fā)、幼苗存活起到積極的促進(jìn)作用,而在高濃度處理下,杉木種子萌發(fā)與幼苗存活則受到抑制,這與已有研究結(jié)果[18,29]一致。由于凋落物在分解過程中會將養(yǎng)分歸還給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因此在初期會促進(jìn)杉木種子的萌發(fā)和生長,而后期隨著化感物質(zhì)的不斷積累,細(xì)胞器受到破壞,植物難以有效地吸收和利用養(yǎng)分與水分,便會逐漸抑制種子的萌發(fā)、幼苗的生長[12]。對不同類型的凋落物而言,化感作用的強(qiáng)度也有所差異,在20、50、100 g/L木荷浸提液處理下,杉木種子的萌發(fā)率、存活率基本上高于杉木浸提液處理下的萌發(fā)率、存活率;在50、100 g/L混合浸提液處理下,杉木種子的萌發(fā)率略高于杉木浸提液處理下種子的萌發(fā)率,說明木荷化感物質(zhì)對杉木有毒化感物質(zhì)起到了一定的降解作用,杉荷混交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杉木連栽所造成的生態(tài)問題,這也是眾多研究者提出的解決杉木人工林更新困難的舉措之一。 化感作用對植物生長產(chǎn)生的影響最直觀的體現(xiàn)便是植株生長形態(tài)的變化,由植株地上、地下部分的形態(tài)變化狀況可以判斷植株受環(huán)境變化影響的程度[30]。劉忠玲等的研究結(jié)果顯示,同一植物在不同凋落物浸提液處理下的變化不同,而且相同植物的不同器官對浸提液處理的響應(yīng)也有差異[31]。在本研究中,杉木幼苗根部在3種不同濃度浸提液處理下最敏感,其根長、根生物量在不同濃度處理下的變化比莖長、苗高及葉生物量和莖生物量明顯,原因可能是化感物質(zhì)對植物生長的影響主要是以土壤為媒介,通過植物根系分泌、植物殘?bào)w和凋落物的分解及雨水淋溶等途徑進(jìn)入土壤中,通過土壤作用對其他植物的生長產(chǎn)生影響,因此,根系對化感物質(zhì)的感應(yīng)程度更加敏感,這點(diǎn)與葉玉娟等的研究結(jié)果[32]相似。當(dāng)?shù)蚵湮锝嵋簼舛葹?0、100 g/L 時(shí),發(fā)現(xiàn)木荷、混合浸提液處理下杉木幼苗的根生物量、莖生物量及總生物量高于杉木浸提液處理,說明在相同高濃度浸提液處理下,木荷凋落物及杉荷混合凋落物累積所產(chǎn)生的化感物質(zhì)與杉木自身凋落物產(chǎn)生的有毒物質(zhì)比對杉木幼苗生長的影響更小。化感物質(zhì)會導(dǎo)致植物幼苗生物量分配發(fā)生改變,本試驗(yàn)結(jié)果顯示,隨著浸提液濃度的提高,杉木幼苗的根生物量占比、葉生物量占比降低,而莖生物量占比升高,這種變化與前人的研究結(jié)果基本一致。在化感作用的影響下,植物會調(diào)整地上、地下部分的分配情況以更好地適應(yīng)環(huán)境[2,33]。從杉木幼苗生長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可以看出,幼苗的根長、莖長、苗高及總生物量在高濃度浸提液處理下均低于對照,可見林下不斷累積的凋落物會影響幼苗的生長。 植物體內(nèi)活性氧的產(chǎn)生和清除維持在一個(gè)相對平衡的狀態(tài),一旦外界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植物的生存受到威脅時(shí),植物體內(nèi)的自我保護(hù)機(jī)制就會發(fā)揮作用,通過抗氧化酶來清除多余的活性氧,SOD、CAT和POD便是控制植物體內(nèi)活性氧積累最主要的酶[34]。本研究結(jié)果顯示,杉木幼苗葉片中SOD活性呈現(xiàn)先升后降的趨勢,原因可能是浸提液濃度較低時(shí),幼苗的自我保護(hù)機(jī)制發(fā)揮作用,而使SOD活性升高,然而隨著浸提液濃度的升高,杉木幼苗的細(xì)胞膜脂過氧化程度加深,導(dǎo)致細(xì)胞受到更多傷害,進(jìn)一步影響到杉木幼苗細(xì)胞內(nèi)蛋白質(zhì)等物質(zhì)的合成,最終導(dǎo)致細(xì)胞抗氧化酶活性降低[35-37]。在本研究中,幼苗葉片的POD活性、CAT活性的變化趨勢與SOD活性相反,浸提液濃度越高時(shí),杉木幼苗葉片的POD活性、CAT活性反而越高,原因可能是在凋落物浸提液濃度較低時(shí),凋落物浸提液會促進(jìn)種子萌芽和前期生長活動(dòng),因而導(dǎo)致POD、CAT活性在低濃度時(shí)的變化并不明顯;但是當(dāng)?shù)蚵湮锝嵋簼舛冗M(jìn)一步提升后,植物體內(nèi)的活性氧過度積累,為了清除植物體內(nèi)的這些有害物質(zhì),導(dǎo)致POD活性、CAT活性顯著提升。MDA含量也能反映植物受傷害的程度,植物在正常生長的情況下,MDA含量處于較低水平,而在逆境脅迫下,MDA含量則會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和逆境的積累而顯著增加,植物器官受到損傷后則會發(fā)生膜脂過氧化作用[38]。本研究結(jié)果顯示,在10、20 g/L低濃度浸提液處理下,杉木幼苗葉片中的MDA含量變化不大,而隨著浸提液濃度的提升,杉木幼苗葉片中的MDA含量大幅增加,高于對照且在100 g/L濃度處理下作用最顯著,說明高濃度的浸提液處理破壞了細(xì)胞生物膜的結(jié)構(gòu)和功能,使得幼苗葉片正常代謝和生長受到阻礙,這與國內(nèi)外其他相關(guān)研究結(jié)果一致,隨著凋落物的累積產(chǎn)生的化感物質(zhì)破壞了杉木幼苗葉片的生理結(jié)構(gòu),不利于幼苗的生長[39]。 在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中,凋落物參與了物質(zhì)循環(huán)環(huán)節(jié),因此其分解產(chǎn)生的化感物質(zhì)會直接對植物的生長造成影響[40]。本研究結(jié)果表明,在3種類型不同濃度凋落物浸提液處理下,杉木種子萌發(fā)率、幼苗的存活率、生物量的累積均隨著濃度的提升呈現(xiàn)“低促高抑”的現(xiàn)象,說明隨著凋落物的累積,分解所產(chǎn)生的化感物質(zhì)對幼苗生長的抑制作用逐漸增強(qiáng),對幼苗的生理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嚴(yán)重破壞。因此,在杉木人工林的種植與日常養(yǎng)護(hù)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凋落物分解所產(chǎn)生的化學(xué)物質(zhì)對林木種子與幼苗的影響,及時(shí)合理地對林內(nèi)凋落物進(jìn)行清理是比較好的解決方法。另外,結(jié)合杉木種子萌發(fā)率和幼苗存活率及后期生長階段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在3種類型的凋落物處理下,木荷凋落物對杉木幼苗生長的抑制作用最小,其次是杉木與木荷的混合凋落物。可見單一的杉木林分是不利于其自身的更新與生長的,可以通過構(gòu)建杉木與木荷的針闊混交林,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杉木純林因凋落物累積所產(chǎn)生的化學(xué)作用而造成的生態(tài)問題。1.3 數(shù)據(jù)處理與統(tǒng)計(jì)分析
2 結(jié)果與分析
2.1 凋落物化感作用對種子萌發(fā)、幼苗存活的影響

2.2 凋落物化感作用對幼苗生長、生物量積累及分配的影響




2.3 凋落物化感作用對幼苗葉片生理特性的影響

3 討論與結(jié)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