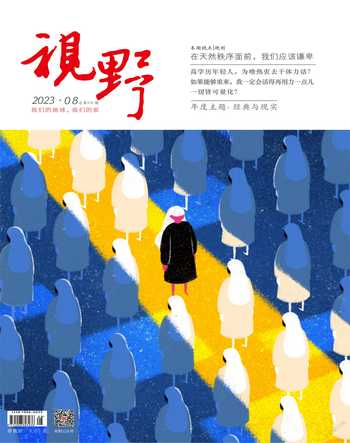留學美國第一年
蘭嶼

高一那年,我主動和父母提出了出國讀書的想法:美國,要走就走得遠些。現在回想起來,總會美化最初的動力和理由,但是時間和現狀告訴我,我當時的選擇沒有錯。我和父母長談了兩次,盡管多年以后我才得知他們對我強烈的不舍,但是在當時,我得到了十足的信任和支持。
于是15歲半的我開始申請美國的高中,準備入學考試、語言成績和面試。在一個波士頓的住校高中,和一個康涅狄格州走讀住寄宿家庭的學校之間,我選擇了后者,因為想體驗完整的美國文化和家庭教育。
2014年的夏天,我踏上了飛往美東的航班。
選擇一個適配自己的寄宿家庭,對獨身漂在異鄉的小留學生來說,非常重要。那時,我和父母選招了機構,由他們負責幫留學生對接美國當地的住宿家庭。美國當地的家庭在這樣的機構注冊報名,學生、美國家庭雙方都會提出一些對另一方的基本要求,例如是否能接受寵物,或者宗教信仰偏好。臨行前兩個月,我收到一封郵件,里面是匹配寄宿家庭的資料,有他們的名字、住址、愛好介紹和照片。
照片上的三個人,第一眼看上去,皮膚是棕色的,三人身形相似,圓圓的頭,圓圓的胳膊,圓圓的肚子,笑瞇瞇的。我對圓潤潤的人印象一般是向好的,比如《神探狄仁杰》里梁冠華老師一直都給人憨態可掬的親近感。
我相信我的父母在看到他們的信息和照片的時候,也是期盼他們能好好待自己的女兒,讓我能在異鄉有一個溫暖的港灣。沒有對比選項,我們都不知道這是否是最優選,但是既來之則安之,我愿意嘗試。
我們給學校付學費,也給寄宿家庭付住宿費,包括我們的飲食,和部分出行。有的家庭可能會同時接兩到三個留學生。后來的生活告訴我,有些家庭非常依賴這樣的額外收入,而有些家庭就算接受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對中文文化也根本不在乎。
為了讓我們對美國校園和生活文化有一些基本了解,美國機構在我們到達后,先讓我們在一個夏令營上兩周課,也就在那時候,我第一次見寄宿家庭。
照片上就是他們,一家三口,男主人Jose,女主人Maria,還有女兒Elizabeth。我到的時候他們已經圍坐在一個桌子旁了。Maria最先進入我的視線,有一頭油黑的泡面頭,人中的部位有一顆黑痣,身穿一個棕色的短袖裙。Jose戴個眼鏡,沒有脖子,眼角笑起來向下耷,很和藹的樣子,穿了一個白短袖,讓他看起來更豐潤,像個大雪人。他們還帶了女兒Elizabeth,活脫脫父母的縮影,也在旁邊笑呵呵的。他們分別給了我熱烈的擁抱,這種擁抱猛烈到讓人需要悄悄咳嗽一下的程度。簡單寒暄了幾句,他們就帶我上車準備開回康州的家。
“我們太開心見到你了。以后你可以和Elizabeth一樣,管我們叫mommy和daddy!”Maria在車上興致勃勃地跟我說,“我來自波多黎各,你知道波多黎各在哪嗎?是美國的一個附屬島,在加勒比海。”我趕緊掏出手機查了一下,波多黎各大概在北回歸線下方了,接近南美洲。
“Jose來自墨西哥,他是因為傳教來到美國的,他還有很多親戚都在墨西哥,我們是個移民家庭。”我點著頭,心里想著,移民家庭也好,會不會比白人多一些同理心呢?他們愿不愿了解中國文化?想著想著,我從書包里掏出從國內帶來的青花瓷優盤還有中國結,送給他們當見面禮。
開車兩個小時后回到了他們的家,已經晚上十一點了,我沒有看清房屋外面是什么樣,直接進了家門,他們讓我先休息,第二天再暢聊。他們帶我去臥室,從廚房旁邊的門進去,我跟著他們一步步下樓,逐漸確認了我將住在地下室。地下很空,我的房間在一個角落,房間有門,里面有簡單的床和學習桌,墻是紫色的,簡單但是溫馨。我沒有住過地下室,所有的“第一次”讓我在一開始都是興奮的。
第一夜很安適地過去,地下室的黑暗很適合入睡。在幽暗的空間里,聽不到清晨鳥叫,聽不到汽車的來來往往,只有烘干機產生的熱浪,還有樓上地板的吱呀聲。
第二天我出門特意看了一眼,這是一個在交叉路口的棕色兩層樓房子,房子前面有一片不大不小的草地。走動中,地板發出吱呀的聲音,應該是個年頭長的房子了。一層是客廳和廚房,很顯眼的是一排胡桃夾子,在壁爐旁,Maria說她特別喜歡收藏胡桃夾子,每年圣誕都會買一個。二層則是他們三個人的臥室。
Jose坐在屬于他一個人的沙發椅上,他窩在里面吃著薯片,看著電視,他的膚色和沙發顏色很像,人和沙發好像融為了一體。那時我不知道,以后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會很厭惡這個身影。
午飯時間,Jose和Maria教我禱告,我們一圈手拉著手感謝這一餐食物,我偷偷睜眼看了他們一眼,再安心閉上,感恩我能平安來到這個國度,有地方住,有飯吃。
第一頓飯后,我主動幫忙收拾餐具。在美國,家庭用一次性餐具很平常,如果家庭人口多,這樣就能避免每一餐都洗很多餐具,所以會用紙盤多一些。不過在他們家,是一次性塑料泡沫盤。我收走了大家手里的泡沫塑料盤,準備丟到垃圾桶,Maria趕緊制止了我,像是我要扔掉一堆黃金一樣。我眼睜睜看著她把塑料泡沫盤放進了洗碗機……
在這以后,他們拿出一張A4紙,上面有大概十幾條“家規”:
“塑料泡沫盤不能用一次就扔掉。”
“每周都要做大掃除。”
“晚上十點以后必須關燈。”
“我不能碰洗衣機,每周的臟衣服需要拿給Jose來洗。”
“不允許在房子內出現茶或咖啡(摩門教中禁止茶和咖啡)。”
“不允許帶零食進入臥室。”
“如果有中國同學在的時候,不能用中文溝通。”
......
我拿著這張紙回到我的地下室,這短短的幾步路一下子讓我對離開自己的家有了實感。青天白日,地下室一片漆黑,不開燈真的伸手不見五指,沒有窗戶。
8月底正午時刻,依然感覺到濕冷。
起初兩周,相安無事,我積極地做家務,每天都開開心心跟“daddy和mommy”擁抱問好。早上我自己做飯,他們家沒有做早飯的習慣。中午就在學校食堂吃,在家里吃晚飯時主動跟他們聊我學了什么。至于晚飯吃什么,Maria一般會在周日和周三做兩頓飯,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則是吃剩飯,反復吃冰箱里面的剩飯,裝剩飯的塑料盒都已經劃痕無數,有了陳年的味道。
但是,本著“入鄉隨俗”“安分守己”的想法,這樣的生活一直延續下去,倒也罷了。
Jose在修車廠工作,應該是個經理的樣子,Maria在一家食品公司上班。他們的女兒Elizabeth在上初中。因為一家子是西班牙拉丁裔,也是屬于少數族裔,所以他們的生活情況和我后來住的白人家對比,還是有些區別的。
Jose的家不是第一次接待留學生,我也不認識上一個,也從未了解他們之間的故事。我在他們面前已然沒有任何“矜貴”,我也從來沒有把“是我在付錢”這樣的態度表現出來。反而,他們每個月拿到了錢,也不愿意多做幾頓飯。家里做的最多的就是炒飯、煮雞肉和煎豬排,還有無窮無盡的玉米片。在學校的午飯時間,我悄悄倒掉了他們給我飯盒里帶的剩飯,已經是三天前的飯了,我看著這干癟的黃色米粒還有冰冷熟透的白色雞肉,嘆了口氣,丟進垃圾桶。我真的寧愿吃食堂的垃圾食品,至少是當天出爐的。在家里晚飯躲不過吃剩飯,我的腸胃開始變差,營養不良讓身型也有一些走樣,我真的怕有一天和他們一樣。
每次學校午餐時間,我們幾個留學生時不時會交流彼此的生存現狀。我了解到有的同學住在單身中年女性的家里,平時的生活倒也簡單,免去了和不同的人磨合。有的同學的住家也有法國黑人、海地人這樣的非白人家庭,體驗著不同的“融合”文化。有的同學住在中產的白人“完美家庭”里,聽起來的生活模式是我一開始想象的在美國的生活。不過后來我明白了,沒有標準的“美國生活”,這里本來就是一個大熔爐。
“那你們會叫住家daddy和mommy嗎?”我邊吃邊問。
“誰會這么叫啊!這太過了,反正我不會。”一個同學說道。
“對啊,這聽著就有點惡心啊。我們都叫名字。”另一個同學說道。
對,其實我也覺得有點惡心,畢竟在后面數年的生活里,無論對美國家里的長輩還是老師,都是可以叫名字的。我心里開始對這過分親密的稱呼有了抵觸。
說起我的學校,在住家相鄰鎮子的腹地。學校所在的鎮子非常富饒,附近居民的房子相隔都很遠,綠油油齊齊整整的草坪讓人看著甚是賞心悅目。住家所在的區域則是本州有名的“貧民窟”——間距很小的居民房子,犯罪率高,流浪漢多,街上破破爛爛的。
我的學校是一個私立天主教高中,同學間很多都是一家子兄弟姐妹都來這個學校上學,很多老師也都是這個高中畢業的,白人濃度非常高,除了中韓留學生,基本沒有少數族裔。那段時日,白天和夜晚,周內和周末,在學校和不在學校的日子,讓我感受到割裂,白人區天主教學校,貧民窟的住家,似乎這中間有一道無形的門,隔開我在不同世界的樣子。
在這里,我開始學習歐洲史、美國歷史、舊約新約圣經、希臘神話、美英文學、小語種這些不熟悉的領域,同時也確實是在數學、化學、生物這樣的課堂中當了佼佼者。有趣的是,英語母語的白人同學有的時候在英語課單詞考試的時候也會偷看我的答案,看來背單詞的痛苦程度沒有國界。
大概開學后第二周的一天,晚上九點半,我還在使勁研讀白天的歷史課本,各種南北內戰里將軍的名字在我眼前跑來跑去,我啃著筆頭,嘴里念叨著。我聽到通往地下室的門開了,一聲“十點了,該關燈了”!嚇了一跳,趕緊去關上房間里的燈。房間的門縫太大了,照出去的光足以在地面樓梯口看到。大抵是看到地下回歸黑暗一片,他們才放心。我拿出手電筒,躲在衣櫥的角落里,抱著和小西瓜一樣重的課本繼續閱讀。
一個周末,他們帶我去商場,臨走時,我買了一杯大杯的冰咖啡。坐車回家也不過是六七分鐘的路。下車以后剛準備進家門,Jose對我說:“別忘了紙上的規矩,茶和咖啡是一律不允許進這個家的。”說這話的時候,他還想故作幽默,但我真的笑不出來,看著這一杯還滿的冰咖啡,我一個人留在外面猛嘬,還伴隨著換手拿和小碎步蹦跳,一口氣喝完之后我感覺自己全身血管都是冰涼的。
Jose和Maria平日輪流開車接送我,但是不直接送我去學校,而是把我送到學校反方向的一個停車場,等待校車,放學亦是如此。他們不喜歡我打破這個規律,當我說我參加了學校的尤克里里俱樂部,需要每周二在學校多留一些時間,Jose冷下臉跟我說:“那你是要我去學校接你唄?”語氣里帶著強烈的不情愿。我只能卑微附和:“真的抱歉給你帶來了巨大的麻煩,非常感謝你,如果你能來接我。”
一天早上做飯時,可能火開大了,煙霧報警器響了,我又慌又急,關了火使勁想拿手驅散開濃煙。這時Jose從樓上下來,直奔廚房,把我趕到客廳,對我厲聲大罵。
平時擁抱,禱告,開玩笑,和藹面容,一剎那都跟著這煙一起散了。他就像是變成了一只猛獸,猙獰的面容,高音量的罵聲就沒有停過。Maria從樓上下來,安慰我說下次注意,然后就去安撫暴怒的Jose了,他們開始用西班牙語快節奏地對話,我猜應該是在抱怨我的。在學校里需要選擇小語種,我也沒有選擇最受歡迎的西班牙語,那段時間我厭惡西班牙語。
日子一天天過去,涼爽的秋天也漸入寒冬。雪一場場地下著,蓋過了那些枯葉。“家里”,噢不,屋子里的人漸漸也開始對我冷淡了起來。我覺得外面的冰雪甚至好過于屋中貌合神離的表面功夫。
后來我發現,Jose愛發火也不是一次兩次了。他經常對Maria還有Elizabeth大吼大叫,就像全天下那些欺負妻女、沒種的男人一樣。他對我如何,我也沒放在心上。但我真的痛恨他在教堂里那虛偽和善的笑容,以及他回家以后經常喜怒無常暴跳如雷的兇悍面孔。他永遠窩在那個沙發里,只要在這個房子里,他不是在臥室睡覺,就是蝸居在客廳的單人沙發上,伸著腳,吃著墨西哥玉米片,看著電視,跟一個發霉長芽的大土豆一樣。
Jose還是當地摩門教教會的一個理事人。家里經常會有一些傳教士來找他,這些年輕的傳教士來自西部的猶他州,他們會經常西裝革履來家里。當然了,Jose見他們的時候也是西裝革履,春風滿面,歡迎著一些來家里和他講經論道的年輕教徒們。他表現出一副圣父的面容,胖胖的體格加上一個個熱情的擁抱讓不了解他的人覺得這是一個傳播愛的人間使者。多么諷刺,裹在表層的慷慨和博愛,遮不住他內在的丑陋、虛偽。
有一天,我發現我的銀鐲子不見了。我問Jose,有看到我的銀鐲子嗎?他窩在那個沙發里,頭都沒轉冷冷回答我“沒有”。說實話,我當時并沒有懷疑,因為在我的理解里,他的“信仰”至少會約束一些行為。但是后來,我還是在他的車庫里的一個很不顯眼的格子里看到了我的鐲子。這不會是隨意掉落,我拿著它去找Jose,說這是我的,為什么在他的車庫里的一個工具箱旁。Jose的神色已經告訴我答案了,他的解釋是不知道這是誰的,就先保留起來了。
Jose已然如此,我在這個家唯一的“依靠”就是Maria了。直到一天夜里,我被敲門聲驚醒,Maria大聲喊我,把我從床上拎出來,讓我跟她去衛生間。我揉著眼睛,適應著有光亮的房間。“這是什么!這是血!是不是你弄到地上的!這是我們的房子!你不能把你的血弄到地上!還讓我看到了!這太惡心了!”Maria對我大聲咆哮。
我徹底醒過來,看了一眼衛生間的地上,有一滴血。是我月經期間不小心弄上的吧。我邊道歉,邊找紙巾蹲下把它擦干凈。兩個女性在深夜的衛生間里,我蹲著擦,她站著罵,因為一滴血。不知道她會不會這么對Elizabeth。
有一次我實在不想再用這些不知道之前誰用過的、快破洞的泡沫塑料的盤子,就把它們丟在垃圾桶里。她還是發現了,就跟每天對這些盤子都有計算著一樣,她把我叫來對我大聲呵斥。“這些泡沫盤子應該進洗碗機,我們會至少使用它們三次以上,我已經強調了很多次!你在浪費!”我站在垃圾桶旁邊被訓得抬不起頭,面對她瞪圓的眼睛和大聲的指責,我感覺我真的做錯什么一樣,我做錯了嗎?沒有服從這些可笑的規則?我真的不知道。
我和自己的親生父母視頻通話,和他們分享在學校發生的有趣的事,分享我是如何同Jose一家抗爭的,我和他們描述起來就像脫口秀一樣,把傷痛的的事情說得好笑,突出我“渡劫神仙”的角色。他們也通過我的眼睛看到了更多的世界,有時候幫我出謀劃策,有時候順應著我的自嘲,也可能有時候在默默心疼吧。
我知道爸爸媽媽是心疼的,但是他們和我一樣,我們三個從來沒有任何放棄和退縮的念頭,我會坦誠地和他們分享喜怒哀樂,但是是滯后的,因為我會讓每一段故事看起來“好玩”一些,而不是單純的痛苦。
這個家,對我來說一點也不像個家,更像一個訓練營。我在國內自己的家里也算不上嬌貴,在親戚和熟人眼里,我一直是一個獨立自信的孩子。但是這個“新家”讓我正向多了一層韌性,和負面多了一層隱忍。如果用顏色來形容自己,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橙色的,我給自己買的小飯盒也是橙色的。和他們住了一年以后,我感覺這層橙色蒙上了很厚一層土,變成了土橘色,沒有了活力。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懦弱的人,我不怕黑暗,不怕權威,不怕兇悍。但是在這個房子里,在Jose一家身邊,我覺得勇敢也起不到什么正面作用。沉默變成了主旋律,躲避變成了唯一的措施。
美東的冬天真長啊,從10月底到4月底都是冷的,經常有暴風雪,雪后會有鏟雪車把雪推到人行道旁,摞得高高的,路上還結冰。那個時候沒有打車軟件,我住的區域也沒有出租車。如果家里不送我,我哪里都去不了。偶爾還是會自己在冰雪里慢慢走著,雪水已經滲進了鞋縫,但我還是走著,只是想離開這棟房子,無論目的地是哪。
當時我總覺得家里有什么味道,除了地下的潮濕和揮之不去的剩飯,還有一種隱隱的說不上來的味道,直到在未來幾年我看了《寄生蟲》,才知道原來那是貧窮的味道。影片里別墅主人們總能聞到傭人一家身上的好像抹布一樣的味道,但是傭人一家自己聞不到。或許也不全是氣味的緣故,或許慢慢了解到他們的房子是在相對窮的區域,也或許是一次次看著他們“病態節約”的行為,再后來,才知道在美國,過度肥胖是一種貧窮的象征,沒有對健康和自律的敬畏。有一個描述更得我心,來自《呼叫助產士》:“貧窮不是指破房子、臟衣服、一大家子擠在一起;貧窮是沒有愛,甚至沒有尊重,不知道愛和虐待的區別。”
說起來,機構理事人也會定期來“家訪”和“校訪”來確保我們的利益,但是這種例行公事又真能問出來什么呢?更滑稽的是,那年中秋,這個白人理事人帶著一塊月餅來學校,給我們六個中國人分。那時候,我們每個人甚至吃不上一口完整的月餅。
其實我的中國朋友們也不都是順風順水,倒也沒有什么極端例子,我的處境就很罕見了,不過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綜合對比下來,我第一年在地獄,后兩年在天堂,其他人在煙火人間。
我以為我會像住在樓梯壁櫥的哈利·波特那樣,自帶主角光環來個絕地大反擊。其實沒有,一個學年終于結束了,那個夏天,我和機構申請了調換住家,因為學期內沒有空缺。機構理事人幫我重新對接了新的一家人,秋天回來以后就直接去了新的住家。
我和Jose他們沒有沖突,沒有告別,因為他們以為我還會回去,但是我沒有。同時我也沒有在心里原諒他們,苦難的意義都是人給予的,但是有些苦難的施加者仍舊不值得被原諒。暑假伊始,Maria送我到紐約肯尼迪機場,我從后備箱拿上行李,還了一個“永別式”的擁抱,頭也沒回走進值機大廳。
我走了之后,Jose一家繼續掙著留學生的錢,繼續他們那一套先禮后兵。另外一個中國女生住了進去,后來了解她和我的處境也差不多。夏天他們不讓她一天洗兩次澡,因為要“節約用水”。我后來搬到了一個真的像家的地方,新家的家人兩年如一日地對我溫柔如初見,八年過去了,我和新家的人還保持著有血緣關系一般的親近程度。
后來,我高中畢業,到了別的州上大學,讀研究生,后來回到了康州工作。24歲這年,我開車路過那棟房子,淺停了一下,望著這個棕色的牢籠,似乎還能看到那個地下室,那個沙發,那身影。嘆了口氣,緩緩駛離。
平心而論,無論有過多少憎惡和怨恨,我最后還是慶幸我不是出生在這樣的原生家庭,在那之后,我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孩子Elizabeth究竟會成長成什么樣子。愛麗絲·米勒在《身體不說謊》里說:“童年被愛著的人不需遵循任何戒律就會去愛他們的父母,被迫遵循戒律絕不可能是愛的基礎。”我希望她能對自己好一點,如果她有了自己的家,希望她不再重復使用塑料泡沫盤,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道路,讓自己身體更健康,不害怕親密關系,生活里不再有咆哮,不做社會強權下的犧牲品……
我走進大學,出入社會,搬過很多次家,結識了許多新的不同種族的人,我一次次迭代自己,用更寬的視野和更豐富的生活覆蓋掉那個房子里的回憶。不過后來我意識到了,它雖然不會成為我前進的助力,但是它會幫我吞噬黑暗。
(汪強摘自微信公眾號“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