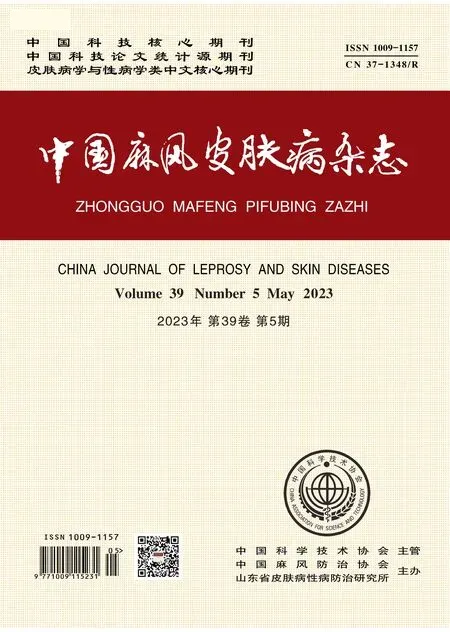惡性梅毒一例
于學紅 王牧原 孫曉靜
1山東大學附屬威海市立醫院,山東威海,264200;2山東第一醫科大學,山東濟南,250000
臨床資料患者,女,52歲。因軀干、四肢皮疹伴發熱1個月于2019年7月就診。1個月前發現軀干、四肢出現散在紅丘疹、結節,觸痛,無糜爛、潰瘍,皮疹逐漸增多增大,近半月來發熱,體溫37.5℃左右,感頭痛、頭暈、乏力,在當地口服“中藥”(具體不詳)治療10天無效。既往身體健康。體檢:T 37.6℃,腋窩、腹股溝未觸及腫大淋巴結,軀干、四肢多發米粒至蠶豆大鮮紅色水腫性丘疹、結節(圖1a),觸痛,部分皮疹中心有干燥結痂,無糜爛、潰瘍。掌跖、口腔、外生殖器無皮疹。各系統檢查未見異常。實驗室檢查:血、尿常規基本正常,血沉80 mm/h,體液免疫、淋巴細胞亞群、抗核抗體無異常。因診斷困難,擬做皮膚活檢,查傳染病四項發現血清TPPA陽性, TRUST 滴度1∶64,HIV抗體陰性,追問病史,患者7個月前有婚外性接觸史。診斷:二期梅毒。為防止吉-海反應,予口服潑尼松片10 mg,每天3次,共3天,繼之給予芐星青霉素240萬U臀部肌注,每周1次,共3次。40天后患者復診,軀干、四肢原有皮疹顏色變暗,但均未消退,呈多發的紫紅色扁平丘疹、結節(圖1b),無觸痛,無新發皮疹,無發熱、乏力。復查血清TRUST滴度1∶64。治療后3個月復診,皮疹呈暗紅色,部分丘疹、結節變平(圖1c),但皮疹均未消退,復查TRUST滴度1∶64。因皮疹持久不消退、血清TRUST 滴度不下降,給予查腦脊液TPPA、 TRUST均陰性,心臟彩超無異常。取皮膚活檢,組織病理示:表皮角化過度,真皮淺中層血管擴張、充血,大量淋巴細胞及少量漿細胞浸潤(圖2)。治療后5個月復診,皮疹顏色進一步變暗,呈褐色斑疹(圖1d),觸之無浸潤感,TRUST滴度1∶16。治療后18個月復診,TRUST滴度1∶2,皮損呈淡褐色萎縮性瘢痕(圖1e)。最終診斷:惡性梅毒。

圖1 1a:初診時軀干鮮紅色丘疹、結節、結痂;1b:治療40天后扁平紫紅色丘疹、結節;1c:治療3個月后丘疹、結節部分變平,顏色變暗紅;1d:治療5個月后皮損呈褐色斑疹;1e:治療18個月后皮損呈淡褐色萎縮性瘢痕

圖2 表皮角化過度,真皮淺中層血管擴張、充血,大量淋巴細胞及少量漿細胞浸潤(2a:HE,×40; 2b:HE,×100)
討論惡性梅毒是一種少見且嚴重的二期梅毒,1859年法國皮膚科醫生Pierre Bazin首次使用“惡性”一詞來描述這種特殊的梅毒,其發生機制尚不清楚,可能與機體免疫抑制、梅毒螺旋體強毒株等因素有關,目前報道的惡性梅毒常見于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患者[1,2],很少發生于免疫力正常的個體。有研究顯示,在11368例HIV感染者中,合并活動性梅毒者151例,其中惡性梅毒占7.3%,是一般梅毒人群的60倍[1]。1969年Fisher等[3]提出惡性梅毒的4條診斷標準:(1)梅毒血清學試驗強陽性;(2)可出現嚴重的吉海反應;(3)特征性的臨床和組織病理學表現;(4)對抗生素治療反應良好。惡性梅毒通常發生在原發性感染后6周~1年[4],其前驅癥狀為發熱、頭痛和肌痛[5],皮損通常開始為丘疹,然后迅速發展為潰瘍、壞死、結痂,很少累及口腔黏膜和掌跖部位。絕大多數惡性梅毒患者經規范化治療后, 全身癥狀迅速緩解, 皮損逐漸消退,預后良好[2]。惡性梅毒可導致瘢痕形成,梅毒后殘留的疤痕(彈性纖維破壞所致)即所謂的斑狀萎縮,是非常罕見的[6]。值得注意的是Yldzhan等[4]報道了1例因肥胖做了袖狀胃切除手術的病例,患者手術1年后發生了克羅恩病并接受阿達木單抗治療,第九次注射阿達木單抗后發現患有惡性梅毒,作者認為此例惡性梅毒的發生與阿達木單抗的免疫抑制、促炎細胞因子釋放作用有關。隨著生物制劑的應用日益廣泛和艾滋病發病率的升高,在看到丘疹、結節、潰瘍、結痂性皮損時,我們應注意排除惡性梅毒。本例患者經芐星青霉素治療后,TRUST滴度下降速度、皮損消退速度均非常緩慢,不除外與患者有潛在疾病導致免疫功能抑制有關,應長期隨訪觀察。另外,對于治療3個月后TRUST滴度下降和皮疹消退均不理想的患者,即使已經排除神經梅毒,也可以給予水劑青霉素和芐星青霉素足療程抗梅毒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