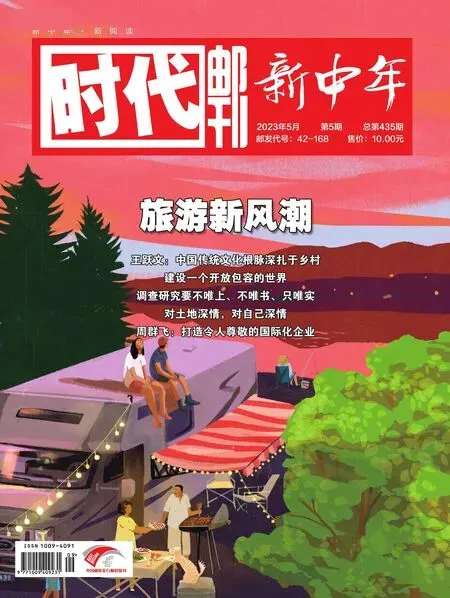“背奶媽媽”的隱秘戰爭
● 侯慶香
選擇成為母親,選擇堅守職場,選擇母乳喂養。這看似平常的三個選項,直到做母親,王廉才真正體會到其中的艱難。沒人告訴過她要怎么一邊不耽擱工作,一邊哺育孩子。
去上班,那怎么實現母乳喂養?帶著焦慮,她逛了一圈母嬰論壇,學到了一個新詞,“背奶媽媽”——在公司吸奶,下班帶奶回家的哺乳期媽媽。這似乎是最優解決方案,于是,一場“戰爭”在她結束產假、返回崗位的第一天拉開了帷幕。戰場上除了她,還有不計其數的母親。

顛沛流離的母愛
早高峰期間,在地鐵擁擠的人群里,“背奶媽媽”是很容易分辨的。她們隨身攜帶的物品格外多,用來冷藏母乳的冰包、電動吸奶器、洗刷用具、哺乳巾、儲奶袋等。
王廉在青島的一家體育用品公司工作,生育之前,她覺得自己的工作不算太忙,朝九晚五,雙休。自從做了“背奶媽媽”,盡管由于剛休完產假,工作量暫時只有之前的一半,她還是感覺自己成了突然被擰緊的發條。
晚上的睡眠被分成很多段,至少每三個小時要給孩子喂一次奶,一夜要起來三到五次。上班期間,一般每二到四個小時需要吸奶一次,每次吸奶大約用時半個小時,生活像她的身體一樣被擠壓。
有時領導布置緊急工作,王廉會盡量連續幾小時不休息不喝水不上廁所,領導說“沒問題”時才長舒一口氣,馬不停蹄跑去吸奶。同事看她拿著大包小包往外走,有時會調侃:“又去做飯啦?”公司沒有母嬰室,她找到了一間很小的廢棄廁所,放置好板凳后,她拿出吸奶器設置好,看著乳汁一點點填滿奶瓶,她感覺自己變成了一座“工廠”。
在一家媒體公司工作的陳蕙運氣好一些,她的公司有一間母嬰室,據說是由雜物間改造而成的。房間緊挨著樓梯,里面有張不小的桌子、三把椅子和一個一人多高的冰箱。第一次走進母嬰室的時候,她發現冰箱不通電,門鎖是壞的,每個人最想搶的是背對門的座位。
陳蕙印象最深的是有次自己背對著門坐在桌前,聽著外面的腳步聲和談話聲越來越響,很快掩蓋了面前吸奶器的嗡嗡聲。她分辨出來,聲音來自公司幾位高層領導,還有陌生的聲音,可能是老板在接待客人。她想:怎么聲音這么近?領導會不會誤入這個就在樓梯邊的小屋?低頭看著面前的吸奶工具和“袒胸露乳”的自己,她驟然緊張。
會議和出差是最讓“背奶媽媽”頭疼的。岳涵經常出差,每次她都要提前和當地酒店溝通,詢問有沒有冰箱,能不能存放乳汁。
出差兩三天還好解決,最長的一次出差時間是12天,岳涵每天都要上課、開會。她特意跟酒店要了一個冰箱,把吸出來的奶放進去。會議一開就是三四個小時,有時開著開著,她發現自己的胸部因為漲奶硬得像石頭,乳汁逐漸溢出,打濕了防溢乳墊。她會沖到離會議室最近的衛生間,拿出吸奶器,吸幾分鐘緩一緩,盡管脹痛的感覺還在,但只能趕緊回去繼續開會。
被吸奶這件事“綁架”了——這是很多“背奶媽媽”的感受,好像有一個四小時計時器懸在頭頂,時間一到,無論手頭上有什么事,都要先停下。
職場?媽媽?
2022年,中國藝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劉新宇出版了《禮俗時刻:轉型社會的嬰兒誕養與家計之道》一書,討論當下社會的母乳喂養環境與現狀。
在研究過程中,他接觸了許多職場媽媽,她們中有的為了無窮無盡的會議放棄“背奶”,有的特意在公司附近租一套房子,中午回家喂一次孩子。盡管母親們會為了最小程度影響工作使出渾身解數,但職場對“背奶媽媽”的“隱性歧視”依然存在,比如在獎金發放、職位晉升中的劣勢,或是被排擠在某個小群體外等。
他采訪過一位在大廠做程序員的職場媽媽,這位媽媽原本承擔的是程序維護工作,產假結束后,她回到公司,被調離原崗位做銷售。在劉新宇看來,“工作和生活”這一選擇題背后的本質是母親的犧牲。
在“職場媽媽”的標簽下,到底“職場”和“媽媽”哪個更重要?王廉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媽媽”。
王廉加入了很多“媽媽群”,在群里,她感受到母親的身份讓所有人形成了一個緊密的“聯盟”。給孩子喂奶是最重要的話題之一。她在有100多人的群里詢問職場媽媽在哪里吸奶,大部分人都說自己的公司沒有母嬰室,有的人甚至邊開車邊吸奶,還有的媽媽抱怨坐地鐵時,安檢員會詢問瓶子里裝的是什么液體,有的甚至被要求“喝一口”,“太尷尬了”。
公司的母嬰室是媽媽們的另一個“小世界”,“母親”這一身份認同在幾平方米的狹小空間里被放到最大。陳蕙第一次在母嬰室遇到別的媽媽的時候,站在門口有些猶豫,她和對方并不熟識,沒想到對方招了招手說:“來呀,一起吸呀。”很快,她也毫無心理負擔地招呼后進來的媽媽“一起來呀”。但走出這幾平方米的“結界”,她們在公司里再觸及母乳話題,總會帶著一些微妙的尷尬。
在母嬰室有冰箱之前,陳蕙試過把母乳放在公司公用的儲物冰箱里。她會封好儲奶袋后再加一層外包裝,但把母乳放在面包、蛋糕、冰淇淋旁邊,總讓她覺得有點不合適,她更擔心這也許會讓別人覺得不適。除此之外,擺在工位上的“背奶包”有時也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同事看到她放在窗臺上的“背奶包”,好奇地問“這是飯盒嗎”,她只能強裝鎮定掩蓋自己的尷尬。
有次陳蕙離開工位去吸奶時,一位年輕女下屬前來詢問工作事項,被另一位男同事告知陳蕙“去吸奶了”。尷尬感同樣包裹住了這位年輕女孩,她覺得自己似乎觸碰到了領導的私人領域。
負重的愛
“不管什么性格的人,做了母親之后,責任感和負罪感都會很強。”白雪成為母親后發現,無論是對孩子還是職場,她總是很容易感到愧疚,“平衡”成為了怎么都完不成的難題。
王廉每天都會記錄自己的吸奶量,有一天,她總共吸出了420毫升母乳,在日記里掩蓋不住興奮,覺得自己“站起來了”。在奶量不足的日子里,她會絞盡腦汁分析到底影響因素是什么,食物?工作壓力?和丈夫吵架了?對寶寶的愧疚感會持續到她下一次吸奶。
每次吸完奶,她也會在媽媽群里“打卡”,記錄吸出了多少奶。有時身體狀況好,她一次能吸200多毫升,但會特意在群里少報一點。“有的媽媽看到自己不如別人奶多,心里會不好受,覺得對不起寶寶。”
“母愛”的負擔越來越重。劉新宇發現,女性在母乳喂養過程中常常感到尷尬和挫敗,并且會因為難以平衡母親身份和社會角色而自責,進而產生愧疚感。尤其近年來,隨著嬰兒養育標準和成本的提高以及社會壓力的增加,女性承擔的社會責任越來越重,愧疚感便越發頻繁地出現。
在研究過程中,劉新宇加入了一個媽媽群,參加了數次線下聚會。媽媽們圍坐在一起,安慰著一位因為身體不適想停止母乳喂養的母親,但也有人勸她還是不要輕易放棄,“不然對孩子的愧疚感可能持續很久”。
一名叫鳳青的母親講述了她的“背奶”經歷,勸其他媽媽“打消這個念頭”。她覺得東躲西藏的自己格外狼狽,如果被男同事碰到,就算表面上“心照不宣”,心里也很別扭。更麻煩的是,她好幾次因為吸奶,在自己的工作環節掉鏈子,她愧疚地覺得自己沒干好工作,對不起團隊。“哺乳本該是在家里處理的‘私事’,而工作單位是公共場合,不應該把‘私事’帶過來。”
鳳青放棄“背奶”后,決定要在職場重整旗鼓,向將她換崗的領導證明自己的能力。但找回工作節奏并不容易,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她的生活重心全部放在孩子身上,突然的高壓工作讓她一下子很難承受,最難以接受的還是她之前指導過的年輕同事職務已經比她高了。“有些后悔沒有早點回來。”
鳳青想過辭職,但算了算養孩子的成本,很快放棄了這個想法。終于熬過“背奶”后,她換了新的著裝和妝容風格,挑了一個假期給鼻子做了微整形手術,決定開始“屬于自己的新生活”。
王廉實在不想在廁所吸奶,她找到人事部門磨了又磨,最終申請到了一間暫時不用的辦公室。但時不時會有同事進來打電話或處理其他工作,她只能趁著沒人使用的時候趕快把辦公室“占住”,有時一邊吸奶一邊能聽到同事在外面打電話的聲音,可能對方并不知道她在里面,但這同樣會讓她覺得尷尬。
王廉希望公司能設置一間專門的母嬰室,但并不敢貿然跟人事部門提出要求。“因為我們只是小眾群體。”但轉念一想,她又覺得哪里不對,畢竟每個女職員都有做母親的可能性。“如果能有個母嬰室,會覺得自己作為女員工得到了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