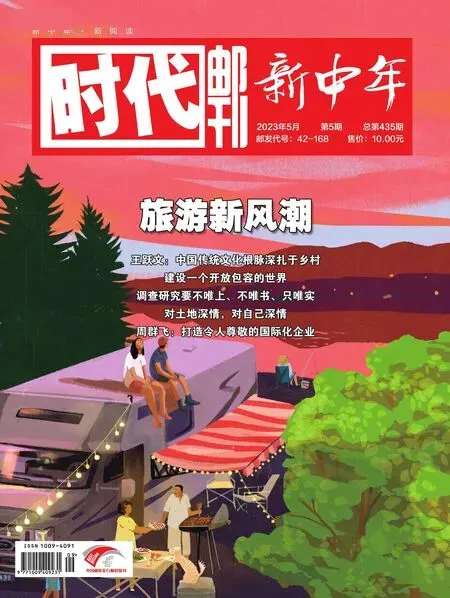他用雙手描摹地球“脊梁”
● 董瑞豐 彭韻佳
中國西南,川滇藏交會處,重巖疊嶂,雄嶺巍峨,是研究歐亞板塊和印度板塊碰撞過程的絕佳位置。
32年前,一名博士生用7年時間走遍南迦巴瓦峰地區,用雙腳丈量著鮮有外人涉足的土地,用雙手一寸一寸畫出這片區域的地質圖,讓喜馬拉雅東部大峽谷的真容第一次呈現在世人面前。
32年間,翻越一座座雪山,經歷一次次科考,對高原地質的熱愛,沉淀為更深摯的情感。歲月化成山風,吹白少年頭,58歲的他已滿鬢風霜,依然奔走在科研一線,勇攀青藏高原構造地質學的“科學高峰”。他就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員丁林。

▲ 丁林 (圖片來源:“北大人”公眾號)
用雙腳丈量地球巨型斷裂
青藏高原是研究地球板塊構造最理想的“天然實驗室”。1988年,剛出北京大學校門的丁林到中科院地質地球所讀研究生,跟隨他的導師、構造地質學家鐘大賚院士第一次到青藏高原考察。23歲的他被安排在中緬邊界地區的高黎貢山進行碩士論文寫作。
“當時很興奮,年輕也不害怕。”丁林回憶說,那個時候高黎貢山還沒有像樣的公路,白天他騎自行車或者走路去尋找新的勘探剖面,繪制地質圖,晚上就住在當地人翻山時借宿的山頂茶館或獵人的窩棚,和獵人“侃大山”,了解當地風俗。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一個多月。
跋涉在山林荒野,風吹日曬是常事。“我們都是鐵人,手里拿著地質錘、羅盤和放大鏡到處跑。”丁林笑著說。
即使在惡劣自然條件下,也要找到研究的“鐵證”。鐵人、鐵桿、鐵證——這是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名譽所長姚檀棟院士對丁林的評價。
“工作做完了,就要打上一顆‘金釘子’。”丁林說,在他看來,獲取“鐵證”最可信的是雙手和雙腳,無人機等現代科技只是輔助工具。“必須把手指放在要研究的斷層面上,獲得最踏實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丁林說。
群山浩蕩,高原遼闊。研究完滇西高黎貢山,丁林順著大山一路向北,挺進藏東南迦巴瓦峰——位于喜馬拉雅山最東邊的一座高山。那時西藏墨脫還沒有通公路,丁林便在每年5月至10月的“窗口期”翻雪山進南迦巴瓦進行研究,一干便是7年。
丁林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他用7年時間親手繪制了南迦巴瓦峰區域地質圖,讓喜馬拉雅東部大峽谷的真容第一次呈現在世界面前。接著,他沿雅魯藏布江繼續向西,首次在日喀則西側發現了印度大陸與歐亞大陸初始碰撞的關鍵證據。西至巴基斯坦北部的南迦帕爾巴特峰地區,東抵印緬交界的那加-若開山脈地區;翻越緬甸野人山,攀登珠穆朗瑪峰……這些人跡罕至的地方,都有他手持地質錘和羅盤奔波來去的身影。
很多人都知道,西藏自治區墨脫縣是西藏最后一個通公路的縣。而丁林在墨脫的山頂上挖開積雪采集樣品的時候,公路還沒修到那里,全靠他一步一步地走上去。
如今,丁林已經扎根青藏高原研究30余年,他的研究成果填補了國內外對于東喜馬拉雅構造結認識的空白,該區域至今仍是青藏高原以及世界地學研究的熱點。
“基礎研究總要有人做”
丁林已經記不清去過多少次青藏高原了。起初,路還沒修通,他從北京到云南昆明再到云南大理,從大理再到西藏墨脫,僅路上就要花費20多天。彎彎繞繞、磕磕絆絆的土路,從來沒有讓丁林停下腳步。
完成東喜馬拉雅構造結研究之后,丁林順著雅魯藏布江繼續向西,首次發現了雅魯藏布江縫合帶碰撞前陸盆地系統,隨后來到了喜馬拉雅山的西構造結——巴基斯坦南迦帕爾巴特峰地區。
對青藏高原癡心不改的求索,也回饋給丁林地球上最鮮為人知的秘密,他不斷拿出刷新世界認知的野外證據,在大陸碰撞、大陸俯沖、高原隆升領域取得了系統性創新成果:他提出了印度與歐亞大陸于6500萬年前首先在中部發生初始碰撞,隨后兩大陸之間的新特提斯洋向東西兩側逐漸封閉。兩大陸于5000萬年前全面碰撞的新模式,引領了國際印度-歐亞大陸碰撞研究,同時還開創了青藏高原大陸巖石圈俯沖研究的新領域。
后來,丁林把自己在青藏高原的科考路線導入地圖,猛然發現自己已經走遍了整個青藏高原,有的地方還被密密麻麻的路線反復覆蓋著。
從2005年到2007年,丁林六赴可可西里,組織完成了3次大規模科學考察。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探尋這片被視為“生命禁地”的無人區。
促使丁林數次帶隊勇闖可可西里的是一個最基礎的科學問題。在青藏高原核心區,有一條長約2500公里、寬約100公里、相對高差1000米的中央造山帶。造山帶以北發源的黃河、長江、瀾滄江等,都流向了太平洋;而造山帶以南發源的怒江、雅魯藏布江、印度河等,都流向了印度洋——它在地質學上的意義,顯然非同一般。那么,這條世界屋脊的“脊柱”,青藏高原的“分水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答案就藏在可可西里。
都說萬事開頭難,可是同可可西里打交道,這么多年從來沒有容易過:他們曾經與荷槍實彈的盜獵分子擦肩而過;曾經有同伴在野外突發闌尾炎,因為沒有條件做手術而命懸一線;他們還遇到過這樣的危急情況:地圖上指示的必經之路已被大水淹沒,只能靠隊員們在冰冷刺骨的湖水里站成一排人墻,指引并保護大型油罐車順利通過……但無論多苦多難多危險,丁林從未想過放棄。

▲ 丁林在藏北野外考察尋找古土壤(圖片來源:“北大人”公眾號)
六進六出,丁林完成了對可可西里的全面地質調查,提出了大陸俯沖誘發高原“隆升”的新理論,重建了高原主要山脈從海底到世界屋脊的差異隆升過程。他的一系列發現,對青藏高原地質形成機理和對環境氣候的研究意義重大,同時也有助于探索這一地區銅、鋰、鉛、鋅、金礦床成礦潛力和分布規律。
有人問他,為什么要做這些研究?“當時沒有想那么多。”丁林坦言,基礎研究總要有人做,如果不做,永遠不知道巖石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不了解我們生活的星球。
近些年,丁林承擔和參加了雅魯藏布江水電開發、川藏鐵路建設等重大工程的前期安全評估工作。“這時候再做基礎研究,就來不及了。”丁林有了新答案,“基礎研究能夠為國家重大工程應用做貢獻。”
“拎包”變“引領”
曾經,有關青藏高原地學研究的前沿領域多由國外主導。
丁林親歷了這一階段。國內儀器設備有限,往往借助國際合作開展青藏高原科考,采集的樣品也需送到國外開展少量分析,再加上對地質學的認識和積累有限,中國在國際青藏高原領域的原創研究很少,話語權很微弱。
篳路藍縷已成過去時。“現在,我們的研究手段不弱,研究理念也先進。”在丁林看來,中國在青藏高原研究領域從“拎包的”變成了“引領者”,地位在不斷提升。
2003年,丁林加入剛成立的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領導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大陸碰撞與高原隆升重點實驗室。實驗室掛牌之前,同行們幫著出主意,想出許多“高大上”的名字。丁林卻敲定了這個最樸實的名字——“大陸碰撞與高原隆升”。
“這個名字最土,卻很實。”丁林笑言,碰撞和隆升正是青藏高原研究的兩個關鍵詞。后來,這個“土名字”在國際上也叫響了。
印度和歐亞大陸持續至今的碰撞導致了青藏高原大規模隆升。近20年來,隨著定量古高度計的發展,高原隆升由定性描述轉向定量約束,科學家突然發現,對青藏高原的隆升歷史還很不清楚。
丁林發現,青藏高原并不是整體抬升,不同山脈各有千秋。
岡底斯山是青藏高原最古老的山脈,在高原產生之前已是一座影響全球氣候的巨大山脈;喜馬拉雅山卻非常年輕,6500萬年前印度與歐亞大陸碰撞之前它還處于海底,2400萬—1500萬年前才快速隆升到現今的高度。
隨著喜馬拉雅山“隆升”,季風大規模北上,來自印度洋的暖濕氣團受阻于喜馬拉雅山前,轉而向東傳輸,給我國東部帶去大量降雨,使得原來被沙漠覆蓋的江南變成魚米之鄉。
“青藏高原21世紀還有地理大發現!”丁林笑著說。他們提出的高原山脈差異隆升模型得到了國內外地理學界的廣泛認可,產生了很好的影響,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山濤風浪,歲月失語,唯石能言。正如高原磐石無聲地講述著滄海桑田,丁林堅守青藏高原研究30余年,用雙手一點點描摹地球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