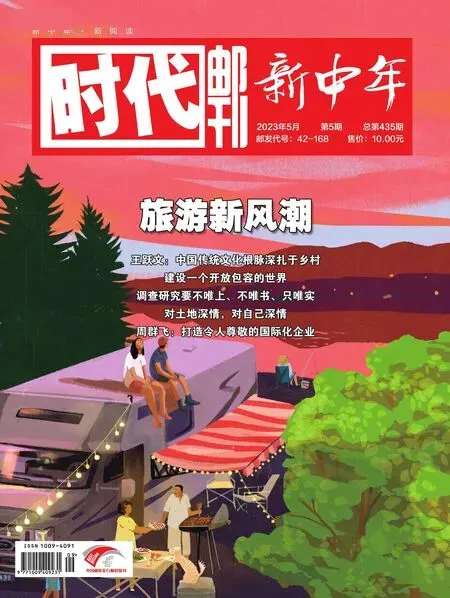堅守40年,他們將電影“譯”進苗侗山鄉
● 楊欣
暮色降臨,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凱里市三棵樹鎮板新村的廣場已經支起了投影幕布。飯后的村民三三兩兩圍攏過來,不一會兒,現場就坐滿了觀眾。這天播放的電影是諜戰片《風聲》,盡管村里的老人們都聽不懂普通話,可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因為電影中的所有臺詞均重新譯制成了苗語。電影里的配音無論是音色還是語氣,都十分貼近原片的角色。
這部電影的譯制工作來自貴州省黔東南州電影發行放映有限公司民族語影視譯制制作中心。此中心成立于1981年7月1日,是全國11家少數民族語譯制中心之一。成立至今,中心累計用苗侗語翻譯電影作品1000多部,放映10萬余場,觀眾達1500多萬人次。

▲ 2017年,貴州省黔東南州電影發行放映有限公司民族語影視譯制制作中心內,配音演員身著民族服飾為電影《戰狼2》配音

▲ 2018年9月,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縣雅灰鄉送隴村,群眾正在觀看苗語譯制電影
在電影里聽到親切的家鄉話
貴州省黔東南州電影發行放映有限公司民族語影視譯制制作中心的門前掛著一年內的譯制計劃:《中國藍盔》《平原槍聲》《懸崖之上》……“這些影片都是主旋律、正能量的電影,我們希望傳遞到基層的文化作品是有品位、有內涵的。”公司黨支部書記宋其生說。
在貴州,部分地區少數民族群眾不同程度存在國家通用語言使用障礙。譯制中心退休配音演員汪蘭剛參加工作那會兒,她們苗寨里沒有一個人會說普通話,就連她自己都只會認字而不會說。
基層群眾的文化發展被封閉了起來。“電影是很好的文化滋養工具,可在民族地區的農村,語言障礙阻擋了這一文化形式走向群眾。”黔東南州演藝集團副總經理李文坤說。
早些年,公司還承擔著到基層放映電影的功能,曾有一幕讓宋其生印象深刻:那天,放的是一部喜劇,聽不懂普通話的老人們,看著周圍的人在笑,他們也跟著笑,問他們笑什么,他們也只是搖搖頭。這讓他挺心疼的。
板新村村民楊文兵仍然記得,16歲那年看的第一部譯制電影是《黃橋決戰》,當聽到精彩的對白變成了家鄉話,他感到親切又激動,從此成了忠實的“影迷”。
“以前放電影,看的人不多,看懂的更少。現在村頭一放電影,基本都是坐滿人的,尤其像我母親這樣聽不懂普通話的老人,可以從電影里了解歷史文化,看懂故事情節。”楊文兵說。
“電影是大眾藝術,也是我們守住民族地區基層文化陣地的一件利器。正是因為這一點,才讓我們堅持了這么多年。”李文坤說。
苗嶺侗鄉里的翻譯家
讓楊文兵第一次看譯制電影就著迷的原因,來自一句臺詞。“電影原本的臺詞是‘你們從左邊走,我們從右邊走’,但翻譯成苗語之后,就變成了‘你們從長方田那邊走,我們從三角田這邊走’。長方田和三角田都是我們這邊的土話,一改成這樣,瞬間覺得電影離我們更近了。”楊文兵說。
這部電影正是宋其生負責翻譯的。1984年入職以來,宋其生從事少數民族語電影譯制工作已經快40年了。“給群眾翻譯電影,未必一定要雅,但還是要講個‘信’和‘達’。”宋其生說。由于最終作品面向基層的群眾,除了直譯,更多要用群眾熟悉的方式進行不失本意的轉譯。
第一部讓宋其生獲獎的翻譯作品是趙本山主演的電影《男婦女主任》。除了要讓大家看明白劇情,更重要的是如何讓西南地區苗侗群眾理解東北喜劇的笑點。“東北的二人轉,如果直接翻譯過來,群眾接受不了。”
宋其生熬了幾個晚上,填詞譜曲,將片中的東北二人轉全部翻譯成了苗歌、侗歌,“這就是大家日常喜愛的方式了,現場觀眾笑得前仰后合。”宋其生說。
臺本翻譯是第一步,配音則是第二步。
1984年,正準備大專入學考試的汪蘭在一次下鄉演出活動中被公司選中,第一次走進了錄音棚,給電影《玉碎宮傾》里的塔娜公主配音。膠片電影時代,電影配音沒有單獨的音軌操作,更不能剪輯,每一句臺詞的語速和感情都要跟上角色的口型,一配到底。“我的臺詞多,每卡殼一次,大家都要陪我從頭來一次。”汪蘭回憶說。雖然沒人怪她,但她看到所有人都在嘆氣搖頭。配音結束后,她沮喪地回去了。
沒想到,幾天后,她收到了公司一位領導的來信,稱贊她的配音非常有神,尤其是她的笑聲,完全把角色的特點“笑”了出來。汪蘭說,這句話讓她懷著失而復得的心情回到了公司。
第一次看到自己參與配音的電影,汪蘭確定了自己一生的事業,當即放棄了大專入學考試。
宋其生第一次配音的角色是戰爭電影《高山下的花環》中唐國強飾演的趙蒙生。這個軍旅角色前后變化巨大,人物故事豐滿,讓宋其生吃了大苦頭。就像繪畫一樣,沒有經驗,只能臨摹,宋其生不得其法,只能一句一句地琢磨,和原片對比。膠片珍貴,多看幾次就會有損毀,那就聽錄音。“這部電影的錄音,我聽了不下100遍。”宋其生說。
在隨后的39年里,宋其生參加譯制配音的電影有530余部,為2000多個角色配過音。就這樣,在200多萬字臺詞、48000多分鐘配音時長的磨礪中,當年的小宋變成了宋老師,越來越專業。
如今的宋其生在錄音棚里,劇情到哪兒,情緒就到哪兒,表情動作也到哪兒。一次配到爭吵時自責的臺詞,宋其生也像電影里的角色一樣,“啪”地給了自己一巴掌。等到結束后摸著火辣發燙的臉頰,才想起當時是怎么回事。
最難的時候連辦公場所都沒了
譯制中心在一棟老舊樓房的頂樓,但他們的錄音剪輯設備卻是嶄新的。“我們的經費主要用在了設備上,這幾套最新的設備加起來200多萬,比這層樓都貴。”公司總經理楊藝林自豪地說。
如今略顯寒酸的譯制中心,是黔東南州電影發行放映有限公司僅剩的業務部門。但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也是很“吃香”的。“以前的電影發行放映由各級放映公司負責,全州的電影發行放映業務都歸我們公司,還有財政補貼,收入很可觀。”楊藝林說。
宋其生曾經是十里八鄉的“土明星”,每次去放電影被人認出來,總是能得到最熱情的款待。“村支書知道是我給配的音,站起來就要敬我三碗酒。”宋其生說。
隨著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制度改革,公司逐漸風光不再。1994年,公司完全轉為企業自負盈虧,失去了財政補貼;2000年,原本多層級的電影發行放映模式變成了發行公司和制片單位直接向院線公司供片模式,中間各級電影發行放映公司業務被架空了。
發行和放映業務取消后,除了一些農村院線,整個公司還有業務的部門僅剩譯制中心。由于他們譯制的電影都是公益放映的,所以這項業務也不是個掙錢的活兒。
公司還活著,但越來越艱難。2002年,公司原來的大樓在政府拆遷范圍內,很快就變成了一處嶄新的廣場,新樓卻還沒開始修建。業務砍了,補貼沒了,最后連辦公場所也沒了,公司50多人集體待崗,每月只能領到198元錢的補貼。
令人驚訝的是,盡管數量減少,譯制中心每年仍有電影產出。“我們租了一個10平方米的小房子,用地毯貼到墻上自制隔音墻。平時做自己的事,一有配音工作就到小房子里開工。”汪蘭說。
他們到底是怎么堅持下來的呢?當年的老員工,有的說是靠自己外出打工兼職補貼撐下來的;有的說是靠主管部門一年幾千塊錢的微薄補貼生活,發著牢騷把活兒干完的;也有的說是2005年新樓修好之后靠收租過下去的:六層樓全部出租,譯制中心蜷縮在頂樓搭建的小房間里。
但宋其生明白,心里沒點牽掛,是撐不下來的。“我回家遇到老人們,他們會問我最近怎么沒電影了,我說不出話。”宋其生說。
汪蘭在公司發不出工資的時候,選擇去省城打工,在一家食品企業做銷售。由于手腳勤快、做人本分,她很快就得到了老板的賞識,不到三個月,就被提拔為區域銷售主任。“我原本想著打點零工補貼家用,有配音的工作就回去。”汪蘭說。可干到了銷售主任,就不可能隨時回去配音了。當譯制中心打電話通知說又有配音工作時,汪蘭在只能二選一的情況下,踏上了回凱里的班車。
十幾年后,那家小公司已經成當地的大企業,汪蘭身邊總有人開著玩笑說,要是她當初不回來,現在肯定發財了。“可我覺得,這幾十年我配的幾百部電影,才是我最大的財富。”她說。
最艱難的日子撐了7年。2009年,少數民族語電影譯制工作進入數字化時代,這一時期的補貼開始增多。黨的十八大以后,國家對于基層文化事業的投入也逐漸加大,各級政府的補貼也開始恢復。2018年,他們的譯制工作被納入國家級項目財政資助,譯制一部電影能獲得7萬元經費,徹底解決了譯制中心的生存困難。
“我們如今有設備,有經費,有人才,一年能完成48部電影的譯制。”宋其生說。除此之外,譯制中心也承擔著各類基層宣講的譯制任務:中央精神苗侗語宣講提綱、就業技能培訓課件、森林防火和疫情防控宣傳視頻等等。“群眾需要什么,我們就翻譯什么,不能浪費現在這么好的條件。”宋其生說。
他們譯制的電影通過更多屏幕走進苗侗山鄉
隨著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義務教育普及,不懂普通話的人越來越少,譯制電影最初的受眾也在收縮。但在李文坤看來,今天少數民族語電影譯制工作“兵強馬壯”,所承載的功能和價值也在不斷增加。
“以前是聽不懂普通話的群眾太多,現在是聽得懂苗語侗語的群眾太少。很多年輕人,都不會說民族語了。”李文坤說,由于苗語侗語沒有相應的文字記錄保存,作為少數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載體,離年輕人越來越遠了。
“現在很多新詞術語不斷出現,但由于語言文化保護措施跟不上時代的變遷,老祖宗原生態的語言漸漸離我們而去。所以我們在翻譯臺本的時候,必須時刻更新漢語知識的學習,鞏固少數民族語言的素材庫。”宋其生說,“最早我們是想要讓老百姓看好電影,如今則是要讓少數民族文化更好地傳承。”
下一步,譯制中心計劃改變現在單一的放映渠道,決定在新媒體上播放電影。“從文化保護的角度來說,我們現在需要更多年輕人成為我們的觀眾,譯制電影的翻譯需要跟上時代,放映渠道也要跟上時代。”李文坤說,“我們的譯制電影,會通過更多的屏幕走進苗侗山鄉。”
楊文兵今年50多歲了,距離他第一次看譯制電影已經30多年過去了,他已經不記得看過多少部電影了。如今每當村頭放電影,他還是會早早地守在那里。現在每次看電影,他還是會有第一次那種感動。他說:“無非就是個飯后消遣的事兒,他說卻還是有人專門用我們的語言來制作,說明我們在這么偏遠的山里,都還是被記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