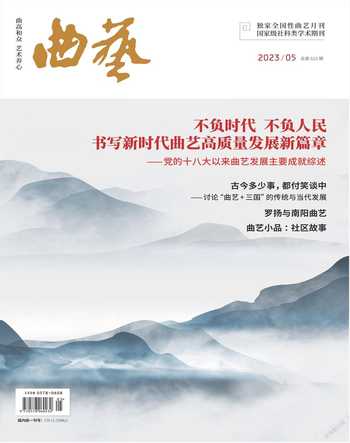永 聲
梁少鋒

2023年3月22日,粵曲子喉表演藝術家譚佩儀先生①走了,享年97歲。嶺南曲藝界的天幕上,隕落了一顆星星。
我是在參加了廈門一個文藝作品評獎活動之后驚悉這個噩耗的。那天早上,我在廈門與幾位中國曲協的領導和專家久別重逢,互相打聽各地故人歷經3年疫情后的狀況,都慶幸老人們躲過一劫。孰料傍晚回到廣州,我就聽愛人說譚老師走了。一剎那間,她的身影、音容,清晰地出現在眼前。
初識譚先生是在2008年廣東音樂曲藝團的春茗座談會上,其時,我剛從廣東開平市文化部門調到廣東省曲協不久,對這個在廣州舉辦的曲藝界名人年度聚會十分期待,并如愿見到了久負盛名的粵曲名家黃少梅、勞艷娟、何萍、陳玲玉、梁玉嶸,曲作家蔡衍棻,粵語相聲名家楊達、黃俊英,音樂演奏家湯凱旋、何克寧等。譚先生低調地坐在側桌,偶爾與旁人細語幾句,當我被同事引介給她時,她像鄰家慈祥老奶奶般微笑著打招呼,還緊緊地拉著我的手,令我感到很親切。
此后,在廣東曲協啟動省內各縣市創建“廣東省曲藝之鄉”的活動中,有幾次我在基層曲藝社團中見到譚先生,知道她經常到“私伙局”中活動,還時常指點年輕的粵曲從業者度曲。我開始格外地關注她的藝術人生特別是退休后的生活狀況,因此,當《中國社會科學報》的記者要我幫忙聯系一位曲藝表演藝術家接受采訪時,我就毫不猶豫地推薦了譚先生。這個采訪是挺費勁的,因為那位記者聽不懂粵語,而譚先生只會講粵語,還聽不懂普通話。我這個中間人還客串了一把翻譯。累是累了些,但我也借此加深了對譚先生的認識。
譚先生原名李素薇,1926年2月28日生于廣東鶴山,4歲喪父,迫于生計,隨母親輾轉來到廣州生活。剛開始接觸音樂,她就有幸師從粵樂“超級發燒友”譚雨初。譚雨初喜歡與樂師們一起“玩”音樂,對于廣東音樂甚至是西洋音樂,都能講得頭頭是道。“我很中意音樂,當初就是在老師家門口偷聽音樂,聽得入迷,連老師出來都沒發現,就這樣被收為徒弟。”這就是譚先生回憶中的師徒緣起。1937年,譚雨初教剛滿11歲的譚先生開留聲機放唱片,并為她精心挑選了合適的揚琴樂曲和粵曲唱段,譚先生就在他家里聽唱片、學彈唱。譚雨初家境殷實,交游頗廣,呂文成、何澤民(何大傻)等名家常來他家中開局,演奏廣東音樂。耳濡目染之下,再有譚雨初收藏的薛覺先、徐柳先、顏思莊(上海妹)、區家駒(千里駒)、肖麗章、張瓊仙等粵劇名家大量唱片的“輔助”,天資聰慧的譚先生很快學會了揚琴等多種樂器的演奏,并在短短一兩年間無師自通地掌握了平喉、子喉、大喉3種粵曲唱法。
13歲時,譚先生已經能自如地演唱一些粵曲名段了,譚雨初則有意識地讓她在一些場合登臺表演。她曾在抗日名將、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的祝壽會上一人飾兩角,演唱了大喉名家熊飛影與源妙生對唱的粵曲《單刀赴會》。蔡廷鍇甚是喜歡,連連贊她“這小姑娘很聰明”。這份贊賞更堅定了她唱好粵曲的決心。而在日本帝國主義加快侵略我國的步伐、廣州黑云壓城的時候,她還有過一段遠赴韶關風灣鄉“走日本仔”的避難日子。在風灣鄉,譚先生經常隨譚雨初向當地的樂師學鑼鼓、揚琴和胡琴等樂器的演奏方式,為日后從事粵曲表演打下終身受用的音樂基礎。對于早年學藝歷程,對恩師譚雨初的教導與保護,譚先生懷念終生。就連“譚佩儀”這個名字,都是譚雨初為保護她而起的。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廣州茶樓幾乎都開設粵曲茶座,甚至一些賭場每晚都會請人唱曲。從韶關輾轉回到廣州后,譚先生與母親相依為命,為了生活,她決意以“譚佩儀”為名登臺獻藝,演唱粵曲。由于她悟性高、學曲快,成為專職藝人后,一些前輩藝人如郭少文、徐柳仙、熊飛影等平喉、大喉表演藝術家都喜歡找當時專攻子喉的她合作對唱曲目,其中熊飛影與她的搭檔更為默契。前輩們很疼愛這個小女孩,傾囊相授,從不藏私,因此譚先生后來提起這些名家時,總是會深情地說一句,“(他們)每一位都是我的師父”。
譚先生從老藝人身上學到了許多新曲目和好唱法,漸漸在曲壇唱出了名聲。抗戰勝利后,在廣州“大東亞”等當地有名茶座,就連尹自重等業內名樂師都常常與她搭檔演出。此后,譚先生在香港、澳門、廣州、梧州等地輪流演出,日益受到觀眾的喜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譚先生先后在徐柳仙的歌劇團、張月兒的新中國歌劇團、廣州音樂曲藝隊、麗聲歌劇團任演員。這期間,已經在香港打下曲藝事業基礎的譚先生回到廣州,代表廣州曲藝界參加了在武漢舉行的中南地區第一屆戲曲匯演,匯演結束后,廣州市文化局領導就找到她和李少芳,以她們為班底成立了曲藝互助組。這個互助組后發展為廣州音樂曲藝隊,譚先生任副隊長。
近代粵曲沒有獨立的藝術地位,主要在私家宅院或茶座等娛樂場所進行助興表演。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粵曲被歸入“曲藝”,才開始進入劇場表演。走紅曲壇后,喜歡粵曲的聽眾沒有誰不知道譚先生的,業內行家都夸她音域寬廣、玲瓏剔透、優雅委婉、字正腔圓。當時,有“粵劇伶王”之譽的薛覺先從香港回到廣州,想找一位唱功好的年輕花旦搭檔演出。在偶然聽到譚先生的演唱后,薛覺先十分賞識,“這個女孩唱得很好,聲音好聽到不得了,形象又好、化妝又漂亮,叫她不要做曲藝了,做粵劇吧。如果這個女孩以后做粵劇,會成為‘子喉王”,并力邀她作為自己的搭檔一起演粵劇,然而,他被婉拒了。
我曾問過譚先生,“為什么沒有選擇跟隨薛覺先這樣一位馳名粵港澳的大佬倌搭檔演粵劇?這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呀!”她說當時沒有想那么多,自己就是喜歡演唱粵曲、喜愛琢磨怎么唱好粵曲,“若現在來選,還是一樣。”我想,這就是她始終不渝的初心吧。而從婉拒薛覺先邀約的那一刻,譚先生的青春、理想、情懷,都與粵曲深深地關聯在一起,她的精神氣質和藝術追求,也逐漸成為了粵曲藝術的重要底色。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國營專業文化團體進一步發展。1954年11月,譚先生加入了廣州曲藝聯誼會,成為該會頗具票房影響的藝人。1958年,廣州曲藝聯誼會第一、第二演出隊與廣東民間樂團合并,組成了專門從事廣東音樂和廣東曲藝表演的專業文藝團體廣東音樂曲藝團。該團擁有劉天一、方漢、梁秋、朱海等一批廣東音樂演奏家,熊飛影、李少芳、源妙生、白燕仔、何麗芳、黃少梅、譚佩儀、李丹紅、勞艷娟等一批曲藝演唱家。
作為廣東音樂曲藝團“唱家班”的臺柱子,譚先生的子喉表演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大量借鑒吸收了眾多名家的腔韻,并精確吸收了一些西洋音樂的發聲方法,逐漸融匯出自己吐字清晰、發聲自然、感情充沛的獨特聲腔藝術風格。粵曲子喉的演唱難度大,對嗓子要求高,講究先天條件,更需掌握科學的發聲方法,由于要用高八度的假音唱出,能夠長期保持不容易,但譚先生很有心得。直到80歲時,她還能唱出音色清亮、韻味濃郁的正宗子喉。
好嗓子要唱好作品,而好作品是不斷打磨出來的。在為粵曲《瀟湘夜雨》作唱腔設計時,她邊做飯邊拿著曲本研究唱腔,嘴里還哼著曲詞,不知不覺中竟夾起一塊煤球放到飯煲里,把一煲白米飯煮得黑糊糊。她與陳笑風對唱的《錦江詩侶》、與白駒榮對唱的《白云松濤》以及獨唱的《蔡文姬歸漢》《姑蘇晚詠》《文成公主》,選段《雷峰塔》《燕子樓》《瀟湘夜雨》等,都是她代表性的作品,在坊間廣泛傳唱,影響深遠。
《錦江詩侶》是譚先生最享盛名、傳唱最廣的曲目。20世紀50年代末,上海一唱片公司來廣州灌錄唱片,希望譚先生和粵劇表演藝術家陳笑風合作一曲。譚先生便邀請陳冠卿譜寫新曲。
陳冠卿的入行與譚先生有著莫大的關系。由于具有扎實的音樂基礎,譚先生對自己演繹的每一首粵曲都有深入的研究,經常根據自己對曲情、人物的理解進行音樂唱腔設計。對于初入行的陳冠卿,譚先生曾以自己的心得給予其創作上的提點。陳冠卿創作的粵曲《寒衣曲》《紅粉飄零》《賣糖歌》,都是因譚先生動情的演繹而流行一時,受到鼓勵的陳冠卿也堅定走上了粵曲撰曲、粵劇編劇的藝術道路。此番受邀創作,陳冠卿仔細琢磨,將自己新編劇目中的一折改寫成了粵曲《錦江詩侶》。

該作主要描寫了不幸淪落風塵的唐代才女薛濤遭西川節度使放逐至邊遠寒苦之地,素仰薛濤才貌的詩人元稹肝腸寸斷,忍悲送別的故事。陳笑風以抑揚委婉、奔放流暢、聲情并茂的【風腔】演繹的元稹,與譚先生以圓潤酣暢、秀麗優雅、婉轉清亮子喉唱腔演繹的薛濤,相得益彰,表現出一雙錦江詩侶互敬互愛但依依惜別的景象。該作灌錄成唱片后,迅速風靡粵港澳,并成為大半個世紀以來曲壇歷唱不衰的經典曲目。談起《錦江詩侶》的成功,譚先生對陳冠卿的才情贊不絕口,稱其曲詞為華彩的“絕配”。
2015年9月1日晚,在廣州中山紀念堂的舞臺上,已90歲的譚先生與92歲的“大哥風”(陳笑風)再度演唱兩人曾在1959年“羊城戲曲花會”上首次合作的《錦江詩侶》,引得滿堂歡呼喝彩。2021年11月29日,陳笑風于廣州逝世,享年98歲,譚先生痛心不已,再無人能與她對唱“情情愛愛,盡化悲哀,傷哉成都,一朝離開,淚飛送別臺”。
譚先生的演唱功力深厚,有豐富的舞臺經驗,對發聲、運氣、行腔等深有研究。作為一位功成名就的曲藝表演藝術家,她除了出色完成自己的舞臺表演,還十分樂意培育新人。從1971年起,譚先生就開始從事藝術輔導教學工作,先后擔任廣州粵劇團和曲藝班的唱腔教師。提及當年接到任教通知的情景,她回憶說,“當時我還在‘干校,有一天,來了兩部車,車上下來的同志對我說,‘譚佩儀同志,現在接你回去,培養黨的事業接班人。”沒有教材也沒有大綱,譚先生從零做起,一點一滴構筑自己的教學方法。在她看來,粵曲的關鍵在“唱”,所以學生首先要有好的嗓音條件,在變聲期時更要注意保護嗓子;其次要有敏銳的聽力,只有敏銳的聽力才能保證音準。此時,廣州市粵劇團與曲藝團有過短暫的合并,而各地劇團因編排樣板戲,需要大量的人才,除了廣州,佛山、增城以及廣西南寧等多地的劇團也選派青年演員長時間集中在廣州粵劇(曲藝)團接受培訓,譚先生的學生中不乏倪惠英、曾慧、關青、梁淑卿、吳偉雄、吳偉明這樣的好苗子。后來,廣州粵劇(曲藝)團被重新分成兩個團,譚先生回歸曲藝團,但倪惠英、曾慧、關青等粵劇團的演員們仍然一如既往地上門請她指導唱功。而曲藝團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招收的一批小演員很快又被交到譚先生手上,其中梁玉嶸、李敏華、潘千芊、廖綺、潘慧貞、王惠蘭、陳芳毅、譚念帖等人成長迅速,成為了中生代演員中的佼佼者。曲藝團的子喉名家黎佩儀曾得益于譚先生的指導,很有進益。4年前,年屆七旬的黎佩儀憑借自己的粵曲子喉表演藝術征服粵港廣大觀眾,進入香港特區的“優才計劃”,移居了香港。
倪惠英、關青、曾慧、廖綺等專業演員是譚先生入室弟子。倪惠英的基礎很扎實,對自己的要求也嚴,對老師的教導有著非同一般的執著。譚先生則在欣慰之余,常常提醒這位她特別喜愛的弟子,“不應該一模一樣地模仿老師,可以向一種流派、一個師父學習,但不要受某一種流派的局限。”倪惠英后來在粵劇舞臺上大放異彩,被譽為“金嗓子”,她與曾慧都獲得了中國戲劇“梅花獎”,成為廣東戲劇界的領軍人物。關青、廖綺的唱功扎實,是戲劇界、曲藝界頗負盛名的藝術家。作為譚先生的關門弟子,廖綺初中畢業就被曲藝團錄取,還是“白紙一張”。但自從在1984級曲藝班上跟譚先生等一眾名家老師初學唱曲后,廖綺就下決心要在曲藝從藝路上追趕那些同期具有良好基礎的大齡同學。她的好學勁頭引起了譚先生的關注。對這些努力上進的學生,譚先生一直都抽時間在家里精心輔導,樂此不疲,有的學生就在她家里住下來,甚至有住了幾年的。譚先生在教學中嚴格要求學生,在生活上她又悉心照顧學生,很多學生都記得譚先生家的湯。倪惠英曾說:“譚老師既是老師,又是長輩,不僅教學生唱戲,而且心胸寬厚、體諒他人,從不講究回報,這些都深深地影響著我們。從舊社會走過來的她,發自內心感恩社會主義新中國,她忠誠黨的文藝事業,一生都在藝術道路上探索追求,具有德藝雙馨藝術大家的風范。”廖綺記得在老師家里上課,譚老師用客廳的鋼琴為她們校正音準,總是認真地做示范,有時到飯點了,譚老師伉儷就會留下大家一起就餐。“陳叔叔人很好,待人和藹,他親自下廚,做出來的飯菜很香。”廖綺告訴我,“在老師這個溫馨而簡樸的家里,我學到了藝術,又學會了做人,從此我就跟當年的譚老師一樣,盡管身處廣州這片改革開放的熱土,曲藝之外的世界誘惑很多,但我仍執著專注地堅守在曲壇,從沒有離開過曲藝事業。”譚先生定居海外的親戚曾想接她去國外安度晚年,她卻總是說,“我舍不得我的學生,培養一個學生需要好幾年,我走了他們怎么辦?”
譚先生的晚年生活非常充實,她每周至少去一次“私伙局”開局唱曲、與徒弟們聚會。記得是在2018年的夏季,一天我帶了一大袋石硤龍眼去拜望譚先生,后被邀去荔灣區參加她徒弟的一個“私伙局”。在康王南路的一個住宅樓里,我與李月玲、張景南等譚先生的弟子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北宋詩人蘇舜欽以《漢書》下酒,我們則以龍眼佐唱。那天,年逾九旬的譚先生雖然沒有唱曲,但是身處眾人中間,興致勃勃,神采飛揚。滿墻紅白盡桃李,一派芬芳報晚晴,她的弟子們都很關心她,身兼數職的倪惠英每隔一段時間都請她喝一次茶,其他徒弟幾乎每周都陪著她打幾圈麻將,讓她動動腦子。我想,這些弟子們都希望譚先生幸福長壽。
晚年的譚先生還常常受邀到各地作藝術輔導,與各地粵曲愛好者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在珠江三角洲城鄉地區,活躍著上千個“私伙局”,人們自娛自樂,成為這個改革開放先行地群眾文化生活的一道獨特風景線。譚先生深受東莞市虎門鎮“私伙局”、妙韻粵樂社負責人倫妙姬的敬重,每年她的壽宴上,譚先生都是座上貴賓。我從2011年在虎門的曲藝活動中認識了倫妙姬后,每年都要參加妙韻粵樂社的周年曲藝活動,“妙姨”就成了我對她的稱呼。妙姨常聯系我充當譚先生的司機,接送她到虎門,最近幾年的盛夏季節,妙姨都委托我為譚先生送上東莞的桂味荔枝,甚至每次與妙姨通電話,最后收線時她都要我向譚先生轉達問候。而每次與譚先生通電話,她首先就是問我最近有沒有到虎門出差,妙姨身體怎么樣。這兩位老人家都把我當成傳聲筒,是希望我這個“年輕人”能多抽出一點時間去關心一下她們所惦念的人。
我是在2011年第一次踏進譚先生位于廣州越秀區大沙頭的家,這間二層、100余平方米的單元房,見證了她數十年的藝術成就。當年我和翟記者為了采訪她,曾坐在這個擺滿紀念獎杯、獎狀、錄音盒帶、唱碟、曲本、譜架、相冊以及掛著名人饋贈書畫的干凈整潔客廳,在這些記載著主人將近一個世紀人生歷程的物件環繞中,與她品茗暢談曲藝。她指著那套音響和鋼琴對我說,誰誰就在這里學唱過曲,還講起她到過的英國利物浦及港澳等地的講學和演出景況,講起那些學生特別是入室弟子們所取得的點滴進步,講到一些歡心悅事的時候,她常常情不自禁地笑出聲來。子喉表演人才的匱乏,以及對曲藝發展的擔憂是她常常提及的一個話題,她說文化藝術部門的領導要多關心曲藝,幫助曲藝,因為現在發展曲藝不容易,優秀人才缺乏,要靠培養。每每憶及這位慈祥長者對粵曲事業那份發自內心深處的摯愛,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2022年疫情緊張,越秀區不時有疫情出現,我在位于越秀的廣東省委黨校兩個月的研修都是全封閉的。譚先生幾次給我打電話,說不能出門,待在家里太悶,約我喝茶,每次通話都是二三十分鐘甚至長達一個小時。我只好安慰她說疫情不會很久,解封了我們就可以聚餐,還可以一起到虎門與妙姨相會。令人難過的是,妙姨在2022年9月病逝,因為考慮到譚先生年事已高,且與妙姨姐妹情深,我一直不敢告訴她這個消息,更不敢主動給她去電話,生怕她再問起妙姨來,直到今年3月譚先生去世。
我卸去了傳聲筒的責任,但耳朵邊空落落的。
對譚佩儀先生的離去,最傷感的除了她摯愛的親友和曾經聆聽過她教誨、得到過她恩澤的徒弟、學生,更有無數喜愛譚先生子喉唱腔藝術的粵曲發燒友。因為譚佩儀先生精心演繹的那些經典曲目,曾經溫潤了幾代廣府人的心靈,而且,還將陪伴人們度過未來許多美好的歲月。
譚佩儀先生,您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
注釋:
① 譚先生原名李素薇,為行文統一,除個別地方,文章中先生的名字均寫作譚佩儀。
(作者:廣東省文聯副秘書長、創作研究部主任,廣東省評協專職副主席)
(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