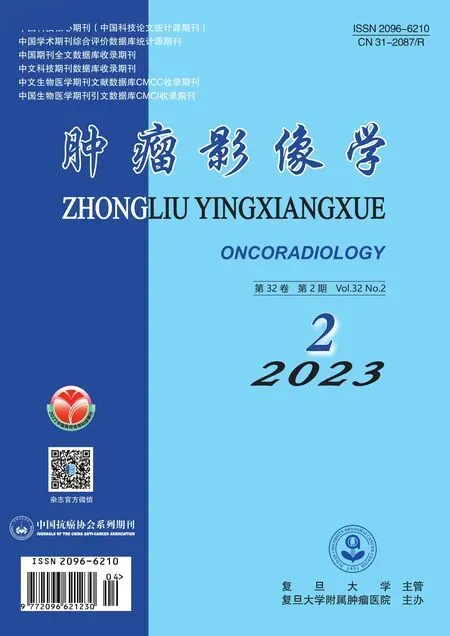超聲引導經皮微波消融治療癥狀性子宮腺肌病患者的療效和安全性
鄧爾雅,李秋燕,朱菁莪,李嘉欣,李小龍,4,張會麗,余松遠
1. 安徽理工大學醫學院,安徽 淮南 232001;
2. 同濟大學附屬第十人民醫院醫學超聲科,上海 200072;
3. 上海超聲診療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上海 200072;
4.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超聲科,上海 200032
子宮腺肌病是一種子宮內膜腺體和間質侵入子宮肌層并呈浸潤性生長,同時伴有周圍平滑肌的肥大和增生的婦科良性病變[1]。子宮腺肌病可引起嚴重痛經、子宮增大繼發盆腔壓迫、月經量大繼發頑固性貧血,并引起生育能力下降甚至不孕不育,嚴重影響婦女生活質量與生殖健康[2]。目前,其發病機制主要包括異位子宮內膜的侵襲和組織損傷的修復,胚胎多能干細胞的增殖和分化,以及炎癥因子和神經源性介質的相互作用等[3]。據研究[4-5]報道,子宮腺肌病常見于30~50歲的女性,發病率為10.00%~65.00%。但近30年來,隨著國內生育觀念的改變及工作壓力的增加,子宮腺肌病的發病率逐漸上升。
傳統針對子宮腺肌病的一線治療方式為長期藥物維持治療,其次為子宮切除術[3]。藥物治療期間出現的長期點滴出血、體重增加等不良反應會導致相當一部分患者因不能耐受而中斷治療。子宮切除術則直接導致部分育齡期女性失去生育能力。目前,保留子宮的非侵入性或微創性醫療干預措施正在逐漸取代傳統療法[6]。保留子宮的手術包括腺肌瘤切除術、病灶減少術、子宮內膜消融或切除術、子宮動脈栓塞術(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UAE)及熱消融等[7]。盡管無法完全切除病灶是所有保守性治療必須考慮的因素,但其對月經和痛經癥狀的顯著改善效果已得到相關回顧性研究[8-9]的支持。其中,熱消融因其微創性、操作靈活性、治療后并發癥少、臨床癥狀緩解率高等特點,在臨床應用中逐漸受重視并被接受[10-12]。
目前,微波消融(microwave ablation,MWA)治療子宮腺肌病的臨床研究有限,缺乏具有可重復性和可靠性的臨床研究[13-15]。本研究旨在全面研究超聲引導經皮MWA治療有癥狀的子宮腺肌病的可行性、安全性,以及短期臨床療效。
1 資料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2020年7月—2021年6月于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就診的38例子宮腺肌病患者,患者中位年齡為38歲。納入標準:① 患者拒絕接受子宮切除術或其他非侵入性治療方法;② 經超聲和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檢查證實的子宮腺肌病患者;③ 患者有臨床癥狀且生活質量受到很大影響;④ 痛經視覺模擬評分(visual analog scale,VAS)>4或非經期血紅蛋白(hemoglobin,Hb)水平<110 g/L。排除標準:① 有嚴重盆腔炎癥的患者(n=1);② 沒有完整的臨床和影像學資料(n=3)。最終,本研究納入34例絕經前的癥狀性子宮腺肌病患者。
1.2 設備
采用南京長城醫療設備有限公司的MTI-5A腫瘤微波治療儀,微波輸出頻率為(2 450±50)MHz;微波熱凝消融針(XR-A2018W)的直徑為2 mm,長度為18 cm,駐波比不大于3.0,匹配阻抗50 Ω。采用單極水冷MWA系統,通過內部液體循環,以減少電極周圍的組織碳化,從而提高凝固性壞死的效率。
采用美國GE公司的Logiq E9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使用頻率為1~5 MHz的凸陣探頭進行檢查、監測超聲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和超聲引導下的MWA。
1.3 術前評估
在了解病史和患者訴求后,術前對血常規、尿常規、凝血功能、肝功能、腎功能、電解質、血清腫瘤標志物、性激素、心電圖、超聲等進行評估,排除治療禁忌證。在MRI和超聲等影像學檢查的幫助下,詳細了解病變位置與周圍毗鄰組織的關系,確定最佳穿刺路徑。
1.4 治療方案
除9例患者強烈要求行全身麻醉外,其余25例(73.53%)患者進行靜脈鎮靜鎮痛。所有局部麻醉參與者,都通過左上肢周圍靜脈給予1.00 mg咪達唑侖和0.05 mg芬太尼的起始劑量,此外額外單次補充0.012 5 mg芬太尼緩慢泵入靜脈以緩解術中疼痛。
經常規消毒、鋪巾后,以2%利多卡因進行局部浸潤麻醉。在超聲引導下用18 G自動活檢針經腹腔行穿刺活檢,將單極MWA天線沿活檢路徑插入目標病變中完成消融。為避免穿刺操作造成的腸道穿孔,在插入單極MWA天線之前,必須用超聲探頭將腸道從腹壁上推開。其中,6例局部麻醉患者因無安全穿刺路徑,需額外通過腹腔內注入500~1 000 mL的生理鹽水將腸道與子宮分開至少0.5 cm。
微波發射功率設定為50~60 W。在消融過程中,采用“移動消融”技術來處理目標病灶[13]。首先對病變底部進行消融,然后將天線逐步拔出,直到病變的邊緣部分。一般來說,在進行單點消融后,天線被拔出2 cm進行下一次消融,直到穿刺路徑被汽化反應引起的云霧狀高回聲所覆蓋。之后,將天線從另一個方向再次引入病灶。重復上述程序,直到整個病變邊緣被汽化高回聲云覆蓋。對于個別有生育要求的患者,另外設定的終點是消融邊界離子宮內膜至少1 cm[16-17]。
術后采用CEUS評估消融是否完全(圖1),造影劑使用意大利Bracco公司生產的聲諾維(SonoVue)。CEUS上的無灌注區被確定為消融后的組織壞死區。如果擬定的消融目標仍有造影劑存在,則有必要在CEUS引導下直接進行額外的消融。

圖1 典型病例1(患者,女性,35歲,子宮腺肌病史36個月)常規超聲和CEUS圖像
1.5 臨床療效判定及隨訪指標
34例患者被建議在MWA后1、3、6 和12個月進行療效評估。評估內容包括子宮體積縮小率(volume reduction rate,VRR)、病灶VRR、痛經程度、經期血量、Hb水平、癥狀嚴重程度評分(symptom severity score,SSS)和健康生活質量評分(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score,HRQL)。在每次隨訪中,通過超聲檢查評估子宮和治療后的腺肌癥的體積。MRI復查被安排在術后2 d和術后1年(圖2)。

圖2 典型病例2(患者,38歲,子宮腺肌病)在MWA前后的MRI圖像
采用橢球模擬體積公式評估靶病灶和子宮體積:V=π/6×高×長×寬。VAS和月經失血圖(pictorial blood loss assessment chart,PBAC)評分分別用于評估痛經程度和月經血量。前者的評分范圍為0~10,其疼痛程度隨著評分的增加而依次增加[18]。后者評分大于100時,認為是月經量過多[19-20]。此外,SSS和HRQL分數從0~100不等。對于SSS來說,分數越高表示臨床癥狀越嚴重,而HRQL分數越高則傾向于表示不理想的生活質量[21]。
1.6 并發癥評價
輕度并發癥界定標準:發熱、腹痛、惡心、嘔吐、陰道流液、陰道出血等;嚴重并發癥界定標準:子宮穿孔、腸道損傷或梗阻、膀胱穿孔、腹腔內大出血、彌漫性腹膜炎等。
1.7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6.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使用Shapiro-Wilk檢驗來評估正態性。連續變量(即子宮體積、病灶體積、VAS、PBAC評分、SSS、HRQL和Hb水平)呈偏態分布,以M(P25,P75)表示,并使用Wilcoxon符號秩和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一般資料
34例有癥狀的子宮腺肌病患者接受了經腹部超聲引導的MWA評估。中位隨訪時間為12.00(10.50,12.00)個月。在隨訪期間,術后1、3、6、12個月于醫院復查的患者分別為34例(100.00%),34例(100.00%),33例(97.06%)和27例(79.41%)。為了保護子宮內膜,對8例(23.53%)有生育要求的患者采用謹慎的保守消融策略。
2.2 術后子宮和病灶體積變化
MWA后12個月,中位子宮體積從基線體積148.45(92.08,215.62)mL減少至87.62(55.90,132.97)mL(P<0.001),中位病灶體積從61.08(31.28,93.38)mL直接減少至13.33(7.95,43.20)mL(P<0.001)。與基線水平相比,中位子宮VRR為37.91%。與術前測量值相比,子宮腺肌病病灶體積呈現下降趨勢,在1、3、6和12個月的隨訪中中位病灶VRR分別達到44.40%、65.07%、69.67%和72.81%(表1)。

表1 術后子宮和病灶體積變化M(P25,P75)
2.3 Hb水平及各類臨床相關評分
在12個月的隨訪中,31例痛經患者VAS從治療前的8.00(7.00,9.25)明顯下降到治療后的0.00(0.00,3.25)(P<0.001)。在月經血量方面,27例月經血量過多的患者中位PBAC評分降至正常范圍內(即PBAC評分<100),盡管11例(40.74%)患者報告通過PBAC評估,月經血量仍高于正常值。Hb水平從117.00(112.25,138.25)g/L增加到130.00(118.75,135.50)g/L(P=0.001)。同時,在每次隨訪中,SSS和HRQL也顯示出統計學上的明顯改善。SSS從基線水平28.18(21.88,35.16)降至12.50(6.25,19.53)(P<0.001),HRQL在術后最后一次隨訪時從57.33(43.10,65.30)上升至77.16(62.50,89.22)(P<0.001,表2)。

表2 治療前后Hb水平和各類臨床相關評分結果M(P25,P75)
Hb水平、VAS、SSS、HRQL和PBAC評分在術后隨訪過程中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臨床結果在治療后6個月最佳,其中一些評價指標,如VAS、SSS、HRQL和PBAC評分顯示改善優勢直接持續到術后12個月。
2.4 并發癥
無重大并發癥發生,且所有的微小并發癥均為自限性。最常見的輕微并發癥為陰道流液,52.94%(18/34)的患者出現陰道流液現象,在治療后40 d內完全消失。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數患者可以在MWA后3 d內恢復工作(表3)。

表3 并發癥
3 討 論
本研究通過比較MWA治療前后的實驗室檢驗、影像學檢查、各類評分和臨床結果,發現超聲引導下MWA可縮小子宮和病灶的體積,有效地緩解女性子宮腺肌病患者的臨床癥狀,并且無嚴重并發癥,表明有癥狀的子宮腺肌病患者可以從超聲引導下MWA中獲益。
本研究結果顯示,子宮中位VRR和病灶中位VRR在術后1年隨訪期間分別為37.91%和72.81%。在術后3、6和12個月的隨訪中,病灶中位VRR至少為50.00%。根據國內專家建議[22],MWA被認為治療效果顯著。本研究結果與Hai等[23]報道的接受射頻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治療的患者(子宮VRR和病灶VRR分別為41.20%和54.70%)和Guo等[24]報道的接受高強度聚焦超聲(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HIFU)治療的患者(子宮VRR和病灶VRR分別為30.42%和43.96%)相比,子宮的改善情況在消融治療后1年相似,且在病灶VRR方面甚至獲得了更好的結果。這可能是由于術中超聲動態監測、“移動消融”技術和術后即時CEUS評估的完美協調。
另外,治療有癥狀的子宮腺肌病最重要的目標是緩解臨床癥狀,從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本研究中評估痛經程度和月經血量的VAS和PBAC明顯下降,并在術后保持在較低水平。而在Scarperi等[25]的研究中,經12個月隨訪,VAS從9.1下降至2.6。手術前后VAS與本研究一致明顯下降。同時,本研究患者在MWA治療后,通過PBAC評分評估的月經血量有所改善,也與Huang等[26]的結果一致。與此同時,Hb水平在隨訪期間也有所增加。SSS和HRQL是評估子宮腺肌病臨床癥狀和生活質量的工具。HRQL和SSS的變化在本研究中表現出明顯的改善,但是與Ma等[27]報告的UAE研究(SSS從56.00下降到13.00,HRQL從39.00上升為94.00)和Liang等[28]報告的UAE研究(SSS從57.00下降到17.00,HRQL從45.00上升為90.00)相比,UAE在改善癥狀和生活質量方面比本研究結果更勝一籌。然而,在De Bruijn等[29]發表的關于UAE的meta分析中,6項研究顯示術后子宮結合帶減少率為13.70%~38.00%,在12項研究中,413例患者中共有361例(87.41%)報告持續腹痛長達2周,13項研究中共有445例患者中28例(6.29%)報告持續閉經。
無論采用何種保守治療方式,臨床癥狀未完全改善的情況都可能存在,與其病因、發病機制、生理結構等因素密切相關。在本研究中,40.74%(11/27)的痛經患者通過PBAC評估顯示月經量沒有減少至正常水平。其中有8例患者由于有生育意愿而盡量避免或減少對子宮內膜的熱損傷。眾所周知,月經血量與子宮內膜厚度息息相關。事實上,對于希望保留生育能力的患者進行介入治療一直存在爭議。但Nam[30]和周春艷等[31]的研究結果顯示,熱消融有望成為確保良好臨床結果的有效方式。Nam[30]的研究顯示58例接受RFA治療后積極嘗試受孕的患者中,29例(50.00%)成功妊娠,并且無子宮破裂發生。周春艷等[31]認為HIFU消融也可能有助于改善子宮腺肌病患者的妊娠結局。
可能出現的并發癥是患者抗拒消融方案的重要原因。在Chen等[32]的研究中,有2例患者在HIFU治療后20 d內出現了腸穿孔,另1例患者在HIFU治療1年半后被發現有側腹綜合征。幸運的是,在本研究中沒有出現需要進一步干預或其他重大的并發癥,并且所有的微小并發癥都具有自限性。超聲監測下經皮引入人工腹水可有效地提供安全的穿刺路徑,并避免子宮相鄰結構熱損傷。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這是一項樣本量相對較小的回顧性研究,需要進一步設計前瞻性、多中心、更大樣本量和更長隨訪時間的研究。其次,隨訪時間太短,無法總結要求保留生育能力的患者的最終妊娠結局。第三,超聲引導MWA技術沒有與HIFU、RFA或切除手術直接比較。
總之,根據本研究結果,MWA是治療癥狀性子宮腺肌病的一種可行的選擇。接受超聲引導MWA治療的子宮腺肌病患者在子宮體積和腺肌癥體積減少的同時,能明顯改善患者的痛經和月經過多等癥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