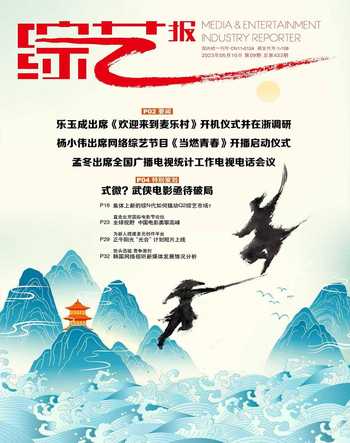以地域影像探索共同體敘事新范式
顧亞奇
一方面,一地一景、五彩繽紛的地理人文,為影像創作提供了無限可能;另一方面,影像奇觀內蘊的思想觀念、價值譜系,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
中國之為中國,山川風物、民族風俗、歷史遺跡、人物軼事,歷經歲月洗禮沉淀為底蘊深厚的地域文化標識。熠熠生輝的地域文化,既世代沿襲又與時俱進,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風貌。近期,《南陽史話》《津門往事》《大運河》《大泰山》等紀實作品接續播出,展現了地域文化的深刻內涵和獨特魅力,以影像敘事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讓中華文明之光穿越時空照耀當下。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的這句名言,朱光潛曾如此闡釋:“沒有一個過去史真正是歷史,如果它不引起現實的思索,打動現實的興趣,和現實的心靈生活打成一片……著重歷史的現時性,其實就是著重歷史與生活的聯貫。”不管多么年深月久,當歷史再次被表達時,實際上是又一次與當下對話。筆者參與策劃并擔任總撰稿的四集紀錄片《南陽史話》,選取張仲景心懷蒼生、范仲淹憂樂天下、諸葛亮鞠躬盡瘁等名人故事,意在以史為鏡,以古圣先賢為范,啟發今天的黨員干部如何踐行“忠誠、干凈、擔當”。《津門往事》以一個城市的歷史折射百年中國,讓冰冷的歷史文物有了生命的溫度。從鴉片戰爭、洋務運動到抗日救亡、天津解放,作品以大量歷史細節和鮮為人知的故事連接歷史與當下,打開近代中國風雨兼程、謀求民族復興的歷史長卷,觀眾的“歷史自覺”與“道路自信”油然而生。對于當下的紀錄片工作者而言,歷史題材創作絕非機械地再現歷史原貌,簡單地復刻歷史現場,而是要立足當下,重新審視、解讀并表達歷史。
人民的英雄,英雄的人民。歷史由“人”構成,也由“人”書寫,被書寫的既有“英雄”,也有“人民”。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都有不同歷史時期影響國家發展的“先鋒”人物。《津門往事》中出現105位歷史人物,包括嚴復、梁啟超、周恩來等。導演祖光特別強調,在茫茫歷史中去發現、挖掘具有當下性的價值、意義,才能打通歷史與現實融通的壁障,“英雄敘事”回歸人性化、個性化才有生命力。《津門往事》所有的歷史敘述,都從現實故事和人物出發推動敘事,歷史人物因為細節得以具象化、立體化。對于“歷史”的理解,法國年鑒學派提供了另一條途徑,即歷史不只是政治史,而是社會的歷史,是包羅人類活動各個領域的“全面的歷史”。人民,既是歷史的劇中人,又是劇作者,所有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人均是紀錄片當仁不讓的主角。無論是《這里是香港》《巴扎》《阿爾泰山》中對生長于斯、情系于斯的普通人故事的抒寫,還是《大運河》這類具有歷史縱深感的紀錄片中“人”的登場、京杭運河與沿線人民的關聯,皆見證了人民的生產實踐和生命歷程,成就了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
地域的,更是中國的。幅員遼闊的中國,地區之間文化形態存在差異,造就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如漢文化、關隴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松遼文化、吳越文化、荊楚文化、嶺南文化等。在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看來,地域文化和中華傳統文化是“多元一體”的關系,“多元”指眾多民族、地方和民間文化小傳統,涉及特定地域的歷史遺跡、生產生活方式、民風俚俗、文藝形態等,“一體”則是指“大家認同的歷史文化大傳統”,簡言之,“一體”即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一方面,一地一景、五彩繽紛的地理人文,為影像創作提供了無限可能,“大片”視聽體驗令觀眾美不勝收、嘆為觀止;另一方面,影像奇觀內蘊的思想觀念、價值譜系,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西泠印社》緩緩道出因金石篆刻聞名的“天下第一名社”的君子之風;《大河之北》描摹濃縮的“國家地理讀本”,將35億年的滄海桑田化為傳奇;《大泰山》則再一次提示人們,在恢宏磅礴的景、物、人、事之下,泰山早已化為“國泰民安”的文化標識與精神圖騰,引領觀眾一起進行文化身份的集體指認。
大國之大,有賴于地域文化的百花齊放。爭奇斗艷、競放異彩的地域文化,像一把把鑰匙漸次破解中華民族的文化密碼。地域紀實影像以高質量視聽語言彰顯歷史、地理、人文特色,展現傳統文化的深度與地域文化的廣度,煥發中華文化的時代光芒,不斷探索“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的影像美學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