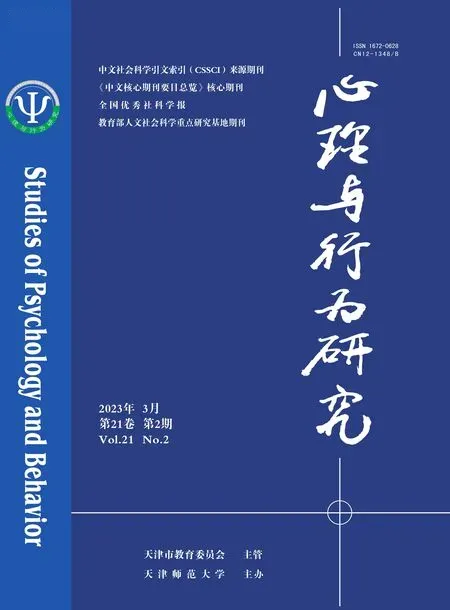注視喜歡效應中的采擇機制 *
周 菘 冷 漫 蔣 濤 孫藝涵 管慶麗 李士一
(1 福建師范大學心理學院,福州 350117) (2 外交學院區域與國別比較外交研究中心,北京 100037) (3 天津師范大學國際教育交流學院,天津 300387) (4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天津師范大學心理與行為研究院,天津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學生心理發展與學習天津市高校社會科學實驗室,天津 300387)
1 引言
眼睛注視作為社會互動的一種有力工具,具有興趣指示和情感表達的含義(Dalmaso et al., 2020;Emery, 2000),人們依靠他人眼睛所傳達的注意力方向及社會信息來指導和解釋社會行為(Frischen et al., 2007)。感知他人注視能夠幫助人們推測他人的心理狀態(Baron-Cohen, 1995)。與未被他人注視的物體相比,人們對出現在注視線索位置的物體反應更快(McKay et al., 2021)。除此之外,注視線索還會影響人們的情感評價,使得人們更喜歡被他人注視的物體(Bayliss et al., 2006; Grynszpan et al.,2017),這被稱為注視喜歡效應(gaze liking effect)。
目前,關于注視喜歡效應產生機制的研究仍存在爭議,主要集中于以下兩種可能的解釋(Capozzi & Ristic, 2020; Driver et al., 1999)。一種觀點認為,對注視線索的加工是一種領域一般性的注意過程。注視喜歡效應可能是由于他人對物體的注視引起了注意轉移,增加了觀察者的注視持續時間,從而提高了對物體的喜好程度(Shimojo et al., 2003)。研究人員發現,無論是閾上的箭頭還是注視線索都會引起注視提示效應,并觀察到微弱的注視喜歡效應,二者不存在顯著差異(Mitsuda et al., 2019)。同時,當用注視或箭頭的口頭描述來代替注視時,喜歡效應仍能產生(Tipples et al., 2019)。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注視線索作為一種社會性信息,與對意圖和心理狀態的歸因有關(Colombatto et al., 2020),注視喜歡效應的產生機制與視覺觀點采擇密切關聯。例如,許多研究證明,面孔的屬性和數量以及注視轉移在注視喜歡效應中起到調節作用(Capozzi et al., 2015; van der Weiden et al., 2010)。這表明高水平的社會認知能力可能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于祎雯 等,2020),注視喜歡效應的作用機制或許與心理理論相關(Corneille et al., 2009)。此外,注視線索具有其特殊性。研究發現,使用箭頭或手指等社會線索將引起強烈的注意提示效應,但并不能引起喜歡效應(Manssuer et al., 2016)。然而,僅是閾下的眼睛注視也能引起對物體的偏好(Mitsuda & Masaki,2018)。Manera等人(2014)通過引入遮擋物,操縱了物體對于虛擬人的可見性,發現雖然虛擬人的注視方向仍指向物體,但對于物體的喜愛僅在虛擬人的注視和物體同時呈現時才增加。這表明,注視喜歡效應是處理他人注視與目標物體間有意關系的結果,依賴于人們的視覺觀點采擇能力。
有關注視線索在喜歡效應中的具體發生機制,學界目前對此尚未得出一致結論。一種常見的思路是探討當被試意識到虛擬人無法看見物體時,是否還會出現喜歡效應,即考察視覺觀點采擇是否是產生注視喜歡效應的前提條件。以往基于此設計的實驗范式存在一定的不足。Manera等人(2014)的研究利用滑塊遮蔽人臉和呈現物體,通過改變物體呈現方式和滑塊移動速度來操縱虛擬人能否看見物體,結果發現喜歡效應僅在被試意識到虛擬人能看見物體時才產生。但這一操縱并不直觀,不同時呈現人臉與物體可能會削弱被試對虛擬人的視覺觀點采擇。因此,本研究借鑒了視覺觀點采擇的點觀點采擇任務范式(dots perspective task)(Samson et al., 2010),在同一場景中呈現虛擬人與目標物體,在二者之間設置障礙物以操縱物體對虛擬人的可見性,進而探討視覺觀點采擇在喜歡效應產生中的作用。
在本實驗中,被試需要觀察一張展示房間內部三面墻的圖片,圖中一個位于房間中央的虛擬人面朝左邊或右邊的墻壁,兩側的墻壁呈現有不同的字母,被試需要回答自己對字母的喜好程度。本研究設計的一個巧妙之處在于,圖片中所有字母對于被試而言都是可見的,但由于遮擋物以及字母的位置改變,使得部分字母對于虛擬人而言是不可見的。因此,若發現被試對虛擬人可見字母的喜好程度與其他不可見字母之間存在差異,則可以推測是否與被試對虛擬人進行了視覺觀點采擇有關。此外,虛擬人的眼睛注視方向、頭部朝向以及身體朝向在實驗中始終保持一致,以此來提示虛擬人的注意力方向。這樣設計的好處在于,第一,經典的點觀點采擇范式為探究人們的視覺空間觀點采擇的作用,虛擬人被呈現為站在房間中央(Samson et al., 2010),為了保留該范式的設計,使場景更具生動性,本研究放棄了以往研究中僅呈現眼睛注視的方式。第二,感知他人的注意力方向通常需要整合多種社會線索,除眼睛注視之外,頭部方向和軀體朝向的信息也會對引導注意力方向作出重大貢獻(Cooney et al.,2015; Emery, 2000; Moors et al., 2016; Vestner et al.,2022)。由于本實驗中虛擬人的眼睛、頭部及軀體的方向是對齊的,因此被試獲得的任何方向性信息都是一致的(Moors et al., 2015)。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通過三個實驗遞進地探討視覺觀點采擇在注視喜歡效應產生中的作用。本研究預期,被試會對虛擬人進行視覺觀點采擇,從而僅僅對虛擬人可見的字母產生更高程度的喜愛,這將為喜歡效應機制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實證支持。
2 實驗1:視覺觀點采擇對喜歡效應的影響
實驗1對以往的注視喜歡效應的研究進行了復制(Bayliss et al., 2006),要求被試對虛擬人注視或遠離的字母進行喜好程度的評價。這種復制存在兩點必要性,第一,本實驗采用了與以往不同的實驗任務,對經典的點觀點采擇實驗范式進行改編,用于探究觀點采擇在注視喜歡效應中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再次驗證喜歡效應是否仍能產生。第二,即使已有許多研究發現了注視喜歡效應,但近年的一項研究使用了更大的樣本量復制了以往的研究卻發現了較小的效應(Tipples &Pecchinenda, 2019)。對于這些不一致的結果,本實驗期望能提供更多的實驗數據。
2.1 被試
本研究的實驗均為在線實驗,通過騰訊問卷平臺在線進行(實驗2和3與此相同),在微信平臺上共招募了287名被試,完成問卷所需時間在三個標準差之上(相當于超過4分鐘)的被試被剔除。篩選后,實驗1中有效被試為268人,其中女性占66.79%,平均年齡為32.76歲(SD=12.33歲)。采用G*Power 3.1.9.7(Faul et al., 2009)對本研究進行事后統計檢驗力分析(post hoc analysis),當前樣本(n=268, effect sizedz=0.38, α=0.05)計算出的統計檢驗力大于0.99,這表明本研究的樣本量是足夠的。
2.2 實驗設計
實驗采用單因素(字母可見性:虛擬人可見、虛擬人不可見)被試內實驗設計,因變量為被試對字母喜好程度的評分。
2.3 實驗程序
首先收集被試的基本信息,然后給被試呈現一張圖片,圖片中一位虛擬人站在房間中央,面朝左或右。房間的左邊和右邊的墻上分別顯示字母“p”和“q”,字母大小為56×97像素,圖片大小為640×480像素。具體如圖1A所示。其中,虛擬人的站立方向以及字母“p”和“q”的位置在被試間保持平衡。每名被試僅觀察一張圖片,之后回答兩個問題,分別是你對圖片中“p”和“q”的喜愛程度,范圍是0~100。數字越大,表示喜好程度越高。本研究采用One-Shot實驗范式,即每名被試在每個條件下僅需完成一個試次的實驗(實驗2和3與此相同)。被試完成實驗后,可隨機獲得0.2~1元的報酬。

圖1 實驗1材料與結果
2.4 結果
根據虛擬人站立方向和字母的位置,可將字母分為虛擬人可以看到的字母和虛擬人看不到的字母。本研究以字母可見性為自變量,采用配對樣本t檢驗對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被試對于虛擬人可見字母(M=63.92,SE=1.51)和不可見字母(M=58.14,SE=1.68)的偏好程度存在顯著差異,t(267)=3.12,p=0.002,Cohen’sd=0.38。被試對虛擬人可見字母的喜好程度顯著高于不可見字母(見圖1B)。
2.5 討論
實驗1結果表明,被試對虛擬人面前的可見字母產生了偏好,而對身后的字母沒有發現這種效應,證明了視覺喜歡效應的產生,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Bayliss et al., 2006)。本研究推測被試由于受到虛擬人注視的引導,而對它進行了觀點采擇,從而產生了對它注視的字母的喜歡效應(李丹惠 等, 2022),視覺觀點采擇在喜歡效應的產生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然而,實驗1不能排除注視帶來的注意定向效果的作用。注視喜歡效應可能只是因為被試更多地關注了虛擬人的注視方向,從而帶來了更強的注意引導,導致對虛擬人注視方向的字母產生了興趣(Callejas et al., 2014;Tipples, 2002)。為排除這種干擾,本研究進行了實驗2。
3 實驗2:注視引導對喜歡效應的影響
實驗2的目的是進一步排除注意力引導在注視喜歡效應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本研究在虛擬人視線前方增添了一個字母,虛擬人視線前方共有兩個字母,其中一個由于遮擋物的設置而對虛擬人不可見。如果喜歡效應是由于注視線索的引導作用而導致的加工流暢性產生的(Bayliss et al.,2006),被試對于虛擬人前方的兩個字母的喜好程度應該相同;而如果被試對前方虛擬人可見字母的喜好高于不可見字母,則可能是由于被試對虛擬人的視覺信息進行了加工從而影響了被試對不同位置字母的評價。
3.1 被試
實驗2招募與篩選被試的方式同實驗1。最終招募了296名被試,剔除無效及錯誤回答的被試數據后,其中273人是有效被試,女性占76.56%,平均年齡為28.02歲(SD=10.67歲)。采用G*Power 3.1.9.7(Faul et al., 2009)進行事后統計檢驗力分析,當前樣本(n=273, effect sizef=0.16, α=0.05)計算出的統計檢驗力大于0.99,表明本研究的樣本量是足夠的。
3.2 實驗設計
實驗采用單因素(字母位置:虛擬人前方可見、虛擬人前方不可見、虛擬人身后)被試內實驗設計,因變量為被試對不同位置字母的喜好程度評分。
3.3 實驗程序
實驗2與實驗1設計基本相同,但存在兩點不同之處。第一,增加了一個字母“d”,并設置了一個不透明的遮擋物,三個字母分別位于虛擬人和遮擋物之間(虛擬人前方可見)、遮擋物之后(虛擬人前方不可見)、虛擬人身后。如圖2A所示。第二,為確保被試對可見字母的喜歡確實是由于采擇了虛擬人的觀點而產生的,增添了三個關于視覺觀點采擇的問題,分別為虛擬人是否可以看到p/q/d。為避免特定字母及方向的影響,三個字母的位置及虛擬人站立方向在被試間保持平衡。

圖2 實驗2材料與結果
3.4 結果
剔除無效作答(17個)、錯誤回答4個觀點采擇問題(6個)的23個被試數據,對273個有效數據進行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發現,三種字母之間的喜好程度差異顯著(M前方不可見±SE前方不可見=55.38±1.56,M前方可見±SE前方可見=62.20±1.59,M身后±SE身后=56.97±1.54),F(2, 544)=7.30,p<0.001,=0.03。經FDR校正后發現,被試對虛擬人前方可見字母的喜歡程度顯著高于看不見的字母,包括虛擬人身后字母[t(272)=5.24, Cohen’sd=0.64,p=0.007]和虛擬人前方不可見字母[t(272)=6.83,Cohen’sd=0.83,p=0.002]。對虛擬人前方不可見與虛擬人身后字母的喜歡程度差異不顯著,t(272)=1.59,Cohen’sd=0.19,p=0.370(見圖2B)。
3.5 討論
正如預期的那樣,實驗2再次發現了注視喜歡效應。首先,被試對可見字母的喜歡程度顯著高于虛擬人身后的字母,這與實驗1結果是相同的。其次,即使是對位于虛擬人前方的注視方向的字母,被試對可見字母的喜歡程度也顯著高于虛擬人看不見的字母。這一結果表明,喜歡效應并不僅是由于虛擬人的注意引導而產生的(Ulloa et al., 2015)。虛擬人的注視引導使得被試對虛擬人面前的兩個字母都可能產生喜歡效應,但結果發現,被試對前方可見字母的喜好顯著高于不可見的字母。這是由于遮擋物的存在使得虛擬人無法看見遮擋物之后的字母,被試對虛擬人的視覺信息進行了采擇,從而忽略了不可見的字母,而僅對可見字母產生了喜歡效應。這與Manera等人(2014)的研究結果是相同的。實驗2進一步驗證了只有在虛擬人視角可見的物體才能引起更高的喜好程度。
然而,實驗2發現的對于虛擬人前方可見字母更高程度的喜歡,可能存在著其離虛擬人更近,而導致被試更偏愛的影響作用。為進一步排除這種因素造成的混雜影響,本研究進行了實驗3。
4 實驗3:空間距離對喜歡效應的影響
實驗2發現的對于虛擬人前方可見字母的偏好可能是由于目標距虛擬人更近,而使得被試對近空間物體的評價更高(Hadjidimitrakis et al.,2011)。因此在實驗3中,通過控制遮擋物和字母的位置,使靠近虛擬人的字母對于虛擬人而言不可見,而距離較遠的字母對于虛擬人而言可見。若被試仍對可見但距離較遠的字母產生了喜歡效應,則進一步為實驗1和實驗2的推測提供支持。
4.1 被試
實驗3招募被試的方式同實驗1,最終招募了302名被試,剔除無效及錯誤回答的被試數據后,有效被試為270名。其中女性占64.44%,平均年齡為29.78歲(SD=11.45歲)。采用G*Power 3.1.9.7(Faul et al., 2009)進行事后統計檢驗力分析,當前樣本(n=270, effect sizedz=0.46, α=0.05)計算出的統計檢驗力大于0.99,表明本研究的樣本量是足夠的。
4.2 實驗設計
實驗采用單因素(字母可見性:虛擬人前方可見、虛擬人前方不可見)被試內實驗設計,因變量為被試對字母喜好程度的評分。
4.3 實驗程序
實驗3相較于實驗2存在兩處改動。第一,改變了虛擬人身前兩個字母的位置,距離虛擬人更近的字母位于遮擋板之后,虛擬人看不見;而另一字母距離虛擬人較遠但未被遮擋住,對于虛擬人而言可見,并刪除了虛擬人身后的字母。如圖3A所示。第二,為進一步保證在詢問喜好程度之前被試能準確感知前方字母的位置遠近關系,將有關視覺觀點采擇的問題修改為以下4個:“虛擬人是否可以看到p?虛擬人是否可以看到q?虛擬人面前的字母是什么?更遠的字母是什么?”虛擬人站立方向和字母位置在被試間保持平衡。

圖3 實驗3材料與結果
4.4 結果
剔除無效作答(13個)、錯誤回答4個觀點采擇問題(19個)的32個被試數據,對270個有效數據進行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發現,兩種字母的喜好程度間存在顯著差異,被試對可見字母(M=57.09,SE=1.54)的喜好程度顯著高于不可見字母(M=49.51,SE=1.50),t(269)=3.77,p<0.001,Cohen’sd=0.46(見圖3B)。
4.5 討論
本實驗的結果仍發現被試對虛擬人可見字母的喜好程度高于不可見字母。對于被試面前的字母,即使該字母位于視野中央且距離虛擬人更近,被試對它的喜好仍顯著低于距離被試更遠但虛擬人可見的字母。這表明實驗2發現的被試對于面前可見字母的喜好的確是由于被試對虛擬人的視覺信息進行了采擇而產生的(Bayliss et al., 2007;Corneille et al., 2009),而不是由于該字母距離虛擬人更近的關系。由于遮擋物的存在僅影響了虛擬人對于面前不可見字母的知覺,而不影響被試對于字母的認知,因而可以推測被試正是由于對虛擬人進行了視覺觀點采擇,而導致了對距離更近的字母的喜愛程度降低,而對距離較遠的可見字母喜愛程度更高(Shimojo et al., 2003)。
5 總討論
本研究采用了在線實驗范式,使用改編的點觀點采擇任務進行了三個實驗。通過控制注視線索及字母的位置,實驗1復制了注視喜歡效應,發現被試對虛擬人可見字母的喜愛程度高于不可見字母,表明對他人視覺信息的采擇可能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實驗2和實驗3通過設置遮擋物,排除了由于虛擬人的注視引導或是字母的位置效應而對結果產生的影響,表明只有在虛擬人方向可見的字母才能引發被試的喜歡效應,進一步證明了視覺觀點采擇在喜歡效應產生中的作用。
視覺觀點采擇(visual perspective taking)作為個體認知發展的重要根基,是指個體能從他人眼中看世界,以獲得關于他人視覺信息的過程(楊繼平等, 2014)。目前的研究發現,當觀察到一個人看向某物時,人們會自動注意到空間中的同一位置,并對其產生興趣和偏好,他人的注視線索會影響到人們對物體的認知和態度(Bayliss et al., 2006;Emery, 2000)。關于這種喜歡效應的產生機制,視覺觀點采擇理論或許可以解釋。人們常常靠近有價值的物體而遠離危險的物體,通過視覺觀點采擇人們獲得了他人對于物品的態度信息,這種信息能夠幫助人們評判物體的價值。因此,人們會對他人注視的物品評價更高(李丹惠 等, 2022)。本研究發現的注視喜歡效應支持了這一解釋,被試僅對虛擬人能看見的字母更喜愛,而對虛擬人身后看不見的字母未發現喜歡效應,即使這兩種字母對于被試而言都是可見的。在虛擬人身前設置了遮擋物后,本研究仍舊發現被試僅對虛擬人身前未被遮擋的字母產生了喜歡效應,三個實驗的結果遞進地證明了被試正是由于對虛擬人的視覺觀點信息進行了采擇,從而僅對虛擬人正在注視的字母有更積極的評價。
本研究支持注視線索作為特定領域的社會性信息,注視喜歡效應的作用機制與視覺觀點采擇緊密相關的觀點(Corneille et al., 2009)。以往研究發現,眼睛注視線索與箭頭相比,二者都能誘發觀察者的注意定向反應,但箭頭卻沒有引發喜歡效應。這表明相比于箭頭,眼睛注視能夠帶來特殊的社會情感價值(Manssuer et al., 2016),更容易使觀察者進行視覺觀點采擇,從而產生喜歡效應。同樣,對喜歡效應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比如面孔情緒及吸引力(Bayliss et al., 2007; Canadas &Schmid Mast, 2017; Landes et al., 2016)、面孔可信度(Kaisler & Leder, 2016)、多張面孔(Capozzi et al.,2015)、運動表征(Ulloa et al., 2015)以及情感背景(Bayliss et al., 2010)等,也可能是由于帶有社會屬性的因素的加入使得情境更具有擬人性和互動性,促使觀察者更能從他人角度采擇信息,從而影響人們對于目標的情感評價。
然而,目前對于喜歡效應的機制的研究仍是不充分的。正如Capozzi和Ristic(2020)認為的那樣,注視喜歡效應的作用機制可能是領域一般注意過程和涉及觀點采擇的社會過程相互作用的結果,無法完全排除其中一者的影響。但無可否認的是,注視喜歡效應是由于知覺過程而引起的對物體情感評價的改變,視覺觀點采擇在注視喜歡效應的產生過程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但是,本研究還存在一些的局限,以待未來進一步探索。首先,本研究的男女被試比例差距較大,這可能對實驗結果造成影響。Mitsuda等人(2019)的研究發現,女性相較于男性更易受到社會線索的影響,因而未來應對性別比例進行控制以探究性別對喜歡效應的調節作用。其次,在觀點采擇任務中經常存在的問題是,觀察者并非都傾向于將卡通人物看作“他人”,這可能會削弱結論的適用性,因此未來研究可以在更自然的互動場景中探索,但這也可能使得虛擬人的方向性作用變得不那么突出(Freundlieb et al., 2018)。最后,本實驗采用了One-Shot實驗范式,在這種范式中,每位被試僅需完成1個試次的實驗。在視覺觀點采擇的研究領域中,One-Shot實驗設計是被廣泛使用的,因為對于某些研究而言,重要的是結果的準確性或比率,而非反應時。且One-Shot實驗設計具有簡單易操作、效率高、樣本規模大、應用范圍廣等優點,因而被不少研究認為是可以接受的(Martin et al., 2021; Samuel et al., 2021; Zhao &Malle, 2022)。但這種設計存在較大的個體誤差,且在線實驗無法有效控制額外變量,這些都會對實驗結果造成影響。因此,未來應該通過更加嚴謹的操作對本實驗結果進一步驗證。
6 結論
本研究使用改編后的點觀點采擇范式,通過操縱字母的位置及可見性來探索視覺觀點采擇在注視喜歡效應中的作用。結果發現,人們往往對他人注視著的物體產生更高的評價。但若由于遮擋物的存在,位于他人注視方向上的物體并不能被他人所看見,那么這種喜歡效應也不會產生。這表明人們對于他人視覺信息的采擇加工在喜歡效應中起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