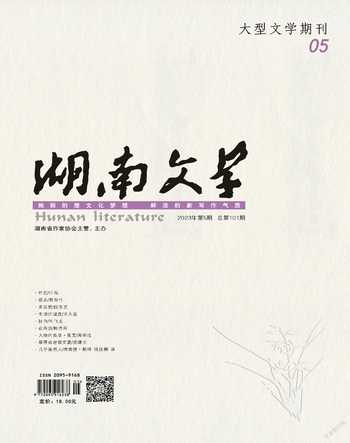阿 姨
陳錕
來陪護我母親的阿姨,護士長介紹了好幾個。
這位有把歲數的阿姨個頭矮胖,天生油頭發,臉上還有點兒皮脂。我母親看了“煩得要死,連喝水都想吐”。每當進餐時,她便蠻橫地指使阿姨避讓出去,站在病房門口,以便隨時聽候她手中不銹鋼湯匙敲擊碗盆之召喚。一般日子,中飯和晚餐,先是幾口白米飯下肚墊底,再來幾小塊番薯填充,算是吃好吃飽了。堅持一日吃兩頓番薯,能與腸胃里的火氣達成和解,也有利于每天大解的順溜。這是她長期在番薯產地蝴蝶島從醫而獲得的一點小常識,也是她漫長人生所積累的一些小經驗。多吃番薯勤放屁。有時不知不覺溜出來,無聲無息。病房里飄蕩起難聞的氣味,她便蹙眉凝神,丹鳳眼半瞇半開,認定那味兒發自阿姨肥大的肚皮。
“喂,我看你里面發酵嘞,少吃一點餓不死的。”母親說道,“這個屁啊,是人體健康的一面鏡子。你經常打臭屁,要當心腸道里生出了啥個壞東西哦。”
不過是一點兒屁事,阿姨也就用手掩嘴鼻,一笑了之。
那時,母親還可以下床走幾步,有些小事情尚能自己動手解決。有次,阿姨主動扶母親上衛生間,母親可能嗅到她身上有什么氣味,便罵她是“賊臭的柴油桶”,推開她,自己走向坐便器,又扭頭折回,尿液就從兩只褲管里流了出來。阿姨忍氣吞聲,忙著幫母親更換褲子、擦洗下身;母親非但扭扭捏捏不配合,還一個勁兒地埋怨“賊臭的柴油桶”。
阿姨去了趟醫護值班室,把母親這一反常現象反映給了護士長;護士長嘀咕著“我看她活得差不多嘞”,叫阿姨提了個醫用尿盆回來。看母親正靠坐著床背打盹,她將它放在床下,用腳尖往里頂去。事實上,這尿盆并沒有躲過母親由瞇縫眼里透出來的尖利目光。她料到人家早晚會來這一手,她最不能容忍有人插手她的下面,痛恨墊放什么東西。
夜里,母親注意著睡于一邊折疊小床上的阿姨,估摸她睡熟了,便起床,使腳勾出床下的尿盆,走去掀起她身上的蓋被,把它硬生生地塞在了兩腿之間。被驚醒的阿姨坐起身來,一手輕拍胸脯,一手拎著耳朵,用她家鄉的傳統方式,呼喚著被嚇飛的魂靈。母親嘿嘿笑個不停,尿液滴漏不止,自己卻不知不覺。
幾天后的一個下午,阿姨準備去買母親想吃的甘草橄欖,天冷換件厚毛衣。
母親發現她那兩只乳房耷拉到肚子上,說“老豬娘,一窩養十崽”,當場就給罵跑了。
阿姨打電話給我大哥,含著淚訴說了一系列的“不幸遭遇”,決定“付我五百塊錢一日也不做啦”。結算去十六天的工錢。
護士長向我大哥推薦一位剛剛空閑下來的阿姨,四十出頭,人清爽精神,在病房里干了好幾年,對難弄的病人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有點“患者家屬搶不到”的意思。大哥心領神會,當然要像上次一樣,塞給護士長一只紅包——介紹費。可誰能料想,就是這樣一位經驗豐富的“搶手阿姨”,來陪護的第五天便栽在了母親的手上。
那天上午,母親不曾聽到洗手聲,就見阿姨大解之后步出衛生間,剝掉一只大芒果的皮兒,用右手的三枚指頭撮著遞給母親。母親一手接了過來,不吃也不響,盯著阿姨看了老長時光,突然朝其臉面砸去——正中鼻梁,鼻血雙股出。
護士長不讓阿姨與聞訊趕來的大哥面對面協商,而是把當事人隔離開來,由她出面在兩人之間斡旋、調解。
阿姨倒沒過分責怪母親,她說自己的鼻子天生很脆弱,硬東西一碰就出血,至于鈔票嘛,除了那五天應得的工錢外,再給兩百塊錢出血補償費,也就算啦。但調解人接受不了,她向肇事方施壓,必須賠償兩千塊錢才能了事。大哥一方面覺得“自己”理虧,一方面想盡快息事寧人,只好依從。護士長從中克扣了幾張百元大鈔,大哥不得而知,我也不好亂說。
護士長去向別的病人家屬推薦“搶手阿姨”,那是不爭的事實。這次,她到手的紅包又增厚了些。暗地里,病人家屬經常互相交流,介紹費嘛,必須逐個兒遞增,就像患者痛苦地爬著醫院樓梯一樣。
這位保養得白白胖胖的護士長,年紀在五十上下。我只見過她一面。在我的感覺中,她的特別之處,便是長著一副斂財的羽翼,扇動起來就不可能做到為病人著想。我這么說并沒有冤枉她。我聽說,她還熱情地引薦上門服務的“醫藥代表”與患者深度接觸。那些跟奸商沒什么區別的“醫藥代表”來推銷的新藥,據稱,可以有效治療心腦血管疾病、精神抑郁和各種疑難雜癥。病人好像都是喜歡吃新藥的。有新藥就是有新武器對付病魔,新武器一旦亮相,老病魔就將逃之夭夭。只要有新東西往嘴里塞,只要是白衣天使推介來的,管它是不是掛著新鮮羊頭而賣出的臭兮兮的狗肉。
“出血”那天下午,母親獨自盤坐于床上唱歌,重復哼唱著幾首“老上海”的片段。聲音時輕時重,讓人聽不清歌詞,只感受到一絲絲哀傷一縷縷凄婉,在病房里纏綿縈紆。護士長進來為“搶手阿姨”拿回兩樣留下的東西。那些飄蕩的音符帶給她的哀訴一直揮之不去,便將窗戶拉開些。母親的歌聲飄飛到窗外,外面刮起的風兒忽然改變了方向,樹上一群麻雀頓時停止了歡鬧,幾個在空地上散步的康復病人也都駐足而聽。這唱的是哪個年代的歌曲?這曲調怎么會撩人毛發、滲入肌理,讓你感到陰涼涼、寒森森?
護士長發現母親的臉上流著淚,就回頭去找主治醫師。她問望月醫生,能否用藥物使母親安靜下來?但實際上,她還有進一步的要求,那就是要望月醫生把母親轉出院去,關進精神病院,直到上西天。像母親這樣蒼老的病人,精神病院一般不接收。護士長聲稱那里“有自己人”,可以幫母親進去,人家只要一筆小小的“幫忙費”。只可惜,這位可能患有更年期綜合征的護士長,一失手而打空了小算盤。她哪里曉得,望月醫生跟母親有著特殊的感情。
蝴蝶島,距離城郭碼頭約四十分鐘航程。
供職于蝴蝶公社醫院的陳醫生,有天接診一位頭胎待產婦,羊水破了老半天,孩子還是不肯出來。這種情況經常會碰到,或許就在那聲“喔喲”之后……陳醫生呢,她守候于一聲接一聲的“喔喲”左右,一直等到天快暗下來,才決定叫上“喔喲”的家人,用擔架抬“喔喲”上機動小船,共同護送去城里的醫院動難產手術。可誰也料想不到,船開到途中,海上望月露臉,太陽般鮮紅——小人冒頭啦!正逢十五大潮汐,在一排又一排波浪的涌動下,小船搖晃得使人站不住也坐不穩。陳醫生忍受著暈船的惡心和頭痛,僅憑旁人掌握的一束手電光、隨身攜帶的紅十字箱里的簡單器件,仰仗嫻熟的接生技術,把一個女嬰接送到其母親的懷抱,使之在浪頭撞過來的一大片月光中發出了生命的第一聲啼哭,又在潮涌卷上來的一大片月光中確立了人生的第一個起點。
航行繼續,向東,向著那個鮮活紅亮的望月站起來的方向。
沒錯,盡管母女平安,但尚需在城里醫院觀察幾天。辦好入院、移交母女等手續,陳醫生回到城中自己的家里,已是半夜。
次日早上我才獲知,她給我這個正處于肝炎恢復期的小兒子,帶來了一帖提高自身免疫力的良藥——曾包裹那小生命的胎盤。那時家用冰箱還是個美好傳說。為了保持胎盤的鮮度,她連夜清洗,切成小塊兒,在煤油爐上煮熟,像紅燒肉丁那樣盛于碗里,叫我分三餐下飯吃。見我瞠目愣怔,一副不想也不敢吃的樣子,她悄聲細語地開導我,本想把胎盤烘干研成粉,分套在一粒粒膠囊里,然后像服藥那樣一次吞幾粒,人就不會有什么心理障礙,可這樣有效成分至少破壞一半,只有新鮮煮來吃,才能充分吸收其蘊含的球蛋白。
掰指算來,三十六個春秋,在同一片風云變幻的天空上翻滾而過,我的肝功能從未出現過異常,是否跟吃了那個鮮胎盤有關,我怎么也說不清。我只能說清,在我咬牙皺眉吃下那大半碗“紅燒肉丁”的第二天,陳醫生前去醫院看望母女倆,那身體狀況良好的母親一見陳醫生,不禁熱淚盈眶。正好,護理員推著保育車進來,將嬰兒抱給母親喂奶,母親就把女兒的兩只小嫩手托起來,一邊“拜”陳醫生為“大姆媽”,一邊替女兒連連說著“謝謝大姆媽喔、謝謝大姆媽喔”。待女兒吃好奶,她懇請大姆媽給小寶寶起個名。大姆媽想都不想,脫口而出:“我看就叫‘望月好嘞。”
望月姑娘讀書一路拔尖,一直讀到浙醫大。獲得碩士學位后,進入我們島城這家醫院,成為一名主治醫師,給她的大姆媽看毛病了。
望月醫生預料到,收治我母親這種病人不可能太平,便特地想辦法,給她安排了一個單間,鬧騰起來,對別的病人影響較小。
前后約半小時,母親斷斷續續地哼唱著那些“老上海”,哼唱到最后幾分鐘,恐怕只有她自己聽得出,歌曲里面走動著踢踢踏踏的腳步聲。
我承認,這么多年來,自己并沒有真正地想到、關注過她的苦痛,靈魂的,情感的。有時候,我還有點兒厭她、煩她。她那發自靈魂,他人聽不到的吁求和呼喊,也許,那時正懸浮在空中,彌漫于病房里,而你則漂在北京車流滾滾的道路上,你呀,在為生存也為所謂的前程東奔西跑著。這是很好的回避理由,更是自欺欺人的借口。你眼不見心不煩,連最起碼的關心和問候,也很少通過電訊傳遞給她。這一切的問題到底出在哪里?有一點,你倒是明白的,她表面上可謂一無所有,但她的心靈里留有太多創傷。粗略一看,她在集中那么些殘余的精力來對付外界,仿佛恐怖和死亡只會從外面向她襲來,而不會出自其內心。對于內心,看來她一點也不懼怕,她好像對自己皮肉里面的東西都抱有信心。
望月醫生進病房來看她,驚異于她兩眼周圍布滿粉紅色的淚痕。不過,在她干癟、灰褐色的臉頰上面,目光仍十分活躍,會吸引你的注意力,使你暫忘一切而產生一種生命飛逝的強烈傷感。我聽聞后十分感慨:昔日時光,昔日的,多少時光,恰似一陣寒風,從母親的心頭猛烈刮過,揚起一蓬“老上海”煙灰——
粉紅色的,
眼睛唱響的歌聲,
黃連般味道……
母親的“惡名”在醫院里傳布開來,再也沒有哪位阿姨敢踏入其病房。
沒人來陪護,望月醫生也束手無策。毫無疑問,這種依賴住院而維持著生命的病人,只好出院回家。人心都由虛弱的血肉組成,這樣見死不救,不忍也不安。母親熬一天多一天。媽媽,姆媽,阿娘,子女喊一聲少一聲。情形危急,得趕緊召開自身符合陪護條件之人的家庭會議,商定一個去醫院侍候老娘的辦法。
這不,與會者按年齡大小,依次是大姐、大嫂、二姐、小嫂,四人湊一桌,各人占一位,就像坐在麻將桌前那樣。
通常的做法,一人十天輪著去,往復循環,看來行不通。
大姐帶頭發言,她左手捂胸,右手打手勢,聲稱自己的胸口憋悶得厲害,醫院檢查結果是心臟出了問題,極有可能,最近要動一次搭支架的手術。這可不是冒一般的風險喲。所以說,她目前活著等于是半條命。
胖乎乎的大嫂不吱聲,臉上保持著笑瞇瞇。要說毛病,上了年紀的女人哪個說不出一些病痛呀。她年輕時精神還出過些問題哩,到湖州的專科醫院都去治過,那種吃了老打瞌睡的藥片足足服用了八年哪。抗戰老早勝利啦,她現在就不好意思再翻厚厚的舊病歷來說事,靜觀其變不失為上策。
輪過去,該輪到特地趕來的二姐拿出態度了。她安家于母親的故里——上海郊外,表示偶爾來幫幾天忙還好說,長住下來陪護姆媽太不現實。家里一攤子事情可以放手不干,而唯一的即將中考的外孫每天要來吃飯,不能撒手不管吧?
小嫂呢,她仍在商場上班,一根蘿卜一個坑,上趟廁所都要掐時間。更要命的是,家里有個癌癥病人需要她照顧。
坐于一旁察言觀色,本來只擔任召集人的大哥,忽地站了起來。
大哥說道:“護理大人,小人個個有責。這個有困難,那個走不開,叫姆媽等死,呃?我看是人人不情愿。去做這種苦差事,是沒辦法,你們說有啥個辦法,呃?誰也甭想推托。”說得硬邦邦的,擲地有聲,卻句句在理,無可辯駁。
大姐說道:“走得出,是該去。實在去不了,出鈔票嘛。”
二姐說道:“那出多少?”
大哥說道:“這是后一步的事情。先要定下誰去醫院陪護。”
至此,三個女親人的目光,幾乎同時投向了沉默不語的大嫂。希望是有的,希望就在那張像彌勒佛一樣笑容可掬的臉上,希望更在那個一餐能裝滿滿兩碗白米飯,量大福大的肚子上。她退休賦閑于家,身沒內患,體無外累,無疑是去醫院照看婆婆的最佳人選。再說,她將每天和婆婆同吃同住同開銷而自己無須花一分錢,又有什么不好?節省下的生活費,難道不是人見人愛的人民幣?
抓鬮。
大哥當機立斷,作出了“誰也甭想推托”的決定和具體實施方案:做四個紙團,誰抓著寫字的那團誰就上。青石板上摔烏龜——硬碰硬,沒有絲毫討價還價的余地。
“再商量商量嘛。”大姐說道。
大哥不予理會。分明早有準備,他走到房里,旋即返回客廳,那雙抱成一團的手,在桌子上方松開,四個皺巴巴的紙團掉落于桌中央,震顫著四位女親人的視線。這么說,四分之一的幾率,千真萬確嘍。而手一抓,就有可能將整個兒的苦差事都握在了手中。
誰也甭想推托。
反正每人遲早要抓一團,大嫂率先伸手去抓,卻被機敏的大姐一聲叫停:“等一等。誰也勿要急,慢慢來。”
這四個貌似一樣的紙團,難道不存在細微的差異?大姐的眼睛可是近視老花加散光啊,叫她如何分辨這種細微差異?而大嫂的視力,好得能看清《電視報》中縫里“月下老人”揮舞的紅絲線,難道大哥和大嫂夫妻倆事前沒有交流溝通,沒有為辨認細微差異而進行過多次演練?大姐認為,姐弟是同胞,人心隔肚皮,在這種將決定去做牛當馬而又得不到病主人一把糧草的事體上,他們兩口子于暗中做不做手腳就難說了。
真是很難說的喲。要是大嫂一抓一個準——空白,那留給大姐“抓著”的概率,便由四分之一猛增至三分之一。這真讓人倒吸口寒氣,汗毛嗖嗖豎起。
于是,大姐不由分說地捉起四個紙團,放在一掌之上,蒙于一掌之下,用力一下一下地揉搓。很顯然,她要憑一己之力,搓掉每一點可顯示特征的棱角,揉出一個家庭的公正、親人間的公平。
大姐將結實、外形完全一樣的紙團放回桌中央,以老大的威勢宣布游戲規則:四人同時出手,好比搓麻將,先共同洗牌,再以她為莊家,輪著抓牌,然后按順序,一個一個地出牌。似乎,真正考驗搓麻者智慧的時刻到了。
莊家大姐首先攤牌,白板。下家二姐緊跟著打牌,也是白板。對家小嫂手上的白板就成了“死子”,想都不用想,扔出去就是。上家是大嫂,她攤出來的同樣是白板。嚯嗬,真是邪了門。
大哥說道:“都把它翻個面。”
四位女親人,在相互監督下,各自翻起了面前的小紙片。
喏,大嫂翻過來的紙面上,趴著一個“阿姨”。
大姐掏出手機,橫向拍攝一張,接著,豎立手機,再來一張。
這個必將載入家族史冊的“阿姨”,由大姐發送至我的手機。下載之后,大姐向我發起了語音通話……
大姐他們這代人,大多被命運折騰得哭笑不得。下鄉插隊落戶,返城進“大集體”做工,下崗自謀生路,自己補交社保,她一樣也沒落下。湊足十五年工齡,晚年“吃碗湯飯”才有了保障。“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李鐵梅的唱詞扎根在她心田,早已長成參天大樹。春夏秋冬的衣著,幾乎都舊遢遢,平日逛菜市場,不買高于三塊錢一斤的蔬菜、超過十五塊錢一斤的魚蝦。
“做人做得心里酸汪汪。”大姐曾對我這樣感嘆。
好在,位于小街的三岔路口,一排老樓房的底層,有套公婆留下來的、較寬敞的房子,還有在綠化帶上有個圍墻圈起來的“事實前院”。院子和客廳經過簡單改造、裝修之后,開起了一家能容納四攤牌桌的麻將館。大姐搜刮出肚子里的幾滴墨水,請人做了一具白底紅字、雙人枕頭大小的燈箱,安裝于院門外一側:“不打不成交——棋牌室。”她逢人就說,這個棋牌室,我連棺材錢都投進去了。
就這樣,大姐既是小老板,又是麻友們的貼心服務員,時不時來給各位續茶水。杯子里泡的并非像別家那樣的粗劣茶葉,而是香幽幽的一級龍井;中場端上來的一碟新鮮水果,也不像別家那樣整個兒連皮帶殼的,你愛吃不吃,而是切成小塊兒或掰為單瓣,一塊一瓣都插著一枚牙簽。每天下午、晚上各一場,幾乎場場爆滿。實實在在的賺頭擺在那兒,讓有些人看了眼紅。大姐呢,心情舒暢,走路噔噔響,卻忙得團團轉。于是,她給經濟獨立,每天百事不管,只管自己吃老酒的大姐夫下了道命令:每場收攤,負責打掃衛生。大姐夫一口承應,向她攤開一只手(老酒吃得五枚手指都發抖),來點老酒錢嘛。
大姐說,每月工錢三百塊,偷懶一天扣十塊。
不幸的是,有天早上,大姐拉開院門,叫出“哎呀娘唷——咻咻”之后,胸口又憋悶了,還伴有隱隱作痛。那個隱痛喲,一陣接一陣。“不打不成交——棋牌室”,被打成了“¤打不成交——棋牌室”。卡在那破洞里的半塊磚頭,發黑發臭,長著幾撮發黃的苔蘚,像是從陰溝里挖扒來的。
要是抓著那個“阿姨”,大姐該咋辦?
大姐和我的語音通話持續了三十八分鐘。
半個多小時,基本上都是她在說話。她那滔滔不絕的話語里,當然有對身處遙遠北方的手足的牽掛和關愛,也有一位大姐對未成家的小弟的教誨,更為重要的是,向“長年累月在外頭當神仙”的小少爺,傳達了家庭會議的主要精神。
姆媽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你不是不曉得。生這種病真叫罪過。她說,你大哥言之有理,護理大人,小人個個有責。你這個小少爺,盡過一點點責任嗎?兩只肩胛扛個骷髏頭,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姆媽生養你,為姆媽的毛病,你操過一分心還是出過半斤力?你大嫂一人挑起了去醫院陪護姆媽的重擔,隨便咋講,不給她經濟補償是講不過去的。眼下雇個阿姨,起碼要六千塊錢一月,自家人打對折,三千塊錢要給吧。你小嫂負責姆媽的衣服換洗,分攤五百。醫院的大鍋菜太難吃,我嘛,隔天燒些新鮮貨給姆媽送去一回,也分攤五百。還差兩千,你和你二姐,啥都不做,啥也不管,各人分攤一千。
好,好好。我說,多虧有大嫂。
大嫂顯然苦不堪言,她的脾氣變得越來越壞,神情怪異,有時竟把怨恨和火氣發泄于我母親身上。我不接受,但也得理解。人們都說,家丑不可外揚。而我在想,“外揚”其實也沒什么大不了的。多少年來,母親和大嫂就是一對始終解不開死結的冤家對頭。這個平時她“連半只眼睛也不要看”的兒媳婦,我大嫂,如今充當著“阿姨”而無法脫身。
她戴著一次性薄膜手套,握緊的雙拳舉在胸前,連接兩只拳頭的是條干毛巾,不知要做什么。見我走進病房,向床頭靠攏,大嫂轉身讓位到了床尾,一臉難看的笑容。我叫了她一聲。她把毛巾往肩上一搭,雙手叉腰,放大笑容,沖著我嚷嚷道:“手像貓腳爪,哼哼,老想扯老想扯,你來弄,你來弄弄看。”
我領悟了大嫂的意思,也明白了她的笑容表示什么。但叫我做兒子的怎么弄?八十三歲的母親,如同出生八十三天的嬰兒,日夜用尿不濕兜底。望月醫生曾跟我形象地說過,飄浮于她腦海上的一塊烏云,還在不斷地擴大。
整個人呢,瘦小得像一只老蝦干。一頭自然卷曲的銀發,一雙還沒有風干的丹鳳眼,以及一盞仍在耗油的心燈,閃亮于我心里,我母親。
一只還握著家庭大權的枯手伸向兒子,我母親。
我簡直成了她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幫她坐起來,讓她上身靠于墊高的枕頭上。好像是,心里話迅猛涌上來,擁塞在喉嚨口。她張嘴輕咳,卻吐不出只言片語。我為她系上棉布圍嘴兒,捧過去插有吸管的水杯,給她吸兩口大嫂調配好的蜂蜜茶。她閉嘴努唇,隨后張口哈氣。看樣子,茶水咽了下去,但眨眼之間,一長溜口水,接著一長溜口水,又像是把堵塞的心里話分流出嘴角,滲入圍嘴兒。
人不再有動靜,包括神情、目光、口水……我母親,仿佛瞬間變成了一尊蠟像。不知她哪里難受,難受得一下子說不清道不明,也無法以肢體語言來表達,哪怕是一個眼神。我撫弄著她的手,手指濕熱、微顫,使我好像沾染到了她流動的血液。是啊,她的手掌上留有我幼年的尿跡,指甲縫里鑲嵌著我頑劣的殘屑。我想她的感知正在逐漸加深——一個中年兒子撫摸著老娘的手。
我輕聲叫喚道:“姆媽,姆媽……”
我姆媽的丹鳳眼開始眨動,閃現幾點磷火般的亮光。閃著閃著,我姆媽慢慢抽回了她的手。這雙手,這雙在三十六年前的一個深夜,為我在煤油爐上煮過紅燒胎盤的手,好像有點不好意思,躲進了被窩。她嘴巴翕動著,卻終究沒說出話來。我姆媽有話要說。我感覺得出。她要對我這個“長年累月在外頭當神仙”的兒子說些什么。肯定要說些什么。我俯臉側耳去引導,一聲細微的語音撞上了我耳膜:“貼著,難熬死嘞。”
哦,我想是尿不濕,一定是那該死的尿不濕,使我姆媽“難熬死嘞”。而我卻不能為姆媽解除這種難熬。不能啊姆媽。我心里的難熬……唉,我說了也是白說,只好讓這種莫可名狀的難熬,在自己心里繼續難熬著。
大嫂拉下肩上的毛巾,像理發師那樣在面前啪嘚啪嘚來了幾下。她說道:“哼哼,我算是看透了,你們一個個都是來了心愿。我生來犯賤,我骨頭輕,我勁道大就活該吃苦頭。阿娘哎,我吃了多少苦頭,你曉得不曉得啊?一個來叫兩聲姆媽,一個再來叫兩聲姆媽,都是空口白話,動嘴不動手,叫煞死都不頂個屁用。你也想來了個心愿就走開,哼哼,你等著,幫忙做對手。”
需要我幫忙做什么,我叫她盡管吩咐。
大嫂說道:“你等著。哼哼。”
母親腦海上的烏云在飄動,我心里有數,下一秒,下一分,掀起驚人的大動作,發出嚇人的叫罵聲,都沒一個準頭。這種時候,你說一千句哄人話,想出一萬種巧妙的騙術,也哄騙不走她腦海上的一絲烏云。好吧,我呆愣著,我只能呆愣著。我這次到寧波參加一個活動,借機來看望母親,是我必須來看她。滿嘴“哼哼”的大嫂,指望我幫上什么忙,做成怎樣對手,我只好等待。其實,在生死兩茫茫的病房里,你這個小少爺的到來,毫無實際意義。在蠟像般的母親面前,小少爺不過是個影子,是她腦海上那塊烏云下的一片固定陰影。她還認得出你,對你有種信任感,不是嗎?向你伸來還握著家庭大權的枯手,那一定是從你身上聞到了她自己血肉的氣味。
骨肉就是骨肉。
大嫂就是大嫂。
大嫂的目光凝聚于母親的下身,暫時看不出有什么動作,便對我說道:“我轉過背,哼哼,她就偷偷扯掉尿不濕,想拉了還不吭聲,拉得床被墊子一塌糊涂,去換一回被那個護士長臭罵一頓,罵得我像個小偷,大氣也不敢出。最近一趟去換墊子,護工一把推我出門,說清爽的用光啦。哼哼,你耳朵沒有聾,要聽進去。”手指頭戳向母親,又說道,“再拉在床上,臭死你,爛煞死。”
大嫂的話語雖然十分難聽,但還是讓我聽出了一些她的苦衷和道理。
不過,母親使尿不濕“難熬死嘞”,墊盆又不管用,你指責她“想拉了還不吭聲”,是十足的廢話。她有像我們這樣“想”的感覺嗎?她能控制自己的“想”,并且“想”得到后果嗎?要是她想拉了就會吭一聲,那你大嫂還會捏著鼻子吃苦頭,遭護士長臭罵被護工推出門嗎?也許有些夸大,因為有望月醫生的關照,護士長和護工不至于做得太過分,至少不會明目張膽地辱罵或者動手。
在這種場合,我只能想想而已。我不好說啊。我說什么都不好。
母親斜睨我一眼,好像是看兒子在不在,有自己兒子在場,她的膽子就壯大起來,哪會怕這個嘀嘀呱呱的“大糊病”。她一直視大嫂精神不大正常。她討厭大嫂監視其一舉一動。而她信得過的親人呢,例如我……
我發現被子里的手動了一下。大嫂隨即將毛巾摜到那個部位的被面上,并對我說道:“看見嗎?貓腳爪又上啦。”收回毛巾,在病床上啪嘚啪嘚來幾下,向母親發出嚴厲警告,“扯,扯,扯,哼哼,再扯,再扯要你好看!”
母親說道:“撮著雞毛當令箭,十三點。”
被窩里的手,又動了一下。
大嫂說道:“自己出屁股,還講人家穿短褲。”
手上啪嘚一下,毛巾又摜了下去。
母親說道:“當面燒香,背后打槍的壞坯子。”
被窩里的手,再動了一下。
大嫂說道:“城隍廟得病,離不開床的東西。”
手上啪嘚一下,毛巾再次摜了下去。
母親說道:“現眼的貨。”
被窩里的手,不停地扯動著。
大嫂說道:“發臭的嘴。”
手上啪嘚一下,毛巾一次接一次摜下去。
母親說道:“豬食槽。”
被窩里的手,一動不動了。
大嫂說道:“破葫蘆。”
手上啪嘚一下,毛巾摜在了自己的肩胛上。
母親又斜睨我一眼,是一種確認嗎?確認自己的兒子就站在床頭邊?我還在疑慮,只見她躬彎的上身陡然挺直,隨著“嗞喇”一聲響,扯拉出一片淡綠色的尿不濕,朝大嫂猛摜過去——整片兒糊在了頭臉上。大嫂一把拉下它,又順手丟向母親的下身,人撲上去,抓住母親的兩只枯手,像對付兩根柴棒那樣上下疊加,臉轉向我,急切地說道:“來來,快來做對手。綁,綁綁,綁住它。用毛巾。哼哼,阿娘唷。”
母親朝我拼命搖頭,還一個勁兒地眨眼。由那雙尚未風干的丹鳳眼里眨出信賴和祈求,又眨出哀傷與淚水……
返京之前,最后一次去病房探望母親。
床頭柜上有個白瓷盆,盆里的熟紅薯塊拼成圓形,一圈一圈、由大到小堆疊為三層,上層的中心豎立一截剝了皮的香蕉,香蕉上插著支已點燃的小紅燭。
大嫂正在為坐靠于床頭的母親梳頭,梳那滿頭自然卷曲的白發。她一手在上面梳著,一手攤在下面迎接著被梳落的發絲。見了我,她又笑開了。
“阿娘生日。”她說道。這一說,笑得有點兒羞澀。
責任編輯: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