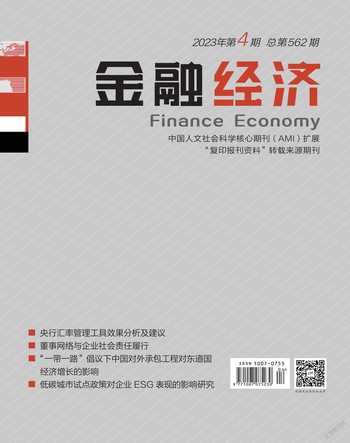公司法修訂背景下我國公司類型的差序規制及實現路徑研究
徐嘉豪
摘要:現行公司法在組織機構設置上未能發揮對公司類型進行區分的作用,無法適應不同類型公司對權力分配、經營效率的要求。兩權分離程度的差異使得公司面臨不同治理矛盾并呈現出多元屬性特征,公司由契約向組織的演變過程也內含著從封閉性向公開性的屬性轉化。公司法應當立足多元理論基礎,為普遍存在的各類公司形態提供豐富的制度供給。具體設計上,應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封閉公司,賦予其組織機構設置的充分自治權。將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公開公司,明確所有者權、經營權和監督權的劃分標準以降低代理成本。以上市公司為治理結構最完備的公司類型,允許其選擇單層制董事會或傳統三會結構治理模式,根據兩權分離程度由高至低,從公司管理方式、監督機構設置上分為非上市公眾公司、封閉型股份公司,并確立針對性的治理要求。
關鍵詞:公司類型;兩權分離;組織機構設置;差序規制
中圖分類號:D922.291.91?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7-0753(2023)04-0084-09
一、引言
2021年12月24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一審稿》)。《一審稿》對公司組織機構的改革引人注目:允許公司選設監事會或董事會下設審計委員會作為監督機構;對規模較小的股份有限公司簡化董事會和監事會的設置要求,并創設一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12月30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草案)》(二次審議稿)(以下簡稱《二審稿》)在《一審稿》的基礎上,允許規模較小的有限責任公司經股東一致同意不設置監督機構。《一審稿》和《二審稿》對現行嚴格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三會結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松綁。對股份有限公司內涵的延伸,實質上承認了實踐中廣泛存在的小型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要地位。但是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在組織機構改革方面基本采用相同邏輯,缺乏對不同類型公司治理需求的進一步考量。以規模大小進行區分的標準在實現股份有限公司概念延伸的同時,也導致了規模較小的股份有限公司與有限責任公司實質趨同。
公司組織機構設置直接關系到內部基礎性權利義務的配置,會使公司呈現出不同的類型特征。但現行立法并未充分發揮組織機構對實現公司類型區分的實質作用,導致日益復雜的商事實踐需求缺乏針對性的制度供給,公司股東、董事、外部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未得到很好的平衡,引發了一系列公司治理危機。過于剛性的三會結構大大增加了公司的運行成本,不適應初創型、中小型公司對扁平化管理的需求。股權集中模式下所有者、經營者與監督者常為利益共同體,形式上的分權制衡名存實亡,控股股東擷取中小股東利益的情況泛濫。從根源來看,這些治理危機源于公司法期望以單一的公司治理理論來構造現實中所有的公司類型,忽視了不同類型公司在治理規則上的本質區別,導致公司理論設計與實踐運行的錯配。以康美藥業案為代表的證券虛假陳述案件背后,反映出公司普遍缺乏完善的內控機制,公司內部財務造假猖獗,監事會和獨立董事未能發揮監督作用。深入考量公司組織機構設置的應然邏輯,探尋如何通過對組織機構的靈活設置,滿足實踐中不同類型公司的治理需求,應當是未來公司法修訂的基礎性問題。
二、公司類型設置的理論探疑:對兩權分離理論的檢視
(一)公司立法理論基礎單一
股份制實現了將分散的私人資本向公司聚集,但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分屬不同的主體,股東與董事不同的利益追求形成了代理成本。傳統理念認為,現代企業以兩權分離為基礎,通過建立公司內部分權制衡機制來降低代理成本。我國公司法也以兩權分離理念,構建了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并存的三會治理結構。
立足現實,兩權分離并非我國公司的普遍運行現狀。根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2020年的數據,我國股東人數在3人以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3 698.9萬家,占比96.52%, 股東人數為5人以上的有限責任公司為33.4萬家,僅占比0.87%; 董事人數在3人以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3 809.7萬家,占比 99.41%。就股份有限公司而言,股東人數在3人以下的股份有限公司為47.2萬家,占比91.01%,股東人數為5人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為2.87萬家,占比5.53%。董事人數在3人以下的股份有限公司為43.3萬家,占比83.55%;董事人數為5人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為1.3萬家,占比2.52%①。股東和董事人數均在3人以下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數量上占據了我國公司總數的80%以上。即使是常被認為屬于大型公開公司的股份有限公司,在股東和董事人數的分布上也與有限責任公司并無明顯區別。這一現象反映了我國公司普遍存在的股權集中、公司所有者與經營者高度重合的現狀。
股權結構對公司治理模式的選擇有著重大的影響。兩權分離產生股東集體行動困境,股東理性冷漠之下管理層掌握了公司實際控制權,在此基礎上建立監事會、獨立董事等制度的主要目標在于解決公司所有者與管理層之間的矛盾。而股權集中乃是我國公司治理面對的首要現實,大股東與管理者往往屬于利益共同體,此時代理成本并非公司治理面臨的首要問題。我國公司治理的首要問題在于兩權高度重合下控股股東濫用控制權侵犯中小股東利益。公司組織機構設置應當優先考量如何實現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利益的平衡,這與西方公司立法中制約管理者的理念存在本質區別。兩權分離程度的高低是公司發展到特定階段的特定狀態,立法者應當立足于現實,回應實踐中普遍存在的公司類型。然而,我國公司法立法中兩權分離成了公司治理應當追求的目標,公司組織機構也是以兩權分離之下以降低代理成本為目的設置的。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對公司規定了嚴格的三會結構,即使在允許簡化的情形下,也在形式上確保了公司所有權、經營權與監督權分權制衡的格局不被打破。忽視不同類型公司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現實,期待以兩權分離作為國內所有公司統一的理論基礎,導致公司法規定與商事實踐嚴重脫節。以我國監事會制度為例,與董事會平行設置之下看似能保證監事獨立行使監督權,但在資本多數決原則下,監事人選實際上由控股股東決定,期待監事監督控股股東自然無用。此時公司治理的重點應當轉向控股股東義務的構建和股東救濟制度的完善。以兩權分離作為現代公司發展的終極趨勢也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隨著資產管理業務的發展,當公司的所有者被區分為資金提供人和資產管理人,公司所有者權利被分解為資金提供者根據投資契約獲得回報的權利與資產管理者利用資金進行投資的權利。原本分散的股東資金又以資管的形式被重新集合了起來(周游,2017)。兩權分離程度的不同是公司發展不同階段所展現出的必然結果,不存在絕對的優劣之分。以兩權分離作為現代公司本質屬性的認知忽視了我國的商事實踐需求,導致實踐中廣泛存在的兩權高度重合的公司在現行立法中缺乏理論基礎,進一步造成了我國公司類型實質單一的局面。公司法應當打破固有認知,承認我國股權集中型公司的存在合理性,在此基礎上創設新的組織架構,并對未來公司形態的發展趨勢預留一定的改革空間。
(二)公司本質屬性差異探析
兩權分離程度高低導致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矛盾,也從深層次影響著公司的本質屬性,而對公司本質屬性的不同理解又將影響到公司整體的治理機制。
對于“公司是什么”這一本質問題的回答,主要有以下幾種經典理論:一是公司契約論,認為公司是各參與人通過明示或默示的權利義務關系所組成的契約網,是用以替代市場進行契約交換和生產的機制。公司法通過各種制度來降低這個契約機制的交易成本。公司契約論主張股東自治,減少國家干預,公司法規范應以任意性規則為主。二是公司財產理論,公司被等同于多元股東及其權利確認和實現,公司的設立是公司財產的集合過程。我國1993年后的公司法采用股東出資及有限責任來定義公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采用嚴格的法定資本制;對國企強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加強對公司資產的行政監管等,都是公司財產理論的體現。三是公司憲政論,認為公司同時具備私人和公共雙重屬性,關注董事會、股東會的權力分配是否合理,決策過程是否民主,并認為股東應當像國家的人民一樣積極參與公司治理(黃輝,2020)。
關于“公司是什么”的激烈討論,其最大的價值并不在于探尋一種最優的公司治理模式,而是力圖揭示公司在特定歷史時期和市場環境下的運行共性,為不同的商事實踐需求提供理論依據。關于公司究竟為契約,還是財產的集合體,抑或是憲政組織的爭論,實際上也是兩權分離程度不同的產物。在兩權高度重合之下,股東與董事身份重合度較高,股東間利益高度一致,公司運行多依賴股東意志進行,此時公司的契約屬性明顯。這種緊密聯系是公司運行的重要基礎,現行公司法第七十一條規定了股東同意權和優先購買權作為有限責任公司股權對外轉讓的限制,此時公司股權結構穩定,呈現出很強的封閉屬性。股權對外轉讓限制也體現了合同理論與財產理論可以并存,公司治理必須關注股東的財產性權益,而對財產利益的安排亦可通過契約來實現。以契約為基礎的公司在域外有著豐富的立法基礎。例如,日本公司法于2005年改革后創設了“持份公司”類型,其中最典型的為合同公司,在內部關系方面可適用合伙的有關規定,每個投資人都享有業務執行權和公司代表權,公司章程自治范圍極為廣泛。再比如,美國有限責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LLC)類型,在成員性質、數量等方面均無嚴格限制。在公司業務執行方面,通常根據出資人之間所訂立的契約確定,一般主要有股東經營模式和委托經營模式兩種(崔文玉和趙萬一,2013)。法國1994年進行公司法改革,創設了簡易股份公司,德國在2008年公司法中,增設了經營者公司作為有限責任公司的子類型(蔣舸和吳一興,2011)。
而當公司的融資需求不斷增加,向公眾大量募集資金稀釋了初創股東的股權比例,股東集體行動困境導致公司控制權逐漸落入管理層手中,公司的兩權分離屬性增強。當公開融資能力成為公司發展的重要因素,便要求公司股份具有較強的流動性,此時公司的公開屬性大大增強。股權結構的分散又帶來股東利益的異質化,公司日益成為協調利益相關者的一種機制。這些都要求公司增強獨立性,創建分權制衡的程式以防范管理層侵害所有者利益的風險。此時,公司的契約屬性減弱,公司治理主要依靠事先制定的法律、章程條款,要求明確股東會、董事會等組織機構的權利分配和運行規則。我國基于國企改制的特殊背景,立法之初公司便具有明顯的國家機構運行特點并延續至今。例如以股東會作為公司最高權力機關,并經由股東會產生董事會和監事會,類似于由全國人大產生一府兩院一委的權力運行方式,民主選舉、分權制衡等理念明顯。但是,公司與國家畢竟在起源、運行和目標上差異巨大,尤其是股東人數較少的中小型公司,若仍然參照國家運行來設計會造成巨大的制度成本,而對于大型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公司憲政理論則具有一定的指導價值。
可見,公司本質為何并無一個應然的答案。隨著兩權分離程度的加深,公司從封閉性走向公開性的趨勢明顯,并在發展的不同階段呈現出特定屬性。我國公司法在發展過程中對制度規則的引進,沒有在理論自覺基礎之上推動規則的一脈相承,導致沒能完整回應現實的挑戰。未來,應當力求實現從“作為規則的法律”,進而到關注整體的“作為系統的法律”,以及作為一個有目標的社會進程的“作為文化的法律”的進程(Van Hoecke 和Warrington ,2008)。
三、我國公司類型劃分的基本邏輯
不同的兩權分離程度引起的公司本質屬性差異與我國立法存在一定契合之處,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的二分結構本可以提供封閉性與公開性區分,并由契約逐步走向實體組織的框架,但在實踐中兩種公司類型卻越發趨同,因此有必要對兩類公司進行屬性區分,并厘清彼此間的關系。
(一)確立封閉公司為基礎公司類型
我國兩種法定公司類型均以兩權分離為基礎進行組織架構,形成了大量的共用性規范,也導致了法律適用上的錯位。例如上市公司與股權轉讓受限的股份有限公司在股權流動性上差異巨大,卻均適用股份有限公司的規定。后者與有限責任公司并無本質區別,卻適用兩套不同的公司法規范。另外,股份有限公司很多規范均可參照適用有限責任公司,又會帶來法律解釋上的困惑:我國公司法是否以有限責任公司規范為一般性規范?那么股份有限公司未作例外性規定的事項,能否適用于有限責任公司規范(錢玉林,2021)?此間的邏輯尚需厘清。
以封閉性和公開性作為公司區分的本質屬性,與公司兩權分離程度的高低可以形成對應,也符合我國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立法定位。有限責任公司對發起設立的股東人數設有上限,股份對外轉讓時需要經過股東過半數同意和優先購買權兩項程序,封閉性明顯。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人數沒有上限,可以向社會公開募集股份,股份對內對外自由轉讓,較之有限責任公司,其公開性十分明顯。以封閉性和公開性進行區分是兩類公司在設計之初便蘊含的理念,可以保留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公司類型的固定稱謂,減少名稱變化帶來的制度轉換成本。從域外經驗來看,以封閉性和公開性作為公司類型區分標準亦有廣泛的實踐基礎。英國公司法于2006年進行大修,公眾公司和私人公司是主要公司類型。日本公司法于2005年改革后,廢除有限責任公司類型,全部統合為股份公司,并以股份能否自由轉讓區分為公開公司和非公開公司。在美國,公司類型在各州存在一定差異,但以公司發行的股票是否進入證券市場流通區分為公開公司和非公開公司則是主流分類標準。可見,盡管各國在公司類型的區分標準上各有差異,但至少普遍認可將封閉性與公開性作為公司類型區分的一對重要標準(Eisenberg ,1976)。在明確了封閉性與公開性的區分標準后,應當考慮在立法技術上實現兩類公司的區分。常見的立法技術是以最普遍的形態作為模板進行立法,并采取例外、參照適用、補充適用等方式給其他形態預留相應的空間,由此實現共性與個性的有機統一。針對我國公司法共用性規范繁多的現象,在立法體例上應當明確一類具有基礎性地位的目標公司類型,凝練兩類公司的共性,并對其他公司類型進行例外規定或在某些規范上參照適用,從而理順兩類公司規范間的關系,實現公司類型的實質區分。立法者應當斟酌公司的經濟影響力以及各種公司的內部成因和內部牽連,尋找最具擴張力的公司作為公司法上的目標公司類型(葉林和劉向林,2010)。2018年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指出,我國中小企業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②。同時,股東、董事人數為3人以下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又占據了我國公司數量的80%以上。可見,中小型、封閉型公司是我國目前乃至將來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的公司類型,應當成為立法中的目標公司類型。具體來說,在公司法體系結構上,宜尊重現有的制度演進邏輯,沿用有限責任公司規范在先、股份有限公司規范在后的順位,在一些同類事項上允許后者參照適用前者的規定。以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公開自由流通的市場作為判斷封閉性和公開性的標準,并以封閉性和公開性對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改造(曹興權,2022)。有限責任公司通過公司自治的程度實現其屬性差異,但應以公開融資為其公開性的上限;股份有限公司在規范上以公開性為預設,根據與公司融資需求相關事實所體現的公開性差異納入不同的監管軌道,并以股份轉讓的自由性為其下限(劉斌,2021)。公司法應以有限責任公司的規定為主線展開,因其涉眾性弱,主要依靠合同機制運行,應提供較多的任意性規范,發揮行為指引作用。股份有限公司因涉及眾多投資者和債權人利益,關乎資本市場有序發展,法律應規定較多的強制性規范作為例外。在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根據其股份流通性的強弱,也應做進一步區分。證監會制定的《非上市公眾公司監督管理辦法》《非上市公眾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等監管規則,已經從證券監管的層面創設了非上市公眾公司類型,對于股東人數超過200人、股票公開轉讓但未在證券交易所公開交易的公司實施特別監管(祁暢,2018)。所以從監管規則來看,我國股份有限公司已實際上形成了上市公司、非上市公眾公司、封閉型股份有限公司三大類型,并對公開性向封閉性的演進實施有針對性的監管。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從數量上看,規模較小的、封閉型特征明顯的股份有限公司占多數,但立法不宜再以封閉公司理念在股份有限公司章節中作重復性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原則上以公開公司理念進行塑造,滿足公司在公開市場融資的需求,對實踐中存在的封閉型股份有限公司,允許其參照適用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方能以最小的成本實現公司類型的實質區分。
除了制度轉換成本上的優勢外,以封閉性和公開性對我國公司類型進行改造,還可以最大限度涵蓋公司治理實踐中權責一體的完全控制模式與兩權分離的委托代理模式。其一,通過對有限責任公司制度的進一步松綁,引入股東自我管理模式,滿足中小型公司減少制度運行成本、提升決策效率的需求。其二,將股份有限公司定位為大型公開公司,便利其融資渠道,并規定其應當具備完整的內部治理結構以實現對外來投資者保護的要求。如此一來,原本缺乏區分度的兩種法定公司類型,在現有的運行框架內,實現了本質屬性上的區分,為我國中小型公司和大型上市公司實現針對性治理提供了框架。
(二)公司權力分配的原則
在明確了公司立法體系后,為不同類型公司設置對應的組織機構就成為立法面臨的主要任務。科斯經典理論認為,企業因節約交易成本而存在,企業的功能就在于將各個要素所有者通過內部契約組合起來,形成一個代表著各種要素集合者利益的獨立人格體(奧利弗·E·威廉姆森和西德尼·G·溫特,2010)。因此有觀點認為應當賦予公司對組織機構設置的充分自治權。但是充分自治并不意味著完全放任,輔助性的強制性規范有助于促進公司利益實現。例如在管理層控制的公司中,管理層有動機通過修改章程使其職位永久保有、允許關聯交易或免除董事義務等方式,令公司財富由股東向其轉移,而股東由于集體行動困境,往往會同意章程修改決議,此時強制性規范便可以有效制止這類利益輸送行為(弗蘭克·H·伊斯特布魯克,2016)。公司組織機構的設置應當實現對公司權力的明確劃分,針對不同類型公司的運行特點,有效實現制約控股股東、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
公司所有者權力與經營權力構成了公司運行的基礎,前者涉及公司存續、發展和股東投資權益,是公司存在的基礎,后者則涉及公司如何在經營中增加財富,兩項權力對公司運行而言缺一不可,故而在組織機構設置中原則上要有代表所有者權力的股東會和代表經營者權力的董事會或經理(梁上上,2021)。股東會作為非常設機構,無法應對復雜多變的商業環境,并不適宜承擔公司的經營職能,而將公司經營權力賦予作為常設機關的董事會或經理則是富有效率的。但是,在股東會與董事會的分權方面不宜采用相同的邏輯,應當以公司類型所體現出的不同治理需求進行差異性規定。在封閉公司內部,兩權分離程度較低,從而降低了股東會與董事會的利益沖突,基于所有者與經營者往往是利益共同體的現象,可以將公司經營權力例外地賦予股東會,允許股東會行使部分董事會職權(趙旭東,2021)。在簡化公司組織機構的同時,要強化控股股東不當侵害中小股東權益的救濟機制。現有的控股股東義務規則、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公司解散之訴、股東退出制度、股東派生訴訟等中小股東救濟制度應以強制性規范形式存在。相較之下,公開公司往往面臨更為復雜的利益博弈格局,在理性冷漠之下,股東極易被公司管理層“要挾”,同意一些有損股東利益的決議。為了避免股東權益遭到剝削,應當對股東會和董事會進行強制分權(許可,2017),明確各方權限范圍,避免越權行事。對封閉公司與公開公司施加不同要求亦是域外立法的普遍做法,例如英國公司法中,只有一個類別股份的私人公司的董事,具有發行該類別股份的授權,而公眾公司的董事以及具有兩個以上類別股份的私人公司的董事,只有經章程或公司決議的授權才可以發行股份③。日本明確了大公司和中小公司概念,在公司機關設置上提出不同的要求,例如大公司被強制要求設立董事會。
在公司經營權力的分配上,應當格外重視經理的作用,作為日常業務執行機關,經理不僅涉及公司內部權力分配,還關系到公司對外行為的法律效力(趙旭東,2022)。我國法定代表人并不享有公司經營決策權和業務執行權,卻可以代表公司對外行為,基于保護交易安全的考量,公司又常常承擔其越權代表的不利后果。而經理同時具備業務執行權與對外代表權,可以確保公司的內部決策與對外行為一一對應,在公司與對外交易方之間形成安全穩定的紐帶。董事會與經理之間的關系是同一性質的經營權在內部分配的關系,為確保公司內外意志的統一,規模較小的公司可以選擇不設置董事會,但應當設置經理。
監督權并非所有公司存續的必要權力,卻也為公司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需。在封閉公司中,基于對自我投資權益的重視,股東在多數情況下充當了有效、盡責的監督角色,此時無需設置單獨的監督機構(張輝,2012),但應當強化對控股股東的規制力度。同時,公司在設立時須進行相應登記,并在存續過程中將自身股東結構、經營狀況、財務狀況等進行一定的信息披露,使得公眾能夠了解到公司運營的基本情況(夏小雄,2019),外部交易方根據這些信息進行交易。相較之下,在公開公司中,隨著兩權分離程度增加,公司管理層濫用權力侵害股東利益的風險增大,公開融資帶來的股東規模擴大也加劇了股東間的利益沖突。股東與管理層、股東與股東、公司與雇員、公司與外部債權人間的利益平衡都成為公司治理的重要任務。此時設置單獨的監督機構以應對公司內部復雜的利益沖突格局應當成為公司法的強制性規范。在資本市場上,公平的證券交易需要公開透明的市場環境,確保市場所有投資者擁有平等的信息獲取機會,因而在信息披露的內容和程序上均對公開公司規定了較為嚴格的監管規則。同時,針對我國公司普遍存在的股權集中現象,對控股股東義務的構建貫穿于所有公司類型,但應隨著股權結構的不同進行動態調整。
在公司權力的分配中注重強制性規范的作用能夠有效制約公司內部人不當擷取股東利益的行為,并通過自我約束機制將公司的負外部性內在化,實現公司、股東、債權人等各方主體利益的平衡,也適應了不同類型公司的治理需要,助力實現公司類型的實質區分。
四、公司組織機構設置的具體展開
以封閉性和公開性對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改造的同時,鑒于實踐中股份有限公司的廣泛樣態,在組織機構設置時還可以將其按照實質區分為上市公司、非上市公眾公司、封閉型股份有限公司。發起設立和股份定向募集的股份有限公司可稱為封閉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的任務在于精準把握不同類型公司的本質特征,在規定對應的強制性規范基礎上,提供豐富的可選性規則供公司自由選擇(Ribstein ,1995)。在總體思路上,可以上市公司作為組織機構最完備的公司類型,在此基礎上對組織機構的強制性要求依次遞減。
上市公司應當具有完備的治理結構,設置股東會作為公司權力機關,董事會負責經營決策。在監督機關的設置上,《二審稿》確立了單層制董事會下設審計委員會和傳統監事會二者擇一設置的治理模式,并將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職能等同化。
對于選擇設置單層制董事會的上市公司,當經理層逐漸上升為公司經營決策的主要力量時,董事會應當從經營決策機構轉變為公司監督機構。在此進程中董事會可能會經歷一個“決策+監督”雙重職能的混合式董事會模式的階段,這源于董事會和經理層的職權分配關系,但屬于公司在自身發展階段中的自治事項。在監督職權的分配上,不宜將監事會與審委會的職能同等化。因為監事會作為雙層制治理模式下唯一的監督機構,需要承擔所有監督職能。而單層制下董事會承擔監督職能,審委會系董事會下設輔助機構,宜負責具體、專業化的監督事項,并由董事會承擔一般性、宏觀的監督職能。為實現業務執行與監督的分離,在董事會及其下屬各專門委員會中應當提升非執行董事特別是獨立董事的比例。《二審稿》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過半數為獨立董事,本文認為審委會成員的獨立性要求應當延伸到有限責任公司中,但允許其以非執行董事替代獨立董事。此外,應當發揮股東會對公司基礎性事項的監控作用,不允許董事會或經理越權行使股東會職權。
對于非上市公眾公司,應當意識到其與上市公司不只是對外投資者規模、數量上的區別,兩者的區別主要體現在證券監管規則層面。現行獨立董事制度應當延伸到非上市公眾公司中,作為強制性規定存在。另外,非上市公眾公司不能在證券市場公開交易,股份流動性較上市公司弱,股權結構相對穩定,股權集中現象較上市公司更為突出,應當加強對控股股東的規制,防止控股股東濫用控制權損害中小股東利益。
封閉型股份有限公司可進一步區分為股份自由轉讓與章程限制股份轉讓的公司。當股份可以對外自由轉讓時,內部存在股東利益異質化的傾向,在對外投資者保護上也產生了持續性要求,故應當保留設置監督機構的強制性要求,但在規模上允許作一定簡化,例如允許以一至二名監事替代監事會。章程限制股份轉讓的公司在封閉性上則與有限責任公司十分接近,股東利益一致性程度高,股權結構穩定。《二審稿》僅允許規模較小的有限責任公司經全體股東同意不設置監督機構,應當將監督機構的選設規范延伸到章程限制股權轉讓的股份有限公司與所有有限責任公司。另外,監督作為公司存續期間的動態事項,會隨著公司利益格局的變化產生新的要求,所以當持有過半數表決權比例的股東認為公司應當重新設置監督機構時,應當允許此類安排。在公司管理上,現行公司法以規模大小作為簡化董事會設置的因素,難以把握尺度,應以公司類型作為更直觀的標準,允許封閉型股份公司設置一至二名董事替代董事會,以提升公司決策效率。除了對實踐中廣泛存在的規模較小的股份有限公司作立法回應,封閉型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大價值在于打通創業者的上市通道,使其擺脫先改制后上市的巨大成本,引導有上市潛力的創業者們積極選擇這一公司類型(趙忠奎和周友蘇,2021)。
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典型的封閉公司,股東與董事身份重合度高,在公司管理上應允許選擇股東直接管理模式或委托代理人管理模式,允許其不設置股東會和董事會,并將監督機構作為選設,股東間可自由安排公司權力的分配(李建偉,2015)。在公司決議作出上允許以股東協議替代股東會決議的方式進行。但有限責任公司應當特別注重人格混同問題,避免股東濫用公司獨立人格損害債權人利益。并且,由于有限責任公司的股份缺乏自由流通市場,當出現控股股東濫權現象時,中小股東退出公司的渠道受限。應當重點完善中小股東救濟制度,包括控股股東義務的構建,完善股東派生訴訟制度、股份回購制度、股東強制解散公司訴訟制度等,賦予中小股東以全面、靈活的救濟途徑。
如此,在區分公司公開性與封閉性本質的基礎上,根據兩權分離程度的高低對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實現差序規制,塑造普遍性與靈活性兼備的公司組織形式,以滿足創業者在不同階段的經營需求。
五、結論
在實現公司類型的實質區分后,我國公司類型設置將呈現出以下多元化格局:一是在公司類型設置的理論基礎上,不再以兩權分離作為唯一理論基礎,而是充分尊重商事實踐中廣泛存在的兩權分離程度不同的公司類型。二是在公司屬性上,以公開性和封閉性作為公司的兩種基本屬性,以股權是否具備自由流通的市場作為區分的標準,并通過設置強制性規范來實現公司類型的實質區分。三是在公司內部組織機構設置上,在堅持公開性與封閉性的基礎之上,根據公司兩權分離程度的高低,以上市公司、非上市公眾公司、封閉型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為序列依次實現內部組織機構的靈活配置,為實踐中廣泛存在的各種類型的公司提供針對性的制度基礎,實現治理結構的多元化供給。
在公司理論多元化的今天,企圖以單一的理論指導,通過法律強制推動公司走向立法者所認可的現代化企業模式已是徒勞,“與其依賴于強行‘變法模式,不如采用充分供給模式;與其因為理想沖突而無法形成‘應然,不如采用‘兼容并包的模式”(鄧峰,2022),尊重商事實踐中產生的實質公司類型,在立法上予以充分尊重。本文提出了對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實現差序規制的基本思路,但在具體配套制度上的供給仍是遠遠不夠的。未來,我國公司法應當在公司基本框架、股東權利保護、公司機關設置等關鍵制度領域的引入過程中主動提供多元選項的模式,實現公司法功能從被動填充到主動選擇的功能演變(周游,2018)。
注釋:
① 以上數據來源于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2020年12月統計數據。
②參見《劉鶴主持召開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http://www.gov.cn/xinwen/2018-08/20/content_5315204.htm,2022年9月8日訪問。
③ 參見英國《2006年公司法》第550條和第551條。
參考文獻:
[1]周游.公司法上的兩權分離之反思[J].中國法學,2017(04):285-303.
[2] 黃輝.現代公司法比較研究:國際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M].2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0:14-21.
[3]崔文玉,趙萬一.美國LLC制度及其對中國公司法變革的啟示——以日、韓修法對LLC制度的引入為視角[J].現代法學,2013,35(06):158-170.
[4]蔣舸,吳一興.德國公司形式的最新變革及其啟示[J].法商研究,2011,28(01):143-150.
[5] VAN HOECKE M,WARRINGTON M.Legal cultures,? ? ?legal paradigms and legal doctrine:Towards a new model for comparative law[J].2008,47(03):495-536.
[6] 錢玉林.我國《公司法》體系的重構——一種解釋論的觀點[J].政治與法律,2021(02):2-15
[7] EISENBERG M A.The Structure of the Corporation:A Legal Analysis[M].Beard Books,1976
[8] 葉林,劉向林.論我國公司法立法結構的變革[J].政法論叢,2010(03):11-17.
[9] 曹興權.公司立法中的中小公司優先主義[J].社會科學家,2022(04):15-25.
[10]劉斌.公司類型的差序規制與重構要素[J].當代法學,2021,35(02):105-114.
[11]祁暢.中國非上市公眾公司監管的結構性變革——兼論中國公眾公司的法律內涵重構[J].云南社會科學,2018(01):76-82+89.
[12] (美)奧利弗·E·威廉姆森(Oliver·E·Williamson)(美)西德尼·G·溫特(Sidney·G·winter)編.企業的性質:起源、演變與發展[M].姚海鑫,邢源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28-42.
[13] (美)弗蘭克·H·伊斯特布魯克等.公司法的邏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81-86.
[14] 梁上上.公司權力的歸屬[J].政法論壇,2021,39(05):68-82.
[15] 趙旭東.股東會中心主義抑或董事會中心主義?——公司治理模式的界定、評判與選擇[J].法學評論,2021,39(03):68-82.
[16] 許可.股東會與董事會分權制度研究[J].中國法學,2017(02):126-145.
[17] 趙旭東.公司組織機構職權規范的制度安排與立法設計[J].政法論壇,2022,40(04):87-96.
[18]張輝.中國公司法制結構性改革之公司類型化思考[J].社會科學,2012(09):90-98.
[19]夏小雄.公司法現代化:制度改革、體系再造與精神重塑[J].北方法學,2019,13(04):89-98.
[20]RIBSTEIN L E.Statutory forms for closely held firms:Theories and evidence from LLCs[J].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1995,73:369-432.
[21]趙忠奎,周友蘇.整合與擴容:公司組織形態變革的本土路徑[J].社會科學研究,2021(01):142-152.
[22]李建偉.公司組織形態重構與公司法結構性改革[J].財經法學,2015(05):5-21.
[23] 鄧峰.中國公司理論的演變和制度變革方向[J].清華法學,2022,16(02):42-56.
[24] 周游.從被動填空到主動選擇:公司法功能的嬗變[J].法學,2018(02):138-149.
(責任編輯:唐詩柔/校對:張艷妮)
Abstract: The current Company Law has failed to play a role in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types of companies i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panies for power distribution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rights make companies face different governance conflicts and exhibit diverse attributes. The evolution of companies from contracts to organizations also contains a transformation of attributes from closedness to openness. The Company Law should be based on a pluralistic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ovide rich institutional supply for various types of companies that exist universally. In specific design,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closed companies, with sufficient autonomy in thei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joint-stock limited compani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open companies, with clear criteria for dividing ownership rights, management rights, and supervisory rights to reduce agency costs. Listed companies are the most complete type of company in terms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are allowed to choose a single-board or traditional three-meeting governance model.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rights from high to low, they are classified into non-public companies and closed joint-stock companies, and targeted governance requirements are established.
Keywords: Company types;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righ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stablishment; Hierarchical reg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