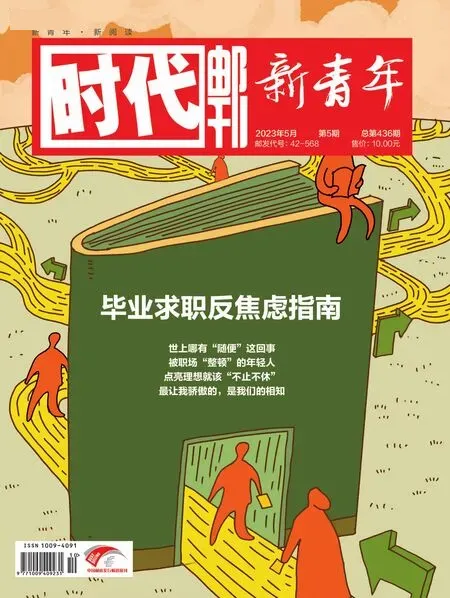一幫00后建了間最快樂的養老院
文 秦楚

在棋牌室牌桌上“浴血奮戰”是老人們的日常活動

拍攝時尚大片現場
在四川雅安,有一所“另類養老院”,是一幫90后、00后創辦、管理的。
常規護理外,這幫年輕人每天帶著老人們拍時尚大片、唱歌、跳舞、玩泡泡槍、種菜……院里累計照顧老人128位,都是自愿來的,甚至很多是點名就要住這家養老院。
從2018年經營至今,在社交網絡上,這所養老院的熱度只增不減。在這個年輕團隊的帶領下,老去好像真的不再那么可怕。
00后、90后提前50年住進養老院
作為養老院里“格格不入”的年輕面孔,佳林和另一位創始人周航都是90后,兩個人在海外分別攻讀材料工程和博物館研究專業,和“養老”毫無關聯。2017年夏天的一次經歷成為她們人生的轉折點。
為了給爺爺找一家滿意的養老機構,佳林拉上多年好友周航考察了成都以及周邊多家養老機構。“我們的第一感覺是老了好可怕,兩三個老人合居在一個房間里面,黑黑的,很壓抑,絕對不能把我的家人送到這種環境里。”
“我開始認真思考養老這件事,城市里到處都是年輕人可以去的各種地方,老人卻沒有地方可以去,那當我們老了該怎么辦?是不是可以創造一個自己老了以后也有安全感、歸屬感的地方?”
“我們參觀完后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當時的沖擊是非常大的。去康復醫院,護士去給老人做翻身動作時,好像并沒有把床上的人當作一個‘真實的人’,就像在翻一個物品;進ICU的病人是赤裸著身體的,因為長期沒有運動,肌肉已經萎縮……這些讓我們感到震撼:人活著的意義到底是什么?”這些經歷堅定了她們要做一家“不一樣”的養老院的決心。
經過半年時間的考慮,2018年初,佳林和周航正式把建一家養老院提上了日程。
因為相關背景欠缺,佳林和周航組建了專業的團隊,并全程參與養老院的籌備工作。大到廚房改建、裝修,小到電器、家具、老人用的餐盤都是她們“貨比好幾家”購置,老人院規章制度、管理辦法、文化體系搜集了厚厚的一冊。
根據老人的行為習慣,她們重新設計了一套導視系統,樓層每一層分橙色、綠色等不同顏色,用4個水果代替,每間房間號碼不超過兩位數,方便老人記憶。老人房間的亞克力鑰匙扣材質也是從耐久性和使用周期綜合考慮后投入使用的。
2018年12月,養老院迎來試運營。“第一位入住的是前縣醫院的護士羅婆婆,她特別喜歡笑,一刻都閑不下來,一度成為我們的‘宣傳大使’。”
慢慢地,靠著社交網絡和院里老人、家屬的口口相傳,養老院迎來了越來越多的住戶。目前常住老人128位,年齡大部分在75至90歲之間。“老人們都是自愿來的,有的甚至連夜帶著行李過來,辦理入住。院里大多數工作人員是90后,甚至00后。我們常‘笑’說,少走50年彎路,畢業直接拎包入住養老院。”佳林如是說。
變裝、跳舞、打牌的“另類養老院”
和一般養老院內集體打拳、做老年操不同,這里的活動由兩位00后負責。在她們的帶領下,老人們一個比一個會“趕時髦”。
露營、拍時尚大片、戶外拍短視頻變裝……“婆婆們會審核所拍的照片和視頻,看看有沒有把她們自己拍好看。”
“我們希望讓老年人和年輕人有更多的交流,把他們拉進我們社會的生活狀態里面,他們會感到沒有被社會拋棄,這是我們做此類活動的目的。”佳林解釋道。
“雖然很多活動是我們年輕人比較喜歡的,但你會發現老人們其實很愿意融進來。任何人都不想老了以后是被孤立出去的,他們還是想去表現自己,去感受、參與外面的世界。”
從第一天來養老院就想辭職、逃跑,到如今入職一年后,兩個00后已經完美融入養老院。“當時覺得是來參加變形計的,絞盡腦汁想怎么才能融入,結果待著莫名和諧起來。很多時候不是說工作要求我每天要干什么,而是自發地想去做。”詠琪如是說。
“和爺爺們下象棋下不過,我們用App照著AI下,被發現了,就說我們作弊。”“我們愛睡懶覺,婆婆們會踩著早餐時間的點把我們拉起來吃早飯,擔心我們起晚了沒飯吃。”“像閨蜜一樣和婆婆們互換服裝拍‘時尚大片’、擦口紅、聊八卦……有時候擦指甲油,婆婆們還會催我們快一點,不要耽誤她們打牌。”
在這里,兩代人之間打破了年齡的差異,不是誰管著誰、誰照顧誰,而是相互了解、陪伴。“老人有了交流的機會,他們的情緒被接納后,他們會覺得有歸屬感,被人重視。”

養老院組織的露營活動

院內老人會自行選取自己有興趣的活動
不同于常規養老院的貼身照顧,在這里,護工大都在兩米開外照看著每位可自理的老人。
究其原因,佳林解釋:“我們提出‘養老無齡感’的概念,是希望可以模糊年齡的界限。社會上總默認老人就需要被處處照顧,很多養老院出于風險防控,也會處處管著他們,我們不希望刻意地強調他們是老人,過多干涉他們。”“90歲的老人,他愿意在我們院里種菜,我們也是說‘去吧’。讓老人知道他對自身是有掌控權的,如果他需要幫助,也是他自己選擇被幫助。”
在這家養老院,可以看到文質彬彬每天堅持讀散文的“文化爺爺”,騎著“三蹦子”帶00后工作人員取快遞的“騎手爺爺”,在棋牌室浴血奮戰的“賭徒婆婆”,還有蹺著腳躺在沙發上閱讀《老年人如何保養自己》《人到老年應該這樣做》的精致婆婆……
“我們在做未來的事情”
2023年已經是這群90后、00后經營養老院的第五年,佳林依然沒有得到家里的支持。至今出去交流、匯報,兩人也還是會遇到質疑,“他們會說兩個這么年輕的小女孩給我談關乎民生的事?認為我們不可被信任。”
相比同齡人生活、事業步入常規軌道,她們創立養老院的行為也不被身邊朋友理解。
“最開始我每天晚上都哭,覺得青春被荒廢了。剛回國的時候20多歲,現在30歲了,也沒有太高的成就。”聯合創始人周航說道。
目前,養老院仍存在多重困境。院內目前沒有配套醫院,主要負責醫療和康復輔助的李軍醫需要24小時陪護老人。院內擺滿192張床,但護工人員供給量不夠。“我國養老模式一度在借鑒美國、日本、德國等成熟體系,還沒有構建出一個適合我們國情的養老體系。相關就業人員儲備也處于需求大于供應的狀態。”
“養老行業最大的隔閡是社會形象和薪資方面能夠給年輕人的回饋太少了,付出、回報不平等。很多縣級養老院員工工資低于2000元,干臟活、累活之外遭受外界的誤解,直接影響年輕人的專業選擇和擇業要求,很難形成正向循環。”但被問及是否覺得后悔或氣餒,兩人卻笑著搖搖頭。“我們有幸能夠在年輕的時候做養老行業,這給了我們另一個角度去思考人生。近距離觀察老人們,他們老了想要過什么樣的生活,那反推過來我年輕時候應該去做哪些事情。我們想要做得更好。”
2021年,養老院內開設了一個特別的項目,年輕人可以申請來“養老”一天。“現在年輕人每天都喊著要‘躺平、養老’,那我們就開放一個渠道,讓他們體驗、接觸老年人的生活狀態,一方面可以拉近他們和老人之間的距離,一方面讓他們看到養老行業的未來,讓我們這一代人不再懼怕衰老,也帶動更多的年輕人從事養老行業。”
2022年,院內嘗試設置臨終關懷師。“人到最后對死亡會有恐懼,但是更多的是淡然,如果意識還清醒,最后他們會道一聲感謝。國內的死亡教育處于探索初期,但推行死亡教育是必要的,培養和提升人們應對及處理死亡事件的能力。”經歷過幾次“送別”的李軍醫說道。
“我們希望能構建一個‘養樂園’。以后老人的老年生活更多可能是在居家狀態中完成,所以需要構建一個社區的體系,而不單是局限在養老院,把我們的理念、服務和連接的人群鋪散開,照顧到更多人。”佳林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