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文化轉型中的書法教育
□ 黃 凰
近代書法教育以一種微妙的方式參與著中國文化現代化的轉型,并發揮了其特有的價值功能與歷史影響。
“書法教育”,狹義者理解為普及性和高等專業的書法教學活動;而廣義者則延擴于整個書寫歷史文化的傳承與研習。本文注重從歷史、文化脈絡層面考察書法教育,研究范疇以后者為主,又在一定程度上兼括前者。也唯有如此,才能在中國文化現代化轉型中清晰見出書法教育的歷史意義。
一、“破立”并舉:近現代書法教育的挑戰與變革
古代書法教育,早先通過“以書為教”的方式,將書法教育和識字教育緊密結合在一起。“書契之興,人文肇始。古六藝之教,書與禮樂同科。”從“六藝”中“書”的概念提出,書法教育,從殷商甲骨文刻劃的師徒傳授已開始承擔它的重要角色。至秦代,施行“以吏為師”,官方設立“學室”,培養刀筆吏,而學吏的第一要務便是學書,即學寫字。漢初,學童自小接受識字和書寫教育,17歲以上方可參加選拔官員的考試。“學童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①。在漢代,低級的文吏如果“能書”,將是其升遷的重要因素。因為上級將“能書”作為考察、提拔的一項重要條件。而漢代“鴻都門學”的設立,則對社會各方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就教育而言,不少論著都認為鴻都門學是我國最早的文學藝術大學。首先,鴻都門學改變了人才選拔制度,其以詔引善文賦及工書鳥篆者的方式,打破了漢代舉薦、考核的傳統入仕途徑,尤其是將文藝才能替代了行義與經學這兩個漢代選士的基本依據,為文學藝術的人才發展提供了空間。其次,漢末以前,書法的功能更多是服務于實用,無論是秦代的刀筆吏,還是漢代的“書寫之官”,其職能都是為官方的文字整理、抄錄服務。而鴻都門學“詔引工書鳥篆者至千人”,并設“工書鳥篆者相課試”,擇優錄之,開啟了對應試者書寫能力的考核,這一舉措,對之后官方書法教育起到了先導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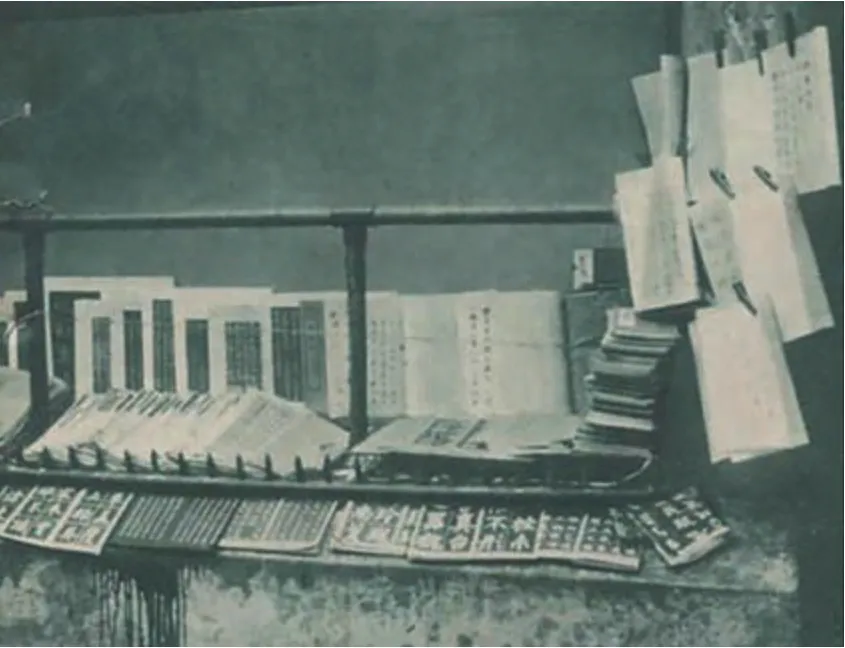
上海街頭各種臨寫字帖

1979年,全國首次書法專業研究生在浙江美術學院招生,閱卷者從左始:陸維釗、沙孟海、諸樂三、劉江。

李瑞清 齊心尚論五言聯 紙本
隋代始行科舉,一方面也催生了書學進入官方教育殿堂。從教師、學生到管理機構等制度隋代已初步建立。而唐循隋制,在繼承隋代書學與書學博士的基礎上,更于國子監設立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六學,將書學列于算學之前。唐代的書法教育在不同的教育場所,有不同的教育性質體現,而這主要都基于教育制度深刻的等級觀念。在國子監這樣的國家正式教育制度中,書學的定位依然是它的實用,以培養書手或從事校勘的文吏,而真正具備書法藝術教育性質的是弘文館、崇文館這類貴族官僚學校的要求。據《唐六典》門下省弘文館學生條注云:“貞觀元年,救見任京官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子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聽于館內學書,其法書內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館,敕虞世南、歐陽詢教示楷法。”②諸生入學館后,由名重一時的書法大家虞世南、歐陽詢二人教示書法,并要求“楷書字體,皆得正樣”③。而這一要求,代表著唐代書法藝術教育的基本走向,即以“楷書正樣”為上。此外,在唐代“以書選官”的制度下,無論是吏部銓選試“書”或唐代科舉考試常科之一的明書科,都強調出對書法的考察,如宋人洪邁所言:“既以書為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④從隋、唐以后的“書學博士”“弘文館”及至清代的科舉制度八股中的“以試帖楷法試士”的考試制度,書法教育,始終以其重要的角色,參與著中國文化延續的進程,承擔著“啟蒙”“教化”等教育重任。
“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⑤而中國傳統教育的變革和新式教育的推進就是在這樣一個新舊文化持續摩擦與碰撞中進行的。這一時期,“中體西用”理論的倡導以及清末學制與教學內容的不斷改革,預示出傳統與現代同步、東方與西方兼容的特殊信號。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書法教育,也經歷著從工具到文字載體變革的巨大挑戰。
當鋼筆因其書寫的便利被引進中國,毛筆書寫的繁瑣與因循守舊,勢必從日常實用中退居后位。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場物質的改變,實際上卻反映了20世紀初文化轉型背景下尊古與崇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變革與爭論。而作為書法載體的文字媒介,所面臨的挑戰在于“漢字革命”使整個古文系統被白話文系統所取代,顛覆了傳統書法教育中的書寫內容與書寫方式,書法藝術所依賴的古典文化結構被掃蕩殆盡。“書法這樣一種以文字為載體,又高度抽象、高度秩序化的藝術,它受思想文化的制約比其他任何藝術種類都來得直接而強烈。”⑥從某一方面而言,中國書法藝術全面體現了這個民族千百年來積淀的思維模式和審美準則。然而,此時書法所依賴的文化模式在逐漸消散,它趨于被動地等待著外界對它的改造。
如果我們將晚清廢除科舉制度看作是一種“破”,破除的是封建思想的禁錮和統治者的集權。那么近現代新學的興起則是一種“立”,將科學與民主立為旗幟,提倡國家精神和個體的解放。這正是近現代書法教育在實現現代化轉型中的重要前提與發展特點。
在這新舊交替、破立并舉的變革中,書法教育的傳播場域發生了轉變。首先,以新式學校為主要形式的現代教育體系應運而起,舊有的“私塾”“書院”大部分向新式學校轉型。其次,是傳習方式的改變。書法教育在20世紀初的新興學堂教育中,從傳統方式的師徒授受轉向了課堂教育。以新觀念下的群體性教學代替了低效率的個別性臨摹指導,從隨意性的無序點撥轉向了程序性的科學教學。再次,教育內容和書寫文本從傳統儒家經典轉向新知識文本,各級學校的考試,已甫脫八股之厄,免受小楷之困,釋放出學習傳播新知識、響應時代精神與服務社會轉型的一個信號。
此外,近現代書法教育的轉型并未僅僅局限在書寫層面,更體現于文化思想領域,與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緊密同步。傳統社會秩序的崩潰,使得由它所支撐的規范、觀念,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傳統封建教育的各個層面統統失去了依托,書法教育的目的也發生了徹底改變,人才教育由服務皇權轉向了服務社會,呈現出中國教育早期現代化的基本內涵,追求民主、崇尚科學、強調實用等特質。而這些都是書法教育在新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批判揚棄中逐步實現現代化轉型的基本表現。
二、從“普及化”到“學術化”:近現代書法教育的研究趨勢
近現代文化轉型的環境為書法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片活躍、勃發的土壤:首先,社會的動蕩,無形中提供了民間力量介入與發揮作用的空間,為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多樣性探索提供了可能。其次,西學涌入,時人在尋找中國教育革新出路的過程中,吸收了各形各色的西方教育理論與學說。通過其他學科門類的著作,書法教育吸收了新穎的理論研究范本,提高了書法理論研究的素養。再次,印刷的普及為書法教育活動的現代化提供了極大的支持。出版事業的蓬勃發展、訊息交流的開闊與發達,推動著書法教育作出了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
在期刊方面大致分為三類:《教育雜志》《初等教育研究》等屬于第一類綜合刊物;《江蘇教育》《京師教育報》等屬于第二類地方教育刊物;而《書學》《草書月刊》等書學專業研究刊物可歸為第三類。這些教育文章的主題和內容,有的從理論、實踐共同出發,闡述書法教育的合理性與重要性;有的對書法教育的弊病提出批判,就教學方法、教學計劃等具體問題給出相應的改進策略;再有者以一線的書法教學工作者為主,力述其親歷親授之經驗,豐富了書法教育的原始素材與資料。
在教材方面,近現代書法教育以書法基礎技法和基礎知識作為主要的教材內容,如俞粲《實用習字教授法》,何維樸、張萌椿《中華初等小學習字帖》等,都是當時經教育部審定的書法實用教材。與此同時,在學校書法教材外還涌現出一批普及性的書法知識讀本,起到了彌補學校教材不足之作用。這類普及性書法知識讀本以“圖文混編”的形式,介紹執筆、結構、章法等書法基礎知識,并提供范字運動圖案的演示與講解,對于初學者起到了有利的指導作用。
此外,書法教育研究在此時體現出一種從“普及化”到“學術化”發展的趨勢。在西學的影響下,學術界確立了四種新的學術范式,分別是新的話語模式、新的思維模式、新的學術精神和學術方法⑦。
首先,新的話語模式體現在書法理論中,表現為白話文應用的普遍性。其特點是將晦澀、高深的傳統書學理論轉化為平白、易懂的口語化表述。話語模式的轉變在很大程度推動了書法理論的普及發展。
其次,確立了兩種思維模式:一為科學模式。“教育科學化”提供了書法理論新的思維模式,如陳公哲《科學書法》、李頌堯《書法的科學解釋》等文章,僅從文章題目就反映出時代背景下作者對“科學”方法的重視與應用,其為書學研究提供了新穎的研究立場。二為哲學思維。受西方美學思想與藝術思想的影響,在梁啟超、鄧以蟄、朱光潛等人的開創下,產生了一條將古典書法與現代西方美學融合的新道路,即書法美學。與傳統的書法研究相比,突出書法研究的思辨性成為了書法美學興起的重要標志。
再次,確立了新的學術精神,即敢于懷疑和嚴謹實證的精神。而懷疑精神開辟了新的書法研究課題,如沙孟海在《隸草書的淵源及其變化》一文中,推翻了字體直線變化的舊論,力述各書體之間復雜的演變過程,并重點對隸書的產生與發展重新作出了判斷、研究。
最后,確立了新的學術方法,即由上述新的思維和精神而來的科學之法與實驗之法。在書法理論中,受西方“科學”洗禮的現象較為突出,不斷探索一條“科學”的書法研究之路,是這個時期書法理論家的普遍共識。而在西方“科學”的感召下,最接近“科學”的研究方法非“實驗”莫屬。留美學生回國與西方教育家來華無形中將西方的科學實驗理論介紹到國內,推動了書法研究領域對于“實驗”的思考。以書法教學為例,研究者開始把從前刻板的臨摹練習過程,重新定義為一種“筋肉的運動”⑧,嘗試從生理和心理等多種角度,探索更適宜的教學方法。而俞子夷在《關于書法科學習心理》中則明確表示實驗法勝于舉例法與觀察法,對于書法學習心理的問題,必須“各有一個根據實驗的解答”⑨。在當時這類關于“書法心理”研究的文章數量并不少,足見對“實驗”之法的推崇。
總體而言,在四種新的學術范式影響下,書法研究展示出從“普及化”到“學術化”的維度變化。其一方面體現了書法教育研究的活力與豐茂,而另一方面,也對“書法學”學科的開辟作出了嘗試和積累。
三、“實用”與“審美”:近現代書法教育的兩個主要成果
近現代書法教育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在文化啟蒙與普及中發揮了積極的社會實用功能,此在中小學教育及社會書法教育領域尤為明顯。從先后改訂的幾次教育宗旨中,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到,實用主義在教育制度中的重要體現。1913年黃炎培在《學校采用實用主義之商榷》一文中探討彼時教育之不當,主張當以實用主義補救。此后,在《實用主義小學教育法》中,黃氏繼續提出了實用主義之書法觀,其言:“書法與實用最有關系,故教授之目的,當全注于此,即小學校教則所謂遇書寫文字務使端正不宜潦草是也。”⑩端正的目的是便于識別,服務于實用。強調書法教育的社會實用功能,其目的即是為了滿足社會工作的職業書寫需求。因此,培養學生學以致用、為社會服務的書寫技能是當時教育宗旨的具體體現。
在新的教育背景下,書法作為中小學的一項附屬教育而展開,主要以“教科書+字帖”的形式出現,一方面,配合教學中“讀”“寫”“作”的訓練進行;另一方面,則是將書法教材分解為不同程度與階段的訓練,以提高學生技能的修養。書法進入中小學校教育后,為了配合學校的實用教學,書法教育者對書法教材進行了多次的修改與調整,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實用為上的書法教育觀念,并出版了多部利于實用的教材與字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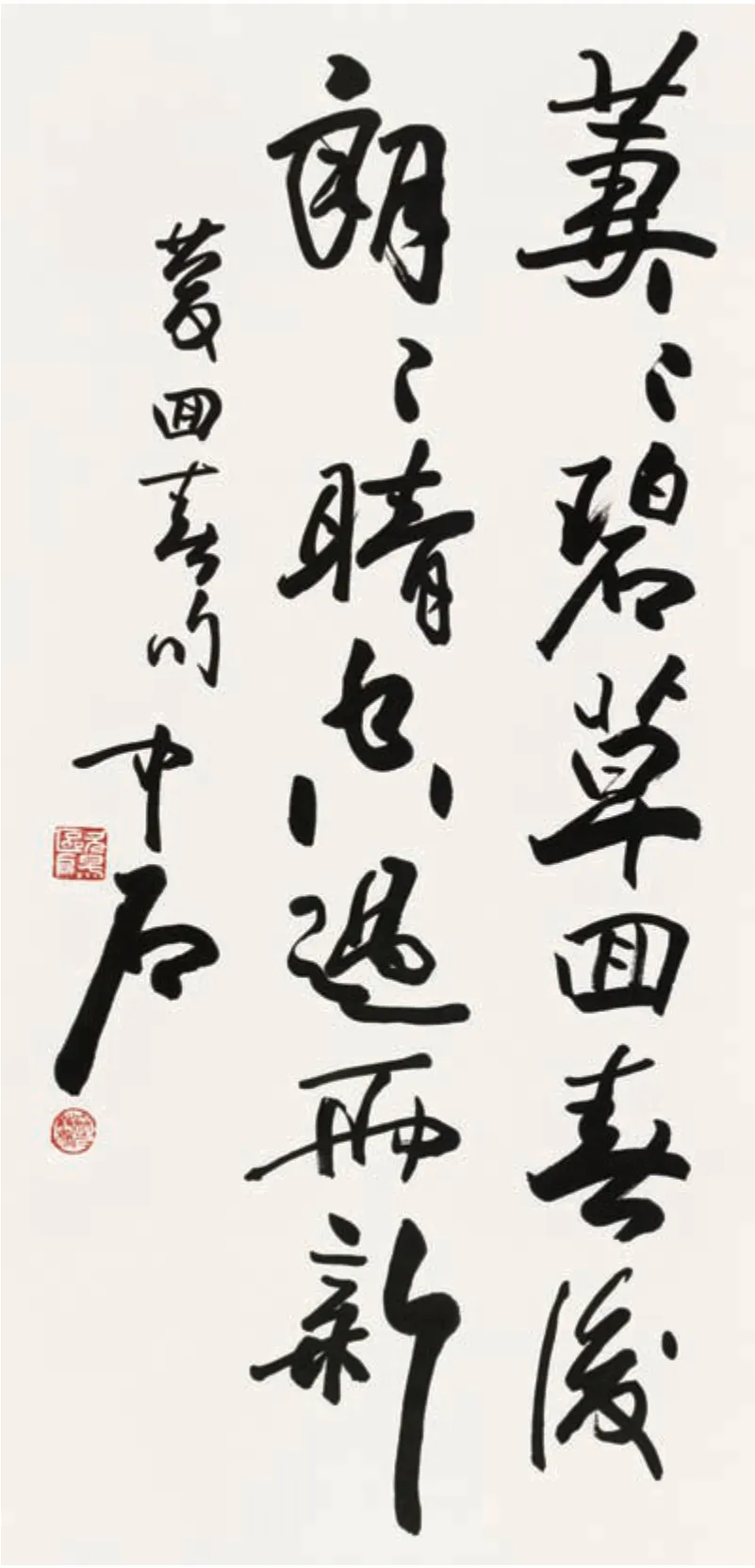
歐陽中石 慶回春句 紙本 2009年
強調實用,也體現在社會書法教育領域。半日學校、平民學校和民眾學校等形式”,在文化啟蒙中發揮了積極的社會功能。一方面,針對國內平民的實際情況,在“千字課”的基礎上編纂了《平民千字課習字帖》,選字根據民眾日常讀寫應用,選定1312常用字來編寫教材。在書寫要求方面,以正確、整齊與敏捷為主,而達實用之目的。另一方面,為教育宏效起見,一些中小學兼辦民眾學校教育,并鼓勵高年級學生擔任知識傳播的重要責任,實行即知即傳人,推行文化普及的快速傳播。
此外,流行于社會中的自發性“習字運動”,一方面,從書法教育的平民化和大眾化趨勢,反映了民主思潮在教育領域中的體現;另一方面,書法教育的工具化和實用化轉變,進一步體現了書法教育擺脫精英與民眾二元分離的舊有模式,呈現出服務社會的重要特征。

沙孟海 二十四詩品·豪放 紙本 南京博物院藏
書法教育的另一重要成果,則是對美育的倡導與推動。“美育在世界教育史上是一位后進,在中國新教育史上更是后進。光緒二十九年的新教育制度,對日本學校的種種方法皆有學習,而獨不及美育。”直至1912年,蔡元培首倡美育并將其納入教育方針之中,確立了美育在教育中的地位。而基于中國傳統書法與繪畫“書畫同源”的關系,當時的書法教育更多地是以美術教育分支的形式在藝術學校中悄然生長。
以美的教育而言,美術專科為特殊的“獨立設施”的一種教育目標,而蒙童、中小學的美育則是普通教育中的一種。在特殊設施上,以1906年李瑞清于“兩江師范學堂”正式設立“圖畫手工科”始,書法教育首次在高等教育中出現。自此之后,各地美術學校相繼成立,一時間形成了辦學高潮。
從課程設置上,以上海美專為例,其校“中國畫系”開設的12門課程中,與書法教育相關的就有5門,分別是美術史、金石學、篆刻、題跋、書法。從課程設置的功能上看,主要是為中國畫的教學與研究服務,但從另一側面也體現出在西學時風沖擊下,當時的藝術學校在對待中國本土藝術上的覺醒和重視。而這些播種發芽,從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現代高等書法教育的基礎。
沿著實用書寫教育和美術教育兩條路線,書法教育走進了中國文化現代化轉型的歷史進程并發揮了時代使命。從早期教育現代化所取得的成績來看,是可觀且來之不易的。
1963年,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書法專業成立。為了此次書法專業的成功開設,潘天壽、陸維釗、沙孟海、諸樂三等先生在招生方案、教學大綱、課程設置、授課內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國高等書法教育本科體制的序幕于此拉開。1979年,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首次開展書法研究生教育,南京師范學院、西南師范大學等也陸續開始招收書法專業研究生。1993年,首都師范大學設立了書法博士點。至此,中國高等書法教育形成了本、碩、博的學科教育框架,“開啟了中國高等書法教育學科化、系統化、專業化的體制。”
注釋:
①華人德《中國書法史·兩漢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8頁。
②《唐六典》卷8《門下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第225頁。
③《唐會要》卷61《崇文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17頁。
④洪邁《容齋隨筆》卷10《唐書判》,中華書局,2005年,第129頁。
⑤汪叔潛《新舊問題》,《新青年》1915年,第31-34頁。
⑥陳振濂《中國現代書法史》,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8頁。
⑦薛其林《西學東漸與現代學術范式的確立》,《湖南社會科學》,2001年,第14-17頁。
⑧杜佐周《書法的心理》,《教育雜志》第21卷,1929年,第37-47頁。
⑨俞子夷《關于書法科學習心理》,《教育雜志》第18卷,1926年,第1-9頁。
⑩黃炎培《實用主義小學教育法》,《教育研究》上海1913,1914(臨時增刊),第63-6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