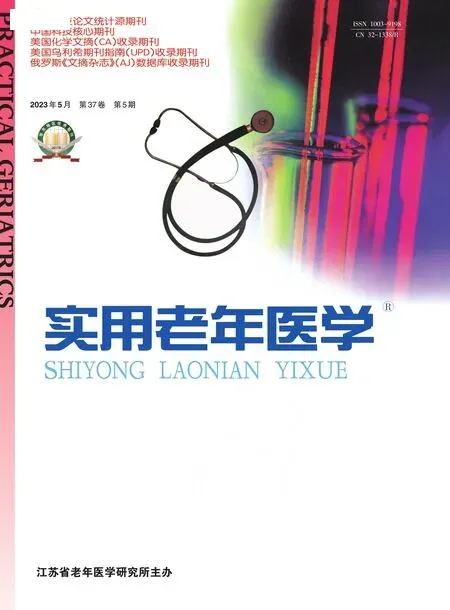預后營養指數對老年女性OVCF病人PVA術后再發椎體骨折的影響
徐鳳周 高開茜 孫亮亮 高學峰 張雄 劉永強 周建偉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骨質疏松性椎體壓縮骨折(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OVCF) 發病率不斷增加,OVCF以持續性腰背痛、脊柱畸形及壓迫癥狀等為表現,影響老年人的生活質量[1]。椎體強化術( percutaneous vertebral augmentation,PVA)是目前治療OVCF的主要方法,具有微創、有效的特點[2]。報道顯示,PVA術后椎體再發骨折發生率為8%~52%[3-4],且高發于老年女性。研究表明,改善營養能改善老年人日常活動并預防跌倒,從而減少OVCF的發生[5]。預后 營 養 指 數( 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PNI)反映了機體的營養狀態,其對髖關節骨折及椎體骨折等骨質疏松性疾病的預后有影響[6-7]。近期也有研究證明,PNI影響老年OVCF術后的近期預后[8]。本研究旨在探討PNI與PVA術后再發椎體骨折的關系,以期為再發骨折的防治提供更多的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納入我院2019年1月至2022年3月因OVCF行PVA術的女性病人共248例,調查截止時間為2022-05-31。根據調查期間是否發生二次骨折分為再骨折組和對照組。納入標準:(1)女性,年齡≥65歲,首次住院手術病人;(2)生活自理者;(3)胸腰段單節段椎體壓縮性骨折,胸腰椎損傷分類及損傷程度評分(Thoraco-Lumbar Injury Classification and Severity score,TLICS)為壓縮骨折、無神經功能損傷、伴或不伴后方復合體損傷;(4)骨水泥彌散好[9]:正側位X線片骨水泥彌散均超過了椎體中線。排除標準:(1)伴有較重的心腦血管、內分泌、免疫系統疾病,曾行手術且因疾病本身或術后長時間臥床可能對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產生影響的病人;(2)腫瘤病人;(3)脊柱后凸大于60°或Cobb角大于25°的脊柱畸形病人;(4)手術過程不順利、術后VAS評分≥4分者;(5)有骨折病史者。
1.2 方法 通過醫院信息系統(HIS)確定納入病人,然后應用醫院隨訪系統調查病人目前健康情況、服用藥物、復診及外院就診等情況。HIS系統調閱病例資料,包括性別、年齡、BMI、入院血常規、血生化指標及BMD、手術情況、術后影像、手術節段、運動情況、民族、曬太陽情況及病人復查情況等。 因死亡、聯系困難及記憶不清等原因排除43例,共納入205例病人。本研究經石家莊市人民醫院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批準(2021-148)。再次骨折時間定義為PVA術后再次發生椎體骨折距離第1次手術的時間。PNI = 血清白蛋白(albumin,ALB)(g/L) + 5×外周血淋巴細胞計數(lymphocyte,LYMPH)×(109/L),以X-tile計算最佳截斷值=44.76,取整數以45為界分類。(術后)椎體高度恢復率(%)=椎體前緣高度×2/上、下鄰近兩椎體前緣高度之和。堅持運動是指每周參加室外運動≥3 d,且每天≥30 min;堅持曬太陽是指在7 d有太陽的日子中曬太陽能達到3 d,且每天>30 min;手術方式包括經皮椎體成形術(PVP)與經皮椎體后凸成形術(PKP)。
1.3 質量控制 調查人員均培訓合格,口徑一致,由2名高年資醫生及2名護士組成。

2 結果
2.1 2組人口學特征 入組205例病人,年齡65~85歲,平均(72.6±5.9)歲,調查時間為PVA術后2~40個月,發生椎體再骨折42例,發生時間為術后2~24個月,發生率為20.5%;再骨折組抗OP藥物治療比例、運動比例、BMD及PNI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1。

表1 2組病人一般資料比較
2.2 多因素Cox回歸分析 以術后再發骨折為因變量(再發骨折=1),納入單因素分析P<0.2的因素進行Cox回歸分析,結果顯示PNI、BMD、年齡、是否服用抗OP藥物是PVA術后再發椎體骨折的獨立影響因素;與低PNI病人相比,高PNI病人PVA術后再骨折風險更低;PNI與是否服用抗OP藥物存在交互作用,高PNI人群服用抗OP藥物對預防PVA術后椎體再骨折的預防作用更好,HR(95%CI)為0.144(0.059~0.351),Pinteraction<0.05。見表2。

表2 老年女性PVA術后再發椎體骨折影響的多因素Cox回歸分析
2.3 PNI的預測價值 根據各個獨立影響因素的聯合概率繪制ROC曲線,相較于年齡+抗OP藥物+BMD,年齡+抗OP藥物+BMD+PNI的ROC曲線面積增加了0.065(0.003~0.127),即PNI對老年女性OVCF病人PVA術后再發椎體骨折有良好的預測價值。見圖1。

注:通過Logistic回歸計算各個因素的聯合概率,利用概率繪制ROC曲線計算AUC。年齡+抗OP藥物+BMD+PNI的AUC為0.923(0.877~0.955);年齡+抗OP藥物+BMD的AUC為0.858(0.802~0.903),△AUC為0.065(0.003~0.127);Z=2.043, P=0.041圖1 PNI對老年女性PVA術后再發椎體骨折的預測價值
3 討論
OVCF是骨質疏松的主要并發癥之一, 臨床常采用PVP及PKP等手術治療方法。但在手術后很多病人仍會出現椎體的再骨折,本研究椎體再骨折率為20.5%,低于Takahashi等[10]報道的26.3%,考慮原因可能為OVCF發病隱匿,導致部分病人未能發現。
對于PVA術后椎體再骨折的危險因素,各報道并不一致,其中BMD及年齡因素已被公認。但是,單純用BMD及年齡來評價再骨折的風險,其臨床意義有限[11]。本研究結果表明,除了年齡、BMD外,PNI也是影響PVA術后發生椎體再骨折的獨立影響因素。ALB與LYMPH均能反映機體的營養狀態,除ALB外,LYMPH<1.5×109/mL也被定義為營養不良。PNI是一個營養狀態指標,能客觀反映病人的免疫水平及營養狀態[12]。本研究證實:調整其他因素后,高PNI是PVA術后椎體再骨折的獨立保護因素。低PNI反映了低蛋白血癥,是PNI影響疾病預后的潛在機制[13]。有研究表明,低蛋白血癥與骨質疏松嚴重程度密切相關[14-15]。低蛋白可以通過核因子κB等通路打破成骨和破骨的平衡,使骨保護素(OPG) 表達減少,加重骨質疏松,甚至骨折[16-17]。Afshinnia等[16]也證實,低蛋白人群中股骨頸、股骨、腰椎骨質疏松發生率提高了4.59~12.46倍。
LYMPH與病人機體免疫力有關,主要反映免疫應答功能及炎癥狀態。B細胞減少導致 OPG生成減少,通過RANK通路促進了血清骨鈣素(osteo-calcium,OC)的分化,從而加劇骨質流失,導致骨質疏松的發生與加重[18],更易出現再發骨折。白細胞和中性粒細胞增多,提示有炎癥可能。研究表明,骨質疏松病人有更高的白細胞和CRP水平、更低的LYMPH[19]。高炎癥狀態導致機體ALB水平下降,而ALB在機體內也是介導炎癥反應的重要角色,參與反應性及適應性免疫應答,不僅參與了對炎癥因子的運輸,而且參與了慢性或急性炎癥的發生發展[20]。不僅如此,低蛋白還降低了對血小板聚集功能的抑制,而炎癥因子加速破壞血管內皮細胞的功能,他們共同作用影響了骨骼內血供,最終導致骨質疏松骨折的發生。此外,營養狀況還能反映營養吸收能力和機體微循環狀況,營養不良伴有更多的肌肉質量下降、握力減退,導致日常生活活動功能減退,出現運動減少相關的骨質疏松。
規律服用抗OP藥物能有效地減少 PVA術后椎體再骨折[21-22],其主要機制是增加BMD,從而減少PVA術后椎體再骨折的發生。然而本研究結果顯示,PNI同是否服用OP藥物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即在高、低PNI人群中,抗OP藥物對椎體再骨折的預防療效是不同的;在高PNI人群中,抗OP藥物的效應值更高,對脊柱再骨折的預防作用更好,相反,對低PNI人群療效欠佳。另外,61.9%的再骨折發生于術后1年內,說明抗OP治療-骨代謝指標改變-BMD變化-骨強度增加是一個漫長的過程[23],這更說明了營養因素的重要作用。這提示我們日常診療過程中強調PVA術后服用抗OP治療藥物的同時,應關注營養狀態,以提高抗OP藥物的療效,降低再骨折的發生率。
除此之外,ROC曲線證實在各種獨立因素中,相對于無PNI因素模型,增加PNI因素后,AUC增加了0.065,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說明PNI對老年女性OVCF病人PVA術后再骨折有良好的預測價值,同時也從側面確認了PNI是PVA術后再骨折的重要影響因素。
由于樣本數量有限,本研究也有不足,無法納入更多的因素來調整對PNI的影響;且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混雜因素較多,尚需前瞻性研究糾正;另外,營養因素與椎體再骨折關系的文獻較少,尚需進一步論證。
綜上所述,PNI不僅是老年女性OVCF病人PVA術后再發椎體骨折的影響因素,而且對PVA術后椎體再骨折有預測價值,高PNI還能通過提高抗OP藥物的療效進一步降低再發骨折發生率。因此,臨床上行PVA的病人除重視 BMD、規范服用抗OP藥物外,還應關注病人的PNI,了解病人營養狀況,以降低PVA術后椎體再骨折的發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