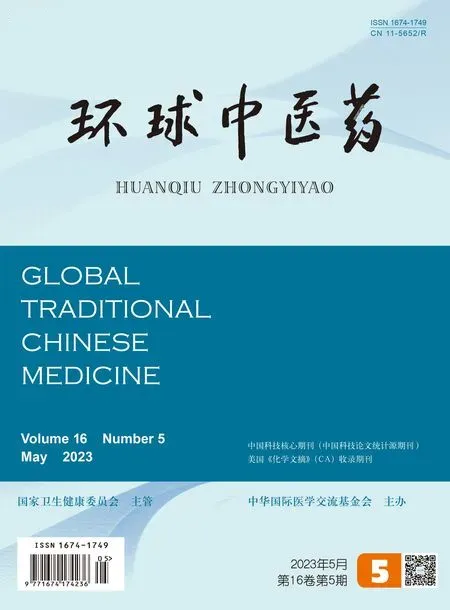中西醫(yī)結合治療慢性腎衰竭合并冷凝集素病一例
申子龍 張正媚 鄭桂敏 趙文景
冷凝集素病(cold agglutinin disease,CAD)是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貧血(autoimmune hemolytic anemia,AIHA)的一種類型,又稱之為冷抗體型AIHA,在寒冷環(huán)境下可引起紅細胞凝集和溶血性貧血[1]。流行病學顯示原發(fā)性CAD是一種罕見疾病,發(fā)病率約為百萬分之1~1.8,患病率約為百萬分之13~16,繼發(fā)性患者多與淋巴增殖性疾病、病毒感染性疾病及結締組織病有關。CAD發(fā)病率明顯低于溫抗體型AIHA,占所有AIHA的20%~25%,高峰發(fā)病年齡為70歲左右,女性多于男性[2-3]。茲介紹中西醫(yī)結合治療CAD驗案1例。
1 病案摘要
患者,女,66歲,主因“雙下肢水腫伴肌酐升高2年,加重2月”入院。2020年7月1入院。患者2018年因咳嗽、咳痰,喘憋,雙下肢水腫,就診于北京某三甲醫(yī)院,查生化:尿素氮:7.59 mmol/L,尿酸522.4 μmol/L,血肌酐257.9 μmol/L,白蛋白:24.1 g/L,尿常規(guī):尿蛋白(3+),診斷為“慢性腎衰竭,肺部感染”,予利尿消腫,抗感染等治療后,水腫好轉出院。2019年1月就診于北京某三甲醫(yī)院查抗PLA2R抗體131 RU/mL,診斷為“抗PLA2R抗體相關膜性腎病”。2020年5月因受寒后高熱,體溫39℃,咳嗽喘憋,就診于某醫(yī)院,自訴查血肌酐400 μmol/L,診斷為“肺部感染”,予頭孢類抗生素抗感染治療后,癥狀改善,具體藥物不詳,2020年5月9日查腎功系列:尿素氮 17.58 mmol/L,血肌酐 422.9 μmol/L,24小時尿蛋白定量:24小時UTP 21000.0 mg/24小時,尿量2100.0 mL。入院2周前受寒后再次發(fā)熱,體溫38.5℃,自服退燒藥及頭孢類抗生素后癥狀好轉,為進一步診治,收入我科。入院癥見:雙下肢水腫,腰酸乏力,活動后胸悶喘憋,偶有干咳,少量白粘痰,夜間可平臥,納差,入睡困難,大便每日一行,小便量約1700.0~1800.0 mL,小便多泡沫,偶有頭暈、頭痛,查體:雷諾氏征陽性,雙下肢中度可凹性水腫。既往高血壓病史20余年,冠心病病史5年,高脂血癥病史3年,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病史3年,支氣管擴張病史1年,反流性食管炎病史1年。入院診斷:中醫(yī)診斷:腎衰病,脾腎兩虛,水濕內(nèi)停證;西醫(yī)診斷:慢性腎衰竭合并心力衰竭,腎性貧血,代謝性酸中毒,高磷血癥,心功能III級(NYHA分級),腎病綜合征,抗PLA2R抗體相關膜性腎病,冠心病,細菌性肺炎,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支氣管擴張,高血壓3級(很高危),高脂血癥,反流性食管炎。輔助檢查:尿常規(guī):GLU(4+),PRO(3+),WBC 8~15/HP,RBC 2~4/HP。24小時尿蛋白定量:24小時UTP 15000.0 mg/24小時,1500.0 mL。腎動態(tài)顯像:雙腎血流灌注差。雙腎近無功能。eGFR 11.28 mL/分鐘,PTH(1~84) 123.30 pg/mL。超聲心動:主動脈瓣退行性改變,左心室舒張功能減低,少量心包積液,EF64%。入院后西醫(yī)方面予凱倫粉針靜點抗感染,慢性腎臟病病一體化治療。中醫(yī)方面予健脾益腎,利水消腫方藥治療。7月9日復查胸CT:與2020年6月30日檢查結果比較:兩肺支氣管擴張合并感染,較前改善。
7月10日晚患者感受風寒,7月11日18:00開始發(fā)熱,體溫最高至39.1℃,伴寒戰(zhàn),汗出,頭暈,咳嗽、咳痰,茶色尿,化驗室回報冷凝集試驗陽性,輔助檢查:急查系列:尿素氮21.35 mmol/L,肌酐518.6 μmol/L,白蛋白28.4 g/L。血液方面:全血細胞分析:白細胞12.88×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80.0%,紅細胞1.13×1012/L,血紅蛋白37 g/L,血小板273×109/L。血凝:凝血酶原時間13.5秒,凝血酶原活動度76.0%,纖維蛋白測定量5.19 g/L,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時間37.1秒,凝血酶原凝固時間18.4秒,D-二聚體2.33 mg/L,纖維蛋白原降解物15.1 mg/L。血乳酸脫氫酶1483 U/L,直接膽紅素19.6 μmol/L,總膽紅素30.9 μmol/L均明顯升高,便OB陰性。骨穿:未見明顯異常,心臟方面:快速心肌功能檢測:N末端腦鈉素原1419 ng/L。免疫方面:直接抗人球蛋白試驗陽性。抗核抗體系列、血管炎抗體陰性。感染方面:檢出酵母樣真菌及菌絲;便:檢出酵母樣真菌。降鈣素原18.42 ng/mL,C反應蛋白84.9 mg/L。腫瘤方面:細胞角蛋白19片段6.69 ng/mL,神經(jīng)元特異烯化酶24.44 ng/mL。其他:球桿比:球菌90%,桿菌10%。患者血紅蛋白較入院明顯下降,膽紅素、乳酸脫氫酶明顯升高,直接抗人球蛋白試驗陽性,紅細胞冷凝集如圖1,血象及C反應蛋白、降鈣素原明顯升高,痰找真菌、便找真菌陽性,考慮CAD,不除外繼發(fā)感染,肺部感染加重合并真菌感染。予加強保暖,西醫(yī)治療予美平0.5 g/天,聯(lián)合大扶康注射液0.2 g,每天一次靜點抗真菌,藥物予甲強龍40 mg每天一次靜點11天后改為醋酸潑尼松40 mg每天一次,口服抑制免疫,靜注人免疫球蛋白20 g,每天一次靜點5天調(diào)節(jié)免疫。所有靜點液體由控溫輸液泵加熱至37℃輸入。

圖1 CAD血標本,提示紅細胞冷凝集

圖2 住院期間患者血紅蛋白變化曲線

7月14日復查血常規(guī):血紅蛋白31 g/L,予輸注洗滌紅細胞2 U糾正貧血,7月16日復查血常規(guī):血紅蛋白52 g/L,予輸注洗滌紅細胞2 U糾正貧血。洗滌紅細胞均由控溫輸液泵加熱至35℃輸入。
7月17日復查血常規(guī):血紅蛋白 67 g/L,患者頭暈喘憋改善,倦怠乏力減輕,進食改善,尚有畏寒肢冷,出現(xiàn)下肢水腫及顏面水腫,舌質淡,苔白,脈沉。辨證:陽虛水停,治法溫陽利水,予真武湯加減,黑順片15 g、干姜10 g、茯苓30 g、蒼術15 g、白芍15 g、生黃芪100 g、當歸20 g、生薏米20 g、炙麻黃9 g、砂仁10 g、焦三仙30 g、車前子30 g、葶藶子30 g、阿膠珠15 g、冬瓜皮30 g、防己12 g、豬苓20 g,4劑。
7月20日復查直接抗人球蛋白試驗弱陽性。
7月21日患者雙下肢及顏面水腫較前減輕,畏寒肢冷改善,尚有脘腹痞悶,舌苔黃膩,脈沉緩,辨證:濕熱內(nèi)蘊,治法:清熱化濕,予三仁湯加減,炒薏仁20 g、白豆蔻10 g、砂仁10 g、厚樸15 g、蒼術15 g、葛根3 g、炙麻黃9 g、葶藶子3 g、冬瓜皮30 g、生黃芪60 g、車前子30 g、炒白術20 g。
7月27日復查直接抗人球蛋白試驗陰性,復查血常規(guī):血紅蛋白94 g/L,血肌酐449 μmol/L。乳酸脫氫酶、網(wǎng)織紅細胞計數(shù)恢復正常患者病情明顯改善出院門診繼續(xù)治療。
2 分析與討論
2.1西醫(yī)對冷凝集素病的認識
冷凝集素是針對紅細胞抗原的自身抗體,絕大多數(shù)冷凝集素均為免疫球蛋白IgM[4]。冷凝集素在正常體溫下與紅細胞的結合較弱,而在較低溫度下則很容易和紅細胞相結合,從而引起紅細胞凝集(圖1)。冷凝集素引起的溶血的機制主要通過補體介導,C1酯酶激活C4和C2,導致產(chǎn)生C3轉化酶,該酶將C3裂解為C3a和C3b、C3b包被的紅細胞被網(wǎng)狀內(nèi)皮系統(tǒng)中的巨噬細胞吞噬,在剩余的循環(huán)紅細胞上,IgM在變暖時解離,但C3b仍然附著,C3b裂解為C3d,可通過直接抗球蛋白測試檢測到[5]。CAD典型的臨床表現(xiàn)有手足發(fā)紺,肢體遠端、鼻尖、耳垂等處癥狀明顯,常伴肢體麻木、疼痛,遇暖后逐漸恢復正常,稱為雷諾現(xiàn)象,暴露于寒冷環(huán)境后出現(xiàn)血紅蛋白尿,伴寒戰(zhàn)、高熱、腰背痛,發(fā)作后虛弱、蒼白、黃疸,肝、脾輕度腫大,嚴重情況下可出現(xiàn)溶血危象。CAD的診斷包括:(1)溶血的證據(jù),如網(wǎng)織紅細胞計數(shù)升高,高LDH,高間接膽紅素,低觸珠蛋白;(2)直接針對C3d的直接抗球蛋白陽性試驗(或少數(shù)情況下為C3d加IgG);(3)4℃時冷凝集素滴度≥64[4]。CAD的治療需分對癥治療和對病因治療,對癥治療主要是輸注洗滌紅細胞糾正貧血;對病因治療主要是糖皮質激素和丙種球蛋白,需要注意的是輸注液體時應將靜脈溶液和血液制品加熱至適當溫度[3]。輸血需輸注洗滌紅細胞,而非懸浮紅細胞,以防加重溶血,同時需注意輸血溫度不能高于40℃。本案患者積極抗感染,激素抑制免疫,丙種球蛋白調(diào)節(jié)免疫,輸注洗滌紅細胞糾正貧血,可暫時控制病情,但激素存在感染加重、消化道出血、水鈉潴留等副作用,治療存在矛盾,需要中醫(yī)進一步治療。
2.2冷凝集素病的中醫(yī)病因病機
根據(jù)CAD臨床表現(xiàn)可將其歸屬于中醫(yī)“血證”“虛勞”“厥證”范疇,病情嚴重,若治療不及時,可致脫證[6],此處厥證有二層含義,其一,暈厥;其二,手足厥冷,在CAD中均可見到。CAD病因病機為勞倦過度,傷及脾腎,或久病及腎,脾腎陽氣虧虛,肢體失養(yǎng),故見畏寒肢冷;再加感受寒邪,寒凝血脈,氣血瘀滯,不通則痛,故見肢體疼痛;氣血失養(yǎng),故見肢體麻木;血不循經(jīng),故可見血尿;陽損及陰,陰陽離絕,可致脫證。《素問·厥論篇》云:“陽氣衰于下,則為寒厥……寒厥之為寒也,必從五指而上于膝者。”可見寒厥的主要病機為陽氣虛衰,主要表現(xiàn)為手足厥冷,甚者可及四肢。《素問·調(diào)經(jīng)論篇》云:“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是故氣之所并為血虛,血之所并為氣虛”,指出氣血喜溫而惡寒,陽氣充足,則氣血流暢無阻;若感受寒邪,則氣血為之凝滯,在這CAD中體現(xiàn)的尤為突出。《素問·生氣通天論篇》:“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wèi)外者也”,指出陽氣具有抵御外邪的作用。明·張景岳在《類經(jīng)附翼·大寶論》中云:“天之大寶,只此一丸紅日;人之大寶,只此一息真陽”,提出真陽在維持人體生命活動中具有舉重輕重的地位。此外,從微觀角度來看CAD患者受寒后血液紅細胞凝集,遇熱后凝集散開,因此中醫(yī)治療需重視溫陽散寒活血治法。
2.3溫陽活血法治療冷凝集素病
溫陽活血治法具體包括溫陽散寒、溫陽益氣、活血化瘀、溫陽利水,常用方如四逆湯、四逆加人參湯、茯苓四逆湯、當歸四逆湯、真武湯等,并隨病情發(fā)展,觀其脈證,隨證治之,如兼有脾虛者,要健脾和胃;兼有氣血虧虛者,要益氣養(yǎng)血;兼有濕熱者,要清化濕熱。本案選用四逆加人參湯加減,《傷寒論》385條:“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清·陳修園《長沙方歌括》云:“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無血也。言霍亂既利而復利,其證惡寒,其脈又微,可知陽氣之虛也。然脈如是,利雖止而非真止,知其血已亡,此亡血非脫血之謂,即下則亡陰之義也……故以四逆湯救其陽氣,又加人參生其津液。”可見四逆加人參湯有溫陽散寒,益氣生津的功效。附子為本方君藥,具有補火助陽、散寒止痛功效,可“通行十二經(jīng)絡”,當有寒邪痼結于臟腑、經(jīng)脈,均可加附子宣通溫散。附子、干姜相須為用,脾腎雙補,生黃芪、當歸、炙甘草、金銀花為芪銀三兩三[7],為周平安教授治療風濕免疫病的經(jīng)驗方,方中重用黃芪大補元氣,且生用補氣而避免其溫燥助火,《本草備要》云:“生用固表,無汗能發(fā),有汗能止,溫分肉,肥腠理,瀉陰火,解肌熱。”黃芪、當歸合用為當歸補血湯,金銀花甘寒,王士雄在《重慶堂隨筆》中談到其“清絡中風火濕熱,解溫疫穢惡濁邪。”周平安教授認為:“黃芪、當歸相配補氣生血,令陽生陰長氣旺血生,血充氣固,陰平陽秘,虛熱自退,當歸通利血脈,養(yǎng)血不留滯,活血而不致血液妄行。生甘草一方面佐黃芪益氣,另一方面金銀花與甘草合為《醫(yī)學心悟》之金銀花甘草湯,能清熱解毒,并調(diào)和諸藥,令藥力威而不猛,作用溫和持久。”山萸肉與人參相配既可以大補元氣,又可以收斂元氣、通利血脈,正如清·張錫純《醫(yī)學衷中參西錄》:“山萸肉味酸性溫。大能收斂元氣,振作精神,固澀滑脫。因得木氣最厚,收澀之中兼具條暢之性,故又通利九竅,流通血脈。”砂仁、焦三仙開胃健脾,炒白術、茯苓健脾滲濕,用少量北柴胡、升麻有補中益氣湯之意,取其升陽作用,馬鞭草活血散瘀。諸藥并用,共奏溫陽散寒,益氣健脾,活血化瘀作用。需要注意的時,活血不可選用破血通經(jīng)的藥物,如三棱、莪術以免加重患者出血。二診,患者畏寒肢冷、頭暈目眩明顯減輕,進食改善,新見下肢及顏面水腫,改用真武湯合當歸補血湯加減,溫陽利水、益氣養(yǎng)血,加用車前子、冬瓜皮、豬苓、生薏米利水消腫,炙麻黃、粉防己祛風利水,阿膠補血止血,焦三仙健脾和胃,有一分胃氣就有一分生機。三診,患者畏寒肢冷、頭暈目眩、乏力倦怠明顯減輕,進食改善,尚有胃脘痞滿,眼瞼浮腫,下肢水腫,舌苔黃膩,為濕熱壅滯三焦之象,遂改用三仁湯清熱化濕,行氣除滿,加用炙麻黃、葶藶子、冬瓜皮、車前子,意在瀉肺利水,給邪以出路。
綜上所述,CAD病情兇險,中西醫(yī)優(yōu)勢互補可提高臨床療效,基于CAD“寒凝血瘀”病機,中醫(yī)治療需重視溫陽活血法應用,并隨證加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