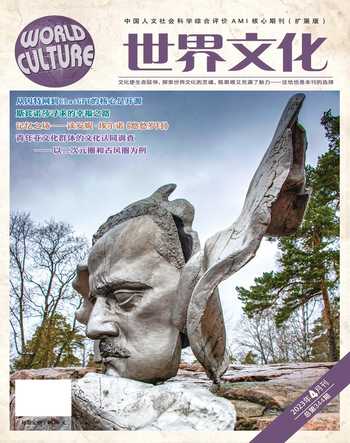從因特網到ChatGPT的核心是開源
王炎

關于ChatGPT
最近媒體炒作起ChatGPT來,有人說這個AI平臺將改變人類的未來,有的甚至聲稱將帶來毀滅,恰似前一段炒作“元宇宙”。新技術的推出,會一次次給媒體帶來新熱點。
從數字技術發展的整個歷史來看,數據規模固然非常重要,但已與機械技術時代非常不同。數據、材料、高精技術、頭腦卓越的科學精英,這些雖然仍是核心硬件,但“開源”與“共享”的互動模式,才是推進數字技術迭代更新的真正力量。向全社會開放數據與技術,讓不同階層、性別、職業和不同教育背景的用戶參與使用,讓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價值觀和專業的頭腦獻計獻策,每一次用戶訪問都是開放平臺的一次調試和升級,頭腦、數據與設備互動起來,人工智能技術才能不斷提高。從20世紀中期互聯網發明開始,新的科技邏輯便逐漸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最終塑造了21世紀的時代精神:只有開放社會,科技才能進步。
發明互聯網
近讀美國學者阿貝特所著《發明因特網》,感觸頗多。從互聯網到ChatGPT的技術邏輯,其實一以貫之的都是開源與共享。
因特網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冷戰”寒徹的美國。美國國防部擔心蘇聯先發制人,以第一輪核打擊摧毀美國的通訊網,使白宮無法下達核反擊的命令,從而輸掉一場核戰爭——情形恰似庫布里克的電影《奇愛博士》(1964),于是成立“美國高級研究計劃署”,撥巨款研發抵御核打擊的通訊技術。
美國科學家保羅·巴蘭提出一個“封包交換”的設想,即設計搭建多重中繼通訊線路,以替代從信息中心輻射各地的階梯式通訊網。他的設想是,讓每一個地方的通訊交換節點,均能自主判斷通過哪條線路傳輸信號。這樣即使中樞或某條線路被摧毀,通訊網分布在不同地方的智能節點仍能自主運行,從而保證命令的上傳下達。這個想法太超前了,顛覆了金字塔式的傳統通訊邏輯。但是要求中繼節點智能運轉,則須由電腦控制,并將模擬信號轉化成數字信號,以避免多重連接帶來的信號衰減。當年計算機體積大、運算慢、成本高,處理數字信號的能力不夠強。最終項目招標的結果是,通訊改造被老牌的AT&T電話公司奪下。AT&T仍保留從控制中樞逐級下達的舊方案,把錢花在深挖洞、加固地下核掩體、提高保護級別、優化線路材質上,而巴蘭的設想則被束之高閣。
但幾年后,英國科學家讀到巴蘭的論文,意識到這項技術可別用他途。英國人的興趣不在軍事,而在遠程用戶如何分享實驗室里的大型計算機。當時還沒有個人終端電腦,用戶要租用科學機構的大型電腦。普通用戶需用電話線連接計算機服務器,從自己的終端發來運算指令,付費讓大型計算機提供運算服務。商用電話線既昂貴又繁忙,用戶發指令時經常遇到占線或發出后阻塞、遺失的情況。同時,用戶操作時常會出現間隙,使計算機空閑下來,其運算能力發揮得不夠充分。巴蘭的封包理論這下派上用場了,可將遠程用戶的指令切割成小塊,按數字信號單位“千字節”,把一條命令分成幾個小信息包——即“封包”。這樣,由聯網的計算機終端充當智能節點,根據線路的忙閑,節點自主選擇不同線路分撥小信息包到目的地,然后再組裝起來,還原為初始信息,這就是所謂“封包交換”。它不僅解決了線路繁忙問題,還可讓多個用戶端同時操作,利用封包原理“分時”共享計算機服務器。
軍事技術服務于商用,巴蘭的初衷是想搭建多重連接的通訊網,提高抗核打擊能力,結果卻給未來的互聯網埋下種子。后來,美國國防部大力資助“阿帕網”,科學家們也秉承兼容開放的理念,讓所有民間用戶根據自己的需要,時時修改、更新界面上的傳輸程序。結果,各國的學者、工程師、通訊公司、軍事機構、民間企業,甚至大學研究生,經過幾十年的切磋、互動,群策群力,從各自的需求出發,以迥然不同的智慧與遠見,讓網絡技術步步升級,一點點搭建起因特網。后來,網絡百科和各種網絡平臺也都承繼了這種開放態度。
其實,至今也說不清到底是誰發明了因特網,因為其間沒有像牛頓、愛迪生、愛因斯坦或居里夫人式的超級英雄,能一人獨慧讓萬世受益,成為關鍵性的決定人物。我們也很難確定到底是哪一年實現的全球聯網,又是誰最先預見到互聯網有改變人類歷史的前景。許許多多的“小人物”在日常工作中不經意間與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合作,一點點勾勒出覆蓋全球的計算機網絡。這不是傳統單向度的供求關系——少數原創者發明技術供給多數使用者的金字塔模式,而是多向度的互動關系——“用戶生成”的平等模式。
中國與國外網絡的連接,也是國際合作的結果。1987年,德國電腦技術專家向中國提供西門子電腦,德國學者幫助中科院攻破了一個個硬件和軟件難關,才向世界成功發出了第一封電子郵件。之后,他們又幫中國申請“CN”域名,與世界上其他普通用戶一樣,簽署TCP/ IP“傳輸控制協議”,中國的計算機才連上全球網絡,因特網的覆蓋面也越來越廣。1989年,英國科學家蒂姆·伯納斯·李創建了“萬維網”,以超文本鏈接開拓出一片廣闊的虛擬信息空間,全球用戶可隨意瀏覽世界各地的網頁,地球變成了一個村莊。

20世紀末,人類告別了機械復制時代,電腦將世界連成一體。從事后來看,我們所謂的全球化,不僅意味著經濟與文化一體化,其更堅實的物質基礎是數字技術。我們能否據此推斷,互聯網技術衍生出了與之相應的知識與文化形態?或追問:既然在數字技術史上呈現出去中心化、多元性、多樣性、流動性、用戶主導以及數據共享的民主化趨勢,那么這是否也預示著“知識民主化”時代的到來?
重新估價“博學”的含義
“老師,您講的內容維基百科上都有。”拿手機的學生淡淡的一句,教授頓覺無地自容。失落的教授變顏正色:“論文不許引用網絡資源,網上的信息都是垃圾,沒有正經學問。”到了期末,學生照樣用搜索引擎搜學術論文的電子版,根據上面的出版信息和頁碼,注釋自己的論文,誰也看不出援引的是紙質出版物還是電子資源。的確,網絡資源良莠不齊,可是信息量極大,關鍵看你會不會搜,實際上并無網上、網下之優劣。
這是學校最普遍的現象,不勞筆墨饒舌。但問題并不在于寫論文該如何查文獻,或者爭論線上、線下哪種知識可靠;問題也不在于紙媒與電子媒體孰優孰劣,此乃器物、枝節之爭,未觸及深層的歷史性斷裂。我們或許應該問:互聯網出現后如何面對碩大無朋的電子記憶?在電子記憶時代,“學習”是否與以前的含義不同?甚至要思考:網絡知識時代,什么才算“真有學問”?
我們耳熟能詳的是文明的延續有賴于文化傳承,傳承是知識薪火相傳。一代又一代人上學、讀書、進圖書館、欣賞藝術、傳播資訊、寫作或做科學實驗,無一不需要記憶力與創造力。所以,考試不允許帶電子設備,學生要憑大腦記憶與思辨力回答試題;評估學術機構時也要考察圖書館規模,衡量精神遺產的藏量;考評高等教育與科研機構等級時,要統計學術成果發表數量,量化科學文化的貢獻。但如今,電子記憶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學術成果和文獻都已電子化,維基百科、百度百科上無所不包,大家都在網上搜索學術資源,那么我們是否仍然需要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換言之,數字時代一定要固守機械時代的評價標準嗎?
網絡新知識型
早在1935年,人文氣質十足的瓦爾特·本雅明被電影這門充斥技術“銅臭”的藝術所震驚,寫下《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一文。他追溯一場在19世紀關于繪畫與攝影藝術孰高孰低的爭論。那時人們認為攝影不算藝術,推及電影也不會有深度。但到1920年代末,電影進入有聲時代后,電影敘事日臻成熟,到1930年代便步入了黃金時代。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本雅明發現前一個世紀的爭論不得要領,攝影算不算藝術是個偽問題;真命題應該是,攝影出現后,整個藝術史不可逆轉地拐入新軌道,世界迎來了機械復制時代。而那場論爭不過表征了歷史轉折的時代焦慮而已。

受本雅明的啟發,我們或許也該重新設置一下問題:與其爭論線上、線下哪種知識更可靠,不如探討一下,互聯網出現之后,整個人類的知識結構是否隨之發生變化?接著還可以問:既然互聯網“供給”與“索取”知識的方式不同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那么傳統的知識論是否還有效?近100年前,本雅明揭示出機械復制時代的新藝術形式與新知識型,那么,經歷了數字革命后,他以媒介技術為切入點分析藝術的獨到角度,似可啟發我們尋覓知識轉型的隱幽線索。或許我們可以追問:數字技術也能像機械復制技術那樣重塑一個時代的知識論嗎?本雅明說,照相技術讓藝術的神韻消失了。那么,經歷了模擬(復制)轉數字的革命之后,文化形態又會發生怎樣的轉變?
從機械復制時代到數字網絡時代
技術與文化本屬兩種性質不同的領域,彼此如何相互影響?新媒體藝術理論家列夫·曼諾維奇所著《新媒體的語言》一書系統闡述了電腦媒介對文化的塑造過程。我們這個時代所有的文化基礎都將被電腦化,因特網成為全球化最實在、最顯著的標志。這是一場最深刻的媒介革命,從文化生產、發行到市場流通,一切均由電腦做媒介。無論是獲取或操縱文化數據,還是存儲文化素材,也不管你采用文本、圖片、視頻、音頻等何種格式,都必須先將資料轉成數據,電腦才能夠讀取,我們也才能夠使用。將文化的所有形態轉譯成二進制數字,是人類文化的未來宿命。
模擬轉數字,是這場革命最深刻的斷裂。回到本雅明的復制(或模擬)時代,電影是連續拍攝多個靜態的照片,儲存在長長的化學膠卷上,聲音存入磁性聲道。放映時,放映機用與拍攝相同的速率,連續讀取膠卷上的一個個畫面,再用強光投射到大銀幕上。肉眼被高速運轉的畫面所欺騙,誤以為銀幕上的幻象是連續運動的,這是模擬方式再現的世界。到了數字時代,數字鏡頭將對象物反射的光線投射到感光器件上,光線被轉化成電荷,再由“模數轉換器”處理成二進制數字,存儲在記憶芯片上。這是“數字化”過程。我們每天接觸的各種文本格式、圖像、視頻、音頻、網頁、通訊信號,都統統由一堆二進制數碼構成。
本雅明雖然不可能預見電影的數字宿命,但他所做的復制時代與前復制時代的藝術形式之間的比較,卻發人深省。他說繪畫以線條勾勒對象世界,是整體性地把握現實;而電影卻把綿延的時間分割成一幀幀彼此獨立的畫幅,然后剪輯拼接,演員因此失去對情節的整體把握,剪輯師將其表演支離破碎地編織到銀幕重構的世界里。而曼諾維奇則認為,復制技術正呼應了工業革命促生的生產模式:福特的第一條生產流水線(1913)便是大工業時代的經典范式——零部件標準化,生產過程被分割成一個個不斷重復的簡單勞動崗位,每一工位前后串聯起來,便形成流水線。工人無需理解全過程,只須天天重復同一工種,便速成熟練工人。流水線上的工人隨時可被替代,正像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一樣。
到了數字時代,世界進入后工業社會,數字媒體同樣也呼應了后工業的邏輯。曼諾維奇的觀點是,后工業生產的邏輯是所謂“按單定制 ”與“按進度配送”。網絡經濟以信息、傳媒為先導,網絡電商投巨資收集用戶信息和消費行為習慣,有針對性地推送廣告,精準投送產品。
從1950年代、1960年代的信息服務經濟,向1970代的后工業轉型,至1990年代的網絡經濟,文化便一直隨經濟形態的變化而一次次轉向,這不正符合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嗎?如果所有文化典籍、教育內容和傳播信息都被電腦化并上傳網絡,那么將來談文明的屬地性與語境化還能成立嗎?
曼諾維奇認為,數字媒介包含文化與技術兩個層面:文化是指百科知識、故事情節、寫作視角、模仿與宣泄、悲劇與喜劇等;技術是指電腦程序與“封包”、分類與進程、計算機語言與數據結構等。如果你使用不同的操作程序,電腦呈現數據的方式也會不同,文化也因此隨之而變。由此可見,文化不僅是抽象的精神活動,更是由“電腦本體論”“知識論”“語用學”三者共同塑造的觀念。人機融合才會實現技術與文化的實質形態,衍生出“電子文化形式”。電腦技術的演進不可避免地會影響文化史的嬗變。
應該說,曼諾維奇是從人文學理論中汲取了靈感,然后在電腦學里尋找技術論證,他稱這種方法為“數碼唯物主義”,以之考察數字時代的文化、社會與組織結構。既然證明技術與文化是一體兩面,科技塑造文化形態,而數字技術的核心要件是開源與共享,那么,知識與文化將必然走上民主化與大眾化的道路。
知識民主化
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說,機械復制技術出現之前,藝術品的價值源于原作的本真性、在場性和作者的權威性,藝術尚有“神韻”,仍對應著傳統社會的倫理、儀式、特權與專屬權。而照相術出現之后,原作與副本相去無幾,收藏藝術品的獨特空間隨巡展與市場流通而消解,儀式功能難乎為繼了,人們不再仰慕藝術而注重消費藝術。隨著藝術神韻的消失,大眾社會與政治現代主義不期而至。1930年代新聞電影里閃現馬路報童的身影,報刊也推出“讀者來信”欄目,讓販夫走卒以鉛印的白紙黑字發表感想。自此,只有少數精英作者的話語特權,被廣大普通讀者漸漸削平,機械復制重構了人們的時間觀與空間觀,此為本雅明在1930年代的觀察。
20世紀末因特網蒞臨,世界從此改變了。原來《不列顛百科全書》是百科知識的權威來源,如今學生上網查“維基百科”了。“不列顛百科”曾延請功成名就的大學者,皓首窮經,誨人不倦,給世界奉獻了權威、普遍的知識。而維基的編者隊伍里竟有送披薩的小哥,不管你有啥知識背景都可參與編寫詞條,維基編委只要求大家遵守編輯規則:即每個詞條必有援引、每句話必有出處。無論大學者還是送餐小哥,每人的編輯權重又都很有限,詞條越熱門,參與的人越多,內容就越豐富、越可靠。個體的貢獻被數量稀釋了。相反,越生僻的詞條,參與編輯的人則越少,個別編輯的傾向性便會凸顯出來,詞條內容也會相對單薄,可靠性隨之下降。這是一個什么邏輯?難道數量多寡能決定知識的含金量嗎?

中國有句老話: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但大家已不再認同這種觀點了,而說一百個臭皮匠,也仍是臭皮匠。諸葛亮是杰出人才,怎能用人數來湊呢?的確,如果所有人在同一個層面上,每個人的思考角度、問題意識、知識背景都差不多,那么臭皮匠再多也頂不上一個諸葛亮。但維基百科或百度百科并非臭皮匠的數量相加。隨著時間的推移,參與編輯百科的人數越來越多,使用范圍越來越廣,詞條不斷更新,可信任度便逐漸提高,成為今天不可或缺的知識源。臭皮匠修成了新時代的諸葛亮,原因何在?從機械時代過渡到數字知識時代,知識的目的已不再僅僅服務于生產。原來知識是第一生產力,如今知識則以創造社會主體為己任。在知識時代,每個人首先是一個知識源,這并非指其受教育程度或社會地位的高低,而是凸顯每個人經驗的獨特以及對他人的啟迪。我們在網上相遇,平凡小人物的日常瑣事一樣啟發無數人思考;即使一技一能,也可以幫他人改善境遇。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特的、神秘的、不可替代的。在這個時代,知識的個人性與經驗的獨特性,超越了以往對普遍性的追求。
如仍固守傳統的偏見,不承認所有人都有智慧,便是否認他人的存在,也是知識時代愚昧、歧視、敵意、仇恨與暴力的根源。“抖音”風靡國內外,這款青年人自娛自樂的短視頻平臺,由網民自己拍攝身邊的場景,或用視頻剪輯、特效軟件編輯各類信息上傳,讓點擊量決定哪款視頻火爆。沒有誰像制作影視戲劇那樣,為創作優秀“抖音”作品而刻意研究節目的美學與規律。“抖音”屬于無名之輩的本色創作,文藝理論對之失語,也找不到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規律,成敗靠網絡的民主機制。
網絡集體智慧
在這個全新的知識、文化民主化時代,網民直接參與知識建構,彼此互動,信息資源全球配置,個人以分子化的結構形成網絡社會。新事物變化之快、復雜性與多樣性之豐富,讓人很難把握甚至無法理解。除了學習與適應這無序、莫測的世界之外,別無它途。因此,法國學者皮埃爾·列維的《集體智慧:賽博空間里的人類新世界》一書引入“集體或共享智慧”這個概念,描述這種跨地域、跨空間、跨貿易的網絡知識空間。網絡知識空間靠運算、重技術,計算機運算將人的思維“外化”,即將人的反思力、記憶力與聯想力轉譯成“鏈接”“打開網頁”“選擇界面”,將個人思想轉化成大規模生成的公共思維,私人想法就加入了共享智慧。
根據列維的觀點,網絡百科首要是獲取技術、機構或概念工具,然后才是收集、過濾大量信息,運算后整合出可導航、可檢索的信息,以鏈接的方式呈現多樣的智慧與想象,搭建有思維縱深的信息平臺。網民以虛擬身份在平臺上彼此辨識,相互激發思考,各自貢獻思維的路徑,深挖思維的潛力,形成“集體智慧”或“大腦超鏈接”,解決傳統知識表達不出、解決不了的問題。比如,維基百科匯聚了大批背景不同的志愿者,大家匿名編撰、修訂、補充、審核、更新詞條。重要的不是收集關于事實的客觀知識,也不局限于匯集角度不同的想法,核心是要改變我們與知識的關系,聯系世界各地千差萬別的人,革新倫理、美學、技術與社會組織方式,重建全球化社會。這與利用網絡技術操縱獵巫(如“人肉搜索”)和網暴南轅北轍。
2012年3月,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宣布停印已有244年歷史的紙版《不列顛百科全書》,從此發行電子版,從線下走到線上。看似一條紙媒轉電媒的消息,含義卻遠比這層深遠得多,這標志著一個時代知識型的結束。網絡百科不再沿襲紙質百科的文本與圖片形式,而集文本、圖像、視頻、音頻等格式為一體,配以人機互動擬像、互動地圖、虛擬現實等跨媒介多模態,覆蓋幾乎所有的符號系統。網絡用戶的人機互動,替代了精英教育的知識單向街,學習未必要找已特權化的教育機構,而上網共享普遍分配的知識。列維相信,專家智慧凝結的百科全書終結之時,也是大眾智慧薈萃的網絡知識空間出現之日;高度復雜的“網絡智能”,將人性投射到無垠的賽博空間里,開源人工智能開發的 ChatGPT,也是沿因特網的技術邏輯向前推進,使得人類的思想探索具有了空前的潛力與變數。
開放是通向未來之路
列維認為,“網絡新人文”打通了個人與群體兩類不同知識的分野,超越了笛卡爾的“我思”——即以個體為中心的認知模式,而進入“我們思”的多元認知時代。
今人之明智在于自知局限與渺小,學會與他人合作共贏,與不曾謀面的陌生人共享知識、共創智慧,以期有所建樹。在民主的賽博空間里開源與互動,將匯集起來的智慧無差別地播散到虛擬世界的每個角落。人人付出,個個收獲,知識棲居在人性之中。
其實,這幾十年來科技上的突破,很少是一人或幾人完成,科學家大多是將研究思路先發表在期刊或開源網站上,新想法可能啟發世界另一角落正思考相關問題的人;這個人又把讀到的數據與自己的研究結合,做出成果后再公開發表,如此又啟發下一個人——如多米諾骨牌,一項技術從最初設想到完善應用,一般有無數科學家的參與。所以,OpenAI(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公司)注重邀請世界上所有用戶使用ChatGPT平臺,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更新和建設,人工智能走到多遠,要靠大量的用戶使用和參與。
開源與共享在概念上不難理解,實施起來卻不容易。列維說電腦技術的產生與西方科學、哲學傳統息息相連,電腦運算的邏輯深植于當代西方知識論與美學之中。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典哲學是從超驗世界里尋找普遍性,而因特網是將散落在不同時空里的真實經驗聯系起來;所以,網絡智慧不是因循柏拉圖的古典腳步,一心要攀登知識的制高點去尋覓“真理”,而是屈尊于蕓蕓大眾的“意見”,在眾生喧嘩、蕪雜多義的個別思考里,披沙瀝金,萃取真知灼見。中國傳統知識論有著強烈的精英化色彩,如今受到了數字技術的全面挑戰。與其擔憂因特網或人工智能將毀滅我們的生活,不如以開放、自信、包容的姿態掌控好這把“雙刃劍”,讓它趨利避害,更好地服務于人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