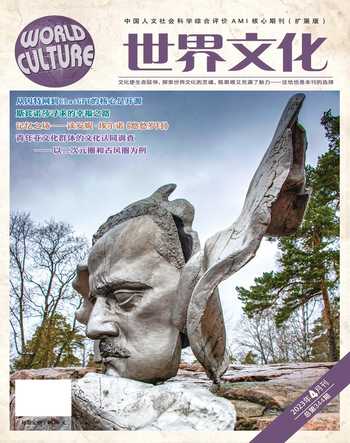記憶之場
孫魯瑤 張丹丹

一塊泡在茶里的“瑪德萊娜點心”把思緒拉回到貢布雷的一個星期天早晨,往昔隨著點心的滋味浮現于眼前——這是法國作家馬賽爾·普魯斯特的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的經典片段。這一“普魯斯特式”的聯想同樣存在于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埃爾諾的文字中,不過,觸發回憶的不是點心,而是一張張記錄過往的照片。《悠悠歲月》(2009)就是這樣一本“影集”,通過描繪和追憶舊照片背后的往事,埃爾諾將個體經歷與集體回憶串聯橋接,以一位女性的一生觀照整個時代的發展歷程。不少人認為《悠悠歲月》就是埃爾諾本人的自傳,因為字里行間的故事和細節都似乎是埃爾諾人生經驗的復刻,但仔細閱讀便會發現,埃爾諾并不愿意以第一人稱“我”為敘事立場,而是使用第三人稱“她”來延展故事和追憶往事,這就與傳統意義上的自傳性文本拉開了距離,也保留了更多文學想象的空間。總的來說,《悠悠歲月》是一部叢集個人經驗和時代畫像的小說,它以回憶建構出法國20世紀40年代至今的文化記憶和歷史框架,表現出對記憶的深刻理解與思考。
攝影術與“她”的往事
“一個肥胖的嬰兒,下嘴唇賭氣地向外突出,褐色的頭發在頭頂形成了一個發卷,半裸地坐在一張雕刻的桌子中央的一個墊子上。”這是《悠悠歲月》呈現的第一張照片。第二張照片緊隨其后:“一個大約四歲的小女孩兒,短發在中間分開,用系有蝴蝶飾帶的發夾向后夾住,……她的衣服看來裹得很緊,帶花邊的裙子由于肚子凸起而在前面掀了起來。”這兩張照片是小說開篇的第一幕,開啟了關于小女孩兒一生的敘事。這個小女孩兒是誰?埃爾諾稱之為“她”,從小說的種種信息推斷,“她”與埃爾諾同歲,有著相似的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似乎就是埃爾諾自己。但“她”這一稱呼卻拉開了觀察者與照片中人物的距離,這一狀況好似人們翻閱照片、試圖與往事建立聯系時的感受——陌生、疏離,它從側面說明了攝影作為記憶術的必要性:記錄被遺忘的歲月,并將其帶入當下。
埃爾諾生活的法國是攝影術的誕生地。1827年,尼埃普斯(Nièpce)用暗箱照相機拍攝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幅長久保存的相片《窗外的風景》。10年后,其友人達蓋爾(Daguerre)發明了“銀版攝影術”,標志著影像時代的開啟。攝影術自誕生之日起就肩負著“捕捉重要時刻”的使命,不論是拍攝個人肖像還是記錄戰爭或社會重大事件,攝影術本質上都是一種記憶術,它不僅能極大程度地還原真實,更重要的是能夠將“時刻”變為“記憶”長久留存。
對于生活在1940年代的法國人來說,照相機已逐漸作為尋常之物進入千家萬戶。埃爾諾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革命性技術對人們生活的改變,她將光影引入創作,以文字化的照片記載和刻錄個體生活的幽微之處。對于很多人來說,照片大多是私人化的。生活中的細節,一瞬間的回憶,甚至是隨手一拍,都真實記錄了個體此時此刻的狀況和心態,這些感受或轉瞬即逝,或長久縈繞,它們就像一個個細小的圖塊,構成了一個人一生的宏觀敘事。從這一點上看,《悠悠歲月》是一部關于“她”的人生檔案,記錄了“她”從嬰孩到耄耋的人生旅程。肥胖的嬰兒,穿深色泳衣的小女孩兒,褐色短發、戴著眼鏡的少女,深色中長發的高個兒少女,身穿畢業服、神態嚴肅的中學生,梳著貼額發、肩膀寬闊的大學生,懷抱孩子、笑容可掬的少婦,與丈夫和兒子同框的優雅女人,冬日花園里溫柔從容的單身女性,懷抱孫女微笑凝視鏡頭的祖母……“她”從幼年漸漸走入老年,由天真爛漫的孩童成長為成熟堅忍的長者,一張張照片捕獲了“她”人生中悄然易逝的瞬間以及“她”作為平凡個體與眾不同的人生時刻。埃爾諾還附上了每張照片的時間和地點,這些影像跨越半個多世紀,拍攝于不同的城市和國家——時空坐標將平面圖像變成了正在言說的充滿意義的事件,使這些影像真正聯動起來,還原出“她”的人生日歷和生活地圖。
與翻閱相冊時的熟悉和親切感不同,埃爾諾似乎時刻向讀者傳遞著一種閱讀往事的陌生感。嬰孩時期的“她”是一個“胖乎乎的”“經歷神秘生活的肉體”;游玩照與“兩年前戴著眼鏡”的模樣大相徑庭;學生照似乎與曾經“擺著挑釁姿勢的女孩兒”毫無關系……這種距離感將照片的主人公和觀看者割裂開來,暗示了個人成長中存在的漠然、遺忘和自我分裂。埃爾諾似乎想表達,個體困惑也許并非源于周遭世界的變遷,而是源于對自身的疏離。此時,人們應該打開相冊,與光影對話,在過往與當下的交匯之中找尋被遺忘的生命時刻,重建關于個人生命的整體性理解。從這一角度看,攝影術不再是簡單的影像記錄,而是建構人生記憶、探尋自身意義的哲學方式。

日常生活書寫與“我們”的歷史
如果說一部影集還原了個體的生活軌跡,那么無數張照片疊加在一起就形成了關于時代的敘事。《悠悠歲月》并未停滯于光影背后的個人故事,而是將筆觸延伸至更為廣闊的外部世界,去建構個體經驗與整個社會記憶之間的整合關系。不過,埃爾諾并未采用宏大敘事,而是使用微觀細膩的日常生活書寫來記錄時代與社會的變遷。從某種意義上說,日常生活書寫是一種更為抽象的攝影術。傳統照片很難表達圖像背后的整體性語境和抽象意義,而日常生活書寫則通過語言連綴起尋常事物中的細碎圖像,把它們重新編制和排列,從而形成一幅關于宏闊時代的全息圖景。
圓珠筆、盒裝洗發膏、桌布軟墊和熱弗萊克斯漆布、百潔布和脫毛膏、吉拉克牌塑料、滌格爾牌滌綸、日光燈、榛子奶油巧克力、腳踏式助動車和葉綠素牙膏……埃爾諾總是用各種各樣的物品串聯起人們對某個時代的回憶。物品是日常生活的標簽,也是人們觀察時間的視角,每個時代似乎都有與某些物品相關的記憶。圓珠筆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人書寫的重要物件,也是當時影響最為廣泛的發明之一;洗發膏和牙膏反映了公共衛生水平的提升;各類布料暗示著人們對生活質感的追求;巧克力和助動車則記錄了食與行的諸多花樣。這些物品就像一幅幅影像側寫,呈現了戰后法國人們的生活樣貌:貨品琳瑯滿目、層出不窮,新鮮事物此起彼伏、躍入眼界。除了物品本身的演進,埃爾諾還通過物品記錄了人們生活節奏的變化:“小袋包裝的濃縮咖啡”方便攜帶,“可米牌壓力鍋”烹飪迅捷,“管裝蛋黃醬”開封即食……種種物件的巧妙設計節省了精力,迎合了人們的生活需求,也說明了一個快節奏時代的來臨。
除了日用品的更新換代,汽車是生活日新月異的重要標志。埃爾諾將汽車定義為“自由的同義詞”,因為其折疊了空間距離,使人們能夠在更廣闊的世界中活動,同時也象征了經濟自由和生活優渥。埃爾諾寫道,“四馬力的汽車被換成了多菲內牌汽車”。“多菲內牌汽車”又叫“太妃車”,是法國本土汽車品牌“雷諾”的經典國民車型。太妃車尺寸小巧,功能實用,價格親民,能夠很好地滿足法國人的出行需要;并且,太妃車的設計非常時尚,生動展現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們對現代交通工具的美學理解——機械感與審美性的完美融合,體現了人們擁抱新技術、享受新生活的時代心理。
隨著物質生活的豐富,法國人也在創造著屬于他們時代的文化生活。“半導體收音機”向人們提供了多樣的聲音節目,從流行音樂到時政新聞,應有盡有。埃爾諾這樣描寫收音機帶給人們的獨特體驗:“這是一種陌生的樂趣,能夠獨自待著而又不孤獨,隨意支配世界上各種各樣的聲音。”這一新生事物充滿誘惑,以至于“我們邊聽半導體收音機邊準備學士學位證書考試”。與收音機類似,電視也成為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各類節目花樣繁多,人們熱衷于討論《天堂的騎士》《我熱愛的女巫》《迷人的馬術》,日間閑談也都與各類影視相關。雖然埃爾諾認為電視使人們“結束了融入社會的過程”,但不可否認,電視也用自己的方式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這種生活方式和社交模式的改變本身就是關于法國社會歷史進程的時代速寫。家用物件、交通工具和娛樂產品都是時代的一面鏡子,記錄著社會進程和民眾生活群像,構建著屬于這個時代的每一個人的歷史與記憶。
敘事與“記憶”擬象
從語言上看,《悠悠歲月》似乎并不易于閱讀,碎裂的場景、中斷的敘事、拼貼的故事和去邏輯化的結構,成為對這部小說的主要觀感。有人將這樣的敘事視為女性書寫的特質,認為埃爾諾意在復原一種反邏各斯的女性話語。不過深入閱讀便會發現,埃爾諾使用去秩序化的語言,除了要表示某種性別立場,其實也在有意識地模擬“記憶”的形態。
埃爾諾在談論自己的寫作目的時曾說道,記憶的機制是她想要描寫和表達的“更高級的事物”。在埃爾諾看來,記憶并非單純的一個事件、一則趣聞或是一種情感,而是一種建構和生成,具有自身的語法和邏輯,這是文學敘事不應忽略的側面。《悠悠歲月》始終致力于將這一本質展現在讀者眼前,平凡日常的描寫中都蘊藏著獨運匠心。譬如,埃爾諾這樣描寫暑假生活:“傾聽環法自行車賽的行程,把獲勝者的照片貼在一個專用的本子里/記下在街上交錯而過的汽車牌照號碼上的省的序號/閱讀當地報紙上她看不到的影片、她讀不到的書的簡介/刺繡一個毛巾架……”一條條片段構成了關于暑期的回憶性敘述,每件事情最多只有二十余字,不論是專用的本子、汽車牌照號碼上的省號,還是報紙上的影片和毛巾架,都只不過是一張照片的敘事量;并且,這些片段不以標點區隔,平行并置,沒有明確的先后關系,凡此種種,都與記憶的形態十分類似。無論印象是否深刻,記憶大多是有限和不完整的,它可能是一閃而過的圖像,也可能是浮于腦海的片段,其軌跡也鮮有邏輯可循,難以推導。這種片段性、圖像性和無預定性,正是埃爾諾意圖臨摹的記憶的特征。因此可以說,《悠悠歲月》不易閱讀的根源或許就在于記憶的不可讀性和復雜性,這正是小說如此耐人尋味的原因之一。
當然,埃爾諾的最終目的并不是讓文字成為“模仿的游戲”,而是希望文學能夠成為記憶的一部分。當回憶被講述和傾聽時,它由過去走入了當下;同樣,當記憶化作文字被讀者閱讀時,它便在每個人對歷史和現實的理解中獲得了新的內容。書寫、閱讀、理解、闡釋,這正是記憶不斷被記錄、講述、傳遞和再生產的過程。因此,擬象并非是簡單的求真,而是意在揭示記憶與文本之間的互文關系:記憶即文本,文本即記憶。從這一點上看,個體的、“她”的往事和群體的、“我們”的歷史,也都不應被理解為單純的文字攝影或是外在于記憶的媒介物,相反,它們就是記憶本身,都需要被傾聽、闡釋和再生產。并且,埃爾諾相信,記憶與文本一樣,都是超越地域、國家和民族的對話,“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歷史不一樣,但是我們在同一個世界上”。人類對記憶有著相通的理解和超乎尋常的默契,廣泛的閱讀和闡釋正在創造出一個宏大的記憶之場,內部充滿了共鳴和回響。因此,《悠悠歲月》的目的不僅在于建構法國人獨特的集體記憶和文化歷史框架,更重要的是,它希望這段記憶能夠放在不同的個體和群體經驗中去理解,給每一位閱讀它的人帶來積極的意義。
本文得到江蘇省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美國猶太大屠殺小說研究”(19WWC001)資助。
作者工作單位:河海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