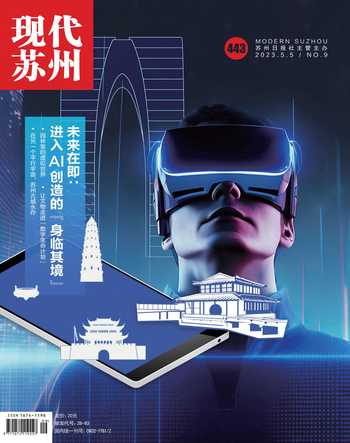讓文物走進“數(shù)字生命計劃”
丁云

就像戴上了阿笠博士給柯南研制的眼鏡:AR眼鏡掃到文物,關于這件文物的分部拆解、相關解析及背后的歷史文化碎片一一在鏡片上自動播放。與此同時,透過鏡片,現(xiàn)實中的文物可以與鏡片上播放的文物一并欣賞。
不僅如此。展柜前里三層外三層圍著觀眾時,只需語音:“打開第X個”,同樣可以指揮AR導覽。通過數(shù)字化手段,可以很直觀地讓觀眾“走進”考古發(fā)掘現(xiàn)場。
一日千里,數(shù)字文化在博物館已經(jīng)體現(xiàn)得如此直觀。
重新定義“如何在博物館生動觀展”
展柜里是一組墓葬里出土的樂器,碼得很規(guī)整,但不影響它們依舊顯得有點“灰頭土臉”。AR導覽眼鏡被觸發(fā)后播放了一段三維小動畫,整了一支小樂隊抱著這組樂器吹拉彈奏。“原來這些樂器是這么使的”“原來它們這么組合”,假想一下子豐滿立體起來。就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求的,“讓更多文物和文化遺產(chǎn)活起來,營造傳承中華文明的濃厚社會氛圍。”
今天,走進博物館,大部分觀眾已經(jīng)不滿足于一個單純的語音導覽,或者普通講解員的講解,他們更希望能夠與專家或者館長深度交流,“因為專家講解更有信服力。”楊曉華,蘇州云觀博數(shù)字科技總經(jīng)理、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迄今已為全國600多家博物館制作了相關的AR項目。
2021年,蘇州博物館有一個大英博物館珍藏古羅馬文物展,云觀博圍繞內容做了三個版本的AR導覽:一個是專家版,請南京大學教授講古羅馬文化,請策展人做導覽。第二版是普及版,把文物拆分,講文物的故事,因為“單看一個立體雕塑的腦袋沒有意義”。第三個是青少版,展覽里有個銅盒講述時間,AR導覽以動畫的形式向孩子們解釋,作品是如何表達時間的流逝的。
讓楊曉華感觸最深的是一對母子。剛開始他們就想進博物館看展覽。看了一會兒出來了,說還得租一臺AR眼鏡,他們看不懂。工作人員告訴母子,租一臺就行,青少版和成人版都在一個眼鏡里,可以換著看。10分鐘后媽媽出來又租了一臺,說“孩子不給我”。AR導覽解決了觀眾參觀博物館的一大“痛點”。
每個博物館的展陳不一樣,動線也不一樣,AR導覽還順勢解決了怎么觀展的問題。眼鏡里可能有100件展品,這100件展品就是必看展品,順著里面的順序看,就相當于看完了重點。“蘇博可能展出幾千件文物,不可能件件都看,可能重點文物就100件左右,就針對這100件文物去做內容的深化和挖掘,也幫助觀眾去解決怎么看的問題。”
不僅如此。大部分省級博物館場館大,展品多,全部看完展覽至少得四五個小時,絕大部分觀眾走不下來,沒看完重點文物又會覺得遺憾。因而可以找個地方坐下來,舒舒服服地把AR導覽里面的內容全部看完,沒準又來勁了,回頭再將文物實物好好欣賞一番。
這種觀展新模式其實解決了博物館現(xiàn)有教育模式的掣肘問題:一堂給孩子們安排的課程發(fā)到網(wǎng)上一眨眼的工夫,二三十個名額一搶而空,根本沒辦法解決大部分孩子想要參與學習的需求,還特別耗時耗人耗力。AR設備就好比一位老師,通過一套設備和一套內容,觀眾可以自行完成在博物館的學習,把被動教育轉化成主動學習。
數(shù)字文博的廣闊未來
目前來看,數(shù)字化給文博行業(yè)帶來的發(fā)展,楊曉華認為大概體現(xiàn)在兩個方向。第一塊在IP授權。各大博物館都在把IP授權轉化為數(shù)字化內容。第二塊通過數(shù)字化采集和數(shù)字化制作,把客觀存在的一件件藏品,變成可以展示和利用的內容,讓消費者來買單付費。這是博物館數(shù)字經(jīng)濟最好的一種體現(xiàn)方式和表達方式。但是,內容得做得足夠吸引觀眾,能夠解決他們參觀博物館時的“痛點”,讓觀眾有獲得感、儀式感。“把這個部分解決掉,博物館的數(shù)字化才真正有價值。”
從2014年、2015年起,國家文物局就開始要求博物館開展數(shù)字化建設,每個博物館都要進行數(shù)據(jù)采集,建立自己的數(shù)據(jù)庫。當年巴西國家博物館遭遇火災后,很多文物無法重塑,而中國保留了所有重點文物的數(shù)據(jù),對文物的修復和保護上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今天,這些數(shù)據(jù)正走出硬盤,走進大眾視野,被越來越多的人看到和了解。
與此同時,數(shù)字展覽這一形式正被博物館越來越多地采用、策劃。按照以往,類似大英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法國盧浮宮等場館的重點文物要來到中國展出,基本不現(xiàn)實。先不說出于對文物保護的考量,文物究竟能不能走出博物館,這些文物如到中國來,運輸、保險費用將異常驚人。中國現(xiàn)有6565家博物館,極少有能負擔得起外展費用的。因而數(shù)字化IP授權一定是未來大型展覽引進來和走出去最好的模式和方式之一,通過數(shù)字技術手段還可以獲得更多的沉浸式體驗,并且能夠更好地向外傳播、提升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和影響力。今年4月,三星堆文化的數(shù)字展覽就在法國巴黎開展。
讓文物走入大眾,又避免泛娛樂化
加入云觀博之前,楊曉華在四川博物院的教育、信息中心、產(chǎn)業(yè)辦等部門任過職,“我們更懂博物館,了解博物館需要什么,更知道博物館應該展現(xiàn)什么東西給觀眾看。”楊曉華說,核心就在不停地思考觀眾需要什么,不斷增加內容,升級技術手段。
云觀博給全國200多家博物館制作智慧繪本課程。“但任何技術變革永遠離不開內容,內容是最重要的。”從最開始用手機做AR體驗,到4年后用AR眼鏡做體驗,展現(xiàn)和表達形式不同,卻永遠改變不了內容為王的核心。
博物館是一個一定不能輸出錯誤的地方,對內容要求非常高。策劃團隊基本以考古文博專業(yè)的研究生為主,做一本繪本要看大量論文才敢下手,去圖書館、檔案館翻閱資料,找相關部門檢索熟讀考古報告等更是家常便飯,以此保證輸出內容必須是正確的,而當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正確,業(yè)界暫無定論時,就選擇不講。
制作過程就是不斷地磨合:先將大綱確定,交由專家審核,專家審定后再開始第二步。美術、視頻、設計、建模等要做得有意思,同時還要嚴謹。比如古人戴個官帽,官帽有多高,什么顏色、什么樣式等都要特別注意,這頂官帽如果跟這個人本身的角色不符就不行。
當然,想要展現(xiàn)給觀眾看的形式和文物本身的專業(yè)性之間,是必定有矛盾的。以數(shù)字化展現(xiàn)的形式越來越廣泛,泛娛樂化的問題就會出現(xiàn)。博物館是一個學習場所,文物不能做得過分娛樂化;但對于大部分普通觀眾來說,卻希望越娛樂化越好,容易懂且有意思。行業(yè)本身是枯燥的,通過什么樣的方式讓它娛樂化而又不泛娛樂化,是一件特別燒腦的事情。
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走進博物館
今天,博物館的定義已經(jīng)被重新刷新。大量家庭把讓孩子到博物館接受文化教育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拓展方向。博物館也正吸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去拍照打卡。“只要他們愿意走進博物館,就會有一個慢慢接觸,逐步學習的過程。”
云觀博是文博板塊最大的數(shù)字藏品發(fā)行方,從文博數(shù)字藏品中也能窺探出數(shù)字化給行業(yè)發(fā)展帶來的推動力。在中國,數(shù)字藏品是禁止二次交易的,只能收藏,但云觀博把文物的故事也一并做到了藏品中。大部分人在最初購買時,只關注這件文物好不好看,而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買的人開始研究文物本身。展廳里,同時出現(xiàn)了一撥舉著手機里的文物數(shù)字藏品與文物本體合影的觀眾。“這是以另一種方式途徑去宣傳了文物和博物館文化。”楊曉華說。
今年“五一”假期,全國各大博物館前方來報,AR導覽出現(xiàn)了人等機子的現(xiàn)象,回一臺搶一臺,“說明大家對文化的了解、認知是有需求的。”2019年,我國博物館接待觀眾12.27億人次。今年,楊曉華預估會往15億人次上去突破,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