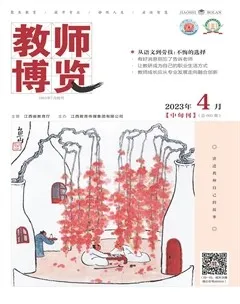鄉村磨坊
陳立武

今天我們食用的面粉,都是從商店或超市購買的。而在五十年前我生活的鄉下,吃面粉全靠自家磨。那時的磨坊和磨面場景成為印刻在我腦海中的永恒的記憶。
村子偏西一隅,孑然而立一間泥草房,面積有二十多平方米,那是村里的磨坊。全村三十幾戶人家,兩百多人吃的面粉,都出自這里。
磨坊向南開門,墻體四周無窗,只留了幾個不大的通氣孔,大概是為了防止“熊孩子”翻窗侵擾。磨坊的中央,砌有二尺高的方形石桌,上面架著直徑一米多的木板圓臺,臺面的正中安置磨坊的核心部件——直徑約半米的一副石磨盤。磨盤分上下兩片,下片固定在臺面,上片則整齊地扣在下片上,兩片以中心鋼軸相連,維修時可將上片卸下。上片轉動,帶動磨盤滑動摩擦,兩片齒條的交替咬合,將涌入其中的麥粒擠壓、碾碎,我們便可獲取面粉。磨坊西側,還有一簡易平臺,留作過篩之用。磨面人從家中帶來一偌大的笸籮,架上由兩條平行竹片制成的籮筐,放上籮篩,倒入碾碎的顆粒,來回推拉,便可篩下細糯的面粉。
那個年代沒有麥收機械,不能將麥子脫粒烘干而直接收儲,需要人工收割,運回麥場,再翻曬打壓。在麥場打下的麥子,難免會摻入一些小石子和沙礫,需要清理,否則,磨出的面粉就會硌牙而難以下咽。所以麥子上磨前,我們要先挑出雜物,篩掉沙礫,然后將麥子放入水中淘洗,去除灰塵,瀝干再攤開晾曬。為防雞鴨偷食、弄臟麥子,晾曬時還要讓家中的孩童看管。
生產隊養了十來頭耕牛,也有兩頭毛驢——主要是為農戶磨面的。磨面前,母親將洗凈曬干的麥子扛至磨坊,我會幫著拿笸籮、笆斗等輕巧用具。然后,母親去生產隊牛棚牽來毛驢,將其上套。為讓驢兒專心干活,需用黑布蒙上它的雙眼。有的驢兒一上套,便又是拉屎又是撒尿,人們說是“懶驢上磨屎尿多”。我倒覺得,毛驢并非畏懼勞作,而是為了卸下負擔,輕裝上陣——屎尿過后,它便昂首一聲號叫,隨即邁開矯健步伐。六七歲的我,手里拿根樹枝,跟在驢屁股后面,模仿駕車人的樣子,儼然像個車把式。
驢圍著磨臺打圈轉,拉動磨盤轉動。母親靠近磨盤中心的磨眼,不停地將麥粒送下。隨著上下磨盤的擠壓研磨,麥粒被碾碎,從磨盤齒縫里擠出。母親一面往磨眼送麥粒,一面用笤帚將蹦到磨盤邊上的顆粒掃向里邊,以防撒落。第一遍磨出來的顆粒很大,極少出粉,一般不過篩,直接收集起來,再行上磨。到了第二遍,磨下的顆粒變小,白花花的。母親便一瓢一瓢地挖到籮篩里,來回推拉,面粉透過篩孔紛紛落入笸籮里。這時的面粉,雪白、細膩、爽滑,粉嫩養眼,應該就是城里供應糧里的富強粉。
聞著麥香,嘴饞的驢兒按捺不住,會悄悄扭過頭來偷吃磨臺上的碎麥粒。于是,驢嘴罩便出現了,它由細竹篾編成,套在驢嘴上讓其偷嘴不成。驢兒也有小脾氣,有時不讓它吃上兩口香糯的碎麥粒,它會偷懶耍滑,甚至駐足不前。這時我會揚起樹枝要教訓它,母親見狀低聲對我說:“毛驢也累,你幫它推一把!”于是,我便使勁推動磨盤上的撬棍,待撬棍觸及毛驢的后腿,它便不得不重新走起來了。
過篩后的粗顆粒,被匯集后重新上磨。我們還會繼續研磨兩三遍,篩下的面粉逐漸變得暗淡,不再雪白。到最后,篩面上只剩下薄薄的一層麩皮了。那時候生活苦,糧食緊缺,各家磨面總要磨四遍以上。磨盤不能空轉,石齒間得有糧食,否則會損壞磨盤齒條。所以每家磨面的最后,都會留些糧食在磨盤里——為下家留“磨底”。磨眼不能空著,與磨盤持平最好。如果吝惜那一把麩皮沒有這樣做,讓石磨“餓了肚子”,會被鄉鄰看不起的。
有時候毛驢被生產隊派作其他活計,家里又等著吃面,我們也會人力推磨。春節前各家碾一些零星雜糧,也會人工推磨。一個人推起來很吃力,需兩個人合力來推。于是,鄉民聚集在一起,你幫我,我幫你,說說笑笑,鄰里互助成為一道風景。即使磨的糧食不多,抱著磨棍推上一兩小時,也會頭暈目眩、渾身發軟,讓人感到整天干著繁重體力活卻只吃草料的牛馬的辛苦,便更加憐惜這些牲畜。
全村三十多戶人家,都要在此磨面,所以要向生產隊牲畜管理員報備,甚至預約排隊,尤其是農忙前后的晴好時日。在與麥粒的終日廝磨中,石磨齒條棱角會逐漸變鈍,溝線不再分明。這時磨面就變得效率低下,不出活,該修理了。修石磨,要用鋼鉆將磨鈍或受損的溝槽棱角線重新鍛鑿出來,我們稱之為“鍛磨”。鍛磨是技術活,普通的石匠是干不好的。鍛磨人讓我好生羨慕,當然,并不是因為鍛磨人技術高,而是他鍛磨后獲得的款待,那焦黃噴香的蔥油烙餅,饞得我口水直流。
除磨麥子,玉米、高粱、綠豆等乃至山芋干也都可放在磨盤上研磨取粉。過年時不少人家將干糯米也放在磨盤上研磨,用來做元宵、年糕,只是磨出的糯米粉沒有石臼搗出來的那么筋道、有黏性。
南方山區的磨坊多為“水磨坊”。它們迎水而建,且在溪流落差較大處。磨坊里有磨面的石磨,也有舂米的石臼,動力自然是山澗跳下的水流。不過,水磨坊的石磨比北方的明顯小了許多——溪水沖力還是沒有牲畜的力量大,畢竟也不都是旺水季。但設計巧妙的水磨裝置,有效利用了自然之力,很能體現山民的聰明才智,那嬌小的磨盤也體現著南方人的清秀、務實和精干。
20世紀70年代后期,鄉下通了電,陸續有了糧食加工機器,機器磨面變得快捷省事,磨坊便很少使用。再后來,鄉民可用麥子換面粉或直接購買面粉,磨坊便被廢棄了。走過那個時代的我們,會時常憶起家鄉的磨坊,耳畔響起“嗡嗡”的石磨聲,像悠長而又古老的歌謠,那么恬靜而安詳……
(作者單位:安徽滁州開放大學)
(插圖:珈 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