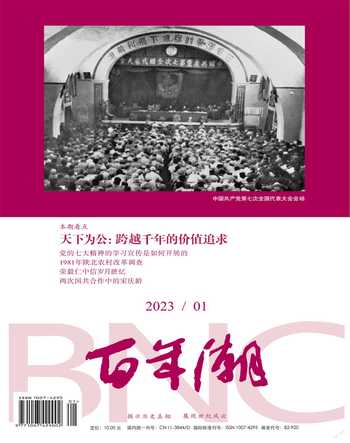回憶股份制改革實踐

傅豐祥
編者按:改革開放是決定當(dāng)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關(guān)鍵一招。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前進(jìn)道路上必須“堅持深化改革開放”。2023年是改革開放45周年,本雜志社與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合作,開設(shè)“口述改革開放”欄目,陸續(xù)刊發(fā)改革開放重要歷程、事件中親歷者的口述回憶文章,記錄改革開放歷史,宣傳改革開放精神。
股份制是在改革實踐中產(chǎn)生的。體制改革是從企業(yè)改革開始的,實際上企業(yè)改革走的路子與農(nóng)村的包產(chǎn)到戶是有關(guān)系的。一開始是國有企業(yè)先搞經(jīng)營承包責(zé)任制,搞了幾年。1985年左右,有很多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開始搞股份制,企業(yè)要發(fā)展,資金來源有限,自然而然就出現(xiàn)了資金入股、勞動力入股這樣一個很初級的股份制形式。然后逐漸影響到城市的工業(yè)企業(yè)。當(dāng)然搞股份制也受到國外的影響,國外搞得比較早。
1991年1月至2月,國家體改委組織了一個證券考察團(tuán)到美國去考察證券市場。考察團(tuán)以“聯(lián)辦”(即“證券交易所研究設(shè)計聯(lián)合辦公室”,由九家全國性非銀行金融機構(gòu)發(fā)起和集資,于1989年3月15日成立,取意“大家聯(lián)合起來辦事”)為主體。我擔(dān)任團(tuán)長,副團(tuán)長是王波明,成員還有上海市體改委主任賀鎬圣、沈陽人民銀行行長、武漢人民銀行行長、深圳人民銀行副行長三位行長,考察了大概一個星期,回來寫了個報告,刊登在《科技導(dǎo)報》上。
考察中,美中經(jīng)濟(jì)委員會組織了一次考察團(tuán)與美國有關(guān)方面人士的座談。座談在一個禮堂里舉行,美國經(jīng)濟(jì)界、政治界的人坐了一屋子。我在開場白中講:代表團(tuán)到美國來資本市場最高、最深的華爾街來考察,說明了中國政府對改革,對中國資本市場,對中國的企業(yè)股份制的態(tài)度。給我印象深刻的有一件事情,美國聯(lián)邦儲備局(相當(dāng)于我們的人民銀行)每周四有一次公開市場日,當(dāng)天對美國的國債進(jìn)行公開的招標(biāo)、拍賣。聯(lián)邦政府通過市場來進(jìn)行宏觀管理,公開市場日是很重要的日子。公開市場日上把國債賣出去就收緊銀根了,放松銀根的話就把國債買回來,把美元放出去。美國財政部或美聯(lián)儲認(rèn)可的大概有40個重點的大銀行、投資銀行、財務(wù)公司有資格參加公開市場日的招標(biāo)、認(rèn)標(biāo)。每周四整12點在美國聯(lián)邦儲備局開會。我們過去參觀學(xué)習(xí),第二天美國報紙報道把我們誤認(rèn)為日本人,我想大概美國媒體也想不到中國人會在這個時候來考察資本市場,考察公開市場日的操作。這向美國說明了中國的改革沒有停,繼續(xù)在走,而且改革更加深入了,走到資本市場這個階段。

這次赴美考察對后來證監(jiān)會的組織建立和交易所的建設(shè)都有很大的啟發(fā)。證監(jiān)會職能分工、分支機構(gòu)的設(shè)立參考了紐約交易所、納斯達(dá)克交易所怎么分工、怎么設(shè)置。考察后,也更加堅定了我們對資本市場的看法。美國的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由市場來決定是有一定優(yōu)勢的。
1991年底,領(lǐng)導(dǎo)同志召開專家座談會,討論的主題首先是總結(jié)蘇聯(lián)解體的教訓(xùn),討論為什么蘇聯(lián)解體了、垮掉了,但是資本主義為什么“垂而不死”,其體制機制和政策有哪些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東西。其次對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劇變進(jìn)行分析,研究是什么因素導(dǎo)致蘇東各國經(jīng)濟(jì)和社會發(fā)展出現(xiàn)停滯和危機,以至于發(fā)生解體和劇變。在對這兩個問題進(jìn)行深入分析基礎(chǔ)上,敞開思想,對我國如何進(jìn)一步推進(jìn)改革開放的重大問題進(jìn)行研討。在這次座談會上,我發(fā)言的主題就是股份制。當(dāng)時對股份制有一些議論。我認(rèn)為,面對那些宣稱股份制就是西方化、私有化的質(zhì)疑,一個好辦法就是用經(jīng)典作家的話去駁斥。我記得,還找了馬克思、恩格斯關(guān)于股份制的論述,其中大概七八條講了股份制的意義。甚至找到恩格斯講“股份制可能是走向共產(chǎn)主義的一個途徑”的原話。我提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單一的公有制,資本主義國家是私有制國家,但是股份制是把公有制變成了社會所有,范圍更寬。幾百人、幾十萬人持有股票,像在中國,可以上億人持有股票,股份制本身就是對私有制的一種改變,所以不能把它看成是私有制。股份制又把資本所有者和企業(yè)的管理者分開了,并不是由出資人自己直接來管理企業(yè),專門有一批管理階層……類似的專家座談會一共開了十幾次,每次都有不同的專家參加,我參加了其中的三次會議。
1992年初,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提出,“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guān)了就是。關(guān),也可以快關(guān),也可以慢關(guān),也可以留一點尾巴。”這些話給大家壯了一個膽,撐了一個腰。當(dāng)時股份制已經(jīng)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大家想了解股份制是怎么回事,證券市場是怎么回事,對中國的經(jīng)濟(jì)改革到底起什么作用。當(dāng)時我的一個重要的任務(wù)就是到處去宣講股份制,到處講課,在解放軍總政治部、國防大學(xué)都講過,也去中辦秘書局講過一次。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來,企業(yè)改革要適應(yīng)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需要。我參加了會議文件起草小組,其中討論到國有企業(yè)改革時,起草小組組長溫家寶提出來,能不能用幾句話把國企改革概括一下。當(dāng)時我是負(fù)責(zé)宏觀體制這方面的,但對企業(yè)體制也很關(guān)心,我提出來四句話:一、產(chǎn)權(quán)清晰。國企產(chǎn)權(quán)要很清晰,這就是要股份化。二、職責(zé)明確。責(zé)任明確,利益也要明確。三、政企分開。四、管理科學(xué)。這四句話實際上是股份制的一些精髓。產(chǎn)權(quán)要清晰,當(dāng)然就是要股份化了;職權(quán)要明確,就要按資本分紅并承擔(dān)責(zé)任;政企要分開,屬于政府、社會的事,不要讓企業(yè)去承擔(dān);管理要科學(xué),就是后來的法人治理結(jié)構(gòu)。這四句話說到底就是現(xiàn)代企業(yè)的標(biāo)志。
當(dāng)時關(guān)于股份制的爭論還是有的。我主張股份制沒有問題,股份制最高的形式是企業(yè)上市,把企業(yè)變成一個社會化的企業(yè),放在市場上在整個社會的監(jiān)督底下運行,絕大部分人都要參與。通過理論、實踐的總結(jié)來引導(dǎo)輿論,股份制這條路非走不可。股份制發(fā)展到今天,現(xiàn)在是不是做到了,也不一定,但是事實證明會是這樣的。
我認(rèn)為,股份制是我們整個改革中比較核心的問題。它不僅僅涉及企業(yè)的體制,還涉及改革的各個方面,比如投資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流通體制改革等等。我曾在證監(jiān)會工作幾年,越來越發(fā)現(xiàn)市場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資本市場的發(fā)展、股份制的發(fā)展對我國全民經(jīng)濟(jì)意識的提高,發(fā)揮了很重要的作用。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當(dāng)然我們資本市場問題還很多,但是至少已經(jīng)有那么多人知道了什么是資本市場,什么是股票市場,怎么投資,怎么取得收益,怎么去選擇企業(yè)。對人們的經(jīng)濟(jì)意識、金融意識的提高,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個意義很大。

全國外貿(mào)系統(tǒng)第一家股份制上市公司上海蘭生(集團(tuán))有限公司證券部職員在觀察和分析蘭生股票在市場上的走勢
我國實現(xiàn)法人股全流通的過程是曲折的。“聯(lián)辦”成立時,一方面要開展股票、資本市場規(guī)劃、研究。另一方面也想自己搞一個市場,從中得到一些實際經(jīng)驗。當(dāng)時上海、深圳兩個交易所規(guī)定個人股可以交易,國有股不能交易。股票市場的兩個交易所個人股的股份不能超過33%,因此,當(dāng)時能交易的只有33%這一部分,還有百分之六七十是不能交易的,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受到限制。那時我在體改委宏觀司,“聯(lián)辦”也是我分管,“聯(lián)辦”的年輕人們提出來要搞一個法人股的交易,因為那時候思想上還有框框,還不敢提國有股,但是可以把法人股先流通起來。所以搞了一個法人股的交易中心,名稱是“法人股納斯達(dá)克”。應(yīng)該是在1992年,當(dāng)時大概搞了六七個企業(yè)到納斯達(dá)克交易中心去交易。我記得珠海恒通置業(yè)在那個交易中心發(fā)行8000萬的股票。雖然這個交易中心在1994年被關(guān)掉了,但是這次試點還是有意義的。譬如恒通要籌資8000萬,在當(dāng)時的情況來看是很困難的,但是通過法人股的發(fā)行一天就籌集好了。就像馬克思講的,一夜之間鐵路就建好了。股份制就是這么大的力量,可以把社會上的資金集中起來干事情。這些對大家是有觸動的。
法人股試點1994年關(guān)掉,1995年又開始搞,由于一些原因又停了,一直停了差不多十年,才實現(xiàn)法人股全流通。當(dāng)時法人股流通,也是妥協(xié)的,僅是法人和法人之間流通,公對公,具體單位之間的流通,公司買公司的股票,還沒到個人可以買賣這一步。當(dāng)然流通過程當(dāng)中難免有些個人也買了法人股,所以就有人反映“你們這是搞什么,搞私有化嗎”?因此,又被關(guān)掉了。到2008年還是2007年,全流通放開,國有股也可以流通,公有股就更沒問題了,現(xiàn)在我們市場才是一個真正的、完全的市場。
除了法人股納斯達(dá)克,股份制試點我知道有好幾個。一個是天橋百貨商場股份制試點。當(dāng)年,北京天橋百貨商場試點股份制時,還曾經(jīng)到體改委來推銷股票,企業(yè)股份制的具體操作是在生產(chǎn)體制司。當(dāng)時還開展了一個山東淄博農(nóng)村股份制流通試點。國務(wù)院頒布一個文件,提出可以在農(nóng)村搞股份制流通試點。1992年上半年,“聯(lián)辦”負(fù)責(zé)人李青原就跟淄博市聯(lián)系,探索在農(nóng)村搞資產(chǎn)流通,組織建立了淄博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投資基金,把淄博市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股份通過基金交換的方式來流通試點。國家體改委直接抓,淄博市體改委配合。農(nóng)村企業(yè)勞動入股、資金入股發(fā)展得很快,中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那幾年發(fā)展得很快。事實證明股份制是有益的。
黨的十四大之后,大中型企業(yè)中開始普遍實行股份制,更多的企業(yè)開始在資本市場發(fā)行上市。但由于缺乏有效監(jiān)管,股票發(fā)售中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比如深圳的“8·10”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決定成立證券監(jiān)管機構(gòu)。
建立證監(jiān)機構(gòu)的過程中我們參考了國外的經(jīng)驗,當(dāng)然并不是完全照搬。比如美國證監(jiān)會,在政府編制之外,證監(jiān)會的主席由國會任命、總統(tǒng)批準(zhǔn),向國會負(fù)責(zé)。而我們要設(shè)立的證監(jiān)會,是一個由專家組成的半官半民的組織,是政府里的一個特殊事業(yè)單位。當(dāng)時對它也制定了一些專門的政策:因為是由專家組成,所以待遇高于一般政府部門;財務(wù)自收自支,而非來自國家財政預(yù)算。后來隨著發(fā)展,這些政策也有些變化。
1992年9月,國務(wù)院下達(dá)文件,決定成立兩個機構(gòu):國務(wù)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簡稱“中國證監(jiān)會”)。國務(wù)院證券委員會由國務(wù)院副總理朱镕基兼任主任,副主任是劉鴻儒和時任建行行長周道炯,委員由13個部委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部門負(fù)責(zé)人組成,這是一個協(xié)調(diào)領(lǐng)導(dǎo)機構(gòu)。國務(wù)院證券委員會副主任劉鴻儒同時任中國證監(jiān)會主席,劉鴻儒讓我協(xié)助他組建中國證監(jiān)會。
組建證監(jiān)會依托了“聯(lián)辦”,辦公地點是“聯(lián)辦”王波明去找的,在保利大廈租了一層樓,租金也便宜。人員主要從幾個方面來:體改委系統(tǒng)的,包括劉鴻儒、我、朱利、李青原,大概20人;從“聯(lián)辦”抽調(diào)了11個人;人民銀行系統(tǒng)抽調(diào)了夏斌、金穎、朱重九等十多人;再有就是從國外回來的一批人,如高西慶、陳大剛、汪建熙、林義相等;還有從國內(nèi)的一些大學(xué),如北大、清華、人大、財貿(mào)大學(xué)招來的一批研究生,加起來不到100人。這個機構(gòu)一開始就是個半官半民的機構(gòu),所以層次比較簡單,辦事效率也很高。我跟劉鴻儒同志商量,副主席盡量不要設(shè)太多,盡量不要招太多人,隊伍要精干,要真正干事的。他也很贊同。
經(jīng)費的解決也很有意思。我們從“聯(lián)辦”借了200萬元,海南證券的張志平拿出了200萬元。之后我又找了財政部,從財政部借了200萬元,于是就有了600萬元的開辦費。我們自己找房子、買家具、找錢、組織人,就這么把證監(jiān)會的架子搭起來了。
開辦證監(jiān)會之前沒有經(jīng)驗可循。雖然這期間我們也在國外考察過,但是畢竟不是直接經(jīng)驗,所以就請了臺灣、香港的一些專家來講座,討論開辦的事情,包括股票應(yīng)該怎么發(fā)行,證監(jiān)會下屬的部門怎么設(shè),學(xué)習(xí)參考了臺灣、香港等地區(qū)和美國的經(jīng)驗。
當(dāng)時我們的收入主要是靠交易所,規(guī)定交易量的1.5‰,1/3分給交易所,1/3給證券公司,還有不到1/3給證監(jiān)部門。另外還規(guī)定,每個上市公司要交5000元上市費,因此經(jīng)費比較充裕。
中國證監(jiān)會開辦后做了幾項工作:一是抓了證券法律法規(guī)的建立。開始籌備時,我們就專門抽出一個小組來起草證券交易管理法規(guī),包括內(nèi)部法規(guī),如證監(jiān)會工作人員守則等。因為證監(jiān)會是一個監(jiān)督管理機構(gòu),本身是有權(quán)的,但是不能濫用權(quán)力。當(dāng)時想來公關(guān)的企業(yè)很多,從一開始發(fā)行股票,就有人想送禮走后門了,把保利大廈都住滿了,甚至連“送給劉鴻儒和傅豐祥一人100萬股股票”這樣的謠言都有,所以我們非常注重廉潔問題,嚴(yán)格審核上市公司資格。對工作人員制定了很詳細(xì)的法規(guī),嚴(yán)格規(guī)定哪些行為絕對不能做。二是抓了中介機構(gòu)的建立,包括會計師事務(wù)所、律師事務(wù)所等。三是輿論發(fā)布,指定某幾家報刊發(fā)布上市公司的信息。另外,還有一些基本工作,比如規(guī)定證券從業(yè)人員資格、抓人員培訓(xùn)等。這些制度逐步地建立起來后,給予了證券市場正確的引導(dǎo),從此中國證券業(yè)走上了規(guī)范化發(fā)展的道路。
(責(zé)任編輯?楊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