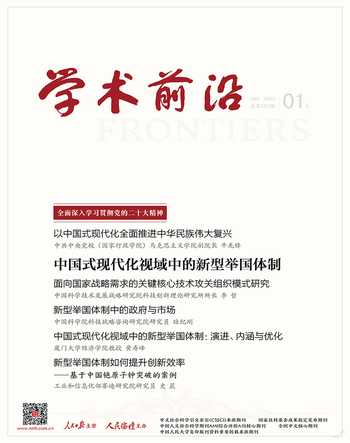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邏輯思考與實踐啟示
丁明磊 黃琪軒
【摘要】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拓寬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需要從大國技術博弈的歷史邏輯、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邏輯、宏觀環境體系的演化邏輯來理解,有效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同時要提出新思路、采用新辦法、創造新環境來避免傳統舉國體制的弊端,突破并超越西方現代化以資本為中心的根本邏輯,走出一條由科技創新強到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的發展道路。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要以國家戰略需求和問題為導向,將“集中力量辦大事”與“激發全社會創新創造活力”有機結合,以長期主義和“超越競爭”促進各類創新要素的新組合和合理流動等。健全新型舉國體制要以改革驅動創新、以創新驅動發展,改善創新制度供給,加強創新政策整體設計和協調配合,推動政策向創新鏈條一體化整體設計轉變,構建有利于創新的生態環境。通過政策引導,充分調動各類創新主體和全社會的創新積極性。
【關鍵詞】新型舉國體制? 中國式現代化? 科技強國? 自立自強
【中圖分類號】? D61?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1.008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完善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統一領導的體制,健全新型舉國體制”,賦予了“舉國體制”新的使命和內涵。舉國體制是在特定領域實現國家意志的一種特殊制度安排,世界主要創新大國在戰略高技術領域都采取過集全國資源、舉全國之力的做法(王志剛,2021)。當前,黨中央提出要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對于把創新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充分發揮我國制度優勢、市場優勢和人才優勢,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具有深遠意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拓寬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需要從大國技術博弈的歷史邏輯、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邏輯、宏觀環境體系的演化邏輯來理解,有效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同時要提出新思路、采用新辦法、創造新環境來避免傳統舉國體制的弊端,突破并超越西方現代化以資本為中心的根本邏輯,走出一條由科技創新強到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的發展道路。
大國技術博弈的歷史邏輯:舉國體制的優勢、缺陷與革新
歷史上,構建舉國體制往往是大國參與技術博弈的應對之策。蘇聯的舉國體制是傳統舉國體制的典型代表,其既快速推進了工業化,提升了技術水平,夯實了蘇聯世界科技強國的地位,卻也終讓蘇聯陷入嚴重困境。我們要從大國技術博弈,尤其是美蘇參與大國技術博弈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傳統舉國體制在以下幾個方面具有顯著優勢:第一,啟動資源耗費多的技術項目;第二,促成協調難度大的技術合作;第三,推進技術風險高的戰略布局。但是,傳統舉國體制也面臨幾項挑戰:第一,缺乏對個體的市場激勵以供應持續的資源投入;第二,具有“正反饋”特點的發展模式會弱化對既定政策的調適;第三,依賴統一布局與頂層設計所帶來的系統風險而缺乏替代選擇。傳統舉國體制的幾個優勢往往同其缺失相伴相生。因此,“新型舉國體制”就是要在發揮舉國體制優勢的同時,彌補缺失、革故鼎新。
傳統舉國體制能夠快速啟動資源耗費多的技術項目,但缺乏對個體的市場激勵以供應持續的資源投入。傳統舉國體制長于“啟動”,卻難以“持續”。美國經濟史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著作《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中總結歷史經驗指出,越是后發展國家,越需要政府的強組織力以促進產業變革。工業化起步較早的英國放手讓私人企業來推動技術變遷;起步較晚的德國靠更強有力的銀行來推動產業升級;起步更晚的蘇聯則不得不借助強大的國家來推動產業變遷。越是后來者,工業化的進入門檻也越高,越需要強組織力(亞歷山大·格申克龍,2012)。蘇聯傳統舉國體制就是強組織力的代表。當時,蘇聯政府集結資源取得了巨大的技術成就,成功研制了核彈、和平利用核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原子能破冰船、完成首次太空載人飛行,等等。同時,蘇聯也依靠自身力量,開發具有自主能力的電子計算機。日本政府亦然。1976年,日本日益感受到美國IBM技術發展帶來的壓力,在通產省的支持下成立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技術研究會。該協會聯合了日本多家公司,組織共同研究,多方參與的共同研究一直持續到1981年。該項目總預算為700億日元,其中,政府出資300億日元(Jeffrey, 1992)。
但是,以蘇聯為代表的傳統舉國體制的可持續性則不如日本。從1962年到1965年間,蘇聯政府對科學資金投入的年均增長率為10.9%;從1965年到1968年間,年均增長率下降到了9.3%;從1974年到1975年間,增長率更是進一步降至5.6%(Timothy, 1985)。蘇聯的太空探索、計算機開發等大型技術項目耗資不菲。由于缺乏市場收益,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蘇聯領導人發現其軍事科研經費捉襟見肘,大量技術項目難以為繼。和蘇聯相比,更依靠市場的日本政府則能更為持續地提供資金。正如塞繆爾斯所言,日本重視技術的民用市場,激活了市場激勵,日本的技術才能不斷從民用轉向軍用(Richard, 1996)。日本政府將從民用市場收獲的資源,轉化到下一輪的技術升級的行動中。如此一來,當蘇聯政府發展高新技術的資金來源捉襟見肘時,日本政府則能持續為其重大技術研發提供資金支持。融合了市場激勵的舉國體制是“新型舉國體制”,為舉國體制找到了“微觀基礎”,保證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有持續的資源支持。
傳統舉國體制能夠促成協調難度大的技術合作,但缺乏市場價格機制帶來的“負反饋”機制對既定政策的調適修正。一般而言,重大技術都需要大范圍的協調。在戰爭時期,美國政府更容易完成大規模協調的工作。青霉素的生產就是很好的例證。盡管英國病理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在1928年就發現了青霉素,但十多年后,青霉素仍停留在實驗室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聯邦政府啟動了一項大規模的青霉素生產計劃,協調了20多家制藥公司、多所大學以及美國的農業部參與其中。通過大規模協調,青霉素才得以從實驗室走向尋常百姓家。又如,二戰期間,美國聯邦政府召集了4個主要的橡膠企業、標準石油公司、各大化工公司,組織了聯合研發計劃,投入了7億美元建設工廠。依靠美國聯邦政府大范圍組織協調,才讓美國合成橡膠技術逐步走向成熟。
蘇聯不僅通過中央計劃協調國內生產,甚至協調蘇東國家關鍵技術的生產。例如,為了協調計算機生產,蘇聯、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匈牙利、波蘭等國建立了政府間計算機技術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 for Computer Technology)。在蘇聯領導下,各國同意生產同一標準的第三代計算機。保加利亞和匈牙利集中生產小型計算機,民主德國和波蘭專注生產中型計算機,而蘇聯則傾力生產大型計算機(Wilczynski, 1974)。日本政府也積極協調各方,推動本國的技術進步。在汽車、半導體、計算機等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歷程中,日本諸多企業都從政府協調的資金與技術項目中獲益。從1966年到1975年,日本通產省啟動了一項耗資100億日元的計劃。該計劃旨在發展超級高性能計算機(Super High Performance Computer)。以這項計劃為杠桿,日本政府促成了多家企業合作,包括日立、富士通、日本電氣、東芝、三菱等。在統一協作下,日本有的企業負責硬件,有的企業專攻軟件(Jeffrey, 1992)。日本政府介入高技術發展的意義還在于為企業的規劃與投資圈定一個焦點(focal point)。在政府部門介入后,向社會各界傳遞了比較明確的信息。各方力量將人員、資金、技術投向該技術領域,該領域的技術演練機會增多,能力積累增多,創新嘗試增多。如此一來,該領域的技術發展就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
但是,一般而言,傳統舉國體制具有“正反饋”特點的發展模式會弱化對既定政策的調適。在傳統舉國體制下,產業政策往往是由政治決策決定;而政治決策容易呈現“正反饋”特點。所謂的“正反饋”機制就是當A值提高造成B值提高,而B值提高后的信息反饋又將導致A值進一步提高。人的特性尤其是政治領域的特性會造就大量的“正反饋”機制(趙鼎新,2015)。要么是各行為體對權力的追隨與尊崇,要么是人通過意識形態論證自身行為的正當性等,“權力”帶來了更多的權力。和傳統舉國體制相關的政策一旦出臺,就會有無數的行為體跟從追隨,它容易被以往的成功所綁架,被意識形態所強化。即便政策遭遇挫折,執政者往往也會論證受挫原因并非政策本身,舉國之力甚至可能推動該政策的實施達到一個新高度。如此一來,舉國體制就會出現“騎虎難下”“上山容易下山難”的局面,只能“華山一條道”不斷往前推進。傳統舉國體制的“正反饋”特點使得其難以自我調適和修正。例如,蘇聯的航天發射中心,從最復雜的發射平臺、測試設施和實驗儀器,到強大的助推器、太空艙以及生命維持系統,加之新式計算機和高靈敏度的儀器設備,這一切都是由蘇聯自主制造的。但是,蘇聯領導人卻心存疑惑地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蘇聯有能力解決如此規模巨大且任務艱巨的難題,為什么蘇聯有時甚至要從國外獲取最簡單的東西(Timothy and Gustafson, 1990)?代表傳統舉國體制的、耗資不菲的蘇聯太空計劃包含了太多政治決定,最終被越推越遠,難以回頭。市場中的價格規律則是一個“負反饋”機制。舉國體制一旦脫離市場,缺乏市場價格機制帶來的“負反饋”機制調適修正,只能被越推越遠,直至出現重大問題。在“新型舉國體制”中,我們就是需要用市場的“負反饋”機制來補充傳統舉國體制中的“正反饋”機制。
傳統舉國體制能夠推進技術風險高的戰略布局,但面臨依賴統一布局與頂層設計所帶來的系統風險而缺乏替代選擇。當代技術發展具有門檻高、投資多、風險大、周期長等特點。僅憑借私人部門的力量,常常不足以克服相關阻礙。例如,在制藥產業,一項新的研發計劃,從項目啟動到結束,耗時約17年。每種藥物的研發需要投資約4億美元,且失敗率非常高,大約只有萬分之一的合成藥物能投放市場。即便新藥能投放市場,也常常會有完全不同的用途。如果單純靠市場,這樣的投資便很難啟動。即便是風險資本,風險投資考慮的項目,一般在三到五年也要看到回報,但很多重大技術的成長周期遠遠長于五年。風險投資對風險的偏好也弱于政府。在新技術發展早期,風險投資失敗的概率非常高。在第一個階段即技術成長的種子階段,新技術失敗的概率為66.2%;到第二個階段,即技術的起步階段,新技術失敗的概率是53%。隨后,失敗的概率才逐漸下降(Mazzucato, 2013)。因此,在技術發展的種子階段,風險投資等私人部門介入的可能性很小。此時,對風險敏感度低的公共部門投資反而最具優勢。1980年,蘋果公司還沒有設計出iPod,亟需資金。此時,美國小企業管理局注冊下的一家小企業投資公司為蘋果公司注資500萬美元。政府投資是“耐心資本”,而風險投資不是。政府投資允許長期回報,而風險投資不能。因此,舉國體制能驅動技術風險高、投資周期長的關鍵技術布局。
日本和蘇聯的技術發展都依靠政府來承擔高風險的投資。在蘇聯,無論是導彈、航天等軍用技術,還是汽車、民航等民用技術,都由蘇聯政府介入來完成布局,以克服高技術帶來的高風險。日本政府亦然,1949年,豐田汽車面臨重大危機。由于當時日本汽車沒有競爭力,投資風險極高,豐田公司難以獲得銀行貸款。因此,日本通產省的官員力排眾議,明確指出救濟豐田汽車并非浪費資源,發展汽車產業有助于刺激其他關鍵產業部門的成長,包括鋼鐵、金屬、機械等行業(Jeffrey, 1992)。事實上,戰后日本企業的資金有70%~80%依靠商業銀行貸款;而這些貸款歸根到底是由日本銀行——即日本的中央銀行提供的(查默斯,2010)。通過協調企業貸款,日本政府為企業發展高技術融資。有“耐心資本”的介入,日本企業克服了發展高技術帶來的高風險。
但是,政府從事高風險投資的最大問題就是“把所有的雞蛋放到同一個籃子里”。由于傳統舉國體制過于強調“頂層設計”“集中攻關”“統一布局”,不可避免容易出現“把所有的雞蛋放到同一個籃子里”的問題。此時,系統風險會不斷地累積。在美蘇競爭中,美國諸多技術嘗試都遭遇失敗,但得益于多元主體的參與,如軍人、官員、學者、商人,甚至還有電子游戲愛好者,各參與主體貢獻迥異的技術標準與方向,因而使美國的技術有更多的替代選擇。蘇聯傳統舉國體制往往集中規劃過度而分散試錯不足。連蘇聯和外資合作的汽車工廠,都高度集中在有限的幾個廠家,如伏爾加汽車廠以及卡瑪河卡車工廠(Holliday, 1979)。過度集中不僅帶來競爭不足且影響技術績效,更容易造成系統風險。日本則不然,在通產省的集中規劃下,日本的企業仍保持了內部的競爭與分散的試錯。1974年,世界上最大的高爐在蘇聯投產,純容量為5000多立方米,但全世界名列第2位~第20位的高爐中,日本就占了13座(都留重人,1992)。這充分體現了日本與蘇聯不同的技術發展特點。研究者發現:在日本,產業集中度并不比歐洲高,同樣一個產業會有多家企業進入。日本的模式是允許國內企業展開競爭,而非選定國家冠軍(Terutomo Ozawa, 2005)。可以看到,無論是鋼鐵、汽車還有芯片,日本國內大體呈現“對外保護,對內競爭”的特點,有多家公司展開競爭和角逐。依靠市場,會有更分散的主體在試錯;有不同的技術在嘗試;有能多方位提供技術積累的平臺;有更多的替代技術選擇,等等。因此,“新型舉國體制”就是要將“分散試錯”嵌入“集中攻關”,以克服傳統舉國體制帶來的系統風險。
由于沒有統籌好安全與發展,蘇聯的傳統舉國體制難以為繼。當前,“新型舉國體制”需要充分發揮市場的力量。如前所述,要利用市場激勵,使技術項目有持續的資源投入;用市場價格機制的“負反饋”特性來彌補政治主導的、以正反饋為主要特征的調適不足問題;要鼓勵市場的多重主體參與,萬眾創新、分散試錯,避免傳統舉國體制過于集中帶來的系統風險。
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邏輯:以“超大市場規模”支撐“新型舉國體制”
要解決傳統舉國體制的難題,就需要整合和拓展一個大市場。而市場開拓有三個關鍵方面:民用市場、消費市場和國際市場。
夯實“新型舉國體制”的民用市場。塞繆爾斯的著作《富國強兵》展示戰后日本的技術進步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由民用到軍用”(spin-on)。相比于蘇聯,美國有更強大的民用市場,而相比于日本,美國的民用市場略顯遜色。為應對蘇聯的威脅,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美國將三分之一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部署在與國防相關的技術領域(Richard, 1996)。不同于美國,日本缺乏一個龐大的軍用技術市場。在美國,往往是軍用技術外溢到民用;而在日本,技術發展路徑是民用技術外溢到軍用。日本的國防需求不穩定,國防預算有限。1963年,政府與軍隊的需求僅占日本電子產品總需求的2.5%;而在美國,這一比例高達61.3%;在英國高達27.6%。美國生產的軍用電子產品類別大約為日本的200倍;而在所有的電子產品中,美國的產量僅為日本的8倍(Richard, 1996)。日本的軍事技術深度嵌套在民用技術當中。通往成功的道路有很多種,從美日蘇的經驗與教訓來看,都離不開一個強大的民用市場來支撐。正是在其“舉國體制”中夯實民用市場,融合了安全與發展,日本的舉國體制才能有更好的表現。
鞏固“新型舉國體制”的消費市場。一般而言,由于安全競爭的驅使,傳統舉國體制容易“生產導向”而非“消費導向”。然而,如果缺乏一個足夠龐大的消費市場,那么高耗費的技術投入終將面臨嚴重的瓶頸。蘇聯曾依靠舉國體制開發出電子計算機,但由于缺乏一個足夠龐大的市場,蘇聯的計算機以及電子產品沒有機會不斷試錯、不斷改良,不斷學習經驗、不斷積累能力。蘇聯沒有美國的消費群體,缺乏足夠的國內外消費者購買私人飛機、私人游艇、錄像機、電視機、照相機、家用電腦等。和美國相比,蘇聯的消費市場不足;和日本相比,嚴重依賴經濟計劃的蘇聯的消費市場也顯著不足。相關數據顯示,1990年,蘇聯汽車工廠生產了將近200萬輛汽車,其中有120萬輛轎車和78萬輛卡車。此時,蘇聯的汽車產量甚至低于十年前的水平(Siegelbaum, 2008)。與日本依靠消費來改進技術不同,蘇聯缺乏一個相應的市場來反饋到生產,激勵生產。研究者發現,與西方發達國家制造的汽車相比,蘇聯汽車存在明顯的技術缺陷,蘇聯的廠商無法向消費者提供質量保證。1960年,蘇聯人為他們的汽車保修6個月或1萬公里;同年,美國的福特汽車將保修期延長到24個月或3.8萬公里(Sanchez-Sibony, 2014)。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就是讓“新型舉國體制”產出的技術產品有多樣化的反饋,有多元化的試錯,有多渠道的改進。
拓展“新型舉國體制”的國際市場。和蘇聯相比,美國的IBM公司在西方世界安裝了70%的計算機,它和其他三家美國公司一起占據了全球計算機市場90%的份額(拜倫德,2016)。由于有世界市場的支撐,美國的計算機產業獲得了更多的資金和技術積累。日本亦然,和蘇聯相比,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就能向世界市場出口技術產品。國際市場的開拓帶動了出口的增加,出口不僅通過增加產出促進了經濟增長,產量的增長還通過大規模生產降低了成本;同時,出口部門進入競爭激烈的海外市場也推動了國內生產效率的改進。通過開拓龐大的世界市場,日本的科技發展穩步推進。1950年,日本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服裝、玩具、紡織類產品;到了1975年,日本出口最多的產品包括鋼鐵、船舶、汽車、收音機等(彭佩爾,2006)。從出口價值來看,自1960年至1970年,日本的鋼鐵產量增長了大約7倍,船舶、金屬制品、摩托車出口增長了5倍,汽車出口增長了4倍(Andressen, 2002)。由于日本存在巨大的國際市場,日本人引進、吸收、擴散外來技術的動力更強勁。蘇聯則不同,購買技術許可證通常被蘇聯人視為一種替代進口的手段,而不是促進出口的手段。獲得技術以后,日本總是積極去改進,而蘇聯則缺乏這樣的努力(Josef, 1985)。當前,通過拓展國際市場,依托內循環,推進外循環,“新型舉國體制”下的新技術將有更廣闊的發展平臺。
綜上所述,蘇聯傳統舉國體制的困境在于:蘇聯既難以為技術發展提供持續的資金支持,又難以為技術產品的改進提供廣闊的試錯平臺,還難以為技術研發的失敗提供多樣的替代選擇。而整合“民用市場”“消費市場”“國際市場”三個市場的意義在于:一個廣闊的市場既提供了持續的資金來源,又為技術產品的改進提供廣闊的試錯平臺,還為技術研發的失敗提供多樣的替代選擇。因此,建設“新型舉國體制”,就需要統籌發展與安全,激發市場活力,依托“超大市場規模”來支撐“舉國體制”。當前,發揮我國“超大市場規模”優勢,促進國內與國際“雙循環”,正是用大市場的力量來補充傳統舉國體制的不足,挖掘“新型舉國體制”的新動能和新優勢。
宏觀環境體系的演化邏輯:新型舉國體制以自立自強為核心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動力系統
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交織、相互激蕩、相互影響,中國發展面臨的環境、任務和需要解決問題的復雜程度已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在此背景下,中國開啟了邁向創新型國家前列和建設科技強國的新征程。未來我們將面臨愈加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和諸多新問題和新任務,統籌好“兩個大局”,必須要有大戰略,關鍵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中華民族奮斗的戰略基點。
新型舉國體制是在建成科技強國目標下,我國從科技大國邁向科技強國的有力保障。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了到2035年我國發展總體目標和未來5年目標任務。就科技發展而言,到2035年,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大幅躍升,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建成科技強國;未來5年,科技自立自強能力顯著提升。科技強國是科技原創水平高、創新引領能力強、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和世界影響力強的國家,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前提條件和戰略支撐,是應對世界變局、實現民族復興的基石,是由發展中大國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丁明磊、黃琪軒,2022)。面向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進一步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的根本性變化,以及在若干重要技術領域逐步形成先發優勢,建設新型國際科技合作關系等,都對科技創新發展提出了新的需求。我們要抓住新時代發展的新機遇,緊密圍繞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需求,發揮綜合優勢,推動科技發展邁上新臺階。
我國正在從科技大國邁向科技強國。我國的科技實力正處于從攻堅突破、加速追趕轉向自主可控、原創引領,從全球創新跟隨者、參與者轉向引領者、貢獻者的新階段。隨著我國的科技創新從跟跑為主邁向并跑為主,應著眼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堅持底線思維、問題導向,立足當前、謀劃長遠;著眼科技發展及經濟社會的關鍵問題,“向科技要答案”,實現“科技突圍”,確保經濟發展不失速、科技發展不中斷,不斷提升我國發展的獨立性、自主性和安全性,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中的支撐引領作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關鍵變量作用。
新型舉國體制以自立自強為內核,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是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重要歷史經驗,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要求。當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疊加,逆全球化盛行,單邊主義、保守主義盛行,國際環境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重塑,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國際政治經濟格局進入深度重構期,大國博弈呈現高度競合態勢,科技創新日益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要戰場,對科技創新制高點的競爭空前激烈。圍繞高科技的封鎖與反封鎖、脫鉤與反脫鉤逐漸展開,成為大國科技競爭“新常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僅在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加大對我國的打壓力度,通過強化對我國多邊出口管制、建立各類技術聯盟、主導科技規則話語權等形式和重塑技術規則、領導技術標準制定等手段,體系化地加強對我國的科技遏制。我國科技領域的外部安全風險仍會持續存在,部分領域風險繼續加大。關鍵核心技術成為科技自立自強的基礎和大國競爭的利器,能否迎難而上抓住科技革命的時代機遇,提升科技創新的體系化能力,前瞻部署戰略科技力量,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
新型舉國體制下的自立自強以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科學技術原創能力強大、重大原創科學思想和科技成果持續產出,優質創新要素高度集聚、創新人才層出不窮、社會充滿創新活力為標志,以堅持自主創新與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合作的辯證統一為特征(劉垠,2022),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支撐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在當前國內外形勢下,健全新型舉國體制,一是為了突破“卡脖子”技術及更大范圍內的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科技突圍,確保科技安全、產業鏈安全乃至國家發展安全;二是為了面向大國戰略博弈贏得主動權,占據有利、主導地位,為構建新的國際話語體系、敘事體系提供堅強支撐。通過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實現“卡脖子”技術突破、若干重大領域關鍵技術引領、未來顛覆性技術領先、技術原創能力和產業創新能力全面提升,在科技領域掌握主動權,在產業高端環節掌握話語權,并以關鍵技術攻關提供新動能,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人類整體科技水平提升。
新型舉國體制強調科技與經濟發展的互動和“正反饋”循環,提高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和促進高質量發展。世界發展的歷史表明,經濟周期與科技革命呈現高度關聯性、耦合性特征。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世界經濟結構深度調整與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變革形成歷史交匯,發展的新能量不斷集聚,可能成為全球生產力新躍升的突破口,對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全局性的影響。從最近幾十年發展看,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關系更加密切。隨著數字化時代科技成果轉化應用周期逐步縮短,科學和技術日益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要素,并在經濟短周期演化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隨著新技術、新產品大規模加入經濟循環,不斷創造新需求、新市場,既能形成新的發展方向和增長點,也可校正經濟發展的走向,在短時間內能夠再度推動經濟繁榮。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各國創新戰略部署進一步積累了突破變革的能量,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正在加速孕育,有可能為新一輪經濟復蘇帶來重大機遇。
從長期看,我國處于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共存并逐步向以創新驅動為主轉變的關鍵時期。支撐發展的要素條件以及競爭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傳統要素的驅動力減弱,依靠科技創新加快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的任務非常迫切。由于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不斷涌現,我們面臨的規則和賽場正在發生變化,迫切需要加快培育應對新規則和新賽場的能力。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我國較好地利用了后發優勢,通過要素和投資驅動,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隨著發展階段的不斷推進和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我們利用后發優勢的空間日益縮小,傳統要素投入的邊際效益日益遞減,迫切需要在繼續用足用好后發優勢的同時,依靠科技創新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通過新要素的高效組合,形成更高水平的生產力,拓展新的戰略空間,實現高質量發展。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和科技強國建設目標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提出新使命和新要求。健全新型舉國體制要運用新的思路推動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從而提升整體效能,通過不斷加強科技與經濟發展的互動和正反饋循環,提升科技引領能力和破局能力,實現經濟發展的高效率和高質量;通過培育科技領軍企業、推進新技術應用、謀劃未來產業、打造創新高地等,謀劃和搶占未來產業發展先機和新賽道,促進數字經濟和智能化變革,打造經濟發展新動能,引領新一輪技術經濟長周期和新范式,塑造新時代更多的“先發優勢”,有力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越走越寬廣。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科技支撐的思路與重點任務
黨的二十大報告擘畫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科技支撐,要堅持黨對科技創新的全面領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堅持激發市場動力和發揮政府引導作用相結合,堅持獨立自主、自立自強,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題,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以市場應用為目標,加強戰略謀劃和系統布局,把政府、市場、社會有機結合起來,把研發、生產、消費同步統籌起來,集中優勢、分工協作,推動技術自主能力和國際影響力雙提升,推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新型舉國體制要將“集中力量辦大事”與“激發全社會創新創造活力”有機結合,實現體制機制“破局”。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一道世界性經濟學難題,也是考察各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面(王偉域,2021)。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與市場有機結合,構成了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的核心優勢。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將“集中力量辦大事”與“激發全社會創新創造活力”有機結合,是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必然要求。
新型舉國體制要實現體制機制“破局”,發展市場化創新機制,構建有利于創新發展的市場競爭環境、產權制度、投融資體制、分配制度和人才培養引進使用機制,形成有利于激發全社會創造力的體制,培育有利于創新資源高效配置和創新潛能充分釋放的社會環境,筑牢發揮科技創新先發優勢的制度基礎。同時,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需要政府加強資源配置優化統籌,加強對重點前沿問題、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等的戰略部署,加快對關鍵領域的戰略部署和傾斜式資源配置,加快實現重點突破。
新型舉國體制要以長期主義和“超越競爭”促進各類創新要素的新組合和合理流動,克服各類問題和障礙。我國生產函數正在發生變化,經濟發展的要素條件、組合方式、配置效率發生改變,面臨的硬約束明顯增多,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成為多重約束下求最優解的過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階段,必須解決好質的問題,在質的大幅提升中實現量的持續增長(劉鶴,2021)。“超越競爭”的新型舉國體制是當前形勢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和內在要求。這意味著以長期的、合作的思維,重新理解和解決目前我們市場經濟在發展中產生的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上的問題,優化戰略、決策和行為,以長期主義和協同合作促進各類創新要素的新組合與合理流動,激勵技術創新,這也是長期戰略能力、創新能力、合作能力的體現(本力,2022)。
當前,健全新型舉國體制仍面臨以下問題和需求:一是面向前沿科技的原創力不足,面向經濟主戰場的產業技術創新主導力不足,面向國家戰略需求的重大創新組織力不足,面向全球價值鏈競爭的關鍵環節控制力不足和面向全球創新資源配置的吸引力不足。二是我國科學技術儲備有待進一步加強,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還未得到根本解決,產業總體上還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科技創新累計投入仍然不足,與發達國家有進一步拉大差距的風險。三是有利于創新驅動的市場環境尚待完善。全社會消費需求特別是帶動經濟增長的新產品新技術消費需求還未得到有效釋放,企業技術創新主體作用發揮不夠,傳統的行政審批、市場準入、標準規范和監管體系制約創新產品的應用發展。四是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格局還未形成。近年來,中央和地方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激勵創新的政策,但部分創新政策落實尚不到位,政策宣傳解讀以及評估監督不足,創新政策制定和實施部門協調難度大,消減了政策的實施效果,同時還存在對新規則和新賽道變化的戰略應對能力不足等問題。
新型舉國體制要以國家戰略需求和問題為導向,做到六個方面的“統一”和五個方面的“堅持”。通過歷史比較分析,健全新型舉國體制需要堅持國家戰略需求導向和問題導向,實現六個方面的統一(丁明磊、黃琪軒,2022):一是新型舉國體制要做到安全競爭與經濟博弈二者并行不悖;二是新型舉國體制要實現政府引導與市場激勵二者交融互補;三是新型舉國體制強調技術生產與技術消費二者齊頭并進;四是新型舉國體制要實現集中攻關和分散試錯二者協力互助;五是新型舉國體制要推動技術自主與技術分工二者相互促進;六是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堅定創新自信與弘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精神譜系相互輝映。
在新型舉國體制的實現路徑上,應當著力堅持以下原則:一是堅持把科技創新作為未來的投資重點和優先領域,引導全社會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充分釋放全社會的創新活力。二是堅持培育新增長點與促進傳統產業升級并重。既要重視提升傳統產業整體創新能力,避免放棄基礎和優勢來打造新動力的急躁,又要重視依靠創新培育新產業,避免錯失產業變革帶來的跨越式發展機遇。三是堅持培育內生能力與整合國際市場資源相結合。充分利用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統籌發揮好內需與外需、內資與外資、內智與外智的作用,形成全方位更高水平的開放創新發展新格局。四是堅持促進創新供給與有效激發創新需求相結合。既要加大科技創新的研發及應用,不斷提高創新產品供給,又要加強需求引導,清除市場障礙,為新技術新產品的應用創造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五是堅持強化創新政策執行與增強精準性協同性并重。完善創新政策落實機制,促進各方改革協同推進,狠抓落實,確保已有政策執行到位;進一步深化改革,不斷提高創新政策精準性和實效性。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措施與政策建議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要以改革驅動創新、以創新驅動發展,改善創新制度供給,加強創新政策整體設計和協調配合,推動政策向創新鏈條一體化整體設計轉變,構建有利于創新的生態環境。通過政策引導,充分調動各類創新主體和全社會的創新積極性。
第一,通過實施一批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突破“卡脖子”技術,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抓緊部署實施一批面向未來的、能夠體現國家戰略意圖、牽引未來經濟增長的重大科技項目和工程。瞄準事關我國產業、經濟和國家安全的若干重點領域及重大任務,研判具有先發優勢的關鍵技術、引領未來的基礎前沿技術,做好國家戰略需求規劃和攻關技術清單凝練,形成完整的目標、任務、時間節點計劃。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重點研發具有先發優勢的關鍵技術和引領未來發展的基礎前沿技術。完善突破“卡脖子”技術的體制機制,建立統一高效的決策指揮體系、有力的動員機制和責任落實機制。統籌各方力量形成可復制、可推廣、自驅動的攻關模式,使產、學、研、金、服等市場主體發揮能動性。
第二,堅持把能力建設作為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基礎,加快提高科技創新的戰略牽引和源頭供給能力。加強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任務的創新載體布局,提高創新創業的要素聚集能力,在整合現有科技創新資源的基礎上,加快建設一批國家實驗室、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等,打造引領發展的戰略科技力量和平臺,探索現代化運行機制,促進產學研協同與國內外創新資源整合,發揮對國家戰略目標的支撐作用。以重大場景引領科技創新,圍繞鄉村振興、制造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等國家重大應用場景,發掘面向未來的新需求、新應用,創造新場景。加快建設新型現代化通用基礎設施,重點加快構建高速低費、泛在智能、安全可控的新一代國家信息基礎設施,為經濟社會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第三,通過不斷完善新型舉國體制重塑科技創新全鏈條,著力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效能。推動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和活力社會更好結合,科學統籌、集中力量、優化機制、協同攻關,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提升體系化能力和重點突破能力,不斷完善高效、協同、開放的國家創新體系。發揮好政府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的組織作用,加強有組織科研,構建協同攻關的組織運行機制,布局戰略科技力量建設,向體制化、體系化、協同化方向發展。強化企業的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緊緊圍繞培育和提升微觀企業創新能力目標,強化市場在企業創新競爭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推進構建以競爭中性為原則的創新政策體系,發展高效強大的共性技術供給體系,提高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成效,全面鏈接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強化跨部門、跨學科、跨軍民、跨央地整合優勢資源和力量。
第四,建立長周期的科教資源協同機制,將新型舉國體制與我國人力資本、市場需求和產業體系及產業鏈優勢相結合。從改變教育和人才培養方式入手,強調把創新思維貫穿于學前教育、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加強科教結合、產教結合,培養人才,將青少年科技教育定位到創新人才培養最前端,以形成更好的人才制度優勢。深化科教協同,加強科學技術前沿問題科研布局和高校學科設置布局的協同互動,形成貫通式創新人才培養體系。堅持引育并重,打造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同時,既要引導弘揚中華傳統的創新精神如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等,也要引導吸收全球多元的創新文化,為營造多元包容的創新環境提供政策支持。
第五,增強改革協同性,形成重大政策措施的聯動效應。高度重視科技創新作用,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加強各項改革措施的協調聯動,做好制度銜接,形成目標一致、相互配合的政策合力。要統籌推進科技領域改革和其他領域改革,狠抓落實,通過評估監督、典型推廣、宣傳引導等多種方式,進一步推進改革及政策的落地。要加強部門間政策協調,把創新政策融合到科技、產業、貿易、教育、財政、金融等各項政策中,各部門政策要體現支持創新的重要導向。要加強中央與地方的政策和行動協調。同時,要根據技術進步、環境保護的要求定期更新技術政策,清理落后的技術規范、標準,為新技術的應用清除障礙。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項目編號:20VMG036]、科技部研究專項“面向科技強國建設的科技能力體系化構建與提升路徑研究”和國家高端智庫重點研究課題“開放合作支撐科技自立自強的路徑、政策和保障措施研究”的階段性成果;科學技術部吳家喜博士、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秦錚博士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本力,2022,《全國統一大市場關鍵在于“超越競爭”》,新經濟學家公眾號,6月2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4487226473435618&wfr=spider&for=pc。
查默斯·約翰遜,2010,《通產省與日本奇跡:產業政策的成長》,金毅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丁明磊、黃琪軒,2022,《以新型舉國體制為加快建設科技強國提供有力支撐》,《國家治理》, 第23期,第40~45頁。
都留重人,1992,《日本經濟奇跡的終結》,馬成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劉鶴,2021,《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11月24日,第6版。
劉垠,2022,《聚焦自立自強 科技政策該如何發力》,《科技日報》,12月20日,第2版。
彭佩爾,2006,《日本的對外經濟政策:國際行為的國內基礎》,彼得·卡岑斯坦編,《權力與財富之間》,陳剛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習近平,2022,《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0月17日,第1~5版。
王偉域,2021,《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經濟研究信息》,第1期, 第17~18頁。
伊萬·拜倫德,2016,《20世紀歐洲經濟史:從自由放任到全球化》,徐昂譯,上海:格致出版社。
亞歷山大·格申克龍,2012,《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張鳳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趙鼎新,2015,《社會科學研究的困境:從與自然科學的區別談起》,《社會學評論》,第4期,第3~18頁。
趙永新,2021,《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權威訪談·邁好第一步,見到新氣象②)——訪科技部黨組書記、部長王志剛》,《人民日報》,1月2日,第4版。
C. B. Josef, 1985, "Soviet-Western Trad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n Economic Overview," in Bruce Parrott (ed.), Trade, Technology, and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S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urtis Andressen, 2002, A Short History of Japan: From Samurai to Sony, Sydney, Australia: Allen & Unwim.
George Holliday, 1979, Technology Transfer to the USSR, 1927-1937 and 1966-1975: The Role of Western Technology in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Boulder, Colo., USA: Westview Press.
J. C. Timothy; Thane Gustafson, 1990, Soldiers and the Soviet Stat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from Brezhnev to Gorbachev, Princeton, NJ, US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effrey A. Hart, 1992, Rival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Western Europe, Ithaca, NY, US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J. Wilczynski, 1974, Technology in Comecon: Accelera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rough Economic Planning and the Market, London, UK: Macmillan.
Lewis Siegelbaum, 2008, Cars for Comrades: The Life of the Soviet Automobile, Ithaca, NY, US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ariana Mazzucato, 2013,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London, UK: Anthem Press.
Oscar Sanchez-Sibony, 2014, Red Globaliz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oviet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New York,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 J. Samuels, 1996, Rich Nation, Strong Ar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Ithaca, NY, US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erutomo Ozawa, 2005, Institution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Japan: The 'Flying-Geese' Paradigm of Catch-Up Growth,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Timothy W. Luke, 1985, "Technology and Soviet Foreign Trad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n Underdeveloped Super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9(3), pp. 327-353.
責 編/張 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