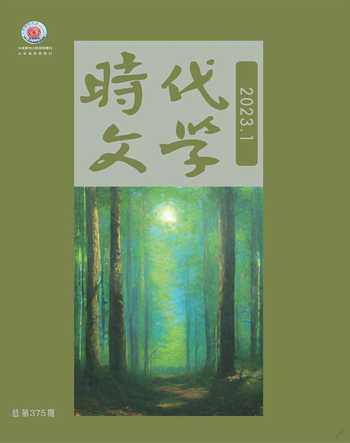印象記:不鳴則已的一鳴
張清華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這聲響亮,最初來自在山東博興縣最南端的一個村子里。
博興,古時為千乘,其南苑與齊國都城臨淄搭界,而齊被稱為“千乘之國”,可見博興一帶戰國時即為齊國屯兵的地方。這在軍事上是完全說得過去的,拱衛都城嘛。加之,這一帶屬魯中平原,南部為低矮的丘陵,臨淄及以北則均是一馬平川的大平原,便于用兵,且須屯以重兵,故稱千乘也。
千乘出了孝子董永,《世說新語》開篇不久就說了董永的故事。而未被人加工過的版本里說,董永因為家貧,父死無錢治喪,便賣身葬父。守喪三年后,董永要履行自己的契約,去給大戶人家當奴,但沒想到這位鄉紳為人厚道,念他孝順,不要他干活。而董永生性誠篤,定要信守承諾,這感動了天上的仙女,以他媳婦的名義,幫他給財主織了一百匹生絲。完工后,二人各歸其家,相忘于江湖,并無痛苦掙扎,也沒有黑暗勢力的阻撓。
說這些,是因為要說博興的歷史地理,大平原,靠近齊都,史上有淳厚的民風,而這是一鳴的生長之地。
說來,一鳴的老家那個村子,已是博興縣的最南端了。在一片海一樣的綠色中,他站在故鄉的地平線上,從青紗帳出發,發出了嘹亮的鳴聲。
我與一鳴相識,其實已是多年以后。我與他同出生于博興縣,但我的家鄉是濱湖一帶的水鄉,與他相隔大概近三十里,所以童年自然是未曾謀面了。后來我大學畢業分配至魯北小城濱州,便聞知了他大名。
一鳴之名氣,可不是一般的響亮,那些年文學是熱門,城市再小,也有一大群文學青年,濱州的文學圈子,提起一鳴沒有不帶著贊許的。可巧那時,一鳴又跑去省城讀書了,而我與他交叉換位,分配到濱州一座師范院校的中文系任教。便只能聞其名,而未能見其人了。
再后來又是若干年,我考取了研究生,回到了省城母校任教,那時再來濱州,才真正見到了一鳴。
彼時的一鳴,已然是真正的青年才俊了,已在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散文,且以剛及三十歲的年紀,已經做到了醫學院的院長辦公室主任;后來在三十五歲時,又一鳴驚人,擔任了醫學院副校長,在職業生涯中,已是占盡風頭,成為小城的青年領袖。至于他和同事們到煙臺海邊篳路藍縷創建大學新校區,那是后話了。
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我終于在一位作家朋友的研討會上,真正見識了才華橫溢、出口成章的李一鳴。
一鳴年輕的時候,確乎是一表人才的,一頭濃密的黑發,高高的個兒,一雙活脫脫的大眼,身材修長且挺拔,就像魯北平原上迎風挺立的一棵白楊——只是膚色稍顯深了一點,談不上黑,反而是如今時髦的“小麥色”。走在路上,一頭詩人的發式,一甩一甩的,見人先笑,一口雪白的牙齒露出來,極富感染力。
一鳴事業上的成功,興許與這副喜人待見的形象有關。誰不喜歡開朗、帥氣的小伙兒,有才而不任性,自信而不高傲,聰明又不耍聰明,確乎是一鳴的做人之道。這當然不是修養出來的,更不是裝出來的,而是先天如此,骨子里帶來的。
這就有了少年得志的一鳴,從那以后,一鳴的人生就是一路飛奔的節奏。
一鳴有一個絕活兒,見過的人都不會忘記,就是可以當場作詩;不但作詩,還即興朗誦出來,一邊想著,一邊嘴里就鏗鏘有力、抑揚頓挫地溜達出來了;不但溜達出來,而且充滿不動聲色的詼諧、現編現造的調皮,讓所有人都笑得捧腹,笑得臉上的肌肉都疲勞酸軟。
那以后,每次有一鳴的場合,最后都要讓他表現這絕活兒。有時會是年紀稍長或有權威的人出題目,有時會讓他現場為每一個人作一首。那效果,至今想起來,還讓人忍俊不禁,仿佛一鳴那一口潔白的牙齒在吐露珍珠瑪瑙,弄得大家滿地找牙——不是被那調皮的詞語給打掉的,是被那爽朗的笑聲給累掉的。
如今,大家聚在一起,他不乏活躍而生動,但那活躍生動里,常常透出老成持重,畢竟,生活的風霜會在人的年輪上刻下印痕,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把這老成與活潑疊合起來,歲月帶走的最美好的年華,總是讓人憶念懷想。
一鳴的文字,樸素而直接,情感飽滿,喜歡歌吟他的故鄉——也是我的故鄉,禮贊那大平原上的一切,那里的莊稼草木,那里的鄉人親友,那里的土地風物,那里的人情百態,對我來說,都是再親切不過的了。讀之會疑心,難不成這是我的文字嗎?
自然,那是此前的一鳴,那時他是一鳴驚其人,如今再鳴則是驚其國了,這國當然主要還是說其同行,其界別。但一鳴的影響,確乎已溢出了故鄉那塊土地,到達了更遠的遠方。一鳴依然低調,并沒有做出一副專事寫作的樣子,端著架子寫散文,還依然是一副頑皮的做派,書寫著他所經歷、所感受的一切。
但散文新作《在路上》,與早期一鳴的作品比,卻有了變化。至少我是感覺到了他的認真,他確乎是開始“下功夫”地寫作了。我注意到,作為自選集,他刻意選擇了那些最能反映他“一路走來”的人生經歷的篇章,“那些人”“那些年”“那些事”“那些地”,分別收羅了他對故友故知、往昔時光、身歷事件、走過地方的描繪,寄托了他對生命歷程的追憶與眷懷。
他做功課是認真的,就像開篇的《遠眺華不注》,就從學生時代的一堂課蕩開,從孔孚先生的詩,談到了元人趙孟頫的畫,從《詩經》談到了李白,從元好問扯到了周密,從《左傳》扯到了《水經注》,幾乎是集三千載于片紙之間,納九萬里于尺幅之內,從容談笑,就把一首詩、一座山、一個涵納古今的故事,渲染得淋漓盡致,叫人讀之愛不釋手。
也長知識。
一鳴的散文其實是很講章法的,不做作,喜實錄,但始終有個“我”在里頭,在現場。人在旅途中,情在山水間,這樣節奏與境界就全出來了,這就叫“有我之境”。《過無錫》《彭山訪故人記》《每逢暮雨倍思卿》諸篇皆是如此,上下古今,思接千載,把古人的命運與處境,通過環境與物的點染醞釀,活脫脫地表現出來,讀之叫人意興湍飛,浮想聯翩,沒法不拍案叫好。
當然我也很喜歡他那些寫童年、憶往昔、懷故人的篇什,如《串楊葉》中,家庭突生變故,懵懂少年的莫名迷惘與悲戚心境,讀之令人愀然;《在路上》中,他清寒且帶著屈辱的童年也叫人揪心;而他一路走來的成長履歷與酸甜苦辣,與多年后孩子考入北大、親子一起漫步燕園的那份喜悅,則叫人百感交集;還有那些記錄他溫暖的家庭生活的篇章,讀之也令人心生艷羨。因為通常人們都不太會在散文中書寫此類內容,而一鳴則毫不隱諱地寫了出來,確乎顯出了他情感的純良與樸實,實在是難得。
常想,文字之道,其實就在乎文字后面的那個人,修身與修心,人物的胸襟就是文字的質地,人的內心即是文章的境界。一鳴正是如此,常人會覺得一鳴有外向的一面,有詼諧的一刻,但他文章中的誠樸,確乎在印證著他的為人。一鳴是有襟懷、懷著大愛的,是一直堅守人生底線與精神之邊界的人,所以才會有了這般令人欣悅的文字。
光陰似箭,白駒過隙。我此刻還在想著一鳴在近二十年中的兩次“蛙跳”。一次是考博士,我在調至北京工作之前,恰巧有機會做了一鳴考博的引渡人,他在四十多歲時考上華中師范大學的博士,上了這班快車,對他以后的人生產生了深遠影響。還有一次就是十年前,他參加全國公選,進入了中國作家協會工作,從一個地方醫學院的副校長位置,來到中國作協工作。這委實是兩次長距離的跨越,因為工作環境的差異,會使他在邁出這兩步時面臨抉擇的困惑。
然而一鳴確是有決斷的人。那時我曾略略擔心,他跨越不同行當,來到人才薈萃、翹楚靡集的中國作家協會,會不會有某種程度的不適。可是并沒有,他一來就如魚得水,人見人愛,工作得熱火朝天了。
這次系統地讀一鳴的散文,除了文字上的收獲,其實也解開了我積久的一個疑問:究竟一鳴為了什么,必定要邁出這南轅北轍的一步,我總算真正懂得了。因為在一鳴的心中,最核心也最原本的那個夢,其實不是別的,乃是文學。青山遮不住,他必定會走出這一步。因為他屬于文學,經過了那么多年的準備,繞了那么遠的路,他最終還是要回歸屬于他的正途。
是的,這會兒,他正在東土城路那棟大樓里,在眾多大家名宿出入的那座殿堂里,心安理得、安之若素地忙碌著,調度著,扮演著屬于他的那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鳴是快樂的,他的快樂,既來源于一種有著難以言喻之神妙的“文學生活”,也來源于比那生活更為久遠的文學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