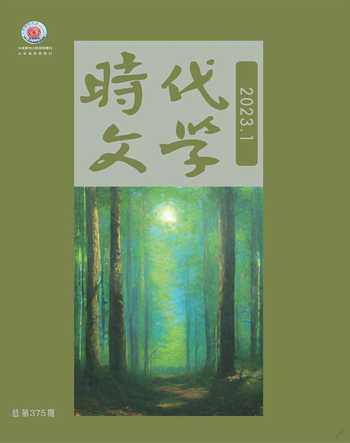隱沒
趙飛燕
“棗紅馬,奮蹄歡騰;長嘶鳴,它也知回歸故里任馳騁。”
風竄過屋子,生了鐵銹的窗戶片子被推搡著吱呀叫喊,拉長的陽光被搗碎一片,斜灑在灰匿的犄角旮旯。糖餳起色,加火燒開,放入泡好的油粉絲,將白細的內酯豆腐倒進油鍋煎炒。巧英嬸兒哼著晉劇炒著菜,氣色卻不減當年,麻利的勁頭不輸那些婆娘們。這幢教職工宿舍的同志們搬的搬走的走,一年下來,新人送舊人便成了常態。城東拆危房,城西起高樓,唯有這背靠天主教堂的兩幢蝸居小樓沒有被歲月淹沒。巧英嬸兒掀開六棱角的木制調料盤兒,撒了把蔥花芝 麻,淋上香油,整個樓道便都是嫩豆腐的味道了。
晌午,學生放學,輕重不一的腳步聲從頭頂咣咣傳來。電瓶車的鳴笛和孩子們嬉笑的叫喊,剎那間劃破了小樓的死寂,也讓這年久失修的老房子有了點生氣。三輪車嘎吱嘎吱地叫嚷,男人呼哧呼哧地喘息,女人潑辣豪邁地催促。“啪嗒”一聲,那是新搬來的對門兒開鎖的聲音。日子如煙,往往總是送走那舊人迎新人。
方寸的陽光窸窸窣窣灑在剛出鍋的豆腐上,也別有一番味。門廳的門沒有關,風穿堂涌入,日歷的扉頁被掀開,在嘈雜的風里沙沙作響。
巧英嬸兒老兩口是前年才搬過來的,自從住進這個小樓,生活便波瀾不驚,如石子墜入深水,不見半分水花。城很小,巷子也很窄,風卻吹不到從前。故人在慢慢離去,往事似乎被時間遺忘。巧英嬸兒看著日歷,漸漸回想起幾年前的舊事。
1
“云淡天高南飛雁,霜染紅葉景朦朧。”
“依依遠村二三里,雀鳥歸巢繞樹林。”
巧英嬸兒愛花,是遠近出了名的花大嬸。野貓發困橫臥在花盆里,壓毀了無數新芽,倚斷了剛努出的嫩枝,看見巧英嬸兒出來,慌得四下逃竄。拿著笤帚的巧英嬸兒四處尋貓,誓要與這“毀花大盜”斗個高下。可終究還是那野貓腿腳靈,此后,庭院便再無貓的痕跡。
別人的院子空空蕩蕩,或許拉根鐵絲晾衣服,便已是生活的全部,巧英嬸兒卻拉著鐵絲養牽牛花,四下里斜斜密密地扯著網,編成一堵春天的花墻。午后,暖風輕輕地吹著,總帶來些花香。巧英嬸兒躺在院落的藤椅上,側臉數著還沒冒芽的花骨朵, 漸漸閉住眼睛。
巧英嬸兒那個年代從不輕言愛,誰也不知道愛是什么。規矩地遵守生活安排,便是最大的本分。退了休的老漢總喜歡研究《易經》,戴著厚厚的老花鏡,掀著一沓信紙寫著什么。似乎字里行間都是學問,但讓他離了那書本說上兩句,卻也只會些陰陽八卦。巧英嬸兒總戲謔地說他不懂裝懂,除了看書啥也不會。殊不知清早院子里的花全是老漢一人澆的。澆多澆少,已經被仔細地測算過。后院的鄰居每次推著大梁自行車咣咣路過,只發現花一日勝于一日,根莖粗壯,葉子肥綠, 整個巷子里洋溢著晚春的氣息。
又或許這院子里的花,不只是巧英嬸兒一人的。
每天人們來來往往,都會駐足欣賞一番,才會興致盎然地各回各家。
紀瞎子是這城里出了名的風水先生,后院有鄰居趕著春天辦喜事,邀他在院子里算算祭拜方位。紀老先生拄著拐杖從前院穿堂,駐足停留,只言這里有靈氣,興許是將春神請進了家。從那時起,這方院子便更有了生氣。巧英嬸兒的街坊經常聚在一起拉家常,扯天說地好不痛快,各家難念的經也往往在一杯茶、幾支煙的消磨中漸漸淡去。或許,也正是從那時起,庭院不僅有了春氣,更有了人間生活氣。
傍晚,淺紫色的牽牛花簇擁著春日的陽光,在風里搖曳。老漢擔著水桶去“水點”把水缸挑滿,巧英嬸兒哼著曲在院落的廚房里做飯。炊煙在空蕩蕩的天上升起,又似乎在書寫著什么。縹緲的煙,繾綣地打著彎,和那被打散的斜陽將天空染成了模糊的金黃色,仿佛兩面煎至焦黃的荷包蛋。
二弟從鄉下騎車進了城。長姐當母,他是巧英嬸兒從小背大的。姐弟倆一向感情深厚。他將一袋子窩子面放在門廳的地上,還帶來了兩罐子剛煮的咸菜。莊稼人面朝黃土背朝天辛苦勞作了一輩子,最幸福的時刻,莫過于糧菜豐足。姐弟二人坐在院中,一邊喝茶一邊寒暄,聊著各自兒女的近況。似乎每年都在變,又似乎每年都沒變。隨著人的年歲漸大,最怕的不是重逢,而是分離。時間推搡著人往前走,誰都無法幸免。巧英嬸兒的母親不喜歡城里的空氣,去年索性隨著她二弟住到了鄉下,可她近來胃口大減,不思飲食,睡眠也不好。
二弟望著一方花墻,縫隙之間卻怎么也看不到太陽。他蹙著眉,講著老母的近況。人老了,或許花期也將近,總以為什么都看開了,又似乎什么也沒看開。有的時候,只是不愿再去想,不愿再與時間紛爭,以為落了一處安閑,心口卻空落落地漏風。吃過晚飯,二弟又騎車趕回鄉下,臨走叮囑巧英嬸兒記得回鄉下看望母親。
午夜,春雨淋漓,牽牛花瓣散落一地。雨中彌漫著的草葉香縈繞在巧英嬸兒的夢中,卻怎么也走不出夢的桎梏。清早驚醒,她佝僂著背,撐傘在庭院中久久凝神佇立,豆大的雨珠子壓彎了花枝。可她卻無心看這滿院的春色,暗暗焦急母親的身體,惱恨自己被這不絕春雨困住了腿腳。有時候,歲月真叫人惱,難事事順心,無法得償所愿,只能慢慢等著。等什么?等待戈多嗎?我們不知道,可能是等花期,又或是等待春天。
2
“漁樵互答盡鄉音,農夫荷鋤田間走。”
“擔頭春酒一瓢多,樹底看山樹底過。”
院井四四方方的天,蒙上了黑色的網。阻斷了惡狠狠的太陽光,卻逃不過酷暑的高溫。老漢緊閉著窗,嚴磕著門,舍不得讓門廳里空調吹出來的冷氣四散出去。德順,是老漢去年養的一只小土狗的名字,它窩在桌腿肚子旁,正吐著舌頭長哈氣。老漢邊吃飯邊用筷子逗弄它,巧英嬸兒看了一個勁兒地說他,嫌這不衛生。老漢卻總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繼續逗弄著德順。
電視里循環播報著新聞,這臺老舊電視年久失修,畫質差,聲音也不好。“刺刺啦啦”的,需要細心再細心才能聽得清。吃過午飯,巧英嬸兒總喜歡在床上側臥著,撐著腦袋打瞌睡。老漢將背心摟在胸前,坐在沙發上,看國際新聞。門廳里的空調早關了,風扇還在左搖右晃地轉著頭,風扇葉劃過空氣的摩擦聲伴著新聞里渾厚的男聲,卻怎么也壓不住已經熟睡的巧英嬸兒的鼾聲。這似乎吵到了臥在老漢鞋旁的德順,它竟不滿地翻了個身,重新找個舒服的位置繼續睡。老漢看著巧英嬸兒,也不滿地把電視的聲音再次調高。
也不知是什么時候,這院子里又熱鬧起來。不再是因為春神的傳言,卻是二拐子的風言風語塞滿了整條巷子。二拐子守寡好多年,兩個兒子都已各自成家,平時就她一個人住在小巷盡頭的一個大雜院里。
事情要從后院鄰居漢林平白無故要在家里養鴿子說起。酷熱的天,人禽共生,且不說衛生與否,長長的臭味充斥著整個庭院。妻子險些被他這興起的養殖業鬧得離婚,帶兒子大包小包搬離了院子。漢林竟也不管不顧,一根筋地喂養起了鴿子。
似乎自那時起,二拐子便天天一瘸一拐地往院子里跑。每次來,總要帶些剩菜葉子,說是給漢林的鴿子吃。有時還會帶一些她做的飯給漢林吃。她雖腿瘸,卻從不拄拐,兩腳落地總輕重不一,好像是用右腿支撐,拖拽著左腿前進。
她總穿著那件頭刮出線頭的西瓜紅T 恤,那件T恤洗得發白。灰格褲子的屁股后面總不干凈,整個人邋里邋遢,卻又風風火火。
巷子的鄰里喜歡在擔水時聚在“水點”扯閑篇。有人說她三只手, 曾經不是本分人;又有人說她嘴很碎,總把別人的家事往別處說。現在她趁漢林妻兒離開之際,跟漢林套近乎,其目的總是讓人想入非非。
看見漢林擔著水桶過來,剛剛喧鬧的人群霎時沒了聲音。水珠子咣咣砸著,濺著水花。這條巷子很窄,窄到一次只能過一輛車。車馬很慢,人很喧囂,日子卻也拉長了。暮色沾染著粉色的晚霞,零零散散地閃著幾處星光。小孩子們聚在巷口扣洋片,隨著晚飯時間臨近,大人們一聲聲催促,小孩們便如鳥雀般散去。
不知什么時候起,老漢開始把德順拴在了院子里。德順本就懶散慣了,現竟試圖掙脫著尋找自由。二拐子一進院門,德順便吠個不已,似乎在邀功,證明自己是條好狗。每當這時,老漢便習慣性地從窗前的縫紉機那兒站起,望著她一瘸一拐的背影消失在里院。老漢重重地吐著煙圈,空氣里一片死寂。
巧英嬸兒卻不以為意,繼續在院落的廚房里做著飯,沒把這進進出出的大活人放在心上。庭院里每天都是各色飯香,或是西紅柿炒辣椒的香辣味裹著烙餅的酥香,或是豬肉餡兒包子的清香帶著倭瓜稀飯的膩歪味,似乎都成了那些閑言碎語的防彈衣。飄進老漢的屋頭,壓住了嗆鼻的煙味。
漸漸的,德順也懶得理二拐子了,偶爾只吠一兩聲,便躺在地上不再出聲。再后來,德順更是自顧自睡它的懶覺。聽不到狗的叫聲,老漢以為二拐子沒再來。每次犬吠,老漢都習慣性地站起來在窗口張望,卻發現只是進來給后院阿姨送牛奶的后生。
莫不是二拐子不來了?
直到某個傍晚,巧英嬸兒與二拐子敞在庭院里,坐在馬扎上聊天。德順竟也溫和地臥在她腳邊,等著喂食。老漢掀開房門窗戶上的厚簾子,定定地看著那吃里爬外的家伙,罵了句狗東西。
似乎誰都不知道真相,又似乎誰都知道真相。其實真相并不重要,或許巷子的鄰里們根本不關心二拐子和漢林到底有沒有一腿。這些也只是生活的談資和小市民的樂趣,真正的生活從來不需要真相。風很聒噪,咋咋呼呼地吹過人們耳畔,躲在樹上的知了叫嚷著夏天,徹夜的星辰卻怎么也抓不住仲夏的尾巴。
3
“馬兒啊,長嘶鳴。 ”
“朝倚窗臺望天空,紅葉紛飛滿城紅,喚起思念滿街是。 ”
葉子漸落,秋意漸濃,厚重的霜裹著微微寒意,萬物似乎又恢復了曾經的秩序。北方的秋風,沒有喜怒哀樂,卻如刀子般刮出干燥的口子。不如冬風凜冽,卻也不似春風和煦。正像那郁達夫所描繪的《故都的秋》,來得特別清,來得特別靜,來得特別悲涼。
似乎秋總是和曠古的孤寂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巧英嬸兒正用手丈量著毛衣的骨架,拆了搭搭了拆,終于找到清晰的路子。老漢竟拾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研究起了中藥材,思索著哪幾種藥材放在一起是袪濕的好方子。似乎環境越靜,人越需要沉下心去打磨自己。冷風拍打著窗戶,刮著門板,老漢親弟竟尋上門來, 找老漢開方子。老漢扶著老花鏡,頓筆思索,藥方講得頭頭是道。巧英嬸兒總擔心把人家吃壞,卻不想老漢還真有兩把刷子,老漢弟弟后來又找老漢開方子,據說在這秋意漸濃的季節,折磨他好多年的舌患竟然再也沒犯。
日子一天天過去,巧英嬸兒老兩口說話越來越少,沉默卻也變成了默契。可怕的并非相顧無言,而是無法相伴相守。人的孤獨已然不再是情感上的共鳴,更多來自事實上的陪伴。老漢總是悶著頭抽煙看書,巧英嬸兒則按部就班做著每一餐飯。誰也不知道生活到底是什么,但看著窗頭明晃晃的太陽,便知道這又是一天。
秋天的暖陽總是陰晴不定,太陽在云際間游離,影子也拉得越來越長。
巷子里挖出了溝渠,工人們半截身子安在地下埋著水管。“水點”的兩大塊青色石板被搬走了,似乎自那之后,“水點”便從這個社會空間消失了,鄰里之間也少了些閑聊的機會。人們好像再也沒見過二拐子,也沒再聽說過她的事情。
老漢也發覺那個一瘸一拐的背影似乎消失了,卻又忘了何時消失。可又感覺這些已經不太重要了,或許又從未如想象中那么重要。德順在腳邊依偎著,曾經吃里爬外的叛徒,現在竟睡得更加慵懶。
整整一個秋天,巧英嬸兒總是打著毛衣,坐在沙發上打,坐在院子里打,躺在床上打,似乎她在織著秋天,又似乎她在等什么人。她也不知道,只是機械地織著,或許織完就可以看到秋的意義。前天從鄉下看望母親回來,她心情又好了許多,母親最近胃口大好,一頓要吃七八個餃子,一覺能睡到天亮。
所幸中秋月圓日留在了秋天,增添了不少節日氣氛。兒女們攜全家回到這座小城探望雙親。平日的忙碌終于有了釋放的空隙,無盡的寒暄讓濃濃的親情不斷升溫。巧英嬸兒今晚特別興奮,她將供奉的火龍果、石榴、團圓餅擺在院落的古架上,竟也映襯了“花好月圓”四個字。
拜月開始了,孫兒孫女在寂靜的夜里追趕打鬧,爭搶著小小的一份月餅。德順竟也加入了這場爭搶,二人一狗竟頗有些樂趣。或許這場追逐并沒有那么重要。但孩子的世界,本就明凈如一汪湖水,看到什么便是什么。最美好的是單純,最讓人忘不掉也是年少的單純。
巧英嬸兒在廚房笑著做中秋節的晚餐,她似乎看到了活著的意義。一陣風起,又吹落了滿枝的枯葉,或許這就是深秋該有的樣子吧!
4
“報個信,木蘭啊,歸來也。”
“萬里歸來一聲嘆,從前友人不復來。 ”
數九寒冬臘月天,冰窗花攀附其上,微微的光暈染開來,便成了萬花筒的眼睛,試圖窺探大自然的秘密。老漢聯系年輕的后生,拉來半卡車煤,一鍬一鍬地裝到塑料袋子里,又碼放到院子的角落。刺骨的寒意鉆進了厚棉襖子,直擊皮膚,似乎要穿透靈魂來個赤裸的擁抱。巧英嬸兒擰了把鼻涕, 將二弟拉來的脫了玉米的干棒子扔進火膛里,勾著火鉗翻攪,火勢愈來愈大。攤著餅子,背火燒,先刷油,后翻面,空氣里充斥著一股說不上來的香。院子里干活的后生們,竟也不自覺地咽了咽口水。“口卜子,火卜子。”老百姓冬天有吃的,有燒的,才會安心過冬。
或許這冬天太過強勢,又或是那天抬中煤拉傷了筋骨,向來不肯服老的老漢, 竟也抱著個腰天天喊疼。巧英嬸兒剛開始以為老漢太嬌氣,又或是不想早起生火罷了,后來才發現,天一寒,老漢走路的背影都有些顛簸,深感歲月不饒人。畢竟有點歲數了,老漢年輕時在公社交公糧一人背兩麻袋麥子上倉庫,氣都不喘一下,現在竟也被歲月壓倒了身板。
冬天的陽光再暖,仍有陣陣寒意。德順也怕冷,它向來就是條懶狗, 吃了睡睡了吃,窩在老漢的鞋旁,似乎在表忠心。老漢反倒沒那么喜歡它了,他骨子里認為不會看門的狗不是好狗,見它在家臥著,竟也看著不順眼,但寒冬臘月趕它出去又有些心疼。
這下,反倒讓它和巧英嬸兒走得更近了。巧英嬸兒一早起來便給這狗切肺子肉,和大塊大塊的饃拌在一塊,它竟也吃得毛色油亮,那條粗大的尾巴總像個掃把似的, 在地上磨來磨去。似乎冬天再冷,德順也很難感受到。或許在它的眼里,世界便只有肺子肉和饃饃頭。
一天大早,巧英嬸兒出門去買菜,才知道二拐子走了,突發腦溢血走的。如果當晚有個人守在身邊,及時發現搶救,她或許不會走吧。巷子里的人們各忙各的,冷風呼呼地刮著,人們匆匆見面也只偶爾說起,好像二拐子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也好像她從未來過世間。
后院的漢林也早就不養鴿子了,許是沒有跟上市場形勢,可老婆孩子卻再沒有回來。滿腹雄心的男人,似乎一夜之間便老了,頭頂冒出縷縷白發, 恰似冬天的白雪飄落,怎么也揮之不去。
人們誰都說不清夏天那些秘密,大家似乎都愿蒙在鼓里,在鼓皮上畫著一個又一個問號,試圖用自身的邏輯求證對方。或許真實的秘密也不那么重要,畢竟有趣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我們洗盡凡塵后的模樣。
年紀大了,對很多事力不從心。年前年后,張羅準備,本是每年最興高采烈的事,現如今也成了巧英嬸兒的煩惱。老漢整日躺在床上看書養神,能不下地便不下地,家務事一件也不做。孩子們擔心母親太操累,索性在飯店訂了一桌子飯。
大廳里,人來人往,大廚子的手藝自然比巧英嬸兒好多了,但飯菜里卻怎么也吃不出年味。噼里啪啦的鞭炮,小孩子穿著新衣,咿咿呀呀地拜年,一年重復著一年。許是時間一直推著人走,可人卻怎么也走不動了。
自那個年之后,巧英嬸兒兩口子便搬進了這幢單元樓,火自然不用自己生了, 省了很多麻煩事,也留下了很多遺憾。規整的樓里,哪有什么地方養花,以前院子里的花,也只能自生自滅。德順已經吃得一身肥膘,懶得不愛動。若在這樓里養狗,可能就像當年的漢林養鴿子般擾民,只能叫二弟拉到鄉下去,幫 他看豬圈,省得母豬生的崽子被偷。
也不知德順那只懶狗,現在過得怎么樣。
冬雪將至,似乎春的聲音也近了。可那個夏天卻再也回不去了。
“過分關,越漢嶺,關山飛渡;信馬由韁且緩行。 ”
巧英嬸兒遲暮地望著地上斑駁的陽光,被框條窗戶杠子切成了四分八塊。端著那碗嫩豆腐,給老漢遞進去,竟又吵著自己還不餓,儼然一個老小孩兒。搬進了這單元樓,舊友們很少來串門。或是路太遠,許是事太雜,沒有人勻得出時間來重逢,寂靜又愜意,或許才是暮年的底色。
“咚咚咚”一陣叩門聲,原來是送牛奶的后生又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