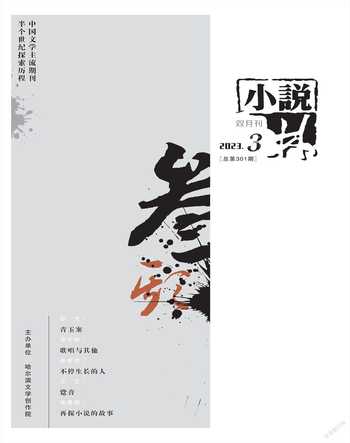饑渴的想象
《青玉案》用非常傳統的小說技法,講了一個發生在匱乏時代的很素樸的故事。它有一種久違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文學氣息,這種文學氣息的核心是純真。這種純真在日后數十年的文學進程中曾飽受寫作者和讀者的質疑,所謂先鋒也好,新寫實也好,乃至新世紀文學中的種種風尚,它們共同針對的或者說企圖顛覆的潛在對手,是純真。因為人們習慣把對新時代的不滿都發泄到舊時代的文學上,一種類似弒父的思想模式,或者就像一個剛剛踏入社會遭遇到一點兒打擊的年輕人,會迅速否定自己學生時代所受到的一些關于美和善的教育,甚至以此為羞恥。當老于世故的人一點點替換掉曾經的那個純真的人,他會把這種替換稱之為成長。
瞞和騙的文學當然始終會存在,但不存在一個完全依靠瞞和騙來支撐和運行的社會。我們自然可以很輕松地質疑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類似“傷痕文學”和“改革文學”中的種種偽善,但我們卻無法否認,在這種由寫作者所制造的偽善背后,有他們真實看見和感受到的,屬于一個特定時代方能涌現出來的集體的善意,正如理想主義可能是虛偽的,但理想卻始終是真實而有力的。
塞繆爾·約翰生曾用“饑渴的想象”來總結人類心靈的這種永遠朝向未知理想的特質,人類心靈總是處于無休無止的饑渴當中,并在饑渴中想象種種滿足自我欲望的手段,因此萌生種種的追求。而這種出于饑渴的追求不能單純用好和壞來評價,在好的寫作者那里,它往往是被既溫柔又無情地審視著。
饑渴的想象,也正是《青玉案》這篇小說的主線。小玉姐的出現就是因為饑餓,為了能夠吃飽肚子,她被送到姨媽家,也是因為能夠吃飽肚子,她就心滿意足地一腳在這個陌生的小縣城扎下根來。一個女孩子輕而易舉地就決定了自己的一生,她要的只是衣食無憂,現世安穩。而在婚姻的選擇上,電影院美工馮克所展現的國營單位身份和一丁點兒藝術才華,就足以令她傾心,因為這兩者都是她所匱乏的。小玉姐可以說是那個“純真年代”留在所有當事人記憶中的某種象征,她意味著某種難以企及又真實存在過的美,而這種美又如此容易消逝。
和一個女性對于良好生活的饑渴的想象相對應的,是那個時代里男性對于性的饑渴的想象。從“自己從哪里來的”這樣一個困擾小男孩們的懵懵懂懂的問題,到軍屬菜社防空洞里朦朦朧朧的糾纏在一起的黑影,再到“我”大學校園里的熱戀與新婚,性饑渴是推動男性成長的基本動力。而在這篇小說中,這種性饑渴也是以相當純真的方式予以呈現的,對于性的饑渴的想象令男性邁入婚姻,正如對于溫飽生活的想象令女性選擇婚姻。從今天來看,這種出于饑渴的想象所產生的種種行為中,當然有虛妄的成分,有被壓抑的成分,但你不能否認其中也有誠懇,類似木心在《從前慢》中所描述過的那種誠懇。
小說的最后,小玉姐的丈夫在歷經出軌和墜落事故之后癱瘓在床了,她所收養的小女孩也漸入令人不安的叛逆期,但生活還要繼續,而一個純真的女性就像一個民族,在夢想破滅之后依舊會堅韌地走下去。
作者簡介:張定浩,作家,評論家。著有文集《既見君子》《取瑟而歌》《愛欲與哀矜》等。現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