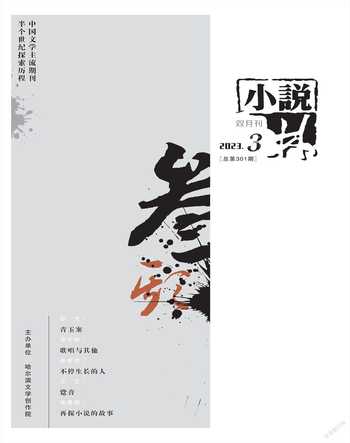再探小說的故事
一、“再探”的由來
必須有好看的故事這是我讀小說的第一印象。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由黃子平開始,有眾多新潮批評家跟進,喧鬧一時,聲稱小說有故事與抒情兩種模式,故事模式不如抒情模式。發展到后來,他們只認抒情模式,好像越是有故事,越是“趙樹理”、越是低層次,相反越是會抒情,越是高檔次、越是“孫犁”。有的“批評家”甚至以為小說可以沒有故事,只要有抒情即心理情緒模式即可。那時我一直堅持小說必須有故事的說法,還拉來法國著名作家巴贊的經典語言為自己立論。我以為舍棄巴爾扎克、陀思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卡夫卡這些世界級小說大師而僅僅把趙樹理和孫犁當作搭建小說創作的地基未免太簡陋和可笑了。我那時特別以為小說不是詩,也不是抒情散文,它是敘事文學,要給讀者演一點兒“戲”,從起伏跌宕的故事看,沒這種“戲”就沒小說。為急于參加討論我還寫過《也論小說的結構形態》一文,被多處轉載。這個話題后來雖然逐漸消隱,可是多年來它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里,我覺得這是一個必須理清的問題,它是小說存在的根本,所以來一個“再探”。
二、故事是小說的原型
形式主義者認為任何藝術的形成,都有它的原型,舞蹈的原型是曲線美,詩歌的原型是句型的協調與音樂美,戲劇的原型是動作與對白在戲臺的演示。小說呢,我以為它的原型就是有好看的故事,也可以說故事是小說的圓心。人們看小說,最感興趣的就是他寫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其實無論中國小說的源頭——南北朝的筆記逸聞,還是西方小說的源頭——傳奇,都是講故事,只是不如現在這么精致、這么完整。現代小說理論十分強調人物形象的塑造。可是人物的性格、形象不能憑空產生,而必須通過故事來站立。沒有故事則談不上小說創作。
而故事者,就是有始有終的事件也。這事件可長可短,但必須是有演進有變化。人們要看的就是這演義和演義的節奏。不管是大故事,還是小故事,不管是一生命運的起伏轉折,還是在某個時差里的坎坷跌宕。而既然是故事,那就必須是有關行動或行為的,具體來說,就是主角做了什么、干了什么。即便完全屬于心理的小說,也都包裹著故事的形態,有心理變化過程,有潮漲潮落,有突起和消歇,而絕不會是平靜如鏡,無一絲波瀾,無始無終。若如此,那只能算心理說明書或抒情散文,而不是小說。如《罪與罰》《變化》都是典型的心理回憶小說。但它們都包裹了故事,一個主人公回憶了他殺人的全過程,一個回憶了和妻子的矛盾并決定不再接情婦到巴黎。
還有一點必須強調,小說既然主要是寫人的,而人又是千差萬別的,所以小說的故事也有千種萬種、以至無窮,而且正是通過這千差萬別的故事,表現出千差萬別的人、千差萬別的性格。小說藝術對人是平等的,只要能吸引讀者,什么人的什么故事都能成為它寫作的對象。因此我們能看到關于英雄的小說,關于智者的小說,關于愚民懦夫的小說,關于橫暴者的小說……小說伸入群的深度可以說無法丈量。
小說雖然主要是寫人的故事,但也有不是寫人的小說,而是寫動物的。比如杰克·倫敦《荒野的呼喚》、王鳳麟《野狼出沒的山谷》,都是寫狼的。這好像跟我定義的小說是關于人的故事相沖突。但其實并不如此,因為這類小說都是人化的自然或自然的人化。也就是它們把人的觀察、人的感覺注入到狼的身上,并根據作為人的理解編撰了狼的故事。像《荒野的呼喚》是杰克·倫敦對人類、再具體一點兒說就是把當年淘金者對冒險性的探求,對詭異、蠻荒之域的踏入移植到狼性的回歸上。《野狼出沒的山谷》是把人性投射到狼的身上,或從狼的身上挖掘出人性的希望。所以它們都不是簡單的關于狼的故事。而是被人性融化的關于狼的故事。自然它們也運演著關于人的故事模式,有狼的行為過程,有它們的起始和終了。《荒野的呼喚》由人性回歸了獸性,從人間走向獸間。《野狼出沒的山谷》相反,被馴化的狼徹底獲得了人性,在主人生命受到威脅時趕走了它曾經混跡其中的狼群。
三、故事必須新奇詭譎
任何一部好小說的故事都必須是吸引人的,能達到讓人愛不釋手,讓人哭,或讓人笑的程度。而要吸引人則必定是個體的、充分個人化的。每個小說家,對于別人都是個異類,他的故事也都是異類。它不但跟任何別的人不同,而且跟任何所謂的群體都不同。他甚至是十分孤立、十分另類的個體。作家在寫作時都是因為直覺到了個體的個別性的魅力,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表現它的沖動,于是讓這個人和他的故事在紙上站立起來。這個故事和故事里的人絕對是獨特性的創造。
當然小說的故事僅僅具有個別性還不行。它還必須是新奇的。新奇不是指那些新發生的事,而是指行為者所造成的事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只是偶然間被作家碰到了、聽說了,于是被形諸筆墨、廣為人知。由于新奇、新鮮,所以有人只取這一點,把這樣的小說叫做新聞小說。老鬼的《血色黃昏》就有幸獲得這種殊榮。南美短篇小說大師博爾赫斯的許多作品都帶有花邊新聞、八卦新聞的性質。新聞小說這種概括雖然不準,但小說的故事確實具有新聞性。
不過能夠構成小說審美意義上的新奇不只是它的新鮮性,一個非常重要的品質在于它具有反常性。也就是跟人們的認知及經驗相反,超出常規。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夫妻都愿意他們的孩子是雙方親生的,沒有哪個男人和女人愿意對方給自己戴上綠帽子。可是哈代的小說《彼特利克夫人》與我們的想象完全相反。女主人公暗戀著一個鄰里青年,他是已經破落的貴族后裔。女主人不但暗戀著他,還想象著她的孩子就是自己和這個貴族青年的。丈夫聽說后不但沒責怪她,反而十分興奮。因為這個孩子改變了他資產者的低俗身份而獲得了高貴的貴族血統。這樣的小說讀一遍就能永久記住。安娜·卡列尼娜的精神追求同樣超乎尋常地異樣。丈夫卡列寧是中國人眼中傳統道德的好男人。他是沙皇的近臣、部長級官員。身份顯赫不說,性情還十分溫和,安娜給他戴上了綠帽子,他還原諒了她。可是就是這樣一個能勾引無數女人青睞的男人卻不被安娜看好。她愛上了一個花花公子渥倫斯基。說她是性情女人也好、思想偏執也好,總之她跟常人的眼光不同,喜歡沃倫斯基光鮮的外表,把他每一個行動都讀成帥哥一般活躍的、浪漫的、浸潤著詩美的、激蕩人心魂的儀態。讓人覺得她好像是專門能從無賴流氓身上感受到野性美的女人,而且能夠投入全身心的愛,還敢于搏擊家庭和社會的倫理,竟然在萬眾矚目的場合下站起來為情人助威,盡失貴夫人的顏面。最后寧愿為失去這種畸形的愛情臥軌自殺。安娜·卡列尼娜的愛永遠像謎一般令人難解。
小說的故事有時還特別詭異、詭譎。在這種詭異和詭譎中,滲透著某種幽暗、神秘乃至令人驚悸的東西。《呼嘯山莊》里的希斯克里夫和凱瑟琳原是一對相愛至深的情侶。但是由于希斯克里夫的貧窮,凱瑟琳嫁給了一個富豪。由于失去,希斯克利夫更加愛戀凱瑟琳,愛得近于瘋狂。加上這時的凱瑟琳已經無法接受他的愛,希斯克利夫變成了施虐狂。他不是為愛人祝福,而是專門給她制造麻煩和苦難。他先是通過賭博把凱瑟琳哥哥富庶的莊園贏到自己的手里,繼而又把凱瑟琳的侄子變成了自己的家奴,就像當年自己被凱瑟琳的哥哥當家奴加以折磨一樣。再后來他又故意把凱瑟琳丈夫的妹妹變成了自己的妻子。他實施的每一步都是對凱瑟琳感情和靈魂的重重錘擊。能說他僅僅是報復嗎?他不愛凱瑟琳嗎?不,凱瑟琳是他的靈魂,正像凱瑟琳把他當作自己的靈魂一樣,凱瑟琳是他存在于這個世界的唯一理由。正是懷念活著時的凱瑟琳的愛他不吃不喝,把自己餓死,死后也要把自己的棺木同凱瑟琳的棺木接通。然而這種詭異的愛又無不散發著陰森、恐怖的氣息。還有《洛麗塔》,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愛上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他的愛不但明顯地帶有反芻性質,而且十分嚴重地觸犯了人類的倫理,因為就在他暗戀小女孩洛麗塔的時候他已經跟她的母親結婚了。可是誰能說他的愛里沒有真誠呢?即使他的愛長時間遭到社會及廣大讀者的排斥,甚至小說被禁止出版,但只要仔細琢磨和認真體驗,又不得不承認他的愛具有直擊人心靈的真實性。他不只愛洛麗塔的童貞、純潔無瑕,還無限地寬容她的調皮、任性和凡俗。正是這種帶有畸形性質的深愛,讓他獲得了無法從正常戀愛里獲得的愉快和甜蜜,既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小說讓我們見識到了日本著名心理學家渡邊淳一描述的那種和諧的情景,正是無限愉悅的性愛讓他愿意為小女孩付出一切,乃至由于憎恨離間者的破壞而甘愿行兇坐牢。《洛麗塔》最終被戴上奇絕創作的桂冠,享譽世界,其作者納博科夫也因為對戀童癖這個人類心理和生理隱蔽角落的坦誠和深刻地揭示而被尊稱為鮮有的詭譎文學的創造大師。其對男人和女人的影響力、對于擴大他們與她們愛的邊界(如少男少女與中老年異性相戀的正當性)簡直達到了前無古人的程度。
四、故事必須有“味”
故事取消論者以為寫故事無味,這不但是一種偏見,也是一種淺見。查看世界上所有著名小說,都有故事,都講求“味”,既有情味又有意味。
關于“情味”,我想著重說的是小說比照詩歌和散文由于體量大能夠表現豐富的情感,其激起人的情感反應也是豐富的。有時甚至讓人產生十分復雜乃至對立的情感,俗話說叫做“五味雜陳”。《洛麗塔》和《呼嘯山莊》都是這類激人復雜情感的小說。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我們都會對主人公的失檢失范行為發出譴責,覺得一個有悖人倫,一個偏激暴戾。但是如果回落到人性與人欲的要求上,我們又能給予理解與寬宥。而且細察他們的選擇,為愛而不惜犧牲自己、作踐自己,其情感和常人相比有一種說不出的深刻和執著。難怪他們的創造者被當作人類情感挖掘大師來稱頌。而另一些人類情感挖掘大師甚至能把我們置于迷失的世界,我們不知道應該付出愛還是恨,贊美還是鞭笞。比如《卡拉馬佐夫兄弟》里的老卡拉馬佐夫,讓我們痛恨至極。閱讀的過程中,我們強烈地感到他根本不配和人生活一起,不配活在世間。可是他一旦被他的兒子們殺死,我們又不置可否了。我們既不想譴責也不想贊賞小卡拉瑪佐夫們。我們嘆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如椽之筆,他把人道主義的尷尬處理得那么絕妙,正像我們經常在生活中經歷的那樣。這種如椽之筆不僅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里,也握在博爾赫斯手里。他同樣把我們的情感置于尷尬境地。他筆下的黑社會頭目既像流氓,又像英雄。我們剛剛對他隨意殺戮的殘暴行為拔出憎恨的利劍,又馬上將其收縮回來,因為我們看到了他扶危濟困、行俠仗義的壯舉。我們不知道憎恨和欽敬哪個砝碼更重,寧愿猶豫在兩者中間,不做任何選擇。我們還會給十分糾結的態度尋找理由,以證明博爾赫斯營造這種故事的真實性和準確性。確實英雄和流氓有時有著同樣的氣質,差別只在于最后一步,是踩到正義的天平上還是踩到邪惡的天平上。有時他們的邪惡和正義感還疊合在一起,讓我們的理智和情感無處安身。
和情味同樣重要的是小說的意味。小說的意味是一種詩思,一種浸透詩情的哲理。這種詩思、這種哲理是作家對生命意義的智慧開掘,是對存在價值的一種新鮮認定。它像一扇被打開的窗戶,撥開我們眼前渾蒙的霧霾,讓我們驚訝地看到了一個清亮的世界,讓我們刷新自己的追求,在人生的航道上標定一個雖然陌生但又倍感親切的前行港灣和棧道。《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寫的不只是一個愛情故事,更是一個重新認定生命價值的故事。小說的女主人公康妮原是一個伯爵夫人。其實她不過是被伯爵養在家里的一只金絲雀。在一次偶然的邂逅中她和守林人發生了性愛。就是這一次性愛激發了她心底的真正的愛,喚起了她重新創造自己生命價值的強烈渴望。為了真正的愛,為了和守林人在一起她寧愿放棄和伯爵在一起的養尊處優的生活而到倫敦去做一個底層勞動者。她感到這才是她活得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選擇。性愛雖然是人類生存的一個母題,但是人類卻又長期生活在談性色變的時代,受到強烈的壓抑。勞倫斯不但敢于掀翻這個壓抑人類的道德巨石,還能從性愛中發掘出帶有創造性的生命哲學,開啟人類的心智,加速推進人類走向高度文明的步伐。
小說家雖然不能等同于思想家。可是從他們藝術編撰的故事里我們卻能夠透析出絕不遜色于思想家通過事實材料提煉出來的真理。看《堂·吉訶德》我們經常捧腹大笑。笑他的子虛烏有,笑他的荒唐滑稽:偏偏要在一個已經消失了騎士的時代當一個偉大騎士,一會兒把風車當惡魔向它發出挑戰,結果被高高摔倒,一會兒把羊群當成敵軍,向它們發起攻擊,結果被牧童打得皮開肉綻。他的所有行為都像出自一個瘋子的幻想,表現出一個精神病患者的癲狂。詭異的是我們對這可笑的騎士并無多少憎惡,還給予不少同情和憐憫。而剝去這個藝術形象身上那些蹩腳的外殼,抽釋出隱藏在他靈魂深處的精神內核,我們會發現人類多數包括我們自己共有的美好向往,就是英雄情結、巨人夢。這種英雄情結、巨人夢多以匡扶正義、馳名天下為己任。它從童年時代延續到我們的成年,最后又多以失敗而告終,充滿為人長嘆的悲劇性。所以看到堂·吉訶德的表演,我們會對這種亙古以來便存在的英雄情結、巨人夢露出會心的微笑。
其實,豈止《堂·吉訶德》,所有偉大小說編撰的故事都能表現出一種人類的精神,讓我們長時間咀嚼玩味不止。像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就可以列入其中。阿Q的精神勝利法不只是落后農民身上存在,就是健康農民身上也存在。不只是愚昧的底層人身上存在,就是看似有智慧的上層人身上也存在。不只是國民性的弱點,也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弱點(羅曼·羅蘭語)。用魯迅先生倡導的“無情解剖自己”的精神來檢視自己,我們一點兒也不比阿Q的精神勝利法少。我們以為現在產生阿Q精神勝利法的土壤已經消失。可是睜開眼睛看看,今天的阿Q比一百年前還多,現在的精神勝利法比當年的阿Q還嚴重。阿Q的精神勝利法只是表現在炫耀祖宗的光榮上,現在的精神勝利法早已經超過了阿Q,還表現在向世界吹噓和夸大自己的力量上。耐心琢磨和玩味魯迅表現的阿Q精神我們不由得不贊賞魯迅的偉大,因為他能在一百年前寫出一百年后人的精神狀態。
五、敘述故事有成法而無定法
幾十年的閱讀經驗告訴我,故事的好看不只是因為故事本身,還因為故事的講述人講得妙。的確,會講和不會講,對于故事的形成來說非常重要。會講才能把故事變成生動有趣的藝術。不會講,好故事也會被弄成木乃伊。就像不會講課的老師,用那種僵化的思想理念、味同嚼蠟的語言能把學生弄得昏昏欲睡一樣。
而要講得好,我覺得首先必須把握住故事的脈搏跳動,安排好故事的節奏節律即故事的演化過程,這個過程不是平面化、直線型的延展,而是曲線型、波浪型地向前遞進,直到終了。小說故事的這種節奏節律和故事本身一樣也是審美欣賞的對象。檢視閱讀過的小說,它們的節律節奏并不遵循同一個模式,而是氣象萬千、變化多端。有的波瀾起伏、跌宕多姿,像《迷人的海》。老海碰子和小海碰子都想當深海捕撈之王。開始他們相互敵視、排斥,明爭暗斗、反復比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同時他們又惺惺相惜,相互取長補短、最后攜手共同成為征服深海的英雄。作為讀者,我們就是在這種顛簸中享受一種陽剛之美。也有的小說節律一直像暗流涌動,緩慢推出,我們被悶在葫蘆里,不知要被帶到哪里。正待我們要失去耐力時,情況突然急轉直下,結果或真相得到爆料——它令我們根本意想不到,讓我們心里受到巨大的沖擊。在接受這種巨大沖擊波時我們感受到了一種強力變化的美。比如馬原的《錯誤》,主人公堅定不移地認為是同屋的一個知青把自己珍寶一般的軍帽給偷了并打斷了他的腿。他打自己認定的小偷的時候沒人為那個知青辯解,軍帽還真的在被打知青的懷里。可是多少年之后他才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原來是他自己和人在場院里打架、把軍帽丟在了那里。那個知青是去救一個被奸污的女知青產婦在路上撿起了軍帽并準備還給他。可當時打人者不容分說就打斷了那個知青的腿,從而把真相遮蓋了。多少年之后他明白事情的真相,想要道歉時卻又晚了,因為那個知青已經和他有幾千里之隔,并患了癌癥不久于人世了。雙重的痛悔令他撕心裂肝。我們跟他一起品嘗那個善良知青無法挽回的人生悲劇,還有他永遠不能實現道歉與贖罪的痛苦。再如后現代鼻祖格里耶的反理性偵探小說,主人公像福爾摩斯一樣費盡心機地去尋找情殺者、仇殺者、見財起意者,可是到最后也沒有結果,當然這種沒結果也是一種結果。總之小說的節律無法定于一尊,它可以是千種萬種、以至無窮。
和節律節奏同樣重要的是敘述。稍稍懂得一點兒小說發展史的人都知道敘事人的出現使小說跟原始故事區別開來,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藝術樣式。無論中國的話本進化到小說還是西方的傳奇演化到小說都是敘事人出現的結果。原始的故事大都是群體性編撰的結晶,有時是同時代人互補,有時是不同時代的人完善。這種原始的故事無論怎樣完美都呈現不出個性化的創造。敘事人的出現終止了混沌的合成而把創造變成現實。而所謂創造就是敘事人對故事的想象、構造作用。換句話說敘事人即作者成了小說的主宰、操縱者。成熟的小說都是個人性的文本,它浸透著作者的體溫和心血,是他個人對世界對人生的感懷、思索。每一個小說里的世界都不同于另一個小說里的世界,那是他獨特的生命價值和審美價值的承載物。可是就是這樣一個經過幾百年探索出來的真理性命題卻被一些所謂掌握新知的先鋒批評家給顛覆了。敘事本可以千變萬化、多種多樣,他們卻只抓住全知敘事的某些弊端(常常是他們自以為的)便否認這種敘事,乃至所有敘事的可行性,片面地強調敘事人隱藏起來。最極端的走向則是把零度寫作當作小說創作的極致,并洋洋得意地聲稱這是現今全世界小說寫作的前衛潮頭。當品讀這些教誨時,我們頭腦里不只是覺得發話者在利用他們先睹為快的優勢把西方新奇的話語當作敲門磚,還特別感到他們對西方文化的不解和誤讀。西方文化的一個優良機制是創新,就是這種創新把人類的文明步步推向更高端。但也不容置疑的是創新者為了割斷同前此文化的聯系,常常把問題推向另一個極端,難免出現文化上的歧義。有時他們甚至拋棄慣常的語言,啟動一種自己才弄得懂的語言。尤其進入二十世紀以后更成為一些思想家共同的追求。從胡塞爾、海德格爾到薩特到福柯到羅蘭·巴特到德里達無不如此。他們晦澀的風格幾乎令人不堪卒讀,只是經過無數個詮釋家艱苦的解讀才被人領略和知曉。零度寫作也是這種模糊晦澀的語言。拆解羅蘭·巴特“零度寫作”的原意無非是想要作家杜絕一切意識形態的寫作。他的用心是良苦的、知趣超凡,但是要想讓作家摒棄所有前人的思想、割斷同傳統文化連接的臍帶是絕對辦不到的。這不僅是因為每一個人都是人類文化的堆積、作為集體無意識——文化已被生物性繼承下來,更因為并不是所有前人類的思想、語言都是荒謬悖理的,也不是所有前人類的思想和語言都是為權力意志者說話的。離開了所有人類精湛的思想和語言,背棄了所有優良的傳統,無疑是在架設一座空中樓閣。而從作家的角度說,取消了創作主體的感知、認識、發現、想象力,還有他的人生理想和審美理想而談創作簡直是子虛烏有。所以超越傳統必須在認可傳統的優質基礎上尋找更好的東西以彌補它的不足。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當我們新潮批評家熱炒“零度寫作”、解構全知敘事的時候,南美爆炸文學的大師馬爾克斯、略薩小說的主觀性都很強,并且都在用全知敘事。特別是博爾赫斯把全知敘事發揮得淋漓盡致,達到了一個嘆為觀止的新高度。他小說里所有的敘事人,其實就是博爾赫斯本人,像飛翔在天空中的精靈,俯視著大地,給我們講述著發生在地球上廣大范圍的事情。博爾赫斯把他作為圖書管理員在閱讀中獲得的知識兌換成哲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地理學家、外交家等等的視角,穿越古今,把故事勾連起來。有時還以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智慧,伸出上帝之手將不同地域不同國家串到一起,讓故事在廣闊的背景里展開。這個敘事人還常常打破一般小說對人物行為的持續性描寫,他的身影閃躲騰挪地在小說文本中跳躍,忽而說這兒,忽而說那兒,穿針引線般地把一些瑣屑的事情連綴在一起,形同散文。但你又不能不把它們當小說來閱讀,而且讀得津津有味。因為那些故事隱含著一貫性,其間的人物被敘事者三筆兩筆就描畫得呼之欲出。閱讀中我們的心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既喜歡博爾赫斯小說里的故事,它們把南美蠻荒時期和資本主義野蠻時期糅合在一起,把那里的風情習俗、牛仔們的兇悍殘忍寫得有聲有色;同時也特別喜歡他的敘事人,這個敘事人煥發出幾近喧賓奪主的魅力,它和故事平分秋色把我們的注意力奪去了一半。我們不斷地贊嘆他神奇的功能,他幽默的風格、淵博的知識、豐富的想象力遠遠超出拉伯雷,他廣闊博大的視野早已把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前輩甩到身后。我們無法想象他怎么會把全知全能的敘事帶到一個全新的高峰,使之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憑此成為少有的小說藝術創造的大師。只是看了他的傳記,才明白他把圖書管理員的淵博和奇趣移植到了全知敘事人的頭腦里。所以面對小說構成的任何一種因素都不可以妄自斷言止步,其無窮的潛力都有待創造者去發掘。
小說完整故事的構成因素還有很多,如敘事語言、如細節描寫等等,但本文只想就新時期以來輕視“故事”本體及敘事等問題發表一點兒淺見。
作者簡介:張景超,黑龍江大學教授。生于1943年,1978年進入大學執教,系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生導師、學科帶頭人。寫有論文170多萬字,出版三部專著,多次獲省社科及文藝大獎。其中《文化批判的背反與人格》在國內特受好評。